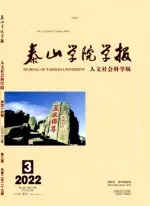困顿中的退守与坚持——论“十七年”文学中的路翎小说
刘成才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对于路翎及其小说在建国后“十七年”的遭遇,人们已经达到了几乎一致的共识,这就是“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位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销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位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1]即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为界线,把路翎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45年 7月 3日,胡风在《财主底儿女们》的序言中铿锵有力地写道:“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时光流转到1952年,舒芜却大声奉劝路翎:“十年过去了,睁开眼睛看一看吧!”“时间所证明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自己和当时读过的人之外,恐怕已没有人听过它的名字。”[2]在这期间,路翎的创作陷入了一种怎样的困境,经历了怎样的坚持与退守,路翎承受了怎样的心理煎熬?研究界在达成上述共识的同时对此却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对路翎在“十七年”中的小说创作的分析,探讨路翎在共和国成立这一新的话语背景中所面临的困顿状态,以及他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退守与坚持。从而以路翎为标本,见证一代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青春,在政治与时代面前失语的尴尬境地。
一、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与宿命
共和国成立之初,路翎有过巴金式的忏悔:“到了阳光中,我身上的疮疤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在毛泽东底旗帜下,劳苦的人民不是像我这里所写的这样无望地生活,这样壮烈地反抗,这样满身血痕,到处要直对障碍而搏击的,在解放了的这广大的土地上,人民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人和新世界的创造者了。”[3]可以看出路翎对于新政权是发自内心的认同的,政治的规训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威力。
1949年南京解放后,年仅27岁的路翎担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穿上军装,进入了共和国队伍的行列,满腔热诚地创作了活报剧《反动派一团糟》,以及反映解放初期工人生活的剧本《人民万岁》(后改为《迎着明天》)。1950年初,路翎调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任创作组副组长。随后,他到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厂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创作了表现解放后工人生活的四幕剧《英雄母亲》以及反映抗美援朝的剧本《军布》。11月,路翎随同剧团到沈阳访问准备出国的志愿军,并于年底创作了剧本《祖国在前进》。1952年 12月,路翎主动请缨,跨过鸭绿江,讴歌“谁是最可爱的人”,直到 1953年 7月朝鲜停战后才回国,长达七个月。他在1981年3月23日写的《〈初雪〉后记》中说:“我在一九五二年底去朝鲜,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后回国。在朝鲜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访问过志愿军几个部队,到过开城、平壤等地,接触到志愿军的一些指导员,听到了在几次战役中中朝人民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和战斗情谊。也到过许多朝鲜人民家里作客,和他 (她)们同桌共餐,欣赏他(她)们的歌唱和舞蹈,听他 (她)们倾诉这几年间经历的患难。我也在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在壕沟里躲避美帝国主义B 26轰炸机……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国际主义精神,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朝鲜人民和军队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都使我感动,并在激动之余写了些东西。”然而,这些积极主动的行为似乎都避免不了路翎被一步步边缘化的宿命。
其实,被边缘化的举措,早在建国前就已经施行。1948年 3月 1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就开始了对路翎的批判:“这位被称为最不沾染‘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确实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他的太强的主观妨碍了他去认真地写出他所看到的工人。”[4]建国后,他 1949年至 1951年所写的四部话剧《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祖国儿女》,一个也未准予上演。这使路翎感到“陷在八阵图里面”:“我说的苦痛,就是在再修改这些剧本时,一定要改成那样,我有一种受摧残的感觉。”他弄不懂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剧本为何要屡屡受到批评,而小说《锄地》“那样一点点简单的东西,他们倒反而说‘明朗’、‘喜欢’。”[5]像所有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样,路翎面临着十字路口的选择:是忠于时代规范还是忠于艺术准则?时代没有给路翎以更多选择的机会,迎向他的是一阵猛似一阵的批判,几年间,路翎不断被主流意识形态“敲打”着。1950年,《朱桂花的故事》、《女工赵梅英》受到批评;1951年,剧本《人民万岁》、《祖国在前进》受到批评,被冠上“一部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的帽子;1952年,舒芜态度与措辞均极其严厉的公开信,在文艺报发表;1953年,《文艺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批判他的有关朝鲜战场的小说;继之,1954年 6月刊登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认为路翎“没有放弃其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用卑鄙的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用腐朽的自由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思想感情,用颠倒黑白的办法来达到反革命宣传的目的。”[6];除此之外,1954年 6月 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主要议题仍是批评路翎,直至 1955年 5月 16日即《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被隔离审查。
在这一连串不断的“敲打”中,路翎——“中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左拉”(刘西渭语)渐渐地沉默了,失语了,最终成了文学史上的“陌生人”。[7]
二、现实政治规训中的无奈退守
其实,侯金镜指责路翎不放弃“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是不准确的。这时的路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必须“转型”。胡风 1949年 5月曾两次致信路翎,建议路翎写一些积极内容的东西,最好是关于新形势、工人的,表现也要明朗一点。具体为:一、要写积极的性格,新的生命;二、述性的文字,也要浅显些、生活的文字;三、不回避政治的风貌,给以表现。路翎在回信中说:“你提的,关于作品的几点,我想可以做到的。”并意识到“我们的不快的情形,在这块小土地上也有模糊的反映了,所以非得争取去做实际的事情不可。”[8]
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路翎创作了 11篇主要以反映工人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1952年结集为《朱桂花的故事》[9]。十一篇小说都聚焦于旧社会让人活不下去、新社会共产党让人新生的主题,表现形形色色的劳动人民从落后到进步的转化过程。转化的内在动力一是苦大仇深的阶级、民族压迫。小说的主人公几乎个个都有一部苦难史,或者是父母被日本人杀害(《“祖国号”列车》),或者是孩子被国民党杀死(《荣材婶的篮子》),或者是自己饱受地主、资本家、反动政府的迫害 (《试探》、《替我唱个歌》、《劳动模范朱学海》、《林根生夫妇》等)。二是革命大熔炉中新的力量的引导。小说中活跃着一支由“军事代表”、“工会主席”、“福利部长”、“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组成的新生力量,他们是光明、进步的象征,有着“即使是一块石头,也会在这革命的熔炉里受到锻炼”的坚定信念,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在旧与新、黑暗与光明、受苦受难与当家作主的一系列对比中,似乎是理所当然地产生出人物精神状态由落后到进步、由消沉到积极的转变。如此集中描写自己不熟悉的工人阶级,对于路翎是首次,在题材方面显示了他在新的历史阶段“更新”自己的尝试。他的创作,从内容到主题和形式,和四十年代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许多路翎式的个性化的独有的标记“雄强的人性”、“原始强力”、“灵魂的搏斗”、“精神的创伤”、“情感的疯狂”、“心理的纠葛”不见了,再也见不到他对“精神奴役创伤”的开掘了,取而代之的是“爱情、友谊、同情”、美丽而柔和的人性。这些变化不能不说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有些难以接受,可以想象路翎当时承受的心灵煎熬与“转型”期的阵痛。然而,主流意识形态仍旧不能满意,仍然做出了不放弃“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的结论。
即使是广受赞扬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路翎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里,也依然能够见到路翎内心深处“放弃”与“退守”的痕迹。在这两篇可以被列入“十七年”最优秀短篇小说之列的小说里,诸如“北京”、“天安门”、“毛主席”、“指导员”、“党”等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入侵处处可见。在《洼地上的“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对人物的直接干预,王应洪与朝鲜姑娘的情感在萌芽时期就受到了组织上的关注和告诫,这种冲突的外在化,正显示了作者已经认可了政治的干涉。而另一部同样写朝鲜战争的小说《战争,为了和平》中,爱情无关人物内心的萌动和对情欲的疯狂,理性压制了情感,张桂珍对英雄赵庆奎的感情首先是有婚姻的,然后是因为其政治上的先进性。而在她眼中,实现爱情的条件,同样是政治上的进步,只有政治上的平等才能“配得上他”。于赵庆奎而言,本来没有多大意义的婚姻,也因为妻子政治上的进步,开始发生了转变,于是有了美的感觉,有了所谓爱情。同样,魏玉兰对于哥哥的牺牲的悲痛也转化为对于革命事业的热情,具体表现为守护河堤。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中,革命最终成为情感的能指,感情的发生依赖于政治的进步或革命的成功,政治的强化作用显得更为明显了。小说中的英雄们在面对各种困难时都是以党的教导为指导,并转化为乐观向上的激情和信心,口号式的标语也越来越多了。
最为明显的是《洼地上的“战役”》中王应洪的一个梦境:他梦见金圣姬在北京天安门前舞蹈,跳给毛主席看。母亲和毛主席在一起,毛主席看着微笑了,毛主席并且也看了看他,对他点点头,他也没有忘记敬了一个礼。特别是毛主席在梦中出现,用路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表现“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是对毛主席抱着神圣的感情的”,是为了“在战士的心灵里,将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感情”相联系。在这篇路翎为自己小说辩护的文章中,他着重提出“在侯金镜同志的批评文章里,摘引我的小说里字句的时候,所有的和被摘引的句子联结着的例如‘毛主席的笑容’、‘想到毛主席’等字句都是被删去的。十分明显,批评家不希望读者知道,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是对毛主席抱着神圣的感情的,批评家只希望读者到处都看到我的小说里的‘个人主义’的。”[10]显然,在路翎看来,他的小说中添加了大量的“毛主席”就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这,也正是路翎在潜意识中退守的一个策略,或者说是,被政治规训潜意识的流露。
三、困顿中执着坚持的力量
“一生两世”的路翎艺术生命与艺术风格在建国后是否确实已经“销磨殆尽,几近于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的确令人感觉到“真正的恐怖”。[11]实际上,通过细读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路翎在“十七年”所创作的小说,在退守中又显现着自己默默执着坚持的力量。
路翎“十七年”小说总的风格是缜密、清新、内蕴的恬淡,特别是他的志愿军题材小说,充满了亲情,即使是殊死的战斗、流血和牺牲,也写得视死如归,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路翎私下里的看法并不象小说中那样乐观,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底屋子周围就荡漾着粗嘎的愉快的歌声,但以我底邻人们看,要拔去旧中国,还需要很多时间。”[12]革命能够建立新社会,但是它自身并不能够立刻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在短时期内制造出新人来。路翎不是不明白,但现实境况令他别无选择。这种困顿与挣扎就凸显在他建国后的创作中,“原始强力”总会或隐或显地出现。《人民万岁》反映的是工人护厂斗争的事件,但路翎重在展示工人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主人公刘冬姑是一个饱受肉体和精神双重饥饿的女性,她挣扎在堕落的深渊,以恶的形式与黑暗的社会殊死抗争。她从孤独、自傲、有能力、有技术的工人李迎财身上获得灵与肉的满足。但在迎接新生的时代,他们必然要在自我与集体、革命与堕落、散漫与纪律的旋涡中浮沉。与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不同,主人公并没有一任“原始强力”的盲目支配,他们身上自发的“原始强力”终于在党的引导下,在工人运动的锻炼中,在精神的自我试炼里,成为自觉的革命力量,双双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关于“人民底原始的强力”,路翎曾诠释:“它就是,反抗封建束缚的那种朴素的、自然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这种自发性是历史要求下的原始的、自然的产儿,是‘个性解放’的即阶级觉醒的初尘的带血的形态,它是革命斗争和革命领导的基础。”[13]因此,在路翎建国后的小说中,人物之间的感情、关系矛盾的解决,并没有通常作家笔下主要靠政治斗争,而是人们之间这种自发性的感情,隐隐约约地可见“人民底原始的强力”的影子。解放初期的小说《女工赵梅英》、《锄地》、《粮食》中,同样都写落后分子与积极分子之间的矛盾,结局都是两者矛盾的缓和。但是,解决矛盾的绝不是落后分子政治觉悟的提高,也不是受到政治口号的感化,或者是组织上的教育,或者是被批斗,等等。使两者矛盾得到缓和的,正是人情。女工赵梅英最终承认错误是因为军事代表不计前嫌来看她,并不扣工钱;刘良感到愧疚是看到工人们工作的热情和老工人的随和;刘长巧改过是因为积极分子朱桂芬将粮食分给大家而没有给自己,而之前朱桂芬发表过一长串的政治理论演讲对她却毫无影响。人情的感化作用已经远远超过政治的号召力量。路翎本意是要体现新中国以来落后分子的积极转化,结果还是逃不出人情隐约地控制。
正因为路翎的小说表现了人与人之间这种自发的淳朴的感情,他的作品才具有了真正动人的魅力。《初雪》一经面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著名文学评论家巴人说:“作者着力之处,在于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的精神世界的描写;在于把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车上的朝鲜妇女、孩子之间结成了一条不可割断的生命线索的描写……只有这一精神,才是鲜血与生命结成的长城,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量。”[14]《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的反响更为热烈,我们可从当时的大批判文章中得以窥见真相。魏巍说:“有人洒了同情之泪,深夜写信向路翎致敬。并且还听说一位教授兼作家惊叹它是解放以来最优秀的作品,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杰作。”[15]陈涌认为:“有关爱情这类感情的问题更容易迷惑读者。路翎这篇作品用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论的观点来歌颂‘爱情’、歌颂‘赤诚的眼光’等等的时候,我们有些读者便相信了,感动了。”[16]
路翎小说的“退”与“守”并非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作家所必须普遍面临的尴尬遭遇。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作家们能够坚守的阵地也越来越狭窄,许多作家处在失语的位置,完全丧失了为个人代言的机会。当他所坚守的位置不允许他再“退守”时,他必然就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丧失了说话的权利,被主流意识形态以“革命”的名义予以手术式的摘除,几致遭受灭顶之灾。路翎成为见证一代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青春,在政治与时代面前失语的尴尬境地的极佳标本。刘小枫的一段话颇有抒情意味:“社会主义事业有如那班定时开出的火车 (历史的必然),某个人与这班火车的个体关系仍然是偶然的”,“在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与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生存裂隙。偶在的个体命运在按照历史进步规律设计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颤然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17]这或许就是个人在历史面前的一种宿命:历史前进的车轮在个人身上碾过,个人则成了历史展开的见证。
[1]冀汸.哀路翎[J].新文学史料,1995,(1).
[2]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N].文艺报,1952-09-26.
[3]路翎.在铁链中[M].上海:上海海燕书店,1949.
[4]胡绳.评路翎的中篇小说[C].大众文艺丛刊 (第1辑),1948.
[5][8][12]晓风.胡风路翎文学书简[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6]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N].文艺报,1954-12-01.
[7]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意[J].读书,1981,(2).
[9]十月文艺丛书 (1)[C].天津:天津知识出版社, 1951.
[10]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N].文艺报, 1955-01-04.
[11]钱理群.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说《路翎未完成的天才》[J].读书,1996,(8).
[13]余林 (路翎).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 [J].泥土,1948,(6).
[14]巴人.读《初雪》——读书随笔一 [N].文艺报, 1954-01-31.
[15]魏巍.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 [J].解放军文艺,1955,(3).
[16]陈涌.认清《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质[J].中国青年,1955,(14).
[1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修订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