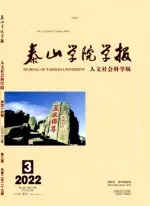再论秦汉以来我国乡村基层行政的专制性
万昌华
(泰山学院历史系山东泰安 271021)
自 20世纪前期开始,中外学者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郡县型的行政体制之下,广大的乡村基层社会是自治的民主政治体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我国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比费孝通“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皇权——乡绅二元模式”的观点走得更远,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上世纪初年造说认为,传统政治之下中国的皇权统治根本就出不了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韦伯说:“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治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治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1](P110)另外,日本学者和田清上世纪七十年代也著有《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一书,专门讲中国所谓的“发达的地方自治”。[2]
本人认为,以上诸人的中国中古时期乡村社会是自治的二元的民主社会的观点与秦代以来我国乡村基层社会的历史实际相背离。另外,如丘吉尔所言,书写历史也就是在创造历史。以上诸人如此的忽悠中国中古时期乡村社会的历史,会给我们当下基层农村的政治社会建构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有关的史实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与分析梳理。
这个工作本人之前已在进行。比如,2008年9月齐鲁书社出版了拙著《秦汉以来基层行政研究》(与兴彬合著),今年 1月同出版社又出版了拙著《秦汉以来地方行政研究》。从网上可以看到,以上二书现已销往北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和港台地区。本文是以上二书中论题的继续。
一
从秦朝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广大乡村实行的是乡里组织与亭组织,两套并行的社会基层控制系统。其中,乡里组织是基层行政控制系统,亭组织是县府派驻到基层社会的主管治安的机构。这种对乡村基层社会实行严厉控制的基层社会行政编组方式,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县令条中写道:“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游缴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缴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我们后边将要讲到,班固这段话中关于当时乡里基层行政组织的记述基本正确,但“亭”的记述不正确。“亭”是秦汉时期县行政之下基层社会行政中的另一分支,主要管弹压,是一种有别于当时正式乡村基层社会行政的准基层行政机构。
《后汉书·百官志》:“乡置有秩、三老、游缴。”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缴掌缴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关于亭,该志另作一条曰:“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与前引《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关的记载相比较,此种表述应更与事实相符。
乡啬夫是秦汉时期统治乡村基层社会的主要乡官之一,为秦国原来的旧制。此事可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田律》、《廐苑律》及《仓律 》。[3](P30,P36)
秦汉时期的另一主要乡官乡三老也为秦制。《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自立为将军、与吴广率起义军入据陈后,曾“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由此可见,秦代的三老都是在乡里有影响的人物。
汉代建立之后承袭秦制,乡官制度继续,同时又有所发展。一是如前引《后汉书·百官志》县官条本注中所云,乡啬夫分成了两种:有秩啬夫与一般的县置啬夫。有秩啬夫由郡府任命。有秩就是有官品、禄秩的意思。二是汉代三老有乡三老和县三老之分。
出土资料也清楚表明了西汉时期主要乡官啬夫有“有秩啬夫”与一般啬夫之分。据《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西汉末年东海郡共有 170个乡;有乡“有秩啬夫”大约 28人,有一般乡啬夫137人。①东海郡的郡置乡“有秩啬夫”与县置乡啬夫二者相加约是 165人,165人这个数字与东海郡有 170个乡的数字非常接近。此事可以证明,两汉时期虽然乡“有秩啬夫”与乡啬夫同是主要的乡官,但二者不是一回事,他们分开设立,有“乡有秩啬夫”的乡就没有县置乡啬夫,有县置乡啬夫的乡就不再设“乡有秩啬夫”的观点正确。另外,从《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以上的有关内容看,当时乡啬夫中郡府任命的“有秩啬夫”与一般县置啬夫的比例大约是 1∶6。
总之,以上史实充分表明了这样几点:乡“有秩”是乡“有秩啬夫”的省称,一般乡啬夫在级别上要低于乡“有秩啬夫”;二者虽秩级有别,但职能相同,都是一乡的行政长官;每乡或设“有秩啬夫”,或设有一般啬夫,没有一乡两个啬夫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乡有“有秩啬夫”,《续汉书·百官志》云乡置“有秩”,这样的简单表述易使人产生歧义。如果再展开解释一下的话,大概当时的乡“有秩(啬夫)”由郡任命,一般的乡啬夫由县署,如同今天的镇长、乡长之设,同是乡镇的行政一把手,有乡级乡镇干部与副县级乡镇干部之别。所以如此,原因是不同秩级的官吏要由不同级别的行政主管部门管辖。副县级级别的乡镇长要由地区级的组织部门任命,一般的乡镇长只要县里任命就可以了。
要之,秦汉时期的乡行政长官,不管是“有秩啬夫”,还是一般的乡啬夫,都是在籍的皇家官员。用现在的话说,是吃“国库粮”的脱产的“国家干部”。凭着这个基础,他们完全可以在皇家的行政体系内继续高升,有的还能当上大官。比如朱邑,宣帝时为舒桐乡啬夫,后官至大司农。[4]再比如张敞,以本乡有秩补太守卒史,然后察廉为甘泉长。[5]
关于汉代设立三老的情况。《汉书·高帝纪》二年二月,“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戎。”这里的县三老,似还是任职于具体的一个乡,只是,有了县三老名义的人身份比一般的乡三老要高而已。以后此制有变化。
据史料,当时各地设立县三老的情况普遍,并且以后还有了更高级别的三老——郡三老。《东观汉记》:秦彭为山阳太守时曾“择民能率众者为乡三老,选乡三老为县三老,令与长吏参职”;《郃阳令曹全碑阴》有“县三老商量”、“乡三老司马集”题名。[6](P189)《后汉书·王景传》:王景“父宏为郡三老。”
《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都说乡有游徼,言“徼循禁盗贼”或“徼循司奸盗”。但其他史籍所见游徼均直属于县廷。
《汉书·胡建传》中有“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之句,《汉书·赵广汉传》中有“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置百石”之句。《汉书·黄霸传》中言黄霸少时为“阳夏游徼”。《汉书·朱博传》中有“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贼发不得,有书。檄到,令丞就职,游徼王卿力有余,如律令”的记载。东汉时期,《后汉书·臧宫传》中有“少为县亭长、游徼”句。《后汉书·郑均传》引《东观汉记》:“兄仲,为县游徼。”《后汉书·王屯传》:一女子诉某亭长枉杀其家人十余口后,“(眉令)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即系,及同谋十余人恶伏辜。”以上所有这些关于游徼的记载均不言乡。不但如此,有的还直称某县游徼,或县游徼,或门下游徼。
门下游徼的称谓又多见于碑刻。如《堂邑令费风碑》、《中部碑》不但有“门下游徼”的记载,而且还列于门下功曹之后,门下贼曹之前。[7]又如《苍颉庙碑侧》,左侧有万年左乡、北乡有秩,莲勺左乡、池阳左乡有秩等等,门下游徼则在右侧列于功曹和门下贼曹之间。[6](P202)
严耕望先生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一书的第五章《县廷组织》中写道:“乡游徼即县职之外部耳,碑传所见游徼,其中或有出部者,惟同是县吏,故统称县职欤?”[8](P228)安作璋、熊铁基二先生则说:“可以认为,游徼是直属于县而派往各乡徼巡者,……巡行于乡以禁盗贼,故名。”二位据《五行大义》引用的翼奉话“游徼、亭长,外部吏,皆属功曹”后指出,“游徼为县职,是分部于各乡的”县令长的直属吏员。[6](P202)以上三位先生的论断正确,但仍有补充的必要——汉代游徼是县令长的心腹属吏无疑,但并不是各乡都派驻。新出土资料表明,汉代各个县的游徼数目与它们所拥有的乡的数目不一致。此点更可进一步证明以上三位先生的论断正确。
前已述及,据《尹湾汉简·集簿》西汉末东海郡共有 170个乡。但东海郡当时并非有如此多的游徼。总计,东海郡当时才共有游徼 82人,游徼的人数不能与东海郡的乡数对应。从具体的记述上看亦如此。比如,海西县是东海郡的大县,有14个乡,但只有游徼 4人;下邳县次于海西,有 13个乡,却有游徼 6人。而厚丘县的游徼相对而言人数更少,9个乡才只有游徼 2人。厚丘县平均 4个半乡才有游徼 1人。
但是,当时东海郡却是每县都有游徼,最多的6人,最少的也有 1人,无一或缺。
从以下《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中各县吏员的排列次序看,游徼是属于县主官令长直接管辖的县府吏员无疑。比如其中记道:“海西吏员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游缴四人,牢监一人,尉史三人”;“下邳吏员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游缴六人,牢监一人,尉史四人”;“郯吏员九十五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游缴三人,牢监一人,尉史三人”。必须指出的是,以上的排列决不是无意的。肯定是有意为之。正是因为县令、县丞和县尉在一县之内的依次是一、二、三,所以才有了游徼、牢监和尉史地位排列的后一个一、二、三。总之,可以这样认为,当时游徼是根据各县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各县具体社会治安状况而设立的,人数并不确定。由于当时游徼长期巡行于乡间司奸捉盗,因而后人在记述有关的历史时不仔细考究,而误认为他们是乡官的一部分了。
为了加深对此点的理解,我们在这里不妨也可以用个中国当代的历史后例来做注释:当时的游徼很像前些年各地县里派往农村的驻村干部。他们虽然是县府隶属的干部,但每年都有很长的时间住在乡间检查与督导工作。
从《尹湾汉简·集簿》和《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中的有关内容看,当时的“亭”不在乡行政系统之内。“亭”与乡、里基层社会行政单位,三者之间无十进制的关系。
《尹湾汉简·集簿》一开始记述东海郡的四项内容,每项都是单列的:第一项:“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侯。都官二”;第二项:“乡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第三项:“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如前”;第四项:“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我们从上述记述中完全可以看清楚,当时亭的组织与乡、里完全不是一个系列。
从《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述的东海郡各属县有关亭的具体情况看,亭亦不与乡相属相统无疑。比如,东海郡海西县有乡 14个,按十进的关系的话应有亭 140,但实际上不是。海西县只有亭 54个。东海郡下邳县有乡 13个,按十进的关系应设亭 130个,但却只有亭 46个。兰陵县有乡 13,按十进的关系应设亭 130,但只有亭 35个。总之,以上史实均清楚表明了,秦汉时期亭的设置与乡行政组织没有直接隶属的关系。
《后汉书·百官志》:“亭有亭长,以禁盗贼。”由此可知亭长与游徼二者在职责上相近。据史籍中的有关内容可以断定,亭长与游徼一样,也是一种县令长的直属吏员;亭是各地县行政机关在自己辖区内分布于基层的固定统治据点。
要之,这里需要正确理解前已揭《五行大义》中所引用的翼奉的话:“游徼、亭长,外部吏,皆属功曹”;以及正确理解《后汉书·臧宫传》与《后汉书·王屯传》中的“少为县亭长、游徼”与旧日亭长“即今门下游缴者也”的话。这些话语中所包含的更多历史信息应是,“部”字不能理解为区别内外的“部门”之“部”,而应理解为动词,“部署”之“部”;虽然游徼与亭长二者有地位高下之分,但职责相同,即他们都是县令长们专门部署在县驻地以外、主要负责弹压与镇制的亲近属吏。游徼与亭长,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1、一般,游徼的管刺监督地区大,是数个乡。亭所管刺的地区要小,往往一乡之地就有几个亭;2、亭长在各乡地界上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亭,而游徼的“办公场所”一般设在县府。大概在当时,亭长只有干好了才能升为游徼。
据史料记载,未统一东方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者就在其统治区内广泛设亭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有“市南街亭求盗才 (在)某里”,“某亭校长甲,求盗才 (在)某里”,“某亭求盗甲告曰”等的记载。[3](P252,P255,P264)由以上的有关内容推断,秦国当时主要是在城镇人口较稠密处设亭。至秦王朝建立后,他们便更广泛设亭于广大乡村地区了。《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在秦朝为泗水亭长时曾使求盗至薛治竹皮冠。《集解》引应劭曰:“旧时亭有两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巡捕盗贼。”应该说,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民警派出所组织的祖宗就是秦代的亭。
至汉代,亭的制度较秦代又有发展。前揭《尹湾汉简·集簿》载,东海郡西汉末年有亭 688个,有亭卒 2972人,邮 34人,另有 408人如前。另据《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当时另有亭长 688人,则当时每亭有亭成员近 6人。此人员数目多于秦国时的每亭校长一人,求盗一人,也多于秦朝时的每亭有亭长一人,亭卒二人。
《汉书·刑法志》中有“狱豻不平”语。服虔曰:“乡亭之狱曰豻。”由此可知,因为亭长有权捕拿犯人,汉代时亭内也设立了关押犯人的场所——乡亭临时监狱豻。
东汉时乡亭制度继续实行。卫宏撰《汉官旧仪》曰:“尉、游缴、亭长皆习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9](P49)
名义上设乡亭、置亭长是促进社会治安的,但其中弄权、欺压人民者大有人在。《后汉书·鲁恭传》:鲁恭拜为中牟令后有治下某亭长借人牛不还,“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敕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后汉书·卓茂传》:卓茂“迁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辟左右问之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人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
《后汉书·百官志》乡官条本注曰:“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另,《宋书·百官志 》:“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乡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在这里,乡佐放在了乡官首位。也是据《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上述记载均不诬。
出土的《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中的乡佐均列于亭长之前。西汉末年东海郡各县大都有乡佐。乡佐与各县乡的数目不尽一致。亦即并非所有乡皆有乡佐。比如,海西县有 14个乡,但仅有乡佐 9人;下邳县 13乡,仅有乡佐 9人;郯县有乡 11个,有乡佐 7人;兰陵县有乡 13个,有乡佐才 4人。但是,在东海郡的下属县邑中,几乎每县都有乡佐。最多者 9人,最少的属县□□和昌虑只有乡佐一人。18个属县中,仅司吾一县无乡佐。由以上《宋书·百官志》的把乡佐列乡官之首及《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中的乡佐列亭长之前可知,乡佐也当是类似于游缴,是县令长们的外部吏。所不同的是,二者虽然同为县令的直属吏员但工作的领域不同。乡佐的工作是在经济领域。
总之,乡佐与游缴一样,也是各地县行政机关直属的工作在乡村基层社会中的下沉官。
上述乡级行政与亭的系统还不是秦汉时期最基层的社会行政治理的承载者。其下还有里组织与什、伍组织。
秦代乡之下就有里组织普遍存在。《史记·高祖本纪》云:刘邦是原秦朝“沛丰邑中阳里人”。原注引应劭曰:“沛,县也;丰,其乡也”。“中阳”当然就是刘邦所在的里之称了。我们这里顺便提及的是,刘邦原来不是丰乡人。是秦统治者用强力把其全家从魏地迁来的。《汉书·高帝纪》引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班固说:“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故其“骨肉同姓少。”按大梁之破在秦王政二十二年 (前 225年),而刘邦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前 256年)②,则刘邦举家被迁到沛县丰乡时他的年龄已在 30岁左右。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述到了汉代的基层行政组织“里”。《尹湾汉简·集簿》“乡里条”也是记述到“里”。里有里正。实际上,不但如此,自秦代起,“里”之下还有组织。《后汉书·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已告监官”。此记大体不诬。大概,此种制度自商鞅变法时起秦国就开始实行了。
《商君书·境内篇第十九》:“五人束簿为伍,一人羽而刭其四人”,“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由以上史源看,司马迁的记述正确。因为是兵民为一,当时一般的成年男子都被编成“伍”。五人一伍,因而其称谓也就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士伍”了。在未正式确定百姓为“黔首”之前,秦国的成年男子被统称为“士伍”。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法律答问》以及《秦律十八种》中有关的内容多多。比如:“士五 (伍)甲盗一羊”;“士五 (伍)甲盗,以得时直 (值)臧(赃),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士五 (伍)甲盗,以得时直 (值)臧 (赃),臧 (赃)直 (值)百一十”。[3](P163,P165,P166)当时,士伍们都在里正的严密管辖之下生活,并且相互间有犯事连坐的法律责任。
很明显是避秦王政之讳,里正当时统称为里典。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的记载亦多。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律曰‘与盗同法’,有(又)曰‘与同罪’,比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3](P159)《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 (伍)丙,告曰:‘疑癘 (疠),来诣,”“爱书: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 (伍)丙经死其室,不智 (知)故来告。”[3](P263,P267)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傅律》和《法律答问》,秦代伍的头目称作伍老。《傅律》:“典、老弗告,赀各一甲”。[3](P143)《法律答问》:“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曰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3](P193)另,《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记述,秦襄王病,百姓“杀牛塞祷”,结果“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以上内容是说,因为讨好统治者讨的不当,里正与伍老都被罚了款。
“编户齐民”一词最习见于汉人的著作。[10]有时,编户齐民又简作编户、编户民或齐民。分别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下》和《汉书·高帝纪下》等。什么是“编户齐民”?就是不分贵贱、无一例外地利用行政权力把全社会所有的人都严密组织起来。《汉书·高帝纪下》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食货志下》引如淳曰:“齐者,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然而,人民之间无有了贵贱,但他们相对于最高专制统治者而言却全部的下贱了。
与秦代相同,汉代的人民也统统进入了最高专制统治者编就的基层社会组织牢笼之中。
《汉书·韩延寿传》:韩延寿为颍川太守时“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师古曰:“若今之乡正、里正也。五长,同伍之中置一人为长也。”《汉书·尹赏传》: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后,曾率部属及“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
以上有关汉代里伍组织的记述中有两点需要补充或展开。一是里正、伍长是汉代常制,不是韩延寿个人的发明;二是其中讲明了汉代里正与伍长之间还有一基层层级。关于第二点,新公布的出土汉律中明确记有田典的乡官官职可以给予说明。③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不只一处记有田典。比如,《二年律令·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 (即里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另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很明显,这里的田典,既不是里的负责人,也不是伍长,就是司马迁写《史记·商君列传》时所见到的汉代的“什长”。另外,以上的“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开;伏闭门”之句所勾勒出的当时广大乡村被严格控制起来的社会状况,应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
秦汉以后,我国广大乡村也是被严密的编组成乡、里、什伍或保、甲、什伍的。只不过是,有时候乡里组织的名称有些变化,或者担任里甲组织的人身份有了变化而已。
比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国家不但严格控制核心地区,而且对非核心地区的控制也十分严密。从 1999年公布的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中的有关内容中,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吴国乡里制度的细部有关情况,以及国家政权对县以下乡里社会进行严密控制的有关情况。简牍表明,不是当时吴统治腹地的长沙走马楼地区也有发达完备的乡、里、丘等社会基层行政设置。即乡与里的行政单位之下,当时还有丘。国家进行户口登记时以丘为单位。所有人户都被编组进了各个丘。各丘中人户姓氏混杂,不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制。人户中所有人的姓名、年龄与生理特征等,都必须详细记录在户口册上。县廷中的专管吏员对自己所管辖的乡里严格管理,必须具保,负有连带的法律责任。以下这几支简就记录了有关的详细情况:“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 (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莂保据”;“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聋颐病,一人夜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逸及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给县吏。辄隐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莂保据”;“东乡劝农掾番琬叩头死罪白:被曹敕,发遣吏陈晶所举私学番倚诣廷言。案文书:倚一名文。文父广奏辞:本乡正户民,不为遗脱,辄操黄簿审实,不应为私学。乞曹列言府。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诣功曹。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11](P32-33)《后汉书·百官志》曰:县廷的“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秋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由此可知,如我们前些年人人都熟悉的农村工作队,劝农掾是当时吴政权从县里下派到各乡村中的下派“干部”。另外由此可知,当时是禁止人们自由外出求学的。不经官府批准老百姓的后代私自外出求学属违法行为,所犯罪的罪名是“遗脱”。晋代,此乡官之制仍基本实行:“凡县五百 (户)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12]
南北朝时期也是沿袭的秦汉的一套基层社会进行严密编制的制度。比如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他们都是如此。北魏的实行邻、里、族党三级乡里制始于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当时是采纳给事中李冲的建议实行的,称做三长制。具体做法是:“三长,谓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13]东魏的乡里组织是以五家为邻比,二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北齐时则是“人居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十有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14]
与前代一样,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在统治县以下广大乡村社会上也费尽了心机。
隋王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就“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15]隋文帝开皇九年 (589年),在苏威等人的奏请下,乡村的党又改称为乡,并扩大辖区:“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16]同时,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但事后一年,即开皇十年,隋统治者即因关东诸道巡省使虞庆奏“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于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赂”,于是又废除乡正理辞讼之权。[14]
唐代的乡里组织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17]乡置乡长与乡佐,里置里正。相比较而言,唐代统治者对里正的选拔与任用更为重视。史载,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掌案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税。”[14]为了更好地发挥里正临民的积极性,唐统治者对其极为优渥,免除他们所有的劳役与赋税。[18](P200)
作为秦汉时期傅籍与编户齐民制度的延续,唐统治者与前代统治者一样,也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且唐代也定期搞貌阅。
唐律中的《户婚律》、《捕亡律》中都有关于户籍制度的规定。《户婚律》首重的是民户户口的脱漏和年状的增减,规定民户、里正和州县官府都必须对这类违法行为负责。脱漏户口指隐瞒户口不在户籍上登记;增减年状指“增年入老,减年入中、小及增状入疾”。唐律对于家长、户主和尊长也有明确的规定,表明了法与礼的结合,反映国家与民户的关系。唐律的《捕亡律》主要内容是逃亡法。其中关于丁夫、杂匠、民户、官奴婢等逃亡罪的规定属于户籍法的范畴,规定了民户和地方行政人员对于上述人员逃亡应负的责任。
唐律还根据《户令》中关于邻、保组织民户互保的有关规定,规定了民户的某些犯罪要追究连带责任,按相纠连坐法惩治。[19]
如有关专门研究者指出的,唐代的户籍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下列方面的内容:
一、为了调查、登记和统计户口,实行了严密的“手实”制度和编制籍帐的制度,规定民户必须如实申报户口和土地,地方行政组织必须定期编造户籍和计帐;
二、为了检核户口、控制民户,实行了定期貌阅户口和对地方行政官员的考核制度,规定地方行政组织要定期检查丁口的实际年龄、形貌、身状是否与户籍登记一致,对于脱户、漏户、逃亡等违法行为,必须按律的规定进行惩治,对于新附入籍的民户进行优待,免除一定时期内的赋税徭役;
三、为了使民户之间互相牵制,规定民户犯罪的相应责任,做到互保相纠。
唐代编造户籍时户主自己先填写家庭所有成员的情况的“手实”,官府逐一核实,装订成册,叫做户籍帐。户籍帐由里到乡,然后到县到州,直至中央。
根据文献记载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经济社会文书,可知唐代户籍的基本内容是由手实与官府人员加名籍 (户口)的详细的脚注两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户主和家庭成员姓名、家庭成员与户主的关系;2.性别;3.年岁;4.年状。唐代如同隋代,也按年龄把人们分为老、丁、中、小、黄几种;5.身状。是否三疾,即病疾、笃疾、废疾;6.身份。分为官、民、贱等几种。
户籍的脚注体现了政府对户籍登记的具体管理,主要包括人口变动、年岁和身状的改定以及是否向政府交纳租调 (课户、不课户)等。如果在两次造籍年份之间民户内有人口死亡,到新造户籍时要据实申报,在脚注中正式削除,注明某年帐后死或籍后死。民户有逃亡或没落,迁入或迁出,有新生、归附(指少数民族内附者)、括附 (隐瞒户口而经检括附籍者)、漏附 (前次遗漏而新附籍者)或者残、疾等情况,也皆须在脚注中注明。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宋元明清时期我国乡村基层行政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人员的身份尽管职役化了,但该组织在控制社会与民众人身方面没有变化。比如北宋,开宝七年 (974年)曾一度废“乡”设“管”,每管设户长,主赋税;设耆长,主盗贼、词讼事;[20]再如南宋时期高宗建炎元年 (1127年)“罢户长催税,复甲头”;绍兴七年 (1137年)下令“大保长仍旧催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又“令保甲催税”。[21]此处,不管是管的户长、耆长也罢,甲头也罢,还是大保长,都只不过是名词与概念的不同,其为最高统治者管束人民的职责与性质与前代没有不同。
宋代保甲制度控制人民的反动性尤其不能低估。它的要害在“保”与“甲”,这些东西是专制国家权力对乡里社会最基层的直接渗透。保甲组织之下,“故有所行,诸自外来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听送所属。保内盗贼,画时集捕,知而不纠,又论如律。”倘若保丁“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22]当时,统治者通过这种人人具结家家犯事连坐的方式,比较容易地把整个乡里社会牢牢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上。
当时此方面具体的事例也不少。比如张咏在蜀时规定“凡十户为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籴,民以此少敢犯法”。[23]有人在讲到该问题时往往认为推行者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因而他的保甲制度也不能否定。但必须清楚,王安石是位君主专制主义者。他有《兼并》诗一首,其中讲:“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操权柄,如天持斗魁;取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24]从此诗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商鞅一样的是一个强调强主弱民、进行被统治者之类的类的自我否定的人。
宋代最高统治者的主要根椐财力将乡里社会人户划分为九等,不管比较富有的人家同意与否,上等户都必须担任乡里职役。不仅如此,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四月辛亥,政府又规定里正负责催税及承担县里的差役,充当衙前。[25]里正一旦充当了衙前,往往被连累得倾家荡产。所以,当时民富者不敢露富,贫者也不敢求富,人们争相逃脱担任里正衙前,甚至出现过民以死求免充里正衙前的惨状。如宋仁宗时韩琦说,“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自经而死”。[14]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自宋代开始,乡里组织的头目一改了在秦汉时位要声显的状况,从而成为了任州县官吏任意驱使的差役。并且一般讲来,这种状况越到后世其程度越加严重。此事表明了,在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大政治环境之下,乡里组织的“干部们”其身份可以是多种形态的:可以给里正们以特权,让他们利益均沾;也可以不给里正、户长们以特权,让他们以奴隶的身份来为自己效劳。但是要之,他们都不代表农民自己与乡村社会本位的利益、愿望及要求。
与宋代大体相同,元代乡职也实行职役化。其中,里正受专制国家的压迫与盘剥尤甚。往往,杂差任务下来后里内的地痞争相逃脱,在此情况下,只好由担任里正的较富裕的人家他们自己承担;一般人户完不成催征了,专制政府也强迫他们支垫贴赔。因而,元代过得较好的人家一旦充任了里正,也往往是不久便倾家荡产。史载,“顺帝至正中,以浙右痛于徭役,民充导正者,皆破产”。[26]
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曾规定广大乡村互相知丁。即规定一村之内的人必须互相知道各家的男人在干什么;如果不在家的话也必须知道此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朱元璋规定的互相知丁互知“务业”的具体内容是:“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具在里甲。县州府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或异四业而从释道者,户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业,必然有效”;“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且于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入可验,无疑为也。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细所为,邻里采知,巨者归迟,细者归疾,出入不难见也。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近水陆,明于引间。归期艰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27]
为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朱元璋另外规定在里甲设专职负责教化人的“老人”。“老人”也是乡役的一种。对于明统治者搞的这种老人制度及其他一些专制措施,当时的一些人曾给予了肯定。比如,海瑞称:“圣制老人之设,一乡之事,皆老人之事也。于民最亲,于耳目最近。谁善谁恶,洞悉之矣。尤择一醇谨端亮者为之。以年则老,识则老,而谙练事务则又老。有渠人,因构一亭书之曰申明亭。朔望登之以从事焉。是不计仇,非不避亲,毋任口雌黄,不凭臆曲直。善则旌之,恶则简之。此亦转移风俗之大机括,而乡落无夜舞之鳅鳝矣”。[28](P149-150)明代另一位士人邓士龙则记述道:“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29]对此,我们应做何思考呢?我想,虽然专制统治者们不大喜欢海瑞,但海瑞却是忠心于专制统治者与专制制度的。这是其一。其二是,朱元璋时的“人间道不拾遗”大概类似于秦国的“民风纯厚”。到过秦国的荀子当时谈到过此事。人都被驯化得不敢有一点的“私心杂念”了,必然的会“人间道不拾遗”。另外,顾炎武也曾说:“太祖损益千古之制,里有长,甲有保,乡有约,宽有老,俾互相纠正,当时民醇俗美,不让成周”。[30]我们认为以上对于朱元璋专制乡里制度的歌颂都是愚见。尤其是顾炎武之论,更是如此。成周时期国人能参政议政,可以自主废立国君,而朱元璋治下的广大乡村小民如同畜栏中任他随便整治的牛马,顾炎武竟将二者硬扯到了一块,实令人不可思议。
在许多方面,清代统治者对乡里社会的控制同样的严厉。比如,清统治者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都实行严格的人口月报制度。有人言,“保甲之法,清查户口,讥查出入,……每乡置循环簿,月朔报县,而县之官吏……年终报郡。”[31](P303)大概从清朝到民国时期,我国在推行保甲之法的日子里,具体情况都是这样的。
还有,清代规定对僧尼道士也实行编甲:“至于寺观,亦分给印牌,备书僧道口数、姓名,稽察出入。”[32]“和尚道士尼姑之庵观寺院,其师徒籍贯年岁田房,本身有无残疾。俗家有无亲人,皆应逐一详注,一律编人保甲”。[33]再比如,清政府把乞丐也组织起来了。乞丐也实行了编甲。史载,其方法与措施“一是选立丐头为管束之人,二是查造丐户牌册,三是驱逐少壮乞丐,四是老幼乞丐建栖留所安置,禁止散处。丐头,……人选可由栖止地段的民户保长择举。也可以由管辖该片的衙役保充。江南农村常按‘坊’承管乞丐。乞丐亦造保甲牌册,曰‘丐头循环册’,开列丐头姓名,承管乞丐人数,年岁、籍贯、体貌特征和栖身处所。由于丐群成员常有变动,在上述各项之后,还须以四柱形式写明每月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人数,按月送县例换。此外,乞丐各有腰牌,两面书写。正面为县正堂示谕,背面记本人姓名、特征及所隶属丐头之名,顺庄编号,常挂腰间……。”[34]清统治者一般不许人异地讨饭。如有此类情况出现,则要求“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察”。[35]
三
除了以上列举的诸多史实能清楚表明我国秦汉以来的乡村基层社会是被专制的国家权力控制与管制的、而不是如费孝通所言是什么自治与民主的之外,有关思想家与学者的一些论述也能加深我们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所谓社会基层的民主与自治应是,一、他们在一般情况下绝无外在的强加的专制政治权力;二、他们在行动上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当地居民的意志、而不是受着更高行政权力的不时的制约与定向。[36](P65-108)具体到我国中古时期广大乡村的实际情况,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认为,“缺乏自治更接近 (传统政治下中国)乡村生活的实情。”[37](P338注释[12])有我国旅居西方国家时间最长的法学家之誉的瞿同祖则认为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中根本就没有自治。他说,“清代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是按同样的原则组成的,所有行政单位,从省到州县,都是中央政府设计和创建的。……所有地方官员,包括州县长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州、县或组成州县的市镇、乡村,都没有自治。”[37](P5)
除了萧公权和瞿同祖之外,当代坚持中国传统社会内没有乡村自治的,比较知名的学者或思想家还有鲁迅、钱端升、刘泽华等人。分别见鲁迅的文章《灯下漫笔》,钱端升著作《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和刘泽华先生的著作《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刘泽华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的广大乡村社会中不但没有自治与民主,人民甚至是些被奴役与被完全制服了的国家奴隶。可分别参见其著作《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的第二章《君主集权国家对人身的支配》与第三章《君主集权国家对土地的支配》。[38]
另外,瞿同祖先生的关于中国中古时期乡绅这一在乡村社会中比较有影响的阶层性质的分析,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士绅的特权地位并不纯粹取决于经济基础。士绅的成员身份,并不像有些学者推测的那样来自财富或土地拥有。无疑,在财富和士绅成员身份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而财富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拥有财富,使人有足够的闲暇接受参加科举考试所必须的教育。……然而,在具备进入特权阶层的条件与特权身份的实际获得之间是有差距的。财富和地产本身不是士绅的身份的充分条件。庶民地主不论拥有多少土地也不属于士绅集团。只有在向政府购买官衔或学衔 (国子监学生身份,监生)成为可能时,财富和身份之间的联系才可能最紧密。售卖官爵功名是清朝时的普遍做法,特别是在 19世纪的危机局势迫使朝廷寻求额外的收入之时。这是唯一绕过科举考试、将财富直接转变为地位的情形。……另一方面,任何有功名或得到官方委任的人,无论是否有地产,也可以马上跻身士绅之列”;[37](P286-287)“中国士绅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是基于政治而产生的。”[37](P285注释9)瞿同祖先生在该书中还指出,“关于士绅,……他们代表地方社区的权利,是得到政府和公众普遍认可的。他们作为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斡旋者,向地方官员提供咨询,经常在地方行政的某些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因为地方社团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经常被视为地方自治的条件,所以问(中国清代)士绅参与 (地方管理)是否意味着地方自治,就是一个依逻辑当然有的疑问了”;要问中国有无地方自治的话,“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参与者仅限于作为少数人群体的士绅。其次,士绅既非地方百姓选举的代表,也不是政府任命的代表。他们只不过凭籍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被(习惯上)接纳为地方社群的代言人而已。但是他们参与政府事务和代表地方社群说话的权利,并没有像西方民选议会那样在法律上正式明确下来。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个士绅成员应该被咨询或应该被邀请参与行政事务,这些都主要随州县官们自便。……实际上,士绅的介入主要是基于个人标准,其效力也主要依赖于特定士绅个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即使士绅有权利在地方政府中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仍然没有代理人去代表地方社会的其它群体。”[37](P337)
以上瞿同祖先生的分析非常深刻,我们完全赞同。另外要补充的是,如一首清代的对联所说的,中国当时地方绅董的地位相对于正式的皇家官吏来地位比较可怜,他们得时不时地向州县官“袖金赠贿”,④即得时不时地向州县官们暗自下礼行贿。
总之,在君主独裁专制主义与极度中央集权主义的中国中古旧时代里,中国的广大乡村中是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自治与民主存在的。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一种集中营式的被管制下的农民“自己人治自己人”的伪自治与伪民主。因此,如果从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建设基层自治与民主的思想与制度营养的话,也只能是像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民政府大员陈立夫一样,找到的是“管、教、养、卫”。[39](陈立夫序)
[注 释]
①《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清楚写明了的乡有秩是 24人。另外有的县之下虽然清楚写明了有“乡有秩”,但数字已失。乡有秩有一县多至 4人或 5人的,以上的估计是取了它们的中间数。
②据《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
③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实行的律令。
④这副清代对联主题是讽刺当时的州县官的,全文是:“见州县则吐气,见道台则低眉,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只解得说几个是是是;有差役为爪牙,有书吏为羽翼,有地方绅董,袖金赠贿,不觉得笑一声呵呵呵。”载《经典杂文》,2008年第 4期。
[1]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和田清.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 [M].东京:东京汲古书院,1975.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4]班固.汉书·朱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班固.汉书·张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下)[M].济南:齐鲁书社,1985.
[7]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
[9]孙星衍等.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刘安,苏非,李尚,伍被.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1]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上)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2]房玄龄.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魏收.魏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马端临.文献通考 (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魏征.隋书·食货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魏征.隋书·高祖纪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7]刘句,张昭远,贾伟.旧唐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A].吾土吾民[M].北京:三联书店,1992.
[19]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0]徐松.宋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1]赵彦卫.云麓漫钞 (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2]脱脱.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3][35]徐栋.保甲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24]王安石.王临川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M].北京:中华书局, 1961.
[26]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7]朱元璋.大诰续编·互知丁业[A].钱伯城等.全明文(第 1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8]海瑞.海瑞集 (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29]邓士龙.国朝典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 1993.
[3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31]闻天均.中国保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5.
[32]昆冈,李鸿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3]叶世倬.为编审保甲示 [A].徐栋.保甲辑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4]王风生.保甲事宜[A].徐栋.保甲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7]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8]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39]黄伦.地方行政论[M].重庆:正中书局,1942.
——三老讳字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