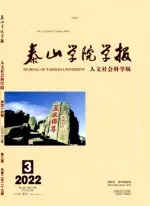中国文化中的“暴力”倾向
刘 凌
(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古今中外,均盛称中国自古“热爱和平”。确实,中国外侵,即非绝无,也是少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蹄,虽曾踏遍欧亚大地,但我们却可辩称,他们是“非我族类”,尽管毛泽东在《咏雪》词中颂其为“英雄”。即使想征服外国,也大多主张“讲信修睦”、“修文德以来之”。以至有人批评中国对外过于“文弱”。大约,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食稻(谷)民族,它既无扩张的冲动,也无扩张的能力吧。
然而,对内还能否这样说呢?
关于“武”的字义,人们每称“止戈为武”,并由此判定传统文化的反战倾向。但这尚需具体分析。杨伯峻先生指出:甲骨文中“武”字实乃“象人持戈以行”[1]。足见最早的“武”字,是“持戈”,而非“止戈”。本字何时演变为“止戈”字形,难以确考。“止戈为武”释义,始见于《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文称:楚庄王大败晋师,大臣请求“收晋尸以为京观”,即积尸封土以示众;而庄王未许,并以“止戈为武”开示。其语云:“非尔所知也。夫文(指“武”字——引者),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罪无所(犯),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显而易见,他是在谈“武”的最终目标和个人理想,而并非给“武”下定义。既然晋国已降,也无大罪,其人民又都能为晋国君尽忠献身,我们又何必要积尸示众呢?这不过是表示楚王的悲悯心肠和宽大为怀罢了。实际上,“止戈为武”只是楚王的个人解释,并非“武”字的基本含义。人们更多的是把“武”理解为“力”、“勇”、“伐”、“勘定”、“刑之大者”[2],也即视为一种强力征服手段,此有众多辞书释义为证。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留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研究,则已成国际显学。常言说:“实践出真知”。任何理论,无不从实践中来。这如许兵书,实乃建立在无数血腥战争之上,而非从“和谐”中来。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李零估计:仅战国四次大战,即杀人百万;山东六国争战,约死伤四百万,完全是“世界大战”水平[3]。可见,《孙子兵法》一类兵书,实为数百万人的鲜血所浇灌。以此而论,兵法发达,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吾邦的悲哀。而《财富论》阙如,则令人不无遗憾。
中国古代,号称“宪章文武”,“各随时而用”;而且是“制胜御人,其归一揆”(《旧唐书·魏元忠传》)。可见,统治者从来没忘过“武”也即“暴力”。《鹖冠子·近迭》还有“人道先兵”之论。齐鲁“八主”之祠,其中就有“兵主”之祠。孔夫子是讲过“焉用杀”(《论语·颜渊》)一类话。但他也主张“君子怀刑”(《论语·里仁》)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刑”和“猛”,就都与“暴力”有关。宋代理学家邵雍,也称“文武之道,皆吾家事”(《文武吟》)。孝文帝《讲武诏》谓:“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魏书·孝文纪》下)可见,历代统治者并未实行过“止戈为武”。
所谓“止战”、“尚同”、“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终难制止住。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就残酷得很,一点也不“和平”。他讨伐蚩尤,活捉对手。为了警告作乱者,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有人或辩称,此乃不可靠的传说。而夏、商时代的惊天酷刑,什么“刑辟”、“炮烙”、“脯鄂侯”、“剖比干”,可是史有明载的吧?后来,又花样翻新,什么“抽肠”、“剥皮”、“凌迟”无所不用其极。中国的刑讯逼供,也是有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是一例。
已如前述,产生《孙子兵法》前后的时代战乱频仍,杀人无数,后来又如何呢?据有人统计,从秦皇统一,到 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汉朝号称“盛世”,但刘、吕权争,刘姓内斗,以及株连臣民,竟至杀人如麻[4]。历代杀戮,既有官杀民,也有民杀官,还有官杀官,民杀民,等等。其中或偶有“战以止战”之战,“杀以止杀”之杀,但大多数却是主动抢夺“权”、“利”之战之杀。就是正统史书,也承认“春秋无义战”呢。即使是止战之战,也不应坑杀降卒,而在中国却司空见惯。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启就坑杀赵降卒四十万。汉王莽攻破翟义之后,竟也夷其三族,诛其种嗣,至皆同坑 (《汉书·翟方进传》)。据统计,自秦汉至明清共有皇帝 209人,被杀和被逼自杀的有 65人,约占三分之一;南北朝有皇帝 48个,被杀和被迫自杀的竟有 28个[5]。
无论朝野,均时有刺杀、劫持等恐怖活动,甚至被当作英雄行为歌颂。自古迄今,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不绝如缕。历代农民起义,也未能避免滥杀。太平天国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向有极高评价。然而,其暴力滥杀也创下纪录。那位号称被“天父”附体、代“天父”传言的精神领袖杨秀清,就是一位暴力滥杀大王。他往往以“天父”名义审判、杀人,或斩首,或五马分尸,或点天灯。他甚至“传言”说:“凡东王打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枷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杀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 (我们)好!”似乎暴力滥杀具有了天然合理性。[6]现代农民革命和民粹式民主,也充斥暴力滥用,从斗地主到斗“走资派”、“学术权威”无不如此。那场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尽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还是动用了棍棒刀枪。在民间关系中,也每每靠拳头争老大,话不投机,即拔刀亮剑,伸拳撸胳膊。民众对剑侠、武功和奇招暗器的推崇迷醉,当今大中学生对战史、兵器的喜好,军事文学的热销,青少年对暴力游戏的热衷沉迷,无不表现出暴力崇拜。从古至今,家庭暴力不断,而且往往发生在文人之家。
既然是“以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必然形成“抢到天下是王,抢不到天下是贼”、“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观。就象帕斯卡尔所说:“人们既然不能使服从正义成为强大,于是他们就使得服从强力成为了正义”[7]。斯大林所谓“胜利者不接受审判”[8],也是这种逻辑。
此种逻辑,乃至波及诗词歌咏和词语构建。岳飞《满江红》词,竟以“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喻其“壮志”。江湖义气,救人急难,被称为“两肋插刀”、“拔刀相助”。《史记·平准书》“以武断于乡曲”语司马贞索隐称:“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凡此,都在崇信践行“持戈为武”,“以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又何“和平”之有?俗谚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是根本不让你“说”。这充分反映了理性法则面对暴力法则的弱势。
确实,“暴力”主宰话语权,“以威势主断曲直”,象一个幽灵,一直在中华大地游荡。谁有暴力,谁就垄断了真理。孔子以思想言论罪诛少正卯,儒学信徒多曲意维护。孟子将杨墨之“道”,诬为“率兽食人之道”(《孟子·滕文公》);荀子希望对“奸言”给予“势以临之”、“刑以禁之”(《荀子·正名)的惩罚;韩非则力主“禁心”、“禁言”(《韩非子·说疑》),“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言获罪,肝脑涂地啊!革命家也未能免俗。陈独秀倡扬白话文时就主张:“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9]此种心态,实乃伴随整个革命进程,故有邓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诗句。时至今日,在最为“自由”、“平等”的网络论坛和博客里,又有多少话语暴力啊!
“和平”、“和谐”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应大力提倡。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普遍存在过“和谐”吗?海峡两岸虽然政治制度有异,但文化根系却多有相似。台湾那种民粹式民主,就动辄诉诸暴力;连议会讨论也时有拳打脚踢。所以,切勿以老祖宗提倡过“和为贵”,就以为我们的文化充满“和谐”。我们而今重提“和谐”,不恰恰因为现实中有过多的不“和谐”吗?
愚以为,在万千论“武”(战)言论中,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一语最为精辟。换句话说:战争就是从政治失序处开始。人类如能平等协商利益分配,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就不会有暴力和战争。然而,人们却往往不愿或不会协商,转而迷信暴力,视其为解决利益冲突的最佳或最后手段。这也是武侠小说常常表现的复仇凶杀、冤冤相报的社会根源。春秋战国恰是个政治无序时代,必然峰烟四起,权谋联翩。刘向《战国策叙录》即谓:战国“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故孟子、孙卿儒士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荀子为战国之后设计了“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荀子·王制》)的政治秩序。但由于由少数人主宰利益分配权,王权确定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各利益群体就很难“相兼临(制约)”。生产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终只有通过武力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的频繁,暴力的泛滥,恰恰彰显出政治的无能。对内的强横,对外的文弱,又必然产生联外打内、“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枭雄。因此,决不可对中国王权文官政治及其影响估计过高。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兵法谋略,确实丰富了中外军事学宝库,并换取了无数军战、商战的胜利,焕发了文艺情采。它还催生出古代哲学,尤其是朴素辩证法。对此,两岸学者都有精辟论述[10]。是的,兵道乃“诡道”,“兵以诈立”,西方文化也承认这一原理,至谓“暴力与欺诈在战争是两种主要的美德”(霍布斯《利维坦》),“在战争行为中,欺诈却是值得称赞和光荣的”(马基雅维里《论利瓦伊的 <罗马史 >》)。但中国兵法毕竟捷足先登,而且发挥到极至。
然而,物极必有返。吾邦兵法的繁荣,也造成了“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魏源)的滥用。这种滥用,首先表现于权力斗争。政治游戏,本应公开透明,按游戏规则来玩,光明正大,君子动口不动手。但中国古代,却是政不厌诈,政不离武,充斥阴谋诡计和暴力;王权更迭,也罕见和平过渡,而多是“马上得天下”。后晋节度史安重荣一语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安重荣传》)此与李逵“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是一个思路。改朝换代,何时不充满刀光剑影?“打天下,坐天下”,成为历代统治者执政模式和执政心理。
宫廷权争,也充满阴狠诡诈、刀剑血腥,甚至君臣、父子、兄弟相残,血案迭起。仅《春秋》一书记载,在纪元前 722至 481年的 242年间,臣弑君的事件就有 100多起。例如,齐悼公在周敬王三十一年 (前 489年)继位,在齐悼公四年 (前 485年)被杀,在位仅仅四年。他的儿子壬继位,是为齐简公。颇为巧合的是,这位齐简公也和他父亲一样,只做了四年皇帝,也被谋杀。杀手就是相国田常。而楚成王则死于儿子之手。根源在于兄弟争权。成王偏爱长子商臣,宣布立其为太子,让潘崇做他的老师。但成王后来又喜欢上商臣的庶弟王子职,便想改立王子职为继承人。商臣确证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他在潘崇策划下,发动宫廷兵变,扔给成王一条束带,逼父亲自缢身亡。晋献公的儿子们,也上演过争权丑剧。晋献公原来确立申生为太子,为丽姬所妒恨。她想让自己生的小儿子奚齐继位,便诬告申生投毒谋害献公,重耳、夷吾也参与其事。结果,逼申生自杀,重耳、夷吾出逃。周襄王元年 (前 651年)九月,晋献公病死于宫中。他临终托付大臣荀息辅佐小儿子奚齐作皇帝。然而,十四岁的奚齐却在服丧的草庐中被大臣里克等人谋杀。荀息再立悼子为君,结果又被忠于重耳的里克等人杀死。荀息自杀身亡。里克得手后迎重耳回国就位,重耳不就,改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其实,不仅春秋时代如此,其后的年代里,以诈术、暴力夺权的事例史不绝书。[11]在权争中,王莽四个儿子,有三个被他杀死,唯一的侄子也无幸免。南朝宋文帝死于儿子刘劭之手,不久刘劭又被兄弟刘骏攻杀,刘骏又杀害其弟刘诞等。刘骏共有28子,竟被刘彧杀了 16个,被后废帝杀掉 12个,一无善终。同室相残,其酷如此!唐代玄武门之变,更是典型的兵不厌诈,和杀兄、害弟、逼父的残酷表演。而李世民大权在握后,却又大批“文不如武”,大讲“文治”与“和平”了。历代君王,无不以诈术治臣,使群臣生活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之中。白居易有诗慨叹:“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太行路》)
可见军事暴力对王权是柄双刃剑,既可为夺权扫清道路,也能伤及自身。为防不测,自赵宋之后,往往采取“以文制武”政策。然而,由于暴力与政治难以剥离,“以文制武”终要通过“以武制武”施行。历朝历代,最大的“文”也即“王”,无不以抓取“武”也即军权为指归。这就带来政治、政争、权力交接的诡秘、恐怖和不稳定。
确如马克思所说,在封建社会,由于不以交换为中介,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往往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力统治为基础”[12];在欧洲封建地产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13]。这话也完全适用于中国。洛克认为:“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14]。中国古代的极权奴役政治,必然使人际关系处于战争和“冷战”状态,“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集权专制,又激发出权力者最卑鄙的情欲,将人类最真纯的情愫包括天伦之情扼杀尽净。所以,洛克指明:“专制权力”,决不能“纯洁人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15]。“仁”、“义”、“礼”、“智”、“信”的倡导与呼唤,只能是软弱无力的的矫正和抗争。
其实,这种兵谋诈术的滥用,又何止于王权争斗,也渗透于仕宦缙绅之家的内部关系。父子算计,姑嫂斗法,兄弟阋于墙,比比皆是。号称封建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对此就有淋漓尽致的揭示。荣宁二府上下人等未必都读过《孙子》,但其斗智斗勇,大可为兵法作注。魏源将天地间之“兵”经由“道”溯源于“情”,但“情”却变化万端。大观园中少男少女的情感“战争”,也不乏“兵法”运用,正可谓“情不厌诈”。在平民阶层,也信奉践行“知人知面不知心”,“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多留个心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类人生准则,从而形成国人城府极深的人格特征。此也是“兵不厌诈”文化熏陶的结果。
孟德斯鸠和洛克都认为:一个正当的立宪政府拥有解决分歧的能力,无需诉诸武力;市民社会是一种和平状态,政府仲裁和法律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公民之间正当自卫权利,无须攻击别人(见《政府论》、《论法的精神》)。苏格拉底曾谓:专制潜主“总要挑起一些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柏拉图《国家》)。霍布斯也说过:专制主义的国王和主权者,“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利维坦》)。这大概就是洛克所论之“理性法则”和“暴力法则”的对立吧。
正是市民社会和宪政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种种“止战”、“去杀”、“和为贵”的倡导,不过是力图改革现实的乌托邦罢了。当然,社会也需要乌托邦,它们能成为批判、矫正现实的武器,并给人以希望。但要让理想成为现实,必须有相应制度安排。否则,乌托邦就可能成为一种自我麻醉,将主张混同于文化现实,从而回避现实矛盾和时代任务。
这里必须指出,笔者称中国文化存在暴力倾向,并非说其他文化就没有这一倾向,也并不否认必要暴力的积极作用。恩格斯说得好:“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16]马克思甚至还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7]我这里所说的暴力倾向,是指由于缺乏平等、权利和协商、妥协机制,充斥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解决方式。
破除“中国自古和平、和谐”的神话,教育国人尤其是执政者,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学会平等政治协商,不以暴力相胁迫,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是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政治改革的紧迫任务呢?
(本文为给美国华裔学者林中明《斌心雕龙》所写书评的一部分,今次发表略有增删)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第 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744.
[2]宗富邦,陈士鐃,萧海波.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82.
[3]李零.兵以诈立[M].北京:中华书局,2007:90.
[4]资中筠.君王杀人知多少 [N].文汇读书周报, 2005-03-04.
[5]常力生.御座血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337.
[6]帕斯卡尔.沉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41.
[7]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35.
[8]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 [M].北京:中华书局, 2007:145.
[9]李泽厚.孙老韩合说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何丙棣.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的翻案[A].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Z].200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4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42.
[12][13]洛克.政府论 (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8.
[15]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