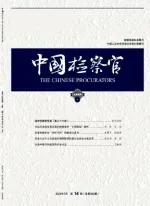公民的创作自由与国家公权力的界限
文◎郭庆珠
公民的创作自由与国家公权力的界限
文◎郭庆珠*
前文两起与公民文学创作有关的热点事件,虽然警方借口不同的罪名对作家进行拘捕,但是该事件公开后,社会普遍猜测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两地的公权力机关及官员认为以上两个作品的内容“诋毁”了当地的形象,触动的官员的利益,有借警察权力不正当打击作家之嫌。以上事件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刑法问题,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古老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如何正确理解公民的创作自由与国家公权力的界限?
一、宪法意义上的创作自由
文学艺术创作是公民自由审美的精神活动外化于文字、图画等艺术形式的过程。公民首先在内心寻求、审视美的东西,然后通过文字等把美创造、物化出来。创作的核心体现为创作者的精神活动,并把精神活动的成果呈现出来。从宪法的层面来讲,创作自由可以归入精神自由的范畴。精神自由是近代宪法所确认的三大自由之一,它与人身的自由、经济的自由一道,共同构成近代以来宪法权利体系的内核部分。[1]我国《宪法》第47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过程可以看出,创作自由是内在和外在的统一,这是和精神自由的特点相统一的。内在精神自由所保障者,主要为与他人、社会与国家(外在环境或对象)无直接关系之内心世界,通常亦不对外造成直接之影响或损害,因此,也较无予以限制之可能性与必要性。所以各国法律对此均不限制,而为绝对的保障。而外在精神自由是指个人将其内在精神活动之结果或精神生活之方式,以语言、文字、图画、肢体动作或其他任何媒介表达于外,而使他人或社会得以知悉其内心之意念的自由。外在精神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2]创作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是一种消极权利,即避免国家公权力干涉的权利,公权力不得对公民创作的自由进行肆意、不当的干涉。
保障公民的创作自由在现代法治社会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公民艺术创作潜能得以充分释放的需要。精神自由是基于人的属性的内在需要,是维护人性尊严的基本条件。[3]在现代法治社会,人在社会关系中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不能借口社会共性完全抹杀个体的需要和自我的实现,这种个体的需要和自我的实现恰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特殊且本质的意义之下形成个人的东西”是人性尊严的核心价值之一,它存立的基础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其心智,这种心智使其具有能力自非人的本质脱离,并基于自我的决定去意识自我,决定自我,形成自我。[4]文学艺术作品有自己的特点,对于美的发现和认知往往需要创作者自身艺术特质的充分彰显来实现,只有充分尊重创作者的“自我”,才会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如果国家公权力可以肆意干涉公民创作自由的话,公民的“自我”必然被抹杀,文学艺术也必然走向凋敝,对于个体“自我”的尊重本身就是人性尊严的应有之义。其次,是尊重和包容不同价值,建立价值多元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在现代社会,利益是多元的,价值的诉求也是多元的,尤其是我国在经济上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后,鼓励和支持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法治的框架下自由竞争,为各种价值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这种多元的价值诉求必然会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体现出来,《大迁徙》和《在东莞》所反映的现象实际上是时代背景和现实价值需求在文艺作品中的反应,面对着这种表达,国家公权力没有必要过度的反应,在文艺作品没有违反必要界限的情况下,国家公权力应该尊重公民的创作自由。
二、国家公权力在公民创作自由中的界限
(一)公权力因什么事由可以进行干预
一般认为,“人民的著作自由之限制,如同人民之言论自由,为保障他人权利(名誉、人格),或为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利益,是可以限制之。”[5]上述限制的事由可以简洁地概括为两个层面,即不得侵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和安全也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这一目的规定了个人权利的行使所不可逾越的外部界限。学术自由不可与这一目的相悖,也就必须对为了这一目的的手段有所尊重。[6]从广义上来讲,创作自由可是算是学术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上述学术自由的限制也是适用于创作自由的。以上两个事由中,不得侵害国家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鼓吹动乱等;不得侵害公共秩序的内容主要包括不得对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信仰构成挑战、不得对宗教信仰进行诽谤或污蔑、不得对公民私生活的自主性或独立性构成侵犯等。[7]
需要特别明确一点的是,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所进行的批评不应该成为干预公民创作自由的事由。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国家公权力本来就源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公权力行使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公民福祉,公民对于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然有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国家公权力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无条件的容忍公民的批评,而不得利用公权力进行报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对公权力的监督、批评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常态。公民在文学作品中对公权力机关进行批评是正当的,不应该成为公权力机关干预创作自由的事由。
(二)公权力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干预
其一,要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公益未必一定优于创作自由等私益。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内涵是多元的,很多事项都可以归入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范畴,但并非每一个事项都会成为限制公民创作自由的法律依据,那种认为所有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事项都可以成为限制创作自由法律依据的认识是十分有害的,必然成为公权力压制创作自由的最完美借口。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是限制创作自由的事由,但并非是每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事项都可以用来限制创作自由。宪法承认公益与私益之间存在对立关系,若凭人民无限制地行使基本权利,会影响社会的其他法益,故须予以限制,但绝不能任意以谋求公益为借口而牺牲私人利益。[8]公权力机关必须要对公益和私益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只有公益的价值大于私益价值的时候,公权力机关才可能对公民的创作自由进行干预。比如,如文学作品鼓吹动乱,公权力予以干预是必要的,因为这时公益的价值明显大于私益的价值。但是若象《在东莞》小说一样,如果其中出于作品的需要涉及到了必要的“情色”描写,虽然表面上有违公共秩序的要求,但是仍然不得以公共秩序为借口干预创作的自由,因为这时“情色”描写只是整个艺术品得以呈现的手段,而并非该艺术品的目的,公益的价值显然低于私益的价值,但若该艺术品的目的本身就是追求“情色”的宣扬,显然公益的价值高于私益的价值,国家就应该予以干预了。公权力在作出决定时,不能片面追求公益或某一方之利益,必须就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通盘考量,客观衡量取舍。
其二,以“必要”为限度。由于创作自由主要是一种消极权利,公权力对待它必须要有充分的宽容和节制。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概念都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有很大的自由决定空间。国家有关机关在判断的过程中应该以“必要”为限度,不可以过度的解读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需要,过度解读必然会对公民自由权的保障极为不利。何为“必要”?应该以可以带来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重要侵害之高度危险性为标准,如直接鼓吹动乱或对社会公认的秩序或伦理规则的违反等。也就是说,公权力对于创作自由应该尽可能的宽容,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即使在近代具有一定专制主义传统的宪政主义国家里,其宪法虽然并不彻底保障一般国民的言论自由等表达自由,然而唯独对文化活动的自由,尤其是对学术自由则网开一面,予以全力保障。 ”[9]
三、结语
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保障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创作自由,防止公权力的肆意干涉,避免公权力的打击报复,这是我国文艺繁荣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保障公民权利的应有之义。
注释:
[1]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2]许志雄等著:《现代宪法论》,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08页。
[3]杜承铭著:《论表达自由》,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3期。
[4]黄桂兴著:《浅论行政法上的人性尊严理念》,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0页。
[5]陈新民著:《宪法导论》,新学林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07页。
[6]何生根、周慧著:《论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
[7]杜承铭著:《论表达自由》,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3期。
[8]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9]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