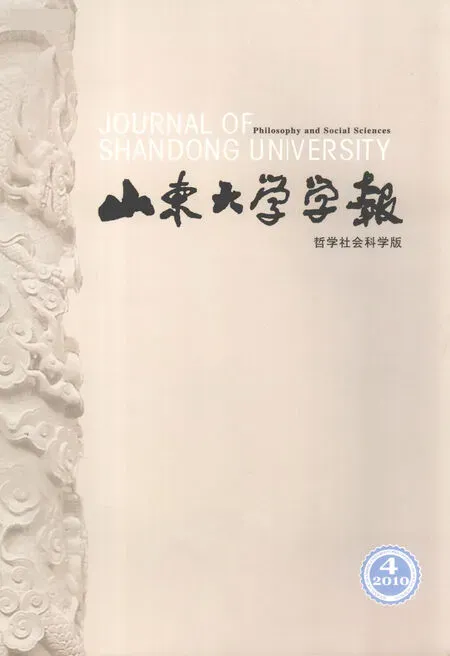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王 佺
干谒行为,古已有之,然以有唐一代最为盛行,视之空前绝后,亦不为过。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文学创作不仅要服务于取士选官的诸多环节,而且它是文人从事干谒活动的重要凭借。以诗、文干谒,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说其最常见,首先是因为二者在文献中现存作品的数量相对较多,常见以“投、赠、寄、呈、上、献、送、奉”等题字名篇;其次,唐代历史上众多著名文人都使用过这两种干谒手段。说其最直接,是因为二者与执贽 (包括行卷)、献书和投匦等通过投献文学作品、间接传达干谒意图的干谒手段不同,干谒诗与干谒文是以诗文形式、直接表达干谒意图的手段,作者的干谒目的和愿望直接通过作品传达。因此,执贽、投匦和献书等行为所涉及的作品,可称作“用以干谒的文学作品”,而干谒诗与干谒文可径称为“干谒文学作品”。虽然同属干谒文学,干谒诗与干谒文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本文择其要者,拟从如下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兴起时间不同
考察《全唐诗》和《全唐文》所存留的作品,初唐九十多年中,除执贽、献书和投匦①按:初唐时期,员半千的《陈情表》是投匦干谒皇帝,且直接表达干进求赏意图的现存惟一作品。之外,文人几乎仅以投献干谒文的方式直接表达干谒意图,而基本不写干谒诗。②按:初唐文人投献之作中,现存干谒诗惟有卢照邻的《赠益府群官》和宋之问的《明河篇》两首。而唐代之前文人以诗歌直接表达干谒意图的做法,更是少见。干谒诗是盛唐以后突然大量兴起的,此后,干谒诗与干谒文才一同成为唐代文人普遍使用的干谒手段。初唐文人几乎不写干谒诗,而独擅于干谒书启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唐代文学文体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探求。
从干谒诗的兴起阶段和作者身份考察,我们可以觉察到干谒文与干谒诗的先后兴起,与唐代取士观念和制度的变革之间应当存在一定的关系。随着唐代统治阶级文治思想的逐渐鲜明,唐代科举制度和考试内容经历了一个发展变革的过程。以进士科为例,初唐前期的进士科是只考策文的,从策问的内容看,统治阶级的初衷是侧重于选拔吏干人才,而非文学之士。初唐进士科取士以试策为主的情况在武则天掌握政权时才开始发生变化,进士试由策论一场试变为帖经、杂文和策文三场试,此后唐代进士试便有了三场试的定制。所谓杂文试,据《登科记考》永隆二年条载:
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即使试分三场,初唐九十多年间,进士试杂文也是箴、铭、论、表之类,这种情况至开元年间才发生变化,诗赋亦可居其中。至天宝末,进士杂文试专用诗赋才成为定制。需要指出,在唐代统治者渐重文治的过程中,诗歌在初唐取士过程中也并非无足轻重。初唐时期吏部选人时,已有垂索文章以供参考的做法。这里的文章也可包含诗歌作品。例如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云:“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惊魂。”②《全唐文》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 2008页。此《帝京篇》便是随此干谒书启并呈于吏部侍郎裴行俭的。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亦云:“伏见铨擢之次,每一诗赋为先。”③《全唐文》卷一八〇,第1829页。除此之外,初唐文人在投献干谒书启时也有附带文章的现象。但考察《全唐文》中的初唐作品,这些文章基本上是赋、颂、箴、铭、策、表诸类,而基本不用诗歌作品。即使是垂索诗歌,也是在吏部铨选之时,而未见进士试前垂索举子诗歌或举子主动呈献干谒诗的现象。可以说,初唐进士试是与诗歌无关的。进士试尚且如此,其他科目就更无投献诗歌的必要了。
在初唐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诗歌创作并未成为取士过程中衡量文人才华的主要文体,而这种现象直到初、盛唐之交才有较大的改观,至开、天之时才基本扭转局面。盛唐时期,进士试诗赋的定制使进士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科,也逐渐形成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社会观念。这种转变也直接影响了唐代文人对干谒手段的选择,毕竟干谒行为是为功名仕途服务的,而干谒手段的选择也必然会与取士制度中的某些考核内容和评判标准渐趋一致。初唐取士注重试策,促使文人对能否写得一手好文章倍加重视。考试以策文优劣为去取标准,必然要求文人有意识地增强文章的写作能力,这种能力是展现才华学识的重要基础。初唐文人的文章创作才能不仅在科举和铨选的过程中大有用武之地,而且可以在为争取及第和授官服务的干谒行为中,充分发挥优势。于是,在可以直接表达干谒目的的文学体裁中,初唐文人首先选择了为时代所重的文章形式作为干谒行为的载体。因此,唐代干谒文早于干谒诗兴起了。
武则天时期渐重文词的取士观念,经中宗朝的发展,加速了盛唐以诗赋取士局面的到来。诗歌创作才能逐渐为时代所重视,此时的唐代文人不仅更加以诗才相标榜,而且在干谒手段的选择上,逐渐看重诗歌这一载体,于是干谒诗开始兴起。盛唐文人干谒诗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源于此前取士观念变革力量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诗歌创作的文坛地位和社会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继干谒诗之后而大行于世的行卷风尚与此亦不无关系。盛唐之后,举子行卷的文学体裁,除中唐古文运动时期,较多出现古文这一体裁之外,诗歌作品则是举子行卷的常见内容。盛唐之后,不仅干谒诗已成为直接表达干谒意图的重要载体,而且“用以干谒的文学作品”中,诗歌也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从此,干谒诗与干谒文便一同作为唐代文人直接表达干谒意图的载体而并行不衰。
除了科举取士观念和考试内容变革的影响外,干谒文早于干谒诗兴起,还可以从唐代文学发展的内部探求原因。初唐时期,对于六朝文学的反思,主要还是着力于诗歌创作领域,而尚未波及当时普遍使用的应用文体——骈文。骈文自先秦发端,至六朝大昌,隋唐一统之后,仍为文人广泛沿用。从唐代贞观之初至开元之季的一百多年间,现存可观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等文章样式,基本都以骈体形式创作。这样一个百年未受较大争议且已相当成熟的文体,在唐代社会具有极大的公认度和惯性。对于初唐文人而言,掌握并熟练写作骈体文应当是驾轻就熟的。无怪乎初唐进士试策和干谒书启也基本是骈体形式。然而,唐代诗歌在如何融汇南北文风于一炉、创造一代文学之新貌的问题面前,于沉沦中演进了近百年,方才迎来盛唐诗歌之气象。
以文章或以诗歌来表达干谒意图、达成干进目的,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相对的难易之别。干谒是十分现实而功利的行为,其原则是行之有效。骈文在唐代社会基本上是一种应用性文体,虽然它的实用性还有待运散入骈、骈散结合的长期变革后,方能进一步提高,但相对于“纯文学”的诗歌而言,骈文的实用性仍是非常明显的。以一种应用性的文体来表达功利性的思想,势必会比以审美性为终极追求的诗歌相对容易。对于创作主体而言,能否接受并有能力驾驭干谒诗,还有待于文学素养和诗歌创作水平的普遍提高。初唐九十多年间,除去少数才子文人能以诗歌驰骋才情、抒咏怀抱之外,诗歌的工具性主要体现为侍从游宴、奉和应制的装饰性和娱乐性,且创作主体多为宫廷御用文人,直接以诗歌表达干谒意图的做法,尚未被接受。因此,初唐文人几乎不写作干谒诗,既有时代对诗歌社会功用的理解性和接受性的局限,也存在创作主体趋易避难心理的影响,当然也同当时文人整体的诗歌创作能力有关。盛唐文人敢于在干谒诗创作方面大胆尝试,也正是建立在时代接受性和自身驾驭诗歌创作的信心和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唐代干谒诗晚于干谒文兴起,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由易而难以及文人逐渐驾驭干谒手段的过程。
二、表达技巧和艺术效果不同
由于诗歌与散文在文体特征、语言风格、写作技巧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要求,干谒诗与干谒文即使有着相同的写作心态和目的,二者的表达技巧和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
诗歌是以抒情言志为主要功能、以艺术性和审美性为至高追求的“纯文学”体裁。干谒诗以“纯文学”形式为载体,一方面体现了诗歌实用功能的扩大,另一方面,干谒诗的写作也会常常面临诗歌艺术性缺失的困境。干谒本是纯功利的行为,而审美通常又是排斥功利的;干谒是一种世俗的活动,而艺术往往追求脱俗的韵味。因此,实现二者的巧妙结合是有较大难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较高的诗歌作品,往往能营造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最成功的干谒诗,通常是既能明确地表达干谒意图,又不失诗歌的意蕴趣味。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精心提炼和设计意象,烘托出干谒意愿和审美韵味巧妙结合的艺术境界。例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①《全唐诗》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 1633页。
此诗前四句以洞庭湖水天相接、雾气笼罩、浩淼无涯起兴,境界阔大,胸襟不凡;“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二句承接,因景设喻,言明心迹,抒发作者有耻于太平盛世却闲居独处的慨叹,借欲渡洞庭而无舟楫为喻,表达积极用世的心情,希望得到张九龄的汲引。“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二句承上引申,“垂钓者”喻指当政者,“羡鱼情”,巧妙化用《淮南子·说林》中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翻出新意,实属难得。此干谒诗妙在托兴观湖、露而不透,既将干进意图委婉表达,又能把个人对仕途的热衷与盛世功业的至公理想融会于一体;既能表现诗人托物言志的创作才华,又不失温文尔雅的才子风度。尤为难得的是将眼前景、心中情、书中典巧妙融合,这一番天衣无缝的裁剪功夫,断非凡笔可为!再如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②《全唐诗》卷五一五,第5892页。
朱庆馀此前曾行卷于张籍,已得其赏识。然临近科考,心中忐忑,遂呈此诗,以新娘自比,以夫比张,以舅姑比主司,就及第前景探听虚实。此诗巧用新嫁娘入洞房次日拜见公婆这一社会风俗,将自己临考前的复杂心态,比作新娘自信而又含羞、期待而又迟疑的心理,可谓通俗贴切,别出心裁。此干谒诗极具言外有言、意外藏意的艺术效果,令人赏爱不已。同孟浩然诗相类,朱庆馀诗的表达同样以比体为之,得含蓄之美。上乘的干谒诗,贵在措辞得体且不失身份;既要干求于人,又非低声下气;既要达成干谒目的,又不能丧失艺术品味。正如高空走钢丝,不是高人,难成佳作。当然,若太过含蓄隐讳,而被干谒者不解其意,则充其量是首好诗,而不能算是好的干谒诗。因此,在艺术加工和表达意图之间,掌握分寸也十分必要。
除极少数上乘之作外,唐人干谒诗中数量较多的是托物言志、设喻形象,而艺术水平和审美韵味稍显不足的作品。这类干谒诗借比兴咏物的手法,委婉表白干进目的,当然也是难得的成功之作。李白是盛唐写作干谒诗最多的文人,其咏物抒怀、托物言志的作品相当多,最著名的莫过于《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③《全唐诗》卷一六八,第1740页。这是李白在天宝四年游北海时投献北海太守李邕的干谒诗。首四句化用《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之典,自比大鹏,豪气激荡。紧接二句直言不得凡俗之人理解,饱藏着奇骏不遇伯乐的感慨。宣父即孔子,唐贞观年间下诏尊称孔子为宣父。《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末二句即借此义劝告李邕不可轻视晚生。此诗言辞颇能代表盛唐文人普遍具有的自命不凡与狂傲不羁,乍看有失干谒诗含蓄得体的分寸感,但在“时人”和“丈夫”、“宣父”的对比之间,巧妙地恭维了李邕超越“时人”之雅量,较好地弥补了表面的缺陷,也成全了诗人纵横洒脱、豪迈自负的个性,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的地方。此诗虽然谈不上什么意境韵味,但诗人敢于险中求胜,又以巧妙的设喻扭转狂言之弊,当然有着高超的干谒技巧。如此干谒诗作,在唐代也是不多见的。
唐代干谒诗中,面目雷同、缺乏新意、艺术平庸、构思模式化的作品占绝大多数。这些作品的造句谋篇、遣词立意等表达技巧方面,多限于一种相似的格局,即先以恭维之词开端,接着慨叹自己沉沦窘困或才高命薄的不幸境遇,最后婉言托出干进意图。当然也并非全然套用这三个层次,有的顺序不同,有的只取其任意二者搭配。这种写作模式与大多数干谒书启的做法基本相同。孟郊的干谒诗在中晚唐文人中算是较多的,粗略统计,可确认为干谒诗的至少 25首。①孟郊干谒诗约 25首:《投所知》、《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西斋养病夜怀多感因呈上从叔子云》、《新卜清罗幽居奉献陆大夫》、《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鸦路溪行呈陆中丞》、《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上河阳李大夫》、《投赠张端公》、《上张徐州》、《上包祭酒》、《献汉南樊尚书》、《赠转运陆中丞》、《赠万年陆郎中》、《古意赠梁肃补阙》、《赠黔府王中丞楚》、《上达奚舍人》、《献襄阳于大夫》、《寄院中诸公》、《寄卢虔使君》、《寄陕府邓给事》、《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送魏端公入朝》、《寿安西渡奉别郑相公》、《江邑春霖奉赠陈侍御》等。唐人模式化干谒诗甚多,在此姑且以孟诗为例,简单介绍此类模式化的干谒诗。孟诗中有一类是上述三个层次俱全的作品,如《投所知》云:
苦心之知苦节,不容一毛发。炼金索坚贞,洗玉求明洁。自惭所业微,功用如鸠拙。……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辙。尽美固可扬,片善亦不遏。朝向公卿说,暮向公卿说。谁为黄钟管,化为君子舌。……而况大恩恩,此身报得足。且将食檗劳,酬之作金刀。②《全唐诗》卷三七四,第4198页。
首四句即言自己苦守节操,以炼金、洗玉自比坚贞、明洁;接下来便称颂知己是存古人心、行古人道;最后表白若蒙恩则必报。第二类是由两个层次构成,或称颂恭维,或自诉潦倒困厄,结尾申白干谒目的。例如《上包祭酒》诗云:
岳岳冠盖彦,英英文字雄。琼音独听时,尘韵固不同。春云生纸上,秋涛起胸中。时吟五君咏,再举七子风。何幸松桂侣,见知勤苦功。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③《全唐诗》卷三七七,第4229页。
此诗首先“冠盖彦”和“文字雄”高度赞扬包佶的才学,称其诗如“春云生纸上,秋涛起胸中”,有建安七子之遗风;后四句表达自己渴望借包佶之奥援而展翅高飞。《寄卢虔使君》则云:
霜露再相换,游人犹未归。岁新月改色,客久线断衣。有鹤冰在翅,竟久力难飞。千家旧素沼,昨日生绿辉。春色若不借,为君步芳菲。④《全唐诗》卷三七八,第4237页。
此诗只言自己的科场再败、久客他乡的惆怅与苦闷;尾二句委婉流露依托之意。
唐代文人多数干谒诗大抵不出孟郊诗作的几种模式,即使是一流大诗人也不免落此窠臼。例如大诗人杜甫,其干谒诗数量与李白几乎伯仲之间,而随手举其几篇典型的干谒诗,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赠比部肖郎中十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丈济》、《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敬赠郑谏议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皆属模式化、格局化的作品,表达方式雷同;先颂对方的品德、政绩、才华,续言自己有志难骋的境况,有时为求同情援引,所言甚是凄惨,有时牢骚满腹、甚至饥不择食。唐代干谒诗多呈现出如此雷同面貌,应当与此类诗的写作难度有直接关系。所谓“难”,一指笔难,二指情难。写作中,干谒诗的功利思想和非功利的审美形式之间很难取得完美统一。多数模式化的干谒诗虽也不失朦胧委婉的特点,但干谒总归是件难为情的事情,干谒诗通常都会满足含蓄二字,择其一二首观之则可,然千篇一律,了无新意,则不免令人生厌。干谒行为说来就是求人援引提携,挖空心思也翻不出多少新花样,何况干谒诗本身并非为了满足艺术创作的理想和追求,若只为干谒目的服务,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当然不必用力甚勤了。对于文人来说,干谒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而干谒诗的写作也就难以品尝到情感的慰藉和审美的愉悦,既然如此,谁又会为艺术而呕心沥血呢?即使是在诗歌繁荣、名家辈出的唐代,也出现不了因致力于写作干谒诗而流芳百世的诗人。因此,干谒诗的写作目的和作者的创作心境,最终决定了其艺术上的佳作是屈指可数的。
干谒书启是以应用文为载体的干谒手段。这种手段不仅可以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干谒意图,而写作技巧也相对容易掌握。就写作特点而言,多数干谒书启都与干谒诗中格局化、模式化的一类作品相似,即赞美恭维——自伤沦落或自视甚高——申明意图。虽然此类格局的干谒文与大多数干谒诗一样,也很难翻出新意,但作为应用性文体,实用性决定了干谒书启常用此格局要比干谒诗更容易接受。就艺术效果而言,干谒文与干谒诗的要求不同:由于体裁有别,干谒诗势必要顾及到意境、意象和声律等固有特质的要求,既要有效表达干谒意图,又须含蓄朦胧、有一定的诗意。另外,诗歌句式、结构和篇幅的形式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干谒思想表达的充分性和灵活度;干谒文几乎全是以书启一类的应用文体写成,这种文体首先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功能性,它与干谒行为和目的的现实性与功利性之间并不矛盾。干谒文没有太多艺术形式上的束缚,因此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方面会更灵活、更策略。干谒书启并不以艺术性和审美性为最高要求,而是为方方面面的实际需要服务的。在清楚论述事实和有效表情达意的前提下,优秀的干谒文,往往观其“文气”和“文势”,而并不在于意境。
唐代著名文人之中,韩愈算得上是汲汲于功名仕途的典型代表,其干谒文数量较多,至少 14篇。①韩愈干谒文篇名:《上贾滑州书》、《上考功崔虞部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与凤翔邢尚书书》、《上宰相书》、《后十九日复上书》、《后二十九日复上书》、《与于襄阳书》、《上李尚书书》、《与陈给事书》、《上兵部李侍郎书》、《上襄阳于相公书》、《上郑尚书相公启》和《上留守郑相公启》等。在此,姑且以韩文为例,大致介绍模式化干谒文的创作特点。第一类属大肆吹嘘型。例如《上李尚书书》,这是贞元十九年,韩愈四门博士任已考满罢秩,始以前资官身份守选期间,干谒德宗幸臣李实的书启。李实其人,史书记载中并无可歌可颂的事迹,其人品德行委实不敢恭维,然韩愈为求李实的鼎力举荐,早日得到一官半职,却说了不少违心吹捧之言,如赞美李实“赤心事上,忧国如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②《全唐文》卷五五一,第5579页。实在溢美太过、无以复加。文末提及的 15篇文,即为谒见之资。事实说明此次干谒效果甚佳,韩愈守选未满,便于同年迁监察御史。第二类属自伤困厄悲愁、怀才不遇与赞美吹捧结合型。例如《上兵部李侍郎书》,这是永贞元年,韩愈在江陵府法曹参军任上,干谒兵部侍郎李巽的书启。开篇即自诉薄命不幸、一事无成、困厄穷愁和怀才不遇,以图博取李巽的同情,继而对李巽大加赞美:“伏以阁下内仁而外义,行高而德巨,尚贤而与能,哀穷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③《全唐文》卷五五一,第5580页。文末提到的旧文一卷和南行诗一卷,即为干谒之资。韩愈这两篇干谒书启,可以代表唐代大多数干谒文的写作模式。
干谒文与干谒诗相比,其篇幅的伸缩性和表达方式的灵活性,决定了干谒策略的选择余地较大。干谒文不仅可以反复申说,甚至可以讲道理、发议论的方式详尽其意,这是干谒诗不易做到的。例如韩愈的《与凤翔邢尚书书》,此文长达 700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干谒文在赞美吹捧与提出请求的同时,还可以较大篇幅讲道理和发议论,以求层层深入、面面俱到的特点,这是干谒文的长处。通常情况下,干谒文所申明的道理不外乎证明干谒者行为的至公性和合理性。如文中所言:“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④《全唐文》卷五五三,第5598页。同样的道理在韩愈其他的干谒书启中也常使用,如《上宰相书》和《与于襄阳书》等等,文章所陈之理皆为说明干谒行为的合理性,无非是上下相求、彼此相须一类的理论,继而推定为朝野的普遍共识。这种干谒理论的运用,既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也与唐代文人习尚的战国纵横干谒技巧有关。
干谒文中上乘之作的评价标准,与干谒诗也有异同之处。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评价,二者均不能以干谒结果的成败为标准,而应当视其文学创作水平、艺术品味、修辞技巧和人文价值。不同之处在于:干谒诗应观其意境和艺术韵味,而干谒文则侧重于文势、文气和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干谒诗贵在以诗意韵味吸引人,而干谒书启贵在以文气情理征服人;干谒诗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艺术形式本身,而干谒文更加注重文本背后折射出的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唐代干谒文中最为后世称道和重视的,往往是那些个性鲜明、神采飞扬,能够展现时代昂扬精神和凸现文人狂傲气质的作品。这些优秀的干谒文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唐代独特的社会文明和人文精神的重要渠道。从《全唐文》存录的作品考察,这些最能代表大唐盛世文人精神面貌的作品,多出自初、盛唐文人之手。例如王勃的《上刘右相书》和《上吏部裴侍郎启》、员半千的《陈情表》、王泠然的《与御史高昌宇书》和《论荐书》、任华的《告辞京尹贾大夫书》和《上严大夫笺》、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与韩荆州书》等等,这些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干谒文,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承载着唐人积极用世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以及家国天下的功业理想和豁达狂放的精神魅力。此类风貌的干谒文的出现,既与唐代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在某个阶段的发展形态有关,也与唐代文人所普遍向往和追求的战国纵横遗风有关。
三、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不同
投献干谒诗与干谒文虽然都是表达干谒目的最直接的方式,在干谒效果上也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就其方式所具备的功能而言,干谒文的功能要大于干谒诗。首先,干谒诗以诗歌表现方式为载体,其篇幅、语言和艺术形式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因此在表达干谒意图时,难以面面俱到,这就是以诗歌表达容量较大的题材时,往往还要借助序言或运用组诗形式的原因。在表现情感和营造意境时,优秀的作品往往会以一代万、以少总多,语言凝练而滋味无穷。然而,当以诗歌形式传达某种现实需要和功利目的时,就不那么容易得心应手了。一首干谒诗所能涵盖的容量毕竟是不易拓展的。而干谒文不仅篇幅和语句的伸缩性较强,对干谒行为相关的人物、事件、缘由和观点以及各种因素的设置安排和表达方式,则可以相对容易地操作。总之,干谒文的写作比较容易做到周全,也相对容易满足干谒者需要。
其次,干谒诗通常只能完成一个较为单一的目的,而干谒文则可以满足多种需要。干谒文既可以用文本内容本身充分表达干谒意图,也可以携带附件来增强干谒的效果。例如执贽干谒,唐代许多干谒文都会附带呈献一些纯文学创作,以为谒见之资。有的是举子行卷的性质,有的则是文人科举及第以后干谒求官的性质。所携之贽可以是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些用以干谒的文学作品,只有借助干谒书启才能发挥干谒的作用,可以说投献干谒书启是执贽干谒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杜牧大和八年作的《上知己文章启》①《全唐文》卷七五二,第7801页。,就是他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府中任掌书记时,干谒吏部侍郎沈传师的书启,文中所言之 7篇作品《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望故园赋》,就是此次投献干谒书启求知己时附带的谒见之资。在这篇干谒书启中,杜牧简要介绍了 7篇作品的创作主旨。再如温卷,它是举子行卷行为的补充和延伸。温卷行为必须借助干谒书启才能实现。如果温卷行为是重复以前投过的卷子,那么书启的作用就是说明温卷的目的和介绍相关的背景;如果不重复投卷,则仅投温卷启事即可,书启中可以交代此前行卷的情况。例如贞元八年,李观的温卷启事《帖经日上侍郎书》。考试期间时间仓促,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誊抄行卷和制作卷轴,此时投干谒启事当然就是惟一可行的温卷方式了。文中“观去冬十首之文,不谋于侍郎矣,岂一赋一诗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献也”②《全唐文》卷五三三,第5415页。,指的是先前行卷的作品,在这篇启事中他又一次介绍了行卷的内容、自我评价,以及可望知遇的心情。这些干谒功能就是干谒诗不具备的。
除干谒功能之外,二者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干谒诗的兴起,体现了唐代文人驾驭诗歌艺术形式的能力和信心的普遍提高;干谒诗的出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题材、增强了诗歌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实用功能;干谒诗创作数量的增加和创作群体的扩大,说明唐代文人对诗歌社会地位的重视,同时也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干谒诗创作对唐诗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并未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唐代诗歌在创作形式和艺术表现力方面,受益于干谒诗创作的因素是相当有限的。在这一点上,干谒诗远不如那些随同干谒文一并呈奉的“用以干谒”的诗歌作品,例如唐代举子行卷中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由于不受干谒思想和功利目的的直接束缚,因而获得了自由表现的空间,较之干谒诗也更加灵活而富有创造力。唐人传世的许多优秀诗篇曾经就是行卷之作,而直接表达干谒意图的干谒诗,名篇佳作就很少了。干谒文对唐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丰富了唐文的表现题材、增强实用功能之外,它与干谒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对唐代散文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唐代干谒文在文体形式上,经历了全然骈体到运散入骈、骈散结合,再到全然散体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不能离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但也不可全然归功于“古文运动”。唐代散文的革新因素,最早发生在各类应用文体当中,干谒文正是其中比重较大的一类。初、盛唐时期,骈体虽然仍是唐文创作的主要形式,但在“四杰”、陈子昂、张说、王泠然、任华和李白等人的干谒文中,散体倾向已渐趋明朗。这种变化一方面取决于唐人的精神气质,尤其是那种追慕战国策士自信豪迈和自由洒脱的纵横精神;另一方面,行文的散化最终还是取决于它的实用性和功利目的。应用文体以切实适用为行文特点,写作时也须兼顾文体的使用效率。干谒文作为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功利性创作,文章的起承转合与遣辞造句都必须为干谒的最终目的服务。初、盛唐干谒书启中的散化倾向是与古文运动无关的,而是基于作家独立自由的时代个性和狂放不羁、自信洒脱的人文精神,而推动文风演变的直接动力,恰恰是传情达意和博取功名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