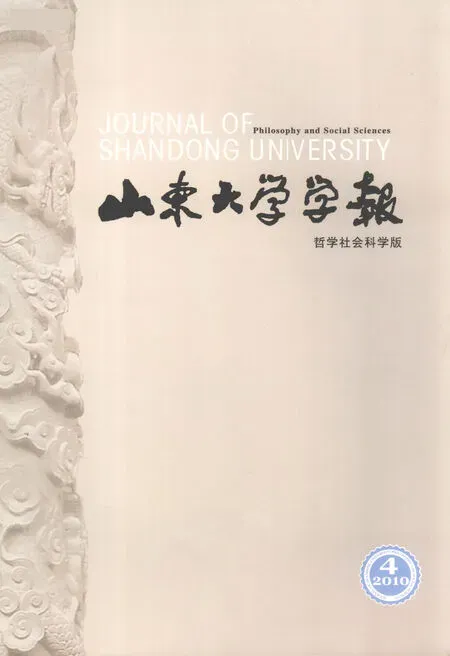章太炎的“文各体要”论
何荣誉
当今对章太炎文学思想的论述,综观之多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复古主义文学观;二是语言学的文学观;三是泛文学观。其中,数复古主义文学观影响最大。然在论者的评述中,或关注其文宗魏晋的复古主义表象,或以为章氏是以复古为革新。①关于章氏语言学的文学观,可参见黄洁《重估章炳麟的语言学文学观》(《求索》2002年第 6期)、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相关章节。关于章氏泛文学观,可参阅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相关内容、沈家庄《章太炎文学论略》(《漳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 1期)。至于章氏复古主义文学观,可参阅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作品集》〈八〉,台湾远流出版社,1986年,第 108-109页)、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 178-184页)、陈雪虎《从当代语境回望章太炎的“文学复古”》(《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 1期)、吴中杰《章太炎复古主义辨析》(《晋阳学刊》1996年第 2期)。但就章氏以何种策略复古,并未有更深入的论析。
据实论之,章太炎是通过“文各体要”论来实现复古魏晋的,并希望以此消除当时梁启超报章文、林译小说等文体之不良影响,平息骈散文之争,进而抵制以西方文论来评价中国文学的做法,坚决维护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一、“文各体要”论的演进
在不同时期,章太炎“文各体要”论的表述有所不同。1906年以前,一般表述为“类例”、“体要”等,这是章太炎对“文各体要”的初步认识。1906年,他在《文学论略》一文中正式提出“文各体要”论,并集中表述为文学的雅俗观。晚年,章太炎的见解又有校正,集中表述为“发情止义”。
1.“类例”、“体要”
早在 1897年,章太炎撰《文例杂论》就表现出了对“文格”的关注,不过当时的表述为“类例”:
余每读顾先生《救文格论》,叹其绳约骫骳,偃矩削墨,后之治文笔者,得是为同律,其远乎鄙倍矣。自桐城方、姚诸子,浸为文辞,传之其人,其所约束,又各以意进退。古之作述,非闳览博观,无以得其条例。惟杜预之《善文》、挚虞之《文章流别》,今各散亡,耗矣!矩则同异,或时时见于群籍。凌杂取之,故不能成类例,亦庶几捃摭秘逸之道也。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49-50页。他从顾炎武《救文格论》获得如下启示:一是认同《救文格论》的论文标准,并提倡以“类例”作为治文笔者的准绳。二是简略地界说了“类例”的涵义:“类例”就是作文的条例,而此条例要通过博览群书,再加以总结才能体认到,并非桐城诸子所谓的作文套式。三是以“类例”来针砭时俗,使治文者“远乎鄙倍”。①1901年 3月 3日,在《与吴君遂》(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信中,章太炎说作有《广救文格论》:“间作《广救文格论》一首,此件宁人原著,意趣稍别,亦以针砭时俗,盖常恐高材者堕轻清魔也。书约两千余言,较去岁赠宋君诗跋,稍益繁重。”《广救文格论》现已未能见,信中所指“去岁赠宋君诗跋”也未可见,然就信中的提示看,盖有针砭时俗之意。这说明章太炎已试图将“文格”论运用于救治时弊的实践之中。
之后,他在《訄书》重订本《正名杂义》中说到:“文辞者,亦因制其律令,其巧拙则无问”。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230页。1902年,他在《文学说例》谈论文辞与口说的差异时指出:“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在文辞则务合体要,在口说则务动听闻。”③刘师培:《文学说例》,见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这里所论“制其律令”、“务合体要”,已表述了对“文格”的具体认知。
此间,章太炎虽论涉“文格”的某些层面,如“类例”、“律令”、“体要”等,但是对于什么是“文格”则没有说明。1906年,他在《文学论略》一文中作了正面解说。
2.雅俗观
在《文学论略》中,章太炎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④章太炎:《文学论略》,《章太炎的白话文(附录)》,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何谓“法式”?赵敏俐先生在《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的序言中说:“这里的法式,显然不仅仅是指‘词法’、‘句法’、‘章法’以及‘修辞炼字’之‘技法’,还应该包括‘明道’、‘宗经’、‘征圣’等作文之‘义法’”。⑤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 12页。赵先生认识到了“法式”有作文之“义法”一层,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对“法式”内涵的界定似嫌过于细密。按章氏本义,“法式”应指下文所提出的雅俗观之“雅”,也就是“文能合格”,即今日所谓文体规范。这也就是说,在章太炎的文学观念里,实蕴涵着“文各体要”论。对此,章太炎论曰:
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悴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⑥章太炎:《文学论略》,《章太炎的白话文(附录)》,第 138页。
这里所提出的“雅”有两个标准,一是“轨则”;二是“便俗致用”。任访秋先生解释说:“从这一段里,可以看出‘便俗致用’之要,在老老实实地叙事说理,让看的人容易理解,这就是‘雅’,至于那些引用古时官名以代时制,用一些陈词滥调与浮夸的语句来表现事理,既不切实际,反令读者莫名其妙,这就是不雅,也就是庸俗。⑦任访秋:《章太炎文学简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文学组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文卷(1949-197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 591页。准此,任先生的解说似有所差。其实,章氏所谓“雅”就是要求文合体要,即合乎其自身的文体规范。不同的文体,“雅”的标准也不一样。“文能合格”就是“雅”,文合乎“轨则”就是雅。至于“便俗致用”,是否可为“雅”的一个重要标准,则尚需辨析。“便俗致用”只是公牍等的文体规范,或者说只是公牍等文体要遵循的“轨则”,并非所有文体求“雅”的要义。公牍是“便俗致用”的文体,对于它来说,“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就已经做到了“雅”,即任先生所谓“老老实实说理,让人容易理解”。但是对其他文体而言,“便俗致用”就不是“雅”的必然要求。所以章氏又说:“诗、赋、箴、铭、哀诔、词、曲之属,固以宣情达意为归,抑扬婉转,是其职也。”⑧章太炎:《文学论略》,《章太炎的白话文(附录)》,第 139页。这是说诗、赋等文体做到“宣情达意,抑扬婉转”就是“雅”,而不必勉强“便俗致用”。
另要注意的是,章太炎论“雅俗”非止一义。在《说林》(下)和《与人论文书》中,他都论涉“雅俗”的问题,但意思似与上述有别,应有所辨析区别。①《说林》所谓“通俗之文”、“通俗不学者”之“俗”,与《与人论文书》所论“文能循俗”、“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之“俗”含义大抵相同,是与学者高文典册相对的通俗致用之文。“王闿运能尽雅”之“雅”是与“俗”相对的“高文典册”。另还有一说是论修辞的:“徒论辞气,大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与人论文书》)这里,“雅”就是指文辞雅训,多见于高文典册之中;而“俗”则是通俗致用之文的语言,其特点是袭用常语,不讲求字词训释、文理逻辑。但在章太炎看来,“俗”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不矫揉造作、自然朴质。不过“雅”、“俗”是可以转换的,在“俗”的基础上略施文采,“俗”就可以变成“雅”了。
3.“发情止义”
1922年,在《国学概论》“国学之进步”一章中②1922年 4月至 6月间,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作国学讲演。《申报》刊登了此次讲演的讲义,但不成系统。后来,曹聚仁将听讲笔记系统整理并在得到章太炎准许后,于当年 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即为《国学概论》。章氏“发情止义”说就是在本次国学演讲中提出的。,章太炎进而提出“发情止义”说:
文学如何能求进步?我以为“发情止义”。何为发情止义?如下述:“发情止义”一语,出于《诗序》。彼所谓“情”是喜怒哀乐的“情”。所谓“义”是礼义的“义”。我引用这语是把彼的意义再推广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③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69-70页。“情”就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发情”就是要说出自己不得不说的话,抒发自己不得不抒发的感情,提倡有为而作。“义”是“作文的法度”,“止义”就是以作文法度为基本准则,即前所论之合乎文格,得其体要。这样,雅俗观之“雅”就被转述为“义”,但其所指内涵并没有变化。不过,他另行引入了“情”的要素,因而又多了一个论文指标。
基于这个理论,他以“发情止义”为标准,来评价近世文学:
桐城派的文章,并非没有法度,但我们细读一过,总觉得无味,这便因他们的文,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王渔洋的诗,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兴趣,也因他偶到一处,即作一诗,仿佛日记一般,并非有所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以明代遗民,心有不平,发于文章,非无感情,但又绝无法度。明末大儒黄梨洲、王船山,学问虽博,虽有兴亡感慨;但黄文既不类白话,又不类语录,又不类讲章,只可说是像批语,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说是不上轨道的。④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 69-70页。
桐城派的文章、王渔洋的诗只能做到“止义”,而忽视了“情”;侯方域、魏叔子的文章,黄梨洲、王船山的著述虽有情,但又没有做到“止义”,所以都不是至文。因之,他顺势推导曰,文学要求进步,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
至于“止义”与“发情”的关系,章太炎更有深论。“止义”是作文的基本要求,“发情”是作文的更高标准,只有先做到“止义”然后“发情”,才能作出好文章,才可成传世至文。所以他说:“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⑤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 69-70页。文学若要传世,就必须以“止义”为基础,然后再“发情”。“那初作文,仅有法度,并无情,用以练习则可,用以传世则不可,仿佛习字用九宫格临帖,是不可以留后的。”⑥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 69-70页。
由此可知,章太炎“发情止义”说是雅俗观的延续与深化,核心内容还是“文各体要”。至于“发情”一义的标举,则是更高的文学追求。
二、“文各体要”论之实质
古代“文体”观念发源于《诗》、《书》。把诗歌和散文分别汇编成书,即表现出对不同文体的认识。根据官府文书用途和体制不同,《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分类,《周礼·大祝》有辞、命、诰、会、祷、谏等“六辞”,《礼记·祭统》更是对“铭”做了详细说明。这些都是上古中国文体观念的萌芽。⑦参见吴承学:《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 4期。延至魏晋时期,有关文体的论著涌现,且论述也较早前精密。曹丕《典论》,论涉及奏议等八种文体的特征;陆机《文赋》,论列了诗、赋等十种文体的特征;嗣后,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等分体理论。至于萧统《文选》,更是依类选文,达 34种之多。降至明朝,文体学再次兴盛,其核心内容就是“体制为先”,所谓先体制后工拙、辨体不辨意、先守正后出奇、先体制后性情。①参见汪弘:《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多种论调,众说纷呈,以致“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②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章太炎的“文各体要”论显然继承了前人重视文体特征、严辨文体的理念,同时又有自己独特的论文标准。他依准陆机《文赋》的文体论,说:“士衡《文赋》,区分十类,虽有不足,然语语确切,可作准绳,……十类以外,传记序记,士衡所未齿列。”③章炳麟:《国学讲演录》,南京: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这就是说,章氏所论之“体要”,多与《文赋》所论诸体特征相当。④在《国学讲演录》中,章氏补充《文赋》未列文体内容如下:“至其所未及者,祭文准诔,传状准史。序记之属,古人所轻。官修书库,序录提要,盖非一人所能为。若私家著述,于古只有自序;他人作之,亦当提挈纲首,不可徒为肤泛。记惟游记可作,《水经注》、马第伯《封禅仪记》,皆足取法。宋人游记叙山水者,多就琐碎之处著笔,而不言大势,实无足取。余谓《文赋》十类之外,补此数条已足。”由此可见,章氏论文崇尚魏晋,服膺魏晋文体论,并以此评价后世之文,抬高魏晋文学地位,来为复古魏晋张目。如在《国故论衡》中编《论式》、《辨诗》中,章氏集中阐述论理文、诗歌的历时流变,大抵采用《文赋》论文之标准,明确标举其文宗魏晋的观点。
逻辑严密、言辞精微简练,这是章氏评价论理文的核心,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标准,章太炎考察历代论理文的发展历程,认为晚周论理文成就最高。这是因为晚周文“辞精微简练,本之名家,与纵横异轨。……内发膏肓,外见文采,其语不可增损。”⑤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 81页。章氏认为,后世只有魏晋论理文能与之媲美,因为“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⑥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第 82页。因此,魏晋论理文被章氏奉为后世学习之楷模:“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⑦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第 84页。也正因如此,章太炎不同意曾国藩所谓“古文不善说理”之说。⑧章太炎不认同曾国藩“古文短于说理”的观点,认为晚周、魏晋论理文实长于说理:“近世曾涤笙言古文之法,无施不可,独短于说理。夫著作之文,原可以说理。古人之书,《庄子》奇诡,《孟》、《荀》平易,皆能说理。韩非《解老》、《喻老》,说理亦未尝不明。降格以求,犹有《崇有》、《神灭》之作,何尝短于说理哉?”又认为曾氏此论缘于门户之见,眼中只有唐宋古文,而将适于说理之魏晋论理文摈除于外:“彼所谓古文者,上攀秦汉,下法唐宋,中间不取魏晋六朝。秦汉高文,本非说理之作。……盖理有事理、名理之别。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笔,名理之文,惟晚周与六朝人能为之。……上之周秦诸子,下之魏晋六朝,舍此文体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论事之辨,固已难矣。……非古文之法独短于说理,乃唐宋八家下逮归、方之作,独短于说理耳。”(参见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 203页。)
章氏依准评述论理文之标准,明确指出其他时期论理文的弊病,如说两汉“雅而不核,近于诵数”;唐、宋“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⑨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第 82页。至于晚清,章氏以为,典礼之文成绩很大,名理之文实不擅长。其中规法魏晋成就最大的汪中、李兆洛二人,也仅限作常文,议礼论政、谈论玄理都远不能与魏晋文相比。其差距也就在于辞不达意,论辩攻守无序。
因此,矫正论理文之弊,惟有效法魏晋论理文一途。他说:“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不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什无计薄之用,文辩非穷理之气,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⑩
章太炎论诗本于性情,主张向“缘情”的传统回归。“诗本性请”是章氏考量诗歌发展历程的核心指标,因为发抒性情不仅是诗歌形制演化的关键因素,还是诗歌繁盛的根本,所谓“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憙杂书,则诗衰。”此外,章氏还重视“风”教,强调诗有寄托。
由此推之,诗歌形制的演化与诗人的才性、学问无关,而系乎性情的抒发。章氏在论述四言诗发展历程时说:
吟咏性情,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汉独有韦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晋,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辞安雅,而惰驰无节者众,若束皙之《补亡诗》,视韦孟犹
登天。嵇、应、潘、陆,亦以楛窳。……非其材劣,固四言之势尽矣。①章太炎:《诗辩》,《国故论衡》,第 88-89页。
这里明确断言,汉以后,四言少有优秀之作,实缘于四言诗势已尽。四言诗盛行先秦,汉代社会风气已变。同是吟咏性情,四言不再能满足汉时需要,故势已尽。即缘于此,五、七言诗应运而生。
章氏之“性情”论不同于公安派、袁枚等所论之“性情”,而强调“风”教。他认为,“古之为诗,以陈国俗,……诗不系国风,无以增怀古之念。”②章太炎:《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四),第 152页。嗣后进一步论说到:“古者陈诗以观民风,《诗》亡而后《春秋》作,次《春秋》而有《史记》。《史记》者,通史也。于屈、贾、相如诸传,独存辞赋。……辞赋本于性情,其芳臭气泽之所被,足以观世质文,见人心风俗得失。”③章太炎:《菿汉微言》,见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47页。不仅如此,他认为诗教不兴导致士风浮靡:“晚世之士,日趋于放僻邪侈而不反者,非徒风俗浇薄使然,实由诗教衰息。”④存萃学社编集:《章炳麟传记汇编》,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第 295页。因此,提倡“风”教,也有矫正士风的意旨。
基于以上认识,章氏考量历代诗歌发展,认为魏晋诗歌最盛:
风与雅、颂、赋所以异者,三义皆因缘经术,旁涉典籍。……独风有异,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⑤章太炎:《诗辩》,《国故论衡》,第 88-89页。
所谓“上念国政,下悲小己”,就是肯定魏晋诗歌既有经世之抱负,又有身世之感叹,因而慷慨激昂。它们“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⑥章炳麟:《国学讲演录》,第61页。
同样基于“诗本性情”,章氏评骘唐代诗歌的成就:古体诗则有本于建安的陈子昂、张九龄、李白,“哀思主文者,独杜甫为可与。韩愈、孟郊,则《急就章》之变也。元稹、白居易,则日者瞽师之诵也”。⑦章太炎:《诗辩》,《国故论衡》,第 90页。其余皆不足讽诵。近体诗更不足论:“篇句填委,凌杂史传,不本情性”。⑧章太炎:《诗辩》,《国故论衡》,第 90页。
“诗本性情”的反面是以学问为诗,而这是章氏所不齿的。因此,他反对宋派诗以经史入诗、以议论入诗。在章氏看来,宋派诗的特点也就成为它的缺点:“(宋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及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⑨章太炎:《诗辩》,《国故论衡》,第 90页。正是宋派诗不本性情,偏离了诗歌文体规范,因而遭到章氏的讥嘲。
最后,章氏断言:“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⑩章太炎:《诗辩》,《国故论衡》,第 90页。
综上观之,章太炎“文各体要”论之实质,就是通过倡导《文赋》论文体之标准,以达到复古魏晋之目的。
三、“文各体要”论的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迫使国人反思洋务运动,另觅他途,以求富国强民。此后,国人把学习西方的范围从技物延伸到思想、制度层面。文学作为宣传工具,也受到了特别关注。为配合政治改革,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文学革命,并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小说界革命”等口号。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倡导“诗界革命”,要求诗应有新意境、新语句,还要融入古人的风格,而所谓新意境、新语句,即欧化之意境和语句。“文界革命”的方向则是其所谓之“新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①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23页。可是,“新文体”大量运用西方语法及新名词,打破了传统文学文体规范和语法规范,造成了时人审美习惯的“紊乱”。
梁启超还发现,小说盛行西方各国而为国人小视。于是,他提出“小说界革命”,有意识地把小说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鼓吹小说社会功能,进而视之为解除社会弊病之良方。“小说界革命”的宗旨就是抬高小说文体地位,将它变成宣传改革的利器。因此,梁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呼吁:“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第 161页。与之相呼应,“林译小说”有力地支持了梁氏的主张。他用典雅古文翻译的西方小说,不仅引起了一般士大夫对小说的兴趣,还改变了他们的小说观念。③参见杨联芬:《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2002年第 4期。
在梁氏的倡导下,伴随着“新文体”、新诗歌、新小说的传播,西方文法、语汇大量涌现在国人面前,给中国传统文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以致引起时人的不安。如胡蕴玉在《中国文学史序》中就认为:“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也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至于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遂至小子后生,莫识先贤之文派。……遂无复文法之可言。”④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见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第 469页。
在此背景下,章太炎标举魏晋文体论,倡言“文各体要”论,意义有三:一是厘清“新文体”、小说带来的文体“混淆不清”的局面;二是平息骈散文之争;三是抵制以西方文论评价中国文学的做法,坚决维护中国文学民族性。
章太炎对当时“新文体”与小说流行的局面很担忧。他认为二体流行导致众多学人不辨文格,而轻意以“新文体”、小说之文法为法。他在 1910年《与钱玄同书》中谈到:“所论嘉兴学生专喜金圣叹、蒲松龄一流文字,益叹梁、夏诸君为作俑也。缪语本易动人,而尸高名者复为诱导,倭人又从旁扇之,微虫腐君毒遍区中,奚独嘉兴尔乎!”⑤章太炎:《与钱玄同书》,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115-116页。因此,他对林纾痛加呵斥:“(林纾)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间,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⑥章太炎:《与人论文书》,见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第 448页。
为了应对“新文体”、小说的流弊,章太炎一方面劝说学子,帮助他们树立“文各体要”的观念:“林纾小说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今学子习作文辞,岂专为作小说、撰报章,而舍书札文牍之恒用邪!若欲专修文学,则小说、报章固文辞之末务。且文辞虽有高下,至于披文相质,乃上下所通。议论欲直如其言,记叙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而小说多于事外刻画,报章喜为意外盈辞,此最于文体有害。既失其末(原注:书札文牍),又不得其本 (原注:高文典册),学此果何为哉?”⑦章太炎:《与钱玄同书》,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 118页。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桐城诸子:“今知古学者既难多得,但令处处有桐城派人主持风气,亦可相观而善,胜梁、夏之窕言多矣。”⑧章太炎:《与钱玄同书》,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 309页。
当时还存在着骈散文之争。骈散文之争的实质,就是骈文跟桐城古文争夺文学正宗地位的斗争。骈文正统论的代表人物是阮元,他继承萧统《文选序》以“沉思”、“翰藻”为文的观点,标举“文言”说、“文笔”说。阮元之后,折衷骈散的观念成为主流,其代表人物有汪容甫、李申耆、王闿运等。晚清刘师培承阮元余绪,再次提出骈文正统论,以“彣彰”代替“文章”,讲究修辞工整和辞藻华美,并认为唐以后之文皆是六朝之“笔”而非“文”,未得“文”之本源,且不讲究“骈俪相偶”,而有违六朝“文”之本质。之后各代以唐宋文为宗的古文,自然也不得“文”之本体,是为伪体。⑨1905年及后 1年半内,刘氏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涉骈散文的文章,如《文章原始》、《论文杂记》、《文说》、《文章学始序》、《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之后,又作《广阮氏文言说》。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刘师培进一步阐述了阮元的“文言说”、“文笔说”说,其主要观点有二:第一,通过对“文”本义的考释,刘师培认为“文”是修饰,从而认同《昭明文选》“沉思翰藻”、“韵文偶语”之文为“文”,因此主张“文章”当为“彣彰”,论文当以“彣彰”为主。第二,刘师培以骈文为文学之正统,讲究修辞的工整和辞藻的华美,因此,疏证、语录之类自然的被排斥在“文”之外。
针对阮、刘论文讲求骈耦和华采俪词的倾向,章太炎提出雅俗观,即“文各体要”论,认为骈、散二体各有所用,各有其体,本不必争。在 1918年 11曰 13日《与吴承仕》一信中说:“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派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①章太炎:《与吴承仕书》,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 115-116页。后来又重申:“骈文散文各有体要。骈文、散文,各有短长。宜言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且“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二者并用,乃达神旨。以故骈散之争,实属无谓。”②章炳麟:《国学讲演录》,第199-201页。
章太炎强调骈散文各自的文体功用,就从理论上解决了骈散文的争论。这较之骈散调和论者单纯强调骈散不可分更有说服力。③李兆洛《骈体文钞序》:“吾甚惜夫岐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包世臣《文谱》说:“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体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天地之道,有奇必有偶。周秦诸子之书,骈散互用,间多协韵,六经亦然。”又谓:“古文参以排偶,其气乃厚。”(转引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259页。)诸论多认为骈散本为一体,不当分,但都未能从理论上回答为何不能分的问题。他反对刘师培的“彣彰”论,实际上庇护了桐城派。从这个角度说,平息骈散文,是与上述提倡桐城文来抵制“新文体”、小说的不良影响是相通的。
章太炎认为“文各体要”是中国文学区别于他国文学的重要特征。西方所谓“美”和日本所论“兴会神味”,只适合西方与日本文学,而不适合用来评价中国文学,因此他反对用西方文学观念评价中国文学:“西方文艺者,盖言希腊、罗马,不独中夏。”④章太炎:《菿汉微言》,见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第 292页。又说:“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取其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⑤章太炎:《文学论略》,《章太炎的白话文(附录)》,第 149页。章太炎批驳了日本武岛虔次郎《修辞学》中称文章不必具备体制的观点。日本武岛氏《修辞学》云:“凡备体制者,皆得称文章;然凡称文章者,不必皆备体制。无味之谈论,干枯之记事,非不自成一体,其实文字之胪列,记号之集合耳,未可云备体制之文章也。”⑥章太炎:《文学论略》,《章太炎的白话文(附录)》,第 150页。章太炎认为其说不然,图画、表谱、薄录、算草都各有各的有体制,“此皆各有其学,故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不皆然。”⑦章太炎:《文学论略》,《章太炎的白话文(附录)》,第 151页。章太炎站在本国文学的角度看待西方文论,也符合他以国粹激励种性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