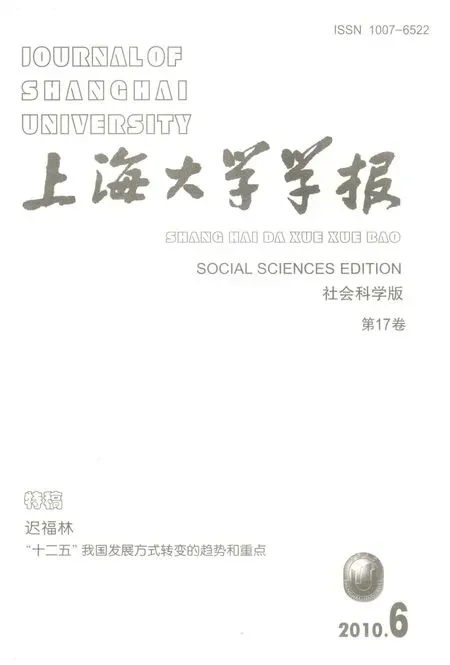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瞿 琨
(上海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44)
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瞿 琨
(上海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44)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该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首先对该理论进行“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指出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调解场域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之间是互动的,信任机制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中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场域中的调解行动发生作用。信任机制的构建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本文认为,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的选拔、该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
调解场域;社区调解;信任机制;构建法则
本文采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调解场域内外各种因素对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的影响,由此得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在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一是笔者之所以在浩瀚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中选择与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因为笔者发现该理论在阐释与分析本研究问题时所具有的“贴合性”。场域、惯习是布迪厄理论的重要分析单位,笔者在借鉴、引进场域理论阐释与分析有关问题时,首先对它进行了“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
二是本文中的社区应当理解为与单位和政府相对的社区,它既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是街道与传统居委会的翻版,而是衔接政府和个人并由社区居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关于社区的定义有许多,笔者采纳以下定义:所谓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1]
三是本文中的社区仅限于城市社区,研究对象是城市的社区调解制度,并且以笔者生活的城市 S市的社区调解制度作为分析样本。这是因为社区有多种类型,常见的社区分类有:按照社区成员的主要活动或社区发挥的主要功能,可以把社区分为工业社区、商业社区、农业社区、文化社区以及军事社区等。按照社区的形成方式,可以把社区分为自然社区与法定社区,自然社区是自然形成的,常以河流、湖泊、空地、山林、道路等作为社区边界的标志;法定社区是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设置的,边界是通过行政程序划定的,但要考虑自然社区的构成。按照社区规模大小,可以把社区分为巨型、大型、中型、小型以及微型社区等。按照社区的结构、功能、人口状况、组织程度等多元综合因素,可以把社区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最后一种分类是社区分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分类,[2]本文就采纳了这种分类,即本文中的社区特指城市社区,而非农村社区。下面笔者运用场域理论展开具体分析。
一、对于社区调解场域的初步认识
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布迪厄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这表现为它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与规则。社区调解场域是社区调解人行动的具体空间。在本文中,这个调解场域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更重要的是具有分析与研究功能的概念。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3]132如社区调解人的调解行动受到外部关系——社会宏观结构与内部关系——调解场域的影响。
布迪厄说,“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3]134“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3]155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因为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行动者,它们之间不断“博弈”,这些行动者运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知。
调解场域由调解行动者、调解组织和调解行动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调解行动者包括社区调解人与纠纷当事人双方以及其他社区调解参与人;调解组织指目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调解机构;调解行动即为调解人进行的社区调解。社区调解人采取各种策略进行调解行动,来获取各种社会资本,以争取有利的位置,力争用自己的逻辑影响和替代纠纷当事人的逻辑。在这里社区调解人想赢得的资本就是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社区调解人争夺的符号资本则是公平、正义以及和谐,当调解成功时,纠纷解决的公平与正义也就实现了。这里的正义应理解为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
调解场域不仅在社会宏观结构中占有位置,它本身也是一个由不同调解行动者构成的场域,具有自己的逻辑和相对独立性。这个独特的逻辑就是:信任产生合作。即社区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出于对社区调解人的信任,将纠纷交由社区调解人调解,他们共同与社区调解人合作,于是,社区调解人开始了调解行动,主持召开调解会,促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该协议。履行调解协议的行动表明纠纷当事人双方之间也产生了合作。
调解场域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同时它也是充满各种意义和价值的“主观世界”,在调解场域里活动的社区调解人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调解惯习。虽然布迪厄将惯习视为一种主观性,但他从来不认为惯习是纯粹的主观性,而认为它是与客观结构即场域相联系的主观性,也就是说,没有孤立存在的惯习,只有与特定场域相关的惯习。
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惯习是历史的产物”,[3]178并且具有“双重历史性。”因为惯习“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过程,在身体上的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3]184布迪厄认为,惯习不是习惯,作为一种在调解行动过程中生成的性情倾向系统,只有从调解行动进行的意义上来理解惯习的能动性。[3]163“惯习,作为一种处于形塑过程中的结构,同时,作为一种已经被形塑了的结构,将实践的感知图式融合进了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之中”。[3]184
惯习作为一种主观性的性情系统和心智结构,它不可能孤立的存在着,必须有一个“寓所”,这个“寓所”就是人的身体。惯习“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3]171社区调解人与纠纷当事人在社会空间和调解空间的位置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个人惯习。
就社区调解人来说,其调解惯习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长时期形成的调解人个人的主观存在,笔者把它称为“个人的本体惯习”,如调解人的处事经验,人生阅历,谈话技巧,对法律道德的知识结构等。另一部分是由传统“和合文化”积淀形成的关于纠纷解决的“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民族心理,制约和支配着调解人的观念和行为,体现在调解人的调解行动上就是情理法融会贯通的驾驭能力,笔者把它成称为“个人的实践应用惯习”。笔者的调研也显示:调解人是将情理放在第一位进行调解的。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也是信任产生的源泉。
调解惯习在调解场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调解惯习,在调解场域中的社区调解人,运用各种不同的调解技巧和策略,进行着成功的调解行动。调解惯习的功能在于:决定调解人在运用调解技巧和策略上的优劣,从而引导纠纷当事人对调解人产生信任抑或不信任,最终导致调解行动的成功或失败。
就纠纷当事人来说,其调解惯习也由历史积淀与个人素质两部分构成,与社区调解人不同的是在历史积淀方面。由于以前成功或失败调解的“经验的传递性”,使得他们对社区调解人产生了高度的信任或者不信任,从而接受或者拒绝社区调解人的调解;而纠纷当事人的个人素质、教育程度、工作背景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于调解人的信任,在具体个案中,就表现为有些纠纷当事人是“讲道理的”,有些则是“难弄的”,从而促进或阻碍调解人的调解行动。
采取场域理论作为社区调解制度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场域与惯习是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正如布迪厄所说,“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3]17调解场域是具有调解惯习的场域,而脱离调解场域的调解惯习也是不存在的。二是场域与惯习之间存在“本体论的对应关系”,布迪厄认为,这种本体论的对应关系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场域与惯习有种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3]171-172作为调解场域的社区在转型时期的发展特征深刻影响着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另一方面,场域与惯习有种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3]171-172调解人通过调解惯习进行的调解行动,也在建构和影响着社区,它化解社区的纠纷,提倡邻里之间互让互谅,促使人际关系和睦,从而使社区有序与稳定。三是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布迪厄认为,“惯习这个概念,揭示的是社会行动者既不是受外在因素决定的一个个物质粒子,也不是只受内在理性引导的一些微小的单子,实施某种按照完美理性设想的内在行动纲领。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是整个社会场域的历史,是特定子场域中某个生活道路中积累的历史”。[3]181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在调解行动中获得积累与增长,又在调解行动中持续发挥作用,它通过成功的调解行动建构充满信任的社区;同时又受到充满信任社区的持续影响,促使社区调解的成功进行,并影响着调解场域,由此,调解场域的本质应当是肯定性的社会互动。
二、社区调解场域的内外因素对于信任机制的影响
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是信任机制。①参见瞿琨:《社区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思考——从社区调解人的行动入手的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 6期 ,第 33-37页。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不仅调解场域与调解惯习互动,调解场域与调解行动互动,调解场域与信任机制也是互动的,从本质上看,信任是一种人的行为体现形式,它的发生和存在依赖于关系所构成的特定情境,这个情境就是调解场域。在调解场域中,信任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极为重要的机制,但它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受到由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结构系统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特定场域的行动而发生作用。笔者在这里再把调解场域作进一步的引申,即这个场域实际上包含了调解人行动时发射出来的一系列的调解信息,这些调解信息在调解场域的传递过程中形成了对社区调解信任机制有支持功能的力量,如源于党的政策对于社区的发展与建设的号召;由居民舆论形成的对于当事人纠纷的褒贬意见产生的压力等,都使得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运作不是纯粹的一个机制的孤独运作,它有众多调解场域元素的陪伴和支持。就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现状而言,它有良性运行的状态,也存在运行困境呈现出来的“信任危机”。
当事人对社区调解人付出信任时,也必须对采取社区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的风险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4]调解人的任何一个哪怕是小小的不符合信任承诺的行动都将破坏当事人对于他们的信任。
信任表达的是施信者与受信者之间的一种对称性的关系,基于信任的回应行为就是信任主体之间的合作,因此,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在社区调解的过程中,存在着双方当事人与社区调解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当事人出于对调解人的信任接受社区调解,这时他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合作关系,这个信任是社区调解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信任,当事人也就不会请调解人介入他们的纠纷了。社区调解的顺利进行,还需要当事人人之间的信任,在调解人的开导下,当事人之间化解了对立,达成了调解协议,还要一起履行调解协议,这时当事人之间不仅有信任,还有信任产生的合作,但这个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是从属于他们共同对于社区调解人的信任。合作的行动也进一步增强了信任,因此,在社区调解中,信任与合作是互动的关系。在整个过程中,受信者社区调解人的行动是主线,是核心,他们如何使一系列的调解行动得到施信者——即双方当事人的认可是关键,这个信任机制是这其中的信任机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社区调解信任作为调解人的行动的反映形式,它的产生和存在与社会空间,即调解场域密切相关,如果把社区调解制度放入社会的大场域中考察,就会发现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发生并不仅仅局限于信任主体之间的互动,主体之外的社会其它因素也深刻影响着这种信任机制的形成,因此,处于调解场域的信任机制同时受到社会的宏观结构和调解场域的双重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一)社区调解人的道德自律产生的影响
就社区纠纷解决而言,社区调解人是属于当事人“可以付诸信任”的社会角色。他们一般被期望为:总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化解纠纷的能力。当社区调解人置身于调解场域中,出于对调解人这个内群体的角色意识,希望以严格自律的行动,增强调解人这个内群体的自尊感和价值感,促使当事人这个外群体理解调解人,并按照调解人的安排去行动,这是一种道德的制约力。有学者指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5]对于社区调解人来说,这个“规范”和“规则”就是广大社区调解人通过在调解过程中的道德自律,获得的“声誉”和“威望”。当然,调解人的“声誉”和“威望”是在长期的调解生涯中形成的一些外部特征以及调解技巧的基础上。
(二)利益平衡导致的理性选择的影响战
置身于现代调解场域中的调解主体,对于社区调解的信任机制,主要有一个利益平衡的考虑,这个利益平衡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任主体双方之间的量的平衡,即调解主体彼此施予信任是否能够实现双方的目标利益的追求;只有当信任主体双方的目标利益追求都能得到实现时,信任主体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才是稳定的、恒久的。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这里所提及的“利益追求”不仅有直接的物质利益,也包括间接的道德上、精神上的利益。前者如纠纷当事人给予调解人信任,得到了化解纠纷的成本低、便利、快捷、灵活的诸多好处。后者如社区调解人通过自己优质的调解行动,有效地化解纠纷,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其次,这里的“利益平衡”是相对意义上的平衡而不是绝对平衡,即调解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不要求付出同等的信任资源,而只要调解主体双方实现了心理预期的利益目标就达到了平衡。
利益平衡的第二个内容是信任主体双方之间的质的平衡,即调解主体彼此施予信任是否能够实现双方的主观心理预期。这个心理预期的计算标准有两个方面:首先,社区调解制度可能带给自己的好处多还是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其次,施信予一方调解主体的,受信者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调解主体只有对上述问题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才会采取信任对方的理性选择。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如果他考虑社区调解人将会使自己享受社区调解在解决纠纷上具有的诸多好处,如成本低、便利、快捷、灵活等,就会作出信任社区调解人、接受调解安排的理性选择。而对于社区调解人来说,他们的考虑主要在于:如何通过自己优质的调解行动,有效地化解纠纷,取得当事人的信任,促进社区调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也会作出不断提高自己调解技巧的理性选择。尽管信任在产生之初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的行动,如齐美尔认为,信任处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6]但由于社区调解的信任机制内在地符合调解场域中各方的利益,因此,这种信任机制的产生就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并会逐渐拓展和传播。
(三)由紧密关系产生的心理契约影响
我们由“差序格局理论”知道情感是建立紧密关系的重要衡量尺度。在社区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就是通过与当事人的频繁接触、沟通,将当事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对于比自己年长的当事人,把他们看作为自己的长辈;对于与自己年纪相当的当事人,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当事人,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家里的小辈,通过这种感同身受的行动,使得当事人与调解人之间产生紧密的关系,并与当事人之间达成对纠纷解决的默契,笔者将这种默契表述为一种“心理契约”。这个心理契约的涵义就是指社区调解人与纠纷当事人之间隐含的没有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的信任机制,即当事人出于对调解人的信任让他介入纠纷的调解,并相信调解人不但会化解纠纷,而且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调解人希望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将社区纠纷交给他处理,并接受他的劝说最终化解纠纷。如果调解人或者当事人违背心理契约,出现失信行为,周围的社区居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轻则遭受居民们的道德谴责,重则难以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区立足。
(四)重复博弈产生“经验的传递性”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的流动加快,社区居民的结构变得复杂。面对社区居民的陌生化与半陌生化,社区调解人与当事人之间呈现出“重复博弈形成信任”的特点,即当事人对社区调解人的信任有一个由“相识、相知到相信”,从“初步相信到深信不疑”的渐进过程,这个渐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当事人对于社区调解人信任“经验的传递性”。这个信任的传递不仅表现为调解人对于某一个社区纠纷的调解过程中,逐渐获得当事人信任;还表现为社区中其他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人的调解,把对调解人的信任拓展到整个社区的调解场域;这个信任的传递还会扩展到跨社区的当事人上门请调解人介入调解,使信任传入社会的大场域中。从反面来看,如果社区调解人采取了不到位的调解行动,也会导致当事人对他们的不信任扩散,后果就是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采取社区调解以外的方式,如法院的诉讼。
(五)伦理与习俗等文化资源的影响
信任的影响因素不仅存在于社区调解主体之间,也存在于调解主体背后的社会宏观结构中。如前所述,调解场域内的信任主要指对于调解人的信任,由于调解人的行动形成了社区居民对社区调解人整体的信任。①此处不考虑个别调解人的不合格的调解行动——笔者注。但作为纠纷当事人,他们给予社区调解人信任的同时,也将信任赋予了社区调解制度背后的伦理与习俗。纠纷当事人对于法院诉讼的认可,表明他们对于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的接受;而对于社区调解的认可,表明他们对于有传统积淀因素的制度的认可,它之所以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认可,是因为世代相传的伦理与习俗等文化资源的作用。众所周知,社区调解制度由传统调解制度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与我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文化资源有关,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惯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调解场域以外影响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因素还有保障因素,如位阶较高的关于调解的法律保障以及经费保障等。
三、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信任机制的构建不仅要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如法律、政策、情理等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笔者认为,由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的分析中,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选拔、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具体内容是:
(一)创设选拔优秀社区调解人的机制
在纠纷当事人与社区调解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中,纠纷当事人的作用是重要的。由于纠纷当事人对社区调解人的可信度进行了衡量和选择,并通过自己接受社区调解的行动将选择结果表现出来,才建立起纠纷当事人与社区调解人之间现实的信任关系。社区调解人的口碑、人品、调解技巧等是纠纷当事人衡量、判断其可信度的重要因素,是成为受信者的前提条件,但最终是否成为受信者,是由纠纷当事人的选择来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在建立现实的社区调解信任关系中,纠纷当事人是具有能动力的;但社区调解人对于是否能够被选择作为受信者并不是没有作为的,而是具有直接的制约力,因此,优秀社区调解人与他们作为受信者的信任度紧密联系。一般来说,信任度包括正直、善意、才能、诚实、公平、可靠、保护、支持等元素,增强社区调解人的信任度,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
1.“法律是一个连续体”的法社会学观点的启示
曾有学者在考察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运作时认为,那是一个多元化的运作。[7]9“家法、行规、地方风俗等活生生的法律扮演了比国法更积极吃重的角色”。[7]8提出的观点是:“视法律为一个连续体,由非正式的调解一直到官府衙门的判决,诉讼过程渐渐正式而繁复化。这是法律程度 (成分)由少到多层层相连的连续体。[7]9有学者在分析荷兰法律社会学家布兰肯堡的观点时指出,布兰肯堡认为,“法律有个似连续体的运作空间,介于调解与判决之间。前者指较少的法律,后者则是较多的法律”,“行使前者成为调解者,行使后者成为判决者 (法官)。”[7]7
应用这个法社会学观点作为理论工具来对比分析当下我国的法官与社区调解人的行动,就会发现:法官审判案件应当严格依照明确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来进行,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法律是其判决的唯一依据,情理因素对判决的影响比较小;根据笔者对 S市的调查显示,社区调解人在调解时首先采用的是情理,是摆事实、讲道理。对纠纷当事人,先采取“背靠背”的说理工作,等“火候”差不多,当事人都有互相谅解、让步的意思时,再进行“面对面”的说理工作,最后督促他们履行调解协议。社区调解中也会应用法律、政策等,也会采取情理法综合运用的方法,但调解人的说理技巧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由此,从法院审判到社区调解,法律成份呈现出由多到少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受到“法律是一个连续体”的法社会学观点的启发,提出将具有“布衣法官”美称的社区调解人纳入到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观点,并进行“准法治化”的建构。
2.实践上提升社区调解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增强社区调解人的信任度,就是树立社区调解人的权威,增强社区调解人的主体性或主观能动性,发展与完善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关键在于提升社区调解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对此,可以从设置规范的社区调解人的准入机制;
设置规范的上岗社区调解人的资格延续考核机制;设置社区调解人参与法院调解前置程序的机制;设置定期总结交流社区调解人经验的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
(二)完善社区调解制度的本体建构
1.扩大社区调解的受案范围
司法部 2002年 9月 26日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 20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这个规定把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纠纷也纳入了调解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调解范围,但对于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对于一般纠纷所导致的轻微刑事案件等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采用社区调解制度,而后者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进行轻微刑事案件采用社区调解的尝试。从理论上分析,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止调解的纠纷,或者说,只要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的权利纠纷案件,都可以采用社区调解,因此,社区调解的受案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包括:(1)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2)《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自诉案件,如侮辱案、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等;(3)民间纠纷之外的其它民事争议,如在城镇,因职工下岗导致的劳务纠纷;因企业亏损、破产而拖欠职工工资引起的劳资纠纷等。这个思路是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切纠纷都纳入到社区调解的范围,以充分发挥社区调解的功能。
2.进一步提高社区调解的成功率
根据笔者的调研,社区调解存在着这种情况:即少量的社区纠纷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反悔,最后进入法院进行诉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区调解的一些比较优势具有两面效果,如调解过程简便、灵活,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随意性,使当事人的程序利益无法实现,有时会影响到实体结果的公正。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过度自治”难免会出现“向穷人出售廉价、低质、粗糙的正义。”[8]因此,社区调解制度在笔者提出的“准法治”建构的同时,为了改变它的非组织化、非程序化的现状,使其符合现代法治对于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可以考虑创造一些条件,适当提高它的法治化程度,将一些法治要素逐步融入到目前的社区调解中。
长期以来,民间调解是以解决纠纷为最终目的,因此是多种手段、多种力量并用,往往要借助社区中有威望的居民、纠纷当事人的亲友等“外围力量”;调解人主要依据的是情理、道德、习俗、舆论、信誉等社会规范,如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现在的社区调解人经常会运用情理法综合规则进行调解,其中,情理是第一位的,法律是第二位的,依法调解成为解决纠纷的一个选择手段;调解人多为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他们调解的成功率主要依靠对当地居民的长期了解、对地方习惯的熟悉、解决纠纷的经验,以及由于自身条件产生的对当事人的影响力。社会的发展变迁加剧了社区居民的流动,使得社区由“熟人”转变为“半熟人”的状态,而社区的“陌生人”成分还在发展和扩大,社区居民原有的“熟人共同体”在瓦解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冲击了固有的信任型调解,影响到他们心目中的社区调解人的信任形象;与此同时,国家的普法宣传提高了人们的法律意识,这些变化也给社区调解带来了一定影响,如调解工作室的出现反映的专业化、规范化变化;对社区调解人知识结构的法律要求等。虽然笔者提出了社区调解不宜过度制度化、规范化的观点,但这与适当提高社区调解的法治成分并不矛盾,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社区调解的成功率,因此,可以考虑社区调解在采用情理规则进行调解的同时,适当增加法律的含量。
一个优秀的社区调解人固然应当是本社区、本辖区的“百家通”,他们熟悉社区中每家每户的情况,具有了解居民个性特征的本领,但社区的流动性加大了“百家通”的难度,因此,对于当下的社区调解人,应当要求具备法律知识。当发生纠纷时,社区调解人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纠纷当事人的个性特点,应用法律基础很快作出判断,找到纠纷的症结,采取针对性很强的调解方案,使调解取得成效,进一步提高社区调解的成功率。
3.建立社区调解的保障机制
(1)给社区调解机构和社区调解人减负
由于在社区调解机构定性上的模糊,使得调解机构和调解人进行了许多调解以外的工作,如笔者对 S市 L区 D街道司法所的调研显示,该司法所工作繁忙,其中的社区调解人更要身兼数职,协助所在街道 (乡镇)工作成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如监督打防疫针、房屋动迁安抚等。因此,给社区调解机构和社区调解人减负,使其专门从事社区调解制度,也是社区调解制度的重要保障。
(2)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目前,除了调解工作室尝试实行政府购买社区调解服务的机制以外,司法所和居委会的调委会的经费都比较紧张。如笔者调研中了解到,有的司法所中享受正式编制的社区调解人的工资只发给 80%,其余的 20%要自筹;至于临时雇佣的社区调解人的工资都是要自筹或者依靠街道 (乡镇)补贴。社区调解人具有的道德素质要求他们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公正廉洁地履行调解职责,这些道德要求需要他们做出较大的付出和牺牲。社区调解从诞生以来一直是免费的,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区调解的不计报酬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并不利于树立社区调解的威信,因此,应当考虑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将社区调解人纳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范畴,在现阶段进行“准法治化”的建设,使社区调解人行动经费的来源稳定与可靠,以此保障社区调解人的尊严。二是以调解工作室为模板,在现阶段大力推行“政府买单”的社区调解,使社区调解组织也有个政府的经济支撑,推动调解组织的工作顺利展开。
(3)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不久前即 2010年 8月 28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总结了从建国时期就开始的人民调解制度实践,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等都作了规定,使属于人民调解制度的社区调解制度“有法可依”。
(三)建立社区调解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
社区调解制度与法院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上各有比较优势与制度本身预先设定存在的劣势,实践中,社区调解还是有一些没有解决的纠纷最后到了法院诉讼,①笔者在调研中曾经打算统计这个数据而没有做到,但了解到这个数据是少量的。因此,如果建立社区调解制度与法院诉讼制度的衔接机制,使实现社会正义的“第一道防线”与“最后一道防线”有机联系,协调配合,就能避免“重复劳动”,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建立社区调解的制度权威。目前,S市已经开始探索社区调解与法院诉讼的“无缝化”衔接,主要有以下内容:
1.加强社区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社区调解协议的执行是社区调解实现“案结事了“的关键,对此,《人民调解法》第33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为了增强社区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还可以采取以下做法:一是在社区调解协议中增设违约金条款,对于当事人拒不履行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就要接受违约金的惩罚。二是借鉴美国的做法,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而提起诉讼,在判决结果低于原调解结果 10%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的一方必须负担对方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原告一方甚至必须在判决数额大于调解结果50%以上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此种责任。[9]
2.建立纠纷分流处理机制
在法治社会中,对于各种纠纷应当根据它所具有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纠纷解决手段,才能更好地解决纠纷,节约社会资源。在社区调解与法院诉讼的协调衔接上,可以考虑建立合理的纠纷分流处理机制,小而简单的纠纷应主要由社区调解来解决,而重大、复杂、疑难的纠纷应当由法官通过审判来解决。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司法资源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存在,因此,法院在立案与审判时,还要充分发挥社区调解的作用,即使是已经立案的轻微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轻伤害赔偿纠纷,都可以委托社区调解来进行,再由法院认可予以执行。
3.建立法院附设的调解制度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是充分发挥了社区调解的功能,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当事人在法院诉讼前的阶段也有选择调解的机会;二是调解人由法院聘用和培训,这改变了过去我国法院调解的调解人与进行审判的法官是同一人的现象,使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自然分开,使调解人与法官各司其职,避免了法官既从事审判,又进行调解容易产生角色错位,从而导致审判结果不公正的弊端。
对于法院附设的调解制度,S市已经开始尝试,试点首先在由 C区和 P新区法院进行,由区司法局和区法院共同设立了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平台——“区联合调委会人民调解窗口”,整合调解与诉讼资源。“窗口”设在法院里,调解人主要是退休的法官。分诉前、审前、审中几种情况:
一是诉前调解,即法院立案前的调解,原告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小额债务、小额损害配赔偿等纠纷向法院起诉,法院立案庭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暂缓立案,而将纠纷交由法院附设的“人民调解窗口”进行调解。“窗口”按照双方当事人发放调解通知书征求意见,如双方当事人同意即受理调解。调节成功的,以“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出具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由法院审查立案。具体做法上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强制调解”的规定,即对于一些特定纠纷,如家庭纠纷、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不动产相邻关系纠纷、财产权纠纷等,除非有例外情形,在起诉前应当由法院先行调解,[10]我们也可以将法院受理的一部分适宜调解的纠纷明确规定为“强制调解案件”,S市已出台类似规定。
二是法院立案后但尚未开庭的调解。即在法院开庭前,如认为案件可以由调解解决的,就由法官向原告和被告直接发放调解征询意见书,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即委托人民调解窗口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方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的执行有法院强制力;调解不成的,由法官依法审理。
三是协助审中调解。是指联合调委会派遣的调解员以陪审员身份参与合议庭案件审理,协助法官进行诉讼调解。独任法官审理部分简易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需要,邀请陪审员列席旁听并委托其调解。审中调解的结案方式按照法院诉讼调节的程序进行。调解人将调解方法融入到诉讼调解中,丰富法院的诉讼调解,提高成功率;调解人通过参与法院案件审理,接受法官的言传身教,进一步提高了业务能力,达到业务培训的效果。
(四)营造充满信任的调解场域
这是指通过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在社区中营造充满信任的调解场域。一项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增强人们之间的情感、认同以及信任。[11]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是社区的基础,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人际关系网络输出的一个主要产品就是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的无形资本。社区中的邻里、同事、朋友通过一些交往、沟通与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理解,使他们彼此都获得情感支持和高度信任。因此,互动频繁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建立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要充分利用社区调解制度的各种机制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促进信任与合作。
社区调解制度有一个比较正式的程序就是召开评议会,评议会是在社区调解人的主持下进行,参加评议会的人有纠纷当事人、楼组长、纠纷见证人、社区中有威望的居民,在评议会上,让大家对发生的纠纷充分发表意见,甚至投票表决纠纷的处理方案。一般是先评议后签字,纠纷当事人双方都同意认可的解决方案要签字确认,参加评议会的所有人员也要签字确认。社区调解人的行动,起到了法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作用。这些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调解,在纠纷调解过程中参与意见,互动讨论,甚至争论,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提高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社区建设从整体上得到加强。有利于扩大社会广泛信任的范围以及提高社会广泛信任的程度,同时也充分发挥了信任所具有的传递性的功能。
信任,是人类的一种情感,也是人类行动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和社会产物。如果说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硬规范”,那么,信任就是促进社会和谐的“软机制”。社区调解制度既打上了传统“和合文化”的印记,同时也具有现代法治的人文精神内涵,其内在的信任机制融传统与现代的优秀元素于一体,对于它的探索与研究,不仅对促进社区调解制度本身的发展有价值,也对推动“东方经验”的传播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33-34.
[2]唐忠新.构建和谐社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4.
[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33.
[5]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0.
[6]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72.
[7]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9.
[9]乔钢梁.美国法院的调解和仲裁制度[J].政法论坛,1995,(3):88-90.下转 93.
[10]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2.
[11]张广利.社会资本与和谐社区建设[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2):1-6.
Abstract:The theoretical frame provided by Bourdieu’s field theory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structure.This theory tries best to seek,between the activity of human and structure,for an interchangeable agent,and,by way of field,habitus and various capitals,explore the mystery of social practice.ForBourdieu,field is a social space characteristic of relative independence,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possessing itsown operational logic and rule.This essay takesBourdieu’s field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tool to analyze the intermediation field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community because the theory and the problems here have a"joint".The socalled intermediation field in the community means the concrete space of the community intercessor’s activity,which consists of such three elements as intercessor,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is study,intermediation field is not only the concrete geographical district but also the concept functioning analysis and research.The author,in using the field theory to interpret the related questions,carrieson a"reformation of community intermediation".On the one hand,the community space for intercessor’s activity is considered as a field,that is,intermediation field;and on the other hand,the intercessor’s quality is regarded as a habitus,that is,intermediation habitus.And,for the intermediation system in the community,the core mechanism is trustmechanism.In the process of the operation of intermediation system in the community,intermediation field and trustmechanism are also interactive.Trust mechanism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finish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of intermediation,and also in simplifying the process of solving community disputes.It is influenced by the macro-structure in the society and the meso-structure in the community,which is brought about through the community intercessor’s activity of the specific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mediation.Not onl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rustmechanism influenced by the intermediation habitusof the community intercessor,but al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intercessor as the trust subject and the interceded perso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rust.While the trust of the interceded person in the intercessor results i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mediation process,the cooperation goes further to strengthens the trust.The author holds that,by an analysis of the abov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ve processes,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 trustmechanism in the community intermediation can be achieved,in detail,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community intercessor,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itself,the cohesive mechanism of court litigation,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st environment in the community.In thisway,the construction of trust mechanism in the community intermediation can be promoted,and the intermediation system in the community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Key words:intermediation field;community intermediation;trust mechanism;construction principle
(责任编辑:梁临川)
The Intermediation Field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 Trust Mechan ism
QU Kun
(School of Law,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D922.1
A
1007-6522(2010)06-0126-18
2008-12-15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1ZS97)
瞿 琨(1964- ),女,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