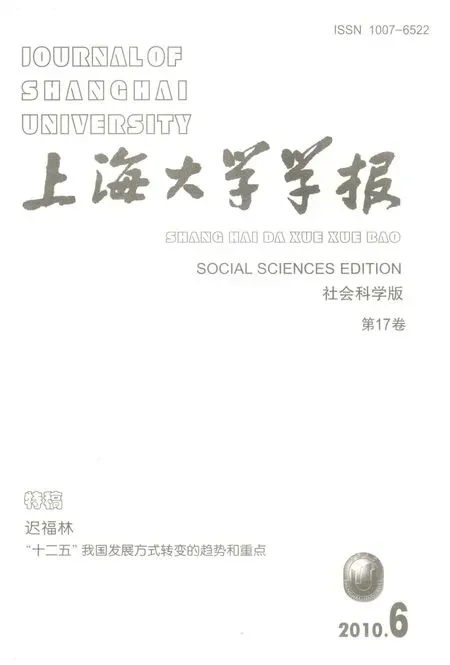当前西方基督教网络传播态势及其研究视野
许 正 林, 贾 兵
(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 200072)
当前西方基督教网络传播态势及其研究视野
许 正 林, 贾 兵
(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 200072)
宗教使用网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80年代,宗教在线研究最早应该在 1995年,其中主要是对基督教网络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抽样与统计、内容分析、量化对比、田野调查和采访等。关注的前沿问题主要包括基督教网络传播的工具空间、基督教网络组织形态、基督教网络移民、基督教抵制网络传播、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权威、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虔诚、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修辞、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身份、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价值等九个方面。这些研究通过对照线上宗教和线下宗教,认为权力、权威和控制问题已经影响到宗教团体的核心利益与价值,在线活动在信仰和实践方面正在挑战传统宗教。
宗教;基督教;网络传播;宗教与社会
基督教网络传播的兴起具有其自身的教理动因。首先,教会一直重视传播的作用,基督教信徒被告知应“出去,到处宣传福音”,(圣经·马可福音.16:20)“教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传播”,[1]宗教应熟练地运用技巧来传播自己。其次,教会也认为传播是合教义的。世界基督教通讯协会(theWorld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mmunication)文件明确指出:传播创建社区,传播是参与,传播是解放,传播支持和推进文化发展,传播是先知。说明教会非常清楚传播的价值。再次,教会还利用传播塑造他们的公共身份,早在 1980年代初期,教会就指示,任何使用大众媒体的教会要发挥效应都需要电脑,以利于发邮件。积极接受当代传播技术,介入当代社会各个公共领域。
宗教使用网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80年代,当时一些热衷电脑的教徒试着用电脑来扩展他们宗教的利益,网上宗教活动包括在线宗教信息、在线教堂礼拜、在线宗教仪式、在线传教和在线交流等。宗教在线的研究最早应该在 1995年,《技术异教的有线网络特征》、《在网络上找到上帝》等文章就调查了包括天主教和索罗亚斯德教在内的多种宗教,概述了大众对新媒体条件下宗教会变成什么样的最初想像。还有如 O’Leary,S.研究天主教和异教徒将网络作为宗教新空间而进行的仪式。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研究者们开始将时间和注意力转到宗教在各种网络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再后来,随着网络传播与宗教的融合日益被视为互联网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相关的研究转向为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下对宗教进行文化解读,神学、精神、伦理和道德规范等成为研究网上宗教的突出主题。
“网络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关注媒介的工具层面和阐释层面两个主要阶段。工具层面涵盖了关于基督教网站的研究、关于使用者的研究、关于网络移民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抽样与统计、内容分析、量化对比、田野调查,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阐释层面,对宗教在各种情境下的媒介使用进行反思,以探讨其中的宗教的、人文的意义。
一、基督教网络传播的工具空间
教会是基于信仰的组织,某种程度上,教会容易受到规范组织传播的组织压力和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教会自认为是向他人传播天国信息的先锋,所以,教会网站的角色便有了一些不确定性。Amanda Sturgill采用对南方浸信会教会网站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 1033个网站进行编码,用电脑随机方法抽取 303个样本,以对所有的样本网站进行内容分析,并通过访问其中几个样本网站深化了编码类别。依据分类表对每一个样本网站进行访问和编码,使用编码-再编码方法和 HOLSTI公式计算内部编码的有效性,结果是 98.5%。
网络上还可以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教会创造或维持的信息、与其他人创造或维持的信息,并与此进行超级链接。相关研究包括教会网站是否提供布道的信息、是否提供布道的信息的链接。关于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信息,涉及教会本身以及教会所从属教派的信息。结果表明,展示教堂的建筑、广告教堂的地址和服务时间,是关于教会的组织信息的较多表述,也说明网站是报纸或电话黄页广告的新路径。另外,结果还表明真正的互动特征在教会网站中并不普遍。
总起来看,将教会作为一个组织来推广是教会网站的首要目标,紧随其后的是教会网站的布道功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组织信息通常是在地方上产生的,而布道的信息却不是。另外,92%的网站有教会服务内容一览表,而仅 56%的网站将救助计划作为其内容。传播创造社区或者说分享的观念,在所考察的网站中并没有得到发展。传播支持、推动文化发展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组织信息、教派链接的支持——如果将教派视为一种文化的话。
尽管网站正在开发新内容,扩展在线领域,布道仍是主要诉求,特征上主要以组织化模式推动全体。Henika,A.认为,一个网站是一个企业及其产品的虚拟存在。一个很好的网站增加组织的价值,互动的网站鼓励用户花更多的时间,这将创建品牌知名度。Haley,E。等人指出,这种现象对基督教机构可能也一样。
皮尤慈善信托互联网项目做了对教会和犹太教网站管理员的电子邮件调查,询问其网站的结构、发展和目的,结果显示,这些组织更容易将网络作为一个单向沟通的载体,基督教会还利用电子邮件在经常聚会的成员间进行沟通;使用网站的目的是吸引网站浏览者来教堂,促进社区里的人到教堂去做礼拜,支持基本教会活动,教会网站功能注重向外传播。Thumma,S.调查了 63个网站管理者,发现:“网站通常是由教会成员发起和维护;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网站是有针对性的,排除一般公众,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网站是一个公共和会员混合使用的网站,只有 7%表示,他们的网站首先是为了集会;网站通常由志愿者开创;有些教派提供足够的帮助建立教会网站。Dart,J.曾建议将基督教延伸到在线媒体等新形式的潜力最大化。”[2]
坎贝尔探讨了网络作为一个神圣空间是如何被研究和设想的。即使用网络的教徒是如何将网络视为适合他们的信仰和行为的一个能独立生存的空间。为了理解这个模式,坎贝尔提到了关于网络的几种主流观念:信息空间、共同的精神空间、身份空间、社会空间。每一种观念强调了网络的一种专门的用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多是依据精神空间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类细化描述,每一种类型都会强调先前的表述模式中所表述的、网络作为神圣空间所包含的特征,并说明网络作为精神工具、宗教身份、个人精神追求的空间、社会精神支持的空间是如何被使用的。但是,网络使用者从网上获得的对这个教会的感受是有别于现实中所获得的。尽管教会对它的许多在线服务做了直播,使用者与使用者之间、与教区居民之间、与神父之间等仍然处于异步模式中。因为“网页是无实体的,使用者不可能对大脑中所形成的关于教会所提供的内容的印象做一个准确描绘,仍然视网站为人工制品”。[3]Brasher,B.预测,“网上宗教,对 21世纪的宗教来说,是最有预示性的发展”。[4]
二、基督教网络传播的组织形态
Cantoni,Lorenzo的研究对全世界范围内5,812个基督教圣会和自治机构进行了调查(约有 858,988个成员),使用电子邮箱发送问卷的调查方法,调查对象首先是至少能够使用电子邮箱的机构或组织 (共有 2285个,占总数的 39.3%),收到了 437个回复 (是邮件使用者总数的 19.1%)。调查结果发现:“中心机构和自治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比后者更大程度地使用网络。”[5]发现使用者倾向和资源占有两个相关因素:采用默祷、与外界沟通的倾向性越小,组织在网络的使用上也更少,或者说几乎不用;为帮助穷人和病人而设立的机构更少地使用网络,原因在于可利用的资源较贫乏。
非商业性的宗教组织持续增长,其中很多都是在组织机构的网站上操作的。但是,SmithMelissaM.研究发现有些机构没有充分使用他们的网站。这些机构不太注意他们网站上的成员,不把他们的网站当作吸收新成员的手段,不知道有多少成员在使用他们的网站,同时也很少雇佣专业人员去维护他们的网站。
Elena Larson概括了 PEW的“网络和美国生活”的项目报告“无线教堂、无线祈祷:网上集会与传教”,[6]17-20特别关注了为宗教目的而使用网络的情况 (叫宗教冲浪者),相关情况如下:宗教冲浪者数量巨大 (美国有2800万),且正在增长 (不到 5年的时间增长了 4%);很多宗教冲浪者使用网络去补充和强化他们本已很强的对宗教活动的承诺;对为宗教目的而使用网络持有积极态度,同时关心相关的潜力开发。这些数据同其他的认为网络宗教是普遍的那些研究者提供的数据是一致的。
Christopher Helland的研究表明,不仅各种教派和运动在使用网络,而且个体也常常在他们的网站上挂出宗教的招牌。许多网络支持传统的宗教,也有反动传统宗教以吸引注意力的,也有以此挑战制度权威的。有些是排挤权威,有些是直接反对。Christopher Helland认为,网络迎合了那些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其宗教和灵性的人,这一点可能会加速正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宗教的变化。
网络同宗教组织的社会资本建构关系一直很少被研究。基于近来对网络、社会资本和宗教的研究,Cheong Pauline hope探讨了宗教组织基于网络同他们的宗教生活的融合而重新建构他们的群体规范、价值和行为的途径。Cheong Pauline hope认为,“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是互补的、变化的、无常的关系,宗教群体往往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宗教组织的群体规范、价值和行为都在拓展。早期的研究没有发现涉及重构组织行为的革新的证据、协调宗旨和服务的证据”。[7]Cheong Pauline hope阐明了一些宗教组织是如何扩展他们的职业范围、重构他们的传播行为以激发出管理性的、可操作的结果的,并认为,和其他的组织一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摆脱包括网络技术在内的科技进步的影响。
三、网络传播与基督教网络移民现象
早在网络传播技术出现之初,人们就担心网络传播形成的社区会将传统社会碎片化,这势必会影响到传统宗教统一性、权威性与价值体系。然而现在的事实表明,网络传播的出现不仅没有肢解宗教,反而更好地解决了宗教信徒的散居问题,实现了更为自由与有效的在线精神交往。这就是所谓的网络宗教移民。
传统的宗教和宗教组织与印刷文化传播技术是紧密联姻的,而不是 Innis-Ong所描述的作为虚拟网络环境中的次级口语传播。那么,进入网络化时代,基督教能否以网络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一个前提,即“线上线下的统一”。Marilyn C.Krough探讨了许多在线宗教社区的共同特征,指出“在一个社区的创建和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的设计目的和策略发挥着重要作用”,[6]205-219可以总结为:为线下发展而联系人们、发展在线聚会、发展在线关系、规划成员的生活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成员的互动和指令在线管理;帮助他人将事做得更好;为在线参与者制定一些群体规则;制定一些规则保持对事务和活动的管理;设定一些仪式日程表和引导指令 (这些大多是将线上和线下参与结合起来的);为了更好地壮大并保持亲密关系而在更大的社区创立次级群体。作者认为,线上和线下的两种版本是共生的而不是对立的。
Glenn Young注意到,在祈祷和阅读中的信息接收和活动参与 (宗教在线的两个方面),当线上线下两方面合到一起时,“构成的网络宗教实践是一种统一而不是分裂。提供信息,是网上一个最主要的宗教传播模式”。[6]93-106然而,也有其他参与性的例子,从祈祷请求到提供可以让使用者作自我引导仪式的材料。一些网站通过聚会、深呼吸、冥想等方式让网络空间变得神圣,相应地,将参与元素带到现实、网络中来。遗憾的是假设真实的宗教参与只能出现在线下,但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结论。
Helen A.Berger探讨了非主流宗教社区,认为尽管有了一些传统宗教狂热者的声明,但是关于网络被用来引诱青少年来崇拜恶魔,仍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对青少年来说,选择宗教的主要门路仍是书。然而,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网络使得信息和仪式活动在更大的范围里更加现成了,也许换成别的环境,这些都无法运作。尤其是考虑到实践,网络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虚拟的环境,在这里大家可以互动。”[6]175-188网络的确动摇了原来的秩序,为消弭距离做出了贡献。
对于网络上成长着的宗教语境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维度,在迅速发展着的网络世界,这种行为的充分影响还有待研究。Christopher Helland承认在“个体能多么快地参与这些宗教事件”的研究上还存在不足,他还在继续研究那些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团体正在寻找的能将实际参与宗教事件的感觉最大化的方法,比如,在“第二圣殿哭墙”这个网站里,通过电子邮件出售写好的祈祷文。
Stephen Jacobs研究了一个特殊的主题:20世纪 90年代后现代主义者对网络传播的热情,宗教通过网络聚集移民,被 Innis-Ong认为是“第二个口语空间”(the secondary orality of cyberspace)[8]的网络而可能产生的革命性的转变。Stephen Jacobs注意到,在涂尔干主义的意义上,有可能在互联网上分离出一个特定的空间,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有可能推动虚拟的仪式建构事件,这些虚拟事件在一个解释学意义上的对话/游戏里将(无实体的)人、(虚拟的)建筑聚集起来。Stephen Jacobs指出,线上的仪式和仪式空间,最初都是模仿线下的情形而建构的。Stephen Jacobs发现,无论是虚拟神殿还是虚拟教堂,两者“在其设计上都是如此地传统”。他认为,事实上它们必须这样,如果它们想用其参与者所企盼的、所要求的方式去成功地传播其内容。
Mark W.McWilliams认为,虚拟朝圣之旅的未来有四个特征:创造一个已经消失了的神圣之地;创造一个互动的礼拜媒介;为旅行者提供一种娱乐形式;提供一个虚拟旅行社区。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气息”,那种神秘的心理意象。“现实中,朝圣之旅的地点如果真的有,也很少,很原始,在当今也早被丢在一边了,人们不得不借助想像去感受一些东西。各种图解、图片、故事都被用来填充这种叙述,即使面对面的现实中的朝圣之旅也需要这样。”[6]223-238新的媒介能将光、声和文本结合起来,通过激发“真实”的感觉来增加虚拟朝圣之旅的灵性价值。很明显,这种虚拟的朝圣旅行并没有真实旅行那样费劲,太快,一般也没有什么痛苦。那种公共感觉当然也不同于那种现实中面对面的,对于很多旅行者来说,那种虚拟的“真实”感觉也是假的。
对于网络宗教传播而言,博客代表了一个有着特别兴趣的场所。Cheong,Pauline Hope根据对一些博主的采访,对 200个提到基督教话题的博客主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博客为教徒提供了一个交流经历的场所,不是异于私人和公共空间的第三空间,而是一个混合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混合了神圣和罪恶的地方”。[9]当信教的博主将他们的博客同那些主流的新闻网站、非教徒的博客、其他的如维基百科一类的在线合作的知识网络链接起来时,他们就启动了不同于传统的以教堂为中心的活动领域。通过记录他们自己生活中每天的信仰经历,这些博主不仅是在同他们的社区或更大范围的公众交流,也是在自我交流。这种将博客作为一种对日常经历的宗教沉思的态度,不同于那种流行的将博客视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态度。
四、网络传播与基督教的矛盾态度
网络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一把双刃剑。关于网络宗教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极端组织会利用新的媒介招募新成员,不仅会从传统宗教组织中吸走成员,可能还会捕捉那些有时并不情愿的人,强迫他们从事消极的事情。针对“网络对崇拜或崇拜之间的纳新来说是不是太肥沃了”,Lome L.Dawson等人调查了30个新的宗教运动网页,发现广告、促销和提供关于各种群体的信息是网络主要功能之一。那些卷入的人,没必要非得是软弱的、有需求的、太木呆的、社会孤立的。也许只是他们太技术化了,因而社会接触对他们来说才是关键。加入者也许有兴趣了,因为网络环境既是新的 /进步的,又较少那些传统宗教群体里的关于地位和阶级的装饰。比起其他的“广播”媒介,在网上发布信息和从事活动,代价并不贵(又容易使用)。“网络也许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环境,而不仅是一个工具;它从整体上改变了社会和机遇。”[6]151-173宗教很可能从一个机构变成了一个文化资源。网络打破了许多障碍提供了一个网络环境,宗教在这里可通过一种传统里不允许的方式繁荣起来。然而,网络不可能对宗教只是有利,它已被商品化了,它撕毁了传统而不是以一种对等的正当的东西代替传统,这可能对宗教有害,一些新的网络宗教社区看起来更像是在游戏而不是奉献。
英国国教信徒认可一种更加静态的制度上的分级,目的主要在于对移民于网络的抵制。在美国,福音教派在采用和适应新技术来传播他们的信息方面总是最活跃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最初感知到的自我属于被边缘化的少数派——包括最先利用当时的新技术,如电影、广播和电视。
在线宗教仅是宗教的强化而不是改革,一些传统也面临神圣和亵渎的更加紧张的关系,这些都与互联网和网络传播技术相关,因此,网络环境被认为不适合他们的信仰的表达。在那些更可能使用互联网的人对宗教的主张所持的批评性态度和那些信徒对他们的传统的明确的主张所持有的较平和的态度之间会有一种紧张的关系,即在网络使用者和批评性态度之间有一种相关性,将宗教作为网络使用者的批评目标。同样,宗教团体并没有狂热地使用网络。宗教和技术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更有可能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假象,而不是我们原来认为的那种敌对关系。有关研究表明,信徒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大,不大可能采用网络传播技术,那些年轻人,对互联网有一定了解的,又不愿意加入传统的宗教。
坎贝尔进行了“通过结合网络和俱乐部文化、基于分享的努力在 Ibiza岛的青年中布道”[6]107-122的尝试,探讨现代电子媒介能否用来并支持在青年文化中布道。因为 Ibiza岛一些青年视俱乐部文化为一个精神空间,在这精神空间里可以发现他们自己和他人联系,所以在线布道项目尝试既利用面对面、又利用网络资源去在这些青年中布道。这个研究注意到,俱乐部的参与者迷失了他们自己,寻求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身份,参加俱乐部成为一种很好的经历。网络起一个杠杆作用,作为交换和建立社区的空间。坎贝尔认为,在线关系的传播和互动比一些面对面的工作更接近宗教社区的核心;线上传播是植入日常生活的,这一点使得它相当真实;同时,“在线”关心每一个人;“在线”融入了日常生活;“离线”向“在线”的转移正在增加。
五、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权威的多重难题
传播的变革总是倾向于质疑权威,在宗教实践领域尤其真实。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而言,他们反对某个人拥有解释“词”的权力。当信息被媒介改变的时候,这种异见最突出。网络的一个最大承诺是提供巨量的信息。问题是,这些信息及其供应者的准确与可信性。网络提供了巨量信息,也暗示着使用这些信息是正当的,另外,尽管不太可能去印证某人在网络上找到的信息,然而仍有人常在网上寻求宗教的信息,还是有一些方法去证明这些信息的权威性的,比如来自梵蒂冈网站的信息。如果不顾这些信息的有效性和使用者验证其权威性的能力,关于权威性的普遍怀疑就会危及权力关系,当权威再也不能控制信息的数量和内容,这种严紧的镣铐就会放松。
在网络环境中,宗教的权威性和权力的关系是个重点研究领域,主题涉及网上宗教,如仪式、身份、结构、群体等。Dawson很早就将宗教的“控制和权威”作为一个着重考察对象。Barker、Barzali、Cowan等人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有强化或威胁各种宗教群体的权威的潜能。坎贝尔认为需要对宗教权威性在网络环境里所表现出的特性有个更精确的认识,这涉及到权威在层级、结构、意识、文本四个不同层面的区别。
首先是宗教语境中权威的含义。由宗教与互联网相遇而引起的权威问题涉及到要研究权威的多个层面。仅说互联网改变或挑战了宗教的权威是不够的,研究者必须辨明宗教中哪些具体的构成和形式正在被影响,诸如传统宗教的领袖的权力地位、已确立的政策决策系统和成员中传播信息的系统、成员全体的意识形态、正式的宗教辞令和教义的角色及解释,研究互联网上宗教的权威应该辨明这些方面以便于发现是否是宗教的角色、体系、信仰正在受影响。《网络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从 1995年 6月到 2006年 7月有 104篇文章提到权威这个概念,但仅有 Ruggiero的一篇文章对这个术语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即“界定和描绘现实的权力”,来凸显新闻在社会中的角色的重要性。另外 103篇文章对权威主要的使用方式、正式结构、体系或等级有所涉及,此外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权威,如道德权威或与统治相关的“更高的权威”。
韦伯认为,有三种可被认可的“纯粹的合理的权威”:[10]法律的、传统的和神赐的权威。宗教的权威不同于一般的权威,宗教的权威描绘的是一种特殊的合法化的形式,经常有一个神圣的源头。宗教权威的表现形式仍然涉及体系、角色和人格化了的信仰。
对线上宗教和线下宗教的关系的认识经常涉及或推及:权力、权威和控制问题是关系到宗教团体的,在线的活动在信仰和实践方面必然会挑战传统宗教。然而,“权威”的概念作为一个研究宗教在线的主题被明确提出来或重点关注还是最近的事。
C.Hojsgaard主编的论集《宗教和网络》中有几章内容直接涉及到这个与宗教权威相关的主题。Lome L.Dawson强调了宗教权威受到在线宗教活动,尤其是在线“礼拜”挑战的三个领域:被特定的宗教群体的反对者或内部不满者故意误报或无意误报的信息的潜在增殖;宗教组织对宗教资源失控;为底层的证据提供新的机会。这就鼓励了那些相对于传统讨论的非正式的或另外的声音的兴起。Barker,E.关注新的宗教是如何发现正受到兴起的互联网影响的权威结构的。这里的“权威结构”指涉一种“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又关联着一个关系的模式结构,这个关系是:“一个有神授超凡能力的领导者在最顶上,传递信息和命令给副手,副手又相应地传给下一级,直到最底层。”[11]在线论坛可能会破坏这个结构,或者宗教组织也可能反过来出卖这些团体或创建另外的论坛来强化他们已建立的组织结构。这个研究展示了作为一个等级结构中的宗教权威可以并如何应对其成员的网上活动。Herring,D.认为,一个在线基督教团体努力去创建一个团体理论,这一行动又需要他们同基于圣经中对宗教权威的传统观点进行协商。在这个团体中,仲裁者处于核心权威位置,依据它的要求,这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鼓励去服从这个仲裁者,将其作为那个被上帝安排在他们中间以管理社会的“管理权威”。[12]确保这个仲裁者的权威是作为一个工具来使这个团体依据圣经的原则而活动是合法的。Herring,D.的研究强调了宗教的组织和角色在讨论宗教权威时是一个核心。D.Cowan讨论了互联网是如何使个体为了宣称成为一个“异教权威”而建构网络身份成为可能的。这里的“权威”不是被一个官方的团体建立的,而是通过一种专家的公共认可。
基督教网络传播对宗教权威带来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对宗教等级 (公认的宗教或团体的领导的角色与感知)的影响、对宗教组织结构 (团体结构、活动模式或正式的组织)的影响、对宗教意识形态 (共同的信仰、对信仰的想法、共同的身份)的影响、对宗教文本 (公认的教义或如古兰经、圣经等一样的正式的宗教书籍)的影响等。
权威的重点表现为一种角色或组织结构。网络被视为提供信息的工具,链接当地教堂与全球基督教堂共享的历史和共同的实践。这样网络就变成了一个资源,便于或转化使用者对全球网络上信仰社区的理解,这些理解也许会强化或挑战传统的关于宗教结构和意识的观念。网络提供了一个新的更招人喜欢的精神或社会互动的出口。这些对福音派尤其真实,福音派经常提倡网络与教堂的关联,尤其是当地方教堂在某种方式上被认为是有限的时候。自由、控制和新机遇是被牧师这些使用者所重视的价值。同时网络也提供强化传统机构的工具。英国国教教徒将网络视为这样的一个空间,强化了个体和集体对重要问题的沉思,这帮助、便利了传统教会。这样,网络就有了这样的特征,既为传统机构提供支持,又提供了一个批评线下教堂的空间。
坎贝尔认为,在研究宗教和互联网的过程中研究权威问题有必要区分出网络环境中对权威的不同表达,需要清晰地区别出权威在实际使用中的特殊的形式,否则就可能理不清线上、线下宗教团体的复杂关系。在任何对在线权威进行的讨论中,都应区别讨论中所涉及的权威是否是等级制的、是否有组织结构、是否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和文本。
关于宗教的等级,需要更多地去关注互联网上新的宗教角色的出现情况,这就意味着需要去确定并界定在特定的线下宗教团体中传统的宗教角色的特征,需要去考虑在互联网上这些角色是否被传播、改变或排挤掉了。还需要去追问这些问题:网上的仲裁者是否扮演着同线下的牧师相似的角色;网上宗教团体的核心成员或经常发帖者是否扮演者同线下的执事或主教委员会相似的角色;在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是否将这些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线下的宗教形象联系起来了。
关于宗教组织结构,需要去探讨线下正式的组织结构或权威渠道同那些在各种网络论坛上形成的组织结构或权威渠道的关系。这需要关注以下一些问题:仔细描绘权威渠道在网络上如何出现并发挥作用;这些权威的渠道同传统的宗教组织结构有什么联系;宗教组织是否力图以某种方式监控或影响网上宗教团体,这种行为达到了什么程度,又有哪些原因;网上宗教活动的官方政策的正式表述在关注什么;为宗教目的而使用网络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等。
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网络的互动性也许能鼓励新的“全球化”宗教身份的形成的观点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伴随着地方性的观点在全球化论坛里被分享和讨论,关于什么是共同的信仰或什么是宗教团体的特征的理解可能会发生改变。这种对不同观点或宗教信仰的分享也许意味着网络环境能激发对教义新的理解、对具体信仰的重新界定。关于在线谈话团体如何接受、反对、重新界定主流神学或他们的特别的教条,需要做描述性的工作。
关于在线宗教团体及其实践中宗教文本的角色和认知,需要去研究:宗教文本是否继续作为权威的首要来源;这些文本是更加肯定还是更加指责网络;网络上宗教文本所扮演的角色与宗教传统有区别吗;在“推崇”和肯定宗教文本方面网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
Turner,Bryan S.认为,在传统社会里,知识被限定在等级链中,通过这种等级,权威有了合法性。因为大部分人是文盲,宗教的知识是通过口头和仪式的方式传播的。然而网络社会却对传统权威提出了重大挑战,它加速了宗教知识和用品的流动。信息在互联网上全球流动,权威不再具体化,个人仅是信息流上的一个节点。互联网的逻辑是,在系统的任一个点上,控制都不可能长时间地集中,知识被界定仅是临时性的,它是在无数节点间民主产生的。在这样的年代,原则上每一个人都有它自己的位置。结果是,“传统的宗教权威形式持续地遇到挑战和破坏,同时,互联网又为福音传播者、宗教组织和牧师创造了新的机会。然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却是未知的”。[13]因此,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权威理论,在后网络时代重构传统的领袖魅力、传统与法定的理性。
六、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虔诚的正负相关性
尽管关于传播和宗教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公认的宗教传播理论”,[14]然而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发展得更快,其中宗教虔诚被视为人类关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关注点涉及宗教虔诚的社会文化、宗教、传播、组织能力等方面。
Holbert,R.L.研究发现,宗教信徒相比于更多的世俗个体不大喜欢使用技术。世俗化理论也认为宗教与各种大众媒介的使用是负相关的关系,并认为大众媒介突出地反映反宗教的、世俗化的社会观点。仅仅是拥护用世俗化理论对宗教信徒使用 (或缺乏)技术进行解释的研究,尽管很宝贵,但是却失之于考察其他关键性的变量,而这些变量相应的解释能力至少不输于世俗化理论。这种失察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那些提出理论的人没有对更大范围内的宏观的组织结构进行考察。
Greg G.Armfield等人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的观念,如人与上帝的关系,其本质都具有天生的多维性。宗教虔诚涉及个人的信仰、行为及对一个组织系统的承诺。无论在哪里,宗教都会被联想及“人的终极关切、在宇宙观和形而上的背景下提供个人的和社会的身份”。[15]宗教虔诚被认为可以确定教徒间的行为模式。历史上,宗教被称为一个包括个体和制度元素的“宽度建构”。[16]然而,近来的观点却视宗教为“窄度建构”,主要关注宗教的制度元素。这些制度元素被认为是宗教组织的硬性结构,它限制或禁止个体的宗教潜能和灵魂。
如果对宗教虔诚在网络使用中的作用失于觉察,就意味着忽视了对一个意识形态中心(如教堂)的组织承诺、组织领导者的论述能力及他们对聚会需求进行规范的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Greg G.Armfield等人认为,研究者“只有真正地理解了存在于较高的宗教化意识与他们会众之间的组织纽带的粘性本质,才能完整地理解他们对网络技术的使用与满足”。[17]
就如世俗理论所描绘的那样,宗教虔诚在决定使用媒介的各种形式时所扮演的角色,反映了社会认同功能。Ruggerio,T.E.认为,随着新兴媒介传播的兴起,去“理解什么东西正在引导个体去使用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个体能从这种网络传播经验中获得什么,已成为内在的需求”。[18]社会认同功能论显示,个体使用媒介是为了强化一套在获得媒介传播经验之前已存在的价值观。有些人认为这种对媒介的需求,有其社会学的基础,有心理学的或个体的对期待价值的评估的动力。尽管社会认同功能的本质尚不清晰,然而,世俗主义理论家能预期个体宗教虔诚与网络使用之间的负相关特征,这其中的一个清晰的原因是: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了更加世俗化的世界观。这种媒介传播并没有承担那些教徒的个体认同功能。
Armfield,G.G.的研究发现,那些说自己的宗教虔诚度较高的网络使用者,对网络的使用少于那些宗教虔诚度较低的。然而,教徒个人使用网络,宗教虔诚度仅是一个独特的因素,所以研究者仍然不确定宗教虔诚度与网络使用的关系的本质,相应地,也无法确定使用网络的教徒是为了满足什么需求。所以,Armfield,G.G.的研究表明,在高度宗教化的群体中,三个要素构成了测量个体宗教虔诚度的可靠尺度:承诺、信仰和行为。对宗教个体来说,使用网络最多的是娱乐、交友、逃避和互动。宗教虔诚度和使用网络之间的关系由于太复杂,仅据一时的研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其关系涉及宗教信仰与媒介的娱乐功能之间的关系。
Armfield,G.G.认为,影响教徒的媒介选择的可能是教堂结构中的组织现象。这种现象可用宗教虔诚的“窄度建构”来解释,这种结构主要聚焦于教堂对个体的信仰和行为的限制。这种宗教组织的结构通常驻留在神职人员的论述能力中。神职人员的权力的主题,在宗教研究中是一个发展不充分的概念,相关的讨论一般聚焦在压抑性影响上,这种影响指的是教堂 (一个有信仰的个体的组合)的集体力量在执行基督的使命时所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能确认并直接将神职人员关于使用媒介的态度同会众对网络的使用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对存在于布道坛和教堂座位间的论述能力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当这个概念运用到宗教组织的独特结构中时,这个洞察就能鼓励研究组织权力的学者去理解这个概念的关联体。
世俗理论认为,宗教与各种大众媒介所存在的联系都是负相关,因为宗教认为所有的大众媒介都在反映反宗教的、世俗主义的社会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徒不使用网络。宗教虔诚度、世俗化、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对这个现象的再研究,应该去探讨个体的宗教虔诚、世俗态度如何影响大众媒介的使用。
七、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修辞策略
世俗世界后现代生活的特征是被私人的、反思自主的个体所界定的,他们重新发现了社会和文化中的宗教和精神维度。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重新迷惑,它更可能是立场、身份、媒体经历之间的协商过程,用一种好玩的、探索的方式来融合媒体和精神的过程。坎贝尔总结了近十年来关于网络使用和宗教研究的九个主题:神学 /灵性,宗教,道德 /伦理 ,实践 ,宗教传统 ,社区 ,身份 ,强势 (力量),网上仪式。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新媒体是如何影响宗教的。这种网络决定论强调技术在以下方面的能力:介入精神;默许传统的敬仰;改变宗教的表达;给创建宗教社区带来利益和挑战。
Stephen D.O’Leary考察了语言的述行本质。在天主教传统里,“词”(the Word)是上帝的,其用法构成了真实;在新教中,“词”仍是上帝的,但已被象征性地使用。网上宗教的媒介化传播实践再一次证明,语言被用来创造一个真实的空间,去进行赞美和举行仪式。O’Leary最主要的洞见是:依靠转换到媒介化的语言形式,对传统实践的调整反映了先前对传统宗教实践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挑战了传统的形式。
1996年夏天,邪教组织“天堂之门”在世界新闻组网络上发出多边性的邮件,试着去寻找会加入他们的精神社区的人。但是,他们没能得到大量的受众,也没能通过网络新闻组找到新会员。Robert Glenn Howard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邮件没有同新闻组讨论所特有的“协商性”修辞策略相一致——协商性修辞策略鼓励反馈,意味着态度的多元化。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天堂之门”1996年的新闻组邮件表明:那些相信他们自己已得到特定知识的个体可以忽略多元化媒介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信仰允许他们去追求一种不同于那些大多数与多元化媒介保持一致的人的价值。这种水平上的修辞门槛暗示了一种潜在的危险的反社会行为。
“天堂之门”的邮件没能实现招募目标的修辞学原因在于,他们的邮件中所展现的那种对一种特殊的启示经历的重视——这种启示经历是唯一的能发现经历者体内有他们所相信的多维存在的途径,这种启示经历能强大到足以说服经历者为摆脱现有躯壳去追求那种灵魂的存在而自杀——使他们忽视网络新闻组能吸引更多受众的那种协商性修辞策略,而采用一种极端的自闭的修辞性语境策略;同时,一个理性的人要加入一个宽容性的宗教群体的目的,是为了分享一种社会经历——一种给他们带来巨大影响的心灵历程——这一点与网络新闻组的语境特征吻合。正是这种冲突致使天堂之门在新闻组里得到的反馈不多,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反馈是抵触它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邮件发送者本来就没有寻求新闻组交流中可持续性的好处。一是这个组织里的确有人善于使用正常的新闻组讨论方法,当需要使用正常的协商性修辞策略说服受众时,他们运用了这种方法;二是所有的“天堂之门”的成员都相当精通网络的使用技术,他们能很专业地建设网站。因此,邮件的发送者一定相当清楚他们的信息不会有大量受众。
Robert Glenn Howard认为,为了一种信仰而放弃生命,是很少见的。那需要一种如此强大的对必然性的感知,以致可以克服对未知的恐惧。在 1997年,宗教性的自杀行为几乎还没有同危机研究联系起来,但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情况变了。伴随着自杀,潜在的暴力行为出现了,因为支持这两者的那种对必然性的感知水平已经超越了任何社会、逻辑或理想对话了。Robert提出,在人们会更重视对话的全球传播时代,那种对会话的抵触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在全球化传播时代,宗教学者会问什么样的交流行为同自杀相联系。在“天堂之门”的例子中,自杀是同一种近乎绝对地轻视可持续性交流相联系的。无论是自杀还是独白式的修辞,都暗示了一种极端的反社会行为,既轻视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也轻视个体自己的生活。这些修辞策略也许暗示了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群体。
2006年,Robert Glenn Howard又以“启示录基督徒谈话”[19]为例,对可持续的修辞策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Robert认为,“启示录基督徒谈话”在网络环境中具有很好的可持续性,一个确定的原因是那种争论的规范植根于极深的叙述可塑性。因为界定这类谈话的权威性的圣经文本和解释性的叙述展现出了极大的弹性,新的事件能被迅速地同化进这种叙述结构。同时,允许谈话具有可持续性的这个特性,也使得谈话绝缘于那些必要的有分歧的观点,而正是这种分歧性的观点孕育了更多的建设性的公共观念。问题至少应该涉及:在宗教传播中什么样的宗教传播行为同公共协商的健谈模式相关,什么样的传播行为鼓励健谈模式的公民接触,特定的媒介是如何鼓励或阻碍这种行为的,网络传播在原已存在的基督徒谈话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
已有的研究表明,参加传统的自闭型谈话的正统基督徒,在他们的网上谈话中已采取了更多的“开放性修辞风格”。[20]推动这种行为模式的一个因素也许是对作为使用网络媒体的主要优点的可持续性资源的认知。
在线谈话,像传统的谈话一样,必须支持将资源转化成价值利益的社会进程。一个可持续性谈话是有适应性、对新想法的开放。参与这样的谈话,应该重视和支持新声音的加入,新的声音也应该产生新的、不同的想法。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谈话应该凭借其通过产生新想法来解决争论的能力来证明它的可适应性。
在线讨论主要是那些表现为随意建构的混合物的内容的频繁交换,比如 UFO信仰、阴谋理论、基督教神学等。无论他们的预言结果如何,这个谈话的中心价值都没有被质疑,原因很简单,他们从来没有确定过。
在大部分乐观派研究者看来,不同思想的杂居可能带来一种网络上的多元化道义。只要讨论被坚持下去,那些我们日常所持的固执偏见就可能被软化甚至消失。社区通过讨论来想像它们自己。从修辞学观点来看,这种想像是一个生成符号的行为。
八、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身份建构
在理解网络技术在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领域已有很大进步,日渐增多的网络使用加速了网民身份的形成。Mia Loveheim发现“自我身份的力量总是同线下实践结合在一起的”。[6]59-73网上,有更多的刺激——可参考的范围更广的信息——和对刺激质量的迷惑,因为个人所接受的关于身份形成的信息的价值已经被分类了。尽管这样,先前的传统宗教的稳定的力量已经被动摇了。青年是变化着的,既是宗教力量的目标,也是商业力量的目标。
Mia Loveheim描述了网络能强化身份建构的四种途径:网络提供同媒介化了的经验进行积极协商的机会;通过更多的信息访问,网络利于重估知识和技能;揭示差异以帮助使用者磨练他们的自我表达;传授处理危机、冲突、情况的新方法。对非传统者来说,尽管网络是个好的信息资源,但是考虑到他们将会遇到的惊人多样化的观点,网络更是一个问题窝 (problematic place)。Mia Loveheim认为,网络为青年宗教身份的形成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对青年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环境,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支持和挑战,也失去了传统约束的稳定性。线上线下,两个宗教环境的混合,对身份形成,并不总是有清晰的结果。
Mia Loveheim认为,宗教变成了一个网络文化资源——严控的组织化中释放出来的文化资源;很明显,网络和其他的电子资源有利于这种释放。青年正在努力适应这些给他们的生活和身份以意义的经历,有时使用传统资源,但是更多时候努力融入流行文化,一如独立的感觉融入他们的追求。网络提供的对宗教更多的选择性,使得青年的世界更加不安全,同时,又提供更多样性的选择以便他们能发现自己的真正需求。就如提供给宗教的一样,网络提供给身份形成的也是一个不明确的领域。
九、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价值的影响方式
宗教和媒介不再是可以相互清晰区分开的领域,神圣和世俗间的区分也不是那么严格了,依据传播观念,两者可以视为都活动在宗教和媒体中。另一条变得更模糊的分界线是直接和间接经验之间的界线,关于宗教有可信的形式和实践的主张也受到了挑战并变得日益模糊。J.Hayles的研究的“闪现意义”让我们重新思考媒介环境中真实性的问题,尤其是其突出了符号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强迫性互动,而正是这些符号和意义正在将当代美国文化中的英雄和圣徒特征化。
Mychal Judge被作为英雄和圣徒,在他转变为一个虚拟符号的过程中,这一符号的存在和意义依赖于这个网络社区参与者的约定。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闪现意义之时,即关于性别和国家身份的充满争议的记忆正在日益增多的在线宗教和文化领域中被协商,我们就会去关注这些流动中的符号的不稳定性及其仍然强大的影响。
人类的信息学总是通过各种思考来适应崭新的社会科技环境。“互联网精神”(spirit of the Internet)指涉人类与我们所造出的最大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个人的、社会的、哲学的、宗教的关系。作为人类,我们通过各类方式与大众传播技术发生关系,在那些已被认可的宗教在线和在线宗教的区别的基础之上,人类的信息成了我们对于互联网来说唯一的价值象征,成了引导古代宗教信仰到达一个网络宗教的动力。
当谈到互联网的“软面”即人的一面时,主要是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规范和管理,一是表达自由和私人空间的独立性。Christo Lombaard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互联网使用者来说,为了网络伦理而去思考对与错、正义和非正义,已经成为一种规则,这“也许取决于我们书写和发送信息的时代的结束”。[21]与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数字化群体关系的道德相呼应,“为将来负责”变成网络道德的重要内容。
互联网不仅是机器意义上的文化复制品,也是我们使用它的途径。事实上,“互联网是一个技术”,它也是个成熟的文化动力,甚至能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个人和组织对互联网的最早的接受与环境有极大关系。
从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这点来看,我们自己也信息化了。决定我们的价值的,不是我们是谁,而是对其他互联网使用者来说我们是什么信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得到使我们彻底智慧化的知识。信息,也是知识,能让我们获得自由;网络信息可以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
互联网作为媒介的信息,与其说提供了答案,不如说提出了问题。比如说,对正义、善和信赖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对于非正义、恶和虚伪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对分析和理解这些情况它又意味着什么。Christo Lombaard认为,“对于互联网的神学的和宗教的可信态度,不是寻找——幻想的——共享价值,或者——假想的——权威,而是在互联网上发展出一种可信的存在,让实在存在的在互联网上具有可接受性”。[22]对互联网的一种特殊的宗教的态度,不应该是为了传播宗教信息而使用这个媒介,也不应该将互联网本身视为宗教的一种启示形式。而应该是为了看、听、接触正在发生的一切而融入互联网。
Todd S.Frobish认为基督教科学派向网络移民,“不是为了接触新的追随者,而是为了应付其线下的信誉的问题”。[23]基督教科学派是一个自封的宗教,坚持寻求来自政府、媒体和批评者的正统性认可。正是这些特征,引起了宗教向网络移民的一些问题,如当以适应或以日益增加的网络上的信徒为目标时,纳新和维持传统的信徒的问题等。Todd S.Frobish提出了建构网络道义的解决方法:“任何宗教组织可通过现实化、实践和自由结社建构社区道义。首先,它可以论证性地实施这些宗教道义,换句话说,为它的受众而执行。它是一种言说 (linguistic action)的道义。”
现在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通过控制信息内容可以维护或控制被接收的价值观,同时将那些不一致的信息描绘成是对一定价值体系的威胁。但是现在的互联网络,凭借它无限的人和资源网络,提供了一种分享海量的不一致信息的可能性。当信息相互冲突时,就会引起一种不稳定、一种不和谐、一种紧张,导致自己对信仰体系的不满。
Zehavit Gross通过讨论两个创新模式研究了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在增强宗教身份和社会化方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24]两个创新模式分别是:“宗教——世俗类型模式”(religious-secular typological model,即RST M),“学习过程和身份形成”模式 (Knowledge processing and identity formation,即 KPIF)。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精神维度,需要通过一种宗教或世俗的方式表现出来。基于此,Zehavit Gross假设:同一个班里的学生可能存在不同的宗教或世俗的身份,具有多元化特征,传统的一元化的精神结构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已经与大部分人不大相关了,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也不太现实了。为了满足每一个学生的特殊的精神需求,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利用先进的信息和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即ICT),因为它涉及广阔的范围,提供多元化的信息。要理解每个学生的唯一的精神特征,需要运用语义分析的工具去精确地刻画它,Zehavit Gross提出了一个界定宗教虔诚度和世俗化程度的模型,即“宗教——世俗类型模式”。但是,鼓励宗教和世俗的精神,不仅涉及认知还涉及影响的范畴。一种价值观如何被授予教育最重要的元价值就是认同独特的身份特征和行为榜样。但问题是信息传播技术 (ICT)的使用能激励认同吗?Zehavit Gross的观点是,现代化的互动特征的信息传播技术和网络,通过视频会议、数字视频、电子邮件的方式使远程学习和一对一、一对多的传播结构成为可能,能够作为同法师、牧师、阿訇之类的行为榜样直接交流的工具,关于他们个人生活的、对他们的采访的电影能帮助学生去理解他们所代表的传统的不同方面。
精神(宗教或世俗)经历可以通过下面三种方式得到发展——社会的、情感的和认知的——所有这三种都通过信息传播技术获得。社会协商: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性建构,通过邮件、互动视频和聊天室,学生能和其同辈一同交换分享信息,能建构知识,协商意义并对其进行反思。情感激励: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包括能激起情感反应的电影、远程演讲、虚拟现实系统 (通过网络上的论坛和聊天室接触)。认知启迪:学生能通过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浏览无限的资源,接触和吸收新的信息,建立一种知识链,导向对问题进行更宽广视野下的理解。通过这个方法,信息转为知识。所有这三种方式——社会的、情感的和认知的,都是个体意义获得过程的重要构成,这是身份建构过程的一个关键阶段。宗教和精神教育,只有当它适应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或世俗类型的受众的需求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1]Schement J R,Stephenson H C.Religion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C]//J M Buddenbaum,D A Stout.Religion and Media Use:A Review of the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Literature.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80:261.
[2]Dart J.Connected Congregations:Church Web Sites[J].Christian Century,2001,118,(5):6-7.
[3]Todd S Frobish.The Virtual Vatican:A Case Study Regarding Online Etho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n,2006,29,(3):38-69.
[4]Brasher B.Give Me that Online Religion[M].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1:3.
[5]CantoniLorenzo.The Use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by Catholic Congregations:A Quantitative Study[J].Journal of Media&Religion,2007,6,(4):291-309.
[6]Lome L Dawson,Douglas E Cowan.Religion Online:Finding Faith on the Internet[C]//New York:Routledge,2004.
[7]Cheong Pauline Hope.(Re)structuring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Capital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J].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2008,11(1):89-110.
[8]Ong W.Orality and Literacy: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M].London:Routledge,1988:135-188.
[9]Cheong Pauline Hope.The Chronicles of Me:UnderstandingBlogging as a Religious Practice[J].Journal of Media&Religion,2008,7,(3):107-131.
[10]WeberM.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328.
[11]Barker E.Crossing the Boundary:New Challenges to ReligiousAuthority and Control as a Consequence of Access to the Internet[C]//M Hojsgaard,M Warburg.Religion and Cyberspace.London:Routledge,2005:67-85.
[12]Herring D.Virtual as Contextual:A NetNews Theology[C]//L Dawson,D Cowan.Religion and Cyberspace.London: Routledge,2005:149-165.
[13]Turner Bryan S.Religious Authority and the New Media[J].Theory,Culture&Society,2007,24,(2):117-134.
[14]Buddenbaum J M.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Media and Religion:Going Forward by Looking Backward[J].Journal of Media and Religion,2002,(1):13-24.
[15]Hill E C,Hood R W.Measures of Religiosity[M].PC Hill: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1999:269.
[16]Pargament K.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Yes and No[J]. International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1999,(9):3-16.
[17]Armfield G,Holbert R 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sity and Internet Use[J].Journal of Media and Religion,2003,(2):129-144.
[18]Ruggerio T E.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in the 21’Century[J].Mass Communication&Society,2000,(3):3-38.
[19]Robert Glenn Howard.Sustainability and Narrative Plasticity in Online Apocalyptic Discourse After September 11,2001[J].Journal ofMedia and Religion,2006,5,(1):25-47.
[20]Howard R G.On-line Ethnography of DispensationalistDiscourse:Revealed VersusNegotiated Truth[C]//D Cowan,J K Hadden.Religion on the Internet.New York:Elsevier,2000:225.
[21]Christo Lombaard.Thinking Through the Spirited Web:Some Clarifcations on the Internet and Embodied Experiences Thereof[J].Communitcatio,2007,33,(2):1-10.
[22]Lombaard C.Afrikaans,reformed and Internetted:SomeOutlinesof CurrentAfrikaans-Espiritualities[J].Studia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2006,32,(1):247-261.
[23]Todd S Frobish.Altar Rhetoric and Online Performance:Scientology,Ethos,and the World Wide Web[J].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2000,4(1):1-1.
[24]Zehavit Gross.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Spiritual Identity via ICT[J].EducationalMedia International,2006,43(1):51-63.
Abstract:Although the usage of the earliest religious network can trace back to 1980s,it is in 1995 that the research for religion online wasmade,which chiefly studies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of Christianity.A-mong itsmain studymethods,there were sampling and statistics,content analysis,quantity contrast,field survey,interview,etc.The concerned front issue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nine aspects:the instrumental space of the Christian network communication;the organizational 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network;the internet immigrant of Christianity;The Christian resistanc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Christia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us authority;Christia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us piety;Christia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us rhetoric;Christia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us identity;Christia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us value.All these studies,by a contrast of online religion and off-line religion,hold that the problems such aspower,authority and control have influenced the kernel benefit and kernel value,and that online activity is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 both in faith and in practice.
Key words:religion;Christianity;internet communication;religion and society
(责任编辑:周成璐)
The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Internet Communic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
XU Zheng-lin,JIA Bing
(School of Film-Television Art and Technology,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072,China)
B911
A
1007-6522(2010)06-0069-16
2010-05-10
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项目(09BZJ011);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8JA860011)
许正林(1958- ),男,湖北沙市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