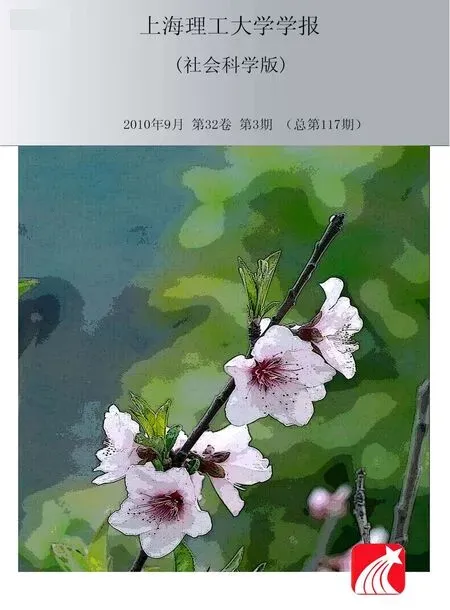透过《离骚》看屈原的悲剧意识
刘 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透过《离骚》看屈原的悲剧意识
刘 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屈原是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是中国悲剧意识的象征。《离骚》作为屈原的血泪之作,蕴含着诗人强烈的悲剧意识。其中现实与幻想的结合、现实与先贤的对比的表现手法更赋予了其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以鲜活的艺术生命力。而将屈原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进行对比时,所折射出的正是中华民族历来传承的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屈原;悲剧意识;表现手法;文化对比
引 言
屈原是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著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其中《离骚》与《诗经》并称“风骚”,在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离骚》不但文辞绚烂,想象丰富,并且凝聚了屈原思想的精华,是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屈原悲剧意识的某些痕迹。
一、悲剧意识的几个层面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忧国忧民而不为世所容,追求崇高的理想却难以实现。在离骚中他把强烈的悲剧意识与忧患意识融为一体,并将其展现为以下几个层次:
1. 自身与社会的不相容
屈原很讲究自身人格的修养。他把自己显赫的家世,高贵甚至有些神秘的出身归结为“内美”(内在的美质),同时他也注重外在的修养,所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当时的楚国,已由强盛转向衰微,但统治阶级仍然纵欲淫乐。在屈原眼中,世人也只知竟相钻营,贪得无厌,追求名利,而不在乎个人的修身养性,甚而把臭草当作香花,自己的弟子也随波逐流。正是“世溷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整个社会风气与他高洁的性情格格不入,诗人痛心之极。鲁迅先生在描述麻木的国民性时有这样一个比喻,一间不透风的铁屋子中,所有人都可能在睡梦中安然死去。此时却有一个人独醒,他感到窒息、痛苦,振臂一呼,并不应者云集。这也正是屈原的悲哀,他便是那独醒之人,深深地感到内心的悲哀与孤独,但他并未因此而“变心以从俗”(《涉江》)。而是在绝世独立、横而不流中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直至生命之终。
2. 政治抱负的无法实现
屈原对于内美和外美的追求,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心理文化背景。先秦诸子,无论是老庄,还是孔墨孟荀,他们无不注重修身——自身的精神修养和锻炼,以期为世所用,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老子谈到“善建”、“善抱”之道时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他把修之于身作为修国、修天下的起点和前提。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尤其重视修身。孟子便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生活于战国末期的屈原,必然受到这些思想的熏陶。他要求自身人格的完善,也正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当时,秦国采用张横“连横”之术,以图统一天下。这严重威胁到楚国的统治。屈原赞成“合纵”,愿为“王道夫先路”,并希望通过修明法度,改革流弊,在楚国实现“美政”,使楚国强大起来。但是楚王却宠信郑袖、上官大夫等一班人,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并不采纳屈原的主张,甚而将其流放。屈原在这时无法求得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但他并不象儒家一样吟唱着“乐道”、“忧道”、“守道”的三步曲,即“夫遇治而赞之,则谓之乐道;遭乱世而救之,则谓之忧道;乱不可救而避之,则谓之守道。”屈原则只是忧道,乱不可救也要救之,知其不可为也要为之。诗中不断吟咏他的“忧心”、“愁心”,显示了比儒家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展示了诗人无尽的悲哀。
3. 不愿去国远游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常周游列国,寻找知人善用的明君,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对于屈原来讲,既然不能施展他的横溢才华,远大抱负,他为什么不顺应时代潮流,离开楚国去寻找他的知音呢?这其中恐怕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与楚人突出的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忧分不开。在楚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楚人的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之中顽强地图生存,在穷乡僻壤中不懈地求发展。由此,养成了楚人强烈的民族利益至上的心理。其次,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家庭,是楚王室的后裔。他以此为荣,认为这是其“内美”的一面。因而从情感上而言,他很难割舍内心的牵挂。他的“忧心”、“愁心”也是为楚国、楚王而忧而愁。即便他也想率领庞大的车队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下升腾离去,但他终究不忍去国远游,而是留在“祖国”苦苦的挣扎。表面上,这是政治的不得志,实质上却是心灵的哭泣。这也导致了屈原最终的悲剧。
二、屈原悲剧意识在离骚中的表现手法
战国时代,学术繁荣,哲学勃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自由活跃的氛围为文学的产生与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诗经衰微,离骚勃起”(《文心雕龙·辩骚》)。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家的第一人,出现在文学史中。作为文学家,在创作中,他必然不会只满足于孔子的“文质彬彬”说,他将自己的情感、主体意识融入于作品中,并通过诗歌展现了个性。尤其是在《离骚》中,诗人更是运用各种表现手法,表达了他的悲哀。
首先,诗人将现实与幻想结合在一起,通过神奇壮丽、想象奇特的神话传说,赋予了其悲剧意识以鲜活的艺术生命力。
诗中神话传说的巧妙运用并不是偶然的,这与屈原所处的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楚立国于西周早期,在春秋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到春秋中晚期,楚国已基本进入封建社会。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历史断层。同时从地域上看楚国在今湖北、湖南一带,这一地区山川相缪 ,夷夏交接,是神话产生的沃土。在上述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影响下,楚国强盛起来以后,从典章制度到风土人情,无不参差斑驳。蒙昧与文明,自由与专制,乃至神与人,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社会色彩比北方丰富,生活节奏比北方欢快,思想作风比北方开放,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就形成了活泼奔放的风格,而奔放活泼的极点便是怪诞以至虚无。在屈原的时代,楚文化中,巫术宗教仍然存在,所以,屈原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诗中运用神话的表现手法便是自然的了。
在《离骚》一开头,诗人先把自己描述为赫赫大神高阳的儿孙,并给自己的出生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把神性、仙性与个性统一于自身。这时,他踌躇满志、满心欢喜,然而随着他驾龙车,乘飞马飞升于天上,他的悲愤,苦闷便溢于言表了。天上与人间一样无是非可言,一样悲告无门。他欲见天帝,天帝不见,转而求女,然而知音难觅。他一片热情与希望到了天上也不被理解,天上实为人间补充性的再现。诗人所面临的现实之黑暗程度与当时心情的沉重可见一斑。
其次,诗人通过现实与先贤的对比,表现了忧国忧民的强烈忧患意识。
中国历来都存在着“逆向”思维,推崇圣贤,所谓“沿圣以垂文”。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更主张“法先王”。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中,屈原也摆脱不了这种思维。在《离骚》中,他把怀王与楚三王加以对照,说明自己欲成楚三王的业绩,而所遇国君却目光短浅,根本无此大志。接着又陈述了圣贤之君美政的典范和昏君亡国的教训,对比现实,他更感到怀王的昏聩和国运的不济,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在此心境下,他只能“就重华而陈辞”,以追求心灵的安慰。这样,屈原的悲剧意识中,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哀叹,更蕴含着对国家,对民生的忧患。
三、屈原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的对比
屈原是一位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他的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我们不妨将贯穿于他诗篇中的悲剧意识放到世界范围内加以比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国,农业文化的特点极为突出。战国时,儒家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屈原的思想中也有着儒家思想的痕迹。他的悲剧意识也是建立在忧国忧民的基础之上的。在《离骚》中,他不但悲叹个人的命运,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而在基本上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中,商业文化的色彩极为厚重。人民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在诗人、戏剧家们的笔下,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们,敢于冒险,英勇无比。但他们的勇敢冒险,并非为了民族的公益,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为了取得王位,为了获得爱情,为了复仇。他们的悲剧也只是个人的悲剧。
同时,农业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们思想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中国的宗教法制社会中 ,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反对人们越礼纵欲,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他们把生存价值理想,都寄托于高高在上的帝王。哪怕象屈原这样一位在中国来说,已极富反叛精神的诗人,也只是悲则悲矣,怨则怨矣,却绝不会想到废黜君主,取而代之。然而在西方开放的商业文化中,人们敢于冒险创新。亚里士多德就公然敢于反对自己的老师柏拉图的文艺理论。因而西方的悲剧人物都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们敢于挑战命运,甚至愤而造反。他们悲就悲得肝胆俱裂,荡气回肠,难怪西方人将悲剧与崇高并列。于是乎将梦境的崇高和醉境的狂欢融为一体的古希腊悲剧中,充满着个性的张扬和激情的宣泄。中国文学也有着“以悲为美”的古典审美传统,但却历来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中和,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含蓄蕴籍的风格。因而可以这样说,中国古文学中不存在悲剧,要有也只是作品中蕴含的悲剧意识,较之古希腊的悲剧而言,屈原的悲剧意识也只是素淡含蓄的了。
结 语
正所谓“悲愤出诗人”。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以《诗经》、《楚辞》为发端,直至古典文学终结,忧患的情绪,悲剧的意识,始终贯穿始末。刘鹗就曾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这种“哭泣”的后面,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努力,是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正折射出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
[1]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赵逵夫. 屈骚探幽.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3]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张亚明. 楚文化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 尼采. 周国平译. 悲剧的诞生. 北京:三联书店, 1986
The Research on Qu Yuan’s Tragic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in lisao
Liu Yua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200093)
Qu Yuan, the great poet of China, is the symbol of the Chinese tragic consciousness. Lisao, as the poet’s greatest work, combines the reality and the fantasy, compares the reality then and the former Saints, thus reflects several levels of his intense tragic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contrast of Qu Yuan’s and the Western tragic consciousness, what we can see clearly i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concerning the people and serving the country,
Qu Yuan;tragic consciousness;method of expression;cultural contr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