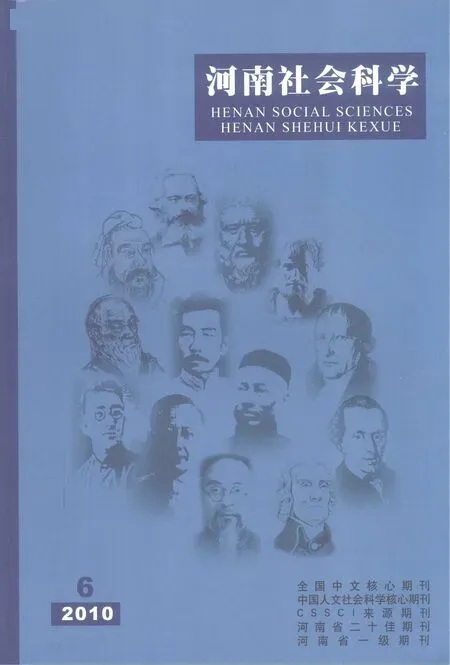论宋濂入仕明朝前的古文观及仕隐观
——当前宋濂研究二热点新探
王魁星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论宋濂入仕明朝前的古文观及仕隐观
——当前宋濂研究二热点新探
王魁星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在入仕明朝之前,宋濂的古文观念经历了由师法司马迁、班固到以六经为本、司马迁及班固为辅的转变,这为他在入仕明朝后向文道合一观念的演进起到了桥梁作用。其古文观念的转变与元代科举程式、婺州理学风尚及师长影响密切相关。得君行道始终是宋濂的政治理想,拒绝元朝之聘、入仙华山为道是他早年所固守的必待君王礼遇才肯出仕观念的集中体现,十年后接受朱元璋之聘则是该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这一变化是岁月虚掷、战乱日益加剧共同作用的产物。
宋濂;入明前;古文观;仕隐观;转变
入仕明朝之前,宋濂的思想观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对于这一变化,宋濂本人也有深刻的认识,并在《赠梁建中序》中进行了比较、总结。因而,从发展的视角对宋濂思想心态进行考察,无疑对全面认识宋濂其人其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截至目前,学界对宋濂古文观念的研究却主要聚焦在他入仕明朝后这一阶段的分析上,对他在元朝时期古文观念的发展流变则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此同时,诸多研究者对宋濂仕隐心态的认识也存在分歧。本文拟对此二问题作一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古文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宋濂早年的古文观念是变化发展的。最初,他以《史记》和《汉书》等秦汉史籍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后来逐步向以六经为本,以司马迁、班固(以下简称迁固)为辅的观念转变。从宋濂现存的相关序文及师友间交往的书信,我们可以大致窥见这两种观念的演变轨迹。在《赠梁建中序》中,宋濂这样概括自己早年的思想历程:
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毁笔砚,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1]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从30岁开始,宋濂在心态上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就总体而言,大致由沉溺于古文辞逐步向以明道为务转变。古文辞即古文,是秦汉之文及后代以此作为学习对象的复古之作。而宋濂早年所沉溺的古文辞却有着更为具体的对象,即把学习重点限定在司马迁、班固之文上。对于这一点,他的师友们也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如陈樵在给宋濂的回信中就指出:“辱惠家范,阅家传,知景濂看《史记》《前汉》精熟,不止词赋赡丽而已。”[1《]家范》为宋濂27岁前后参与编纂的郑氏义门的治家规范,那么,该书信当作于《家范》成书后不久,即在宋濂27岁左右所作。此外,在至正十年或次年,即宋濂41岁或42岁时①,他的老师黄在给他的书信中也指出:“辱下询作文专法《史》《汉》,何足以语此?”[1]因而,宋濂早年把《史记》和《汉书》作为自己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但对于该观念转变的确切时间,却又很难作截然划分。大约在30岁前后,宋濂就已开始向以六经为本、迁固为辅的观念演进了。《华川书舍记》②是宋濂古文观念转变的一个信号:
独荀况氏粗知先王之学……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1]
宋濂在该文中已明确指出,迁固等人之文是“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只有孟子、周敦颐、二程和朱熹才是真正理解圣人之文的人。40岁前后所作的《太乙玄征记》③,是该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玄征记》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讲述了宋濂最初学习司马迁、董生、扬雄、司马相如和韩愈等人之文达到了“一日不治,若芒刺肌”[1]的痴狂状态,但太乙却告诉他,“史迁诸子”[1]仅是“葩叶”[1],六经才是“根”[1],才应成为作文师法的对象。而作者的文章也正是在太乙的指引下取得了进步。入仕明朝后,宋濂的文学观念进一步向宗经、征圣方面演进,但仍会流露出对迁固的偏爱,如《〈吴潍州〉序》:“唐子西云:‘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班固。六经不可学,学文者舍迁、固将奚取法?’呜呼,斯言至矣。”[1]紧接着,他极力赞赏了迁固之文高超的艺术成就。虽然该序文的落脚点是劝诫吴德基不要局限于唐子西之言,更应向六经学习,但对迁固之文的充分肯定也说明宋濂对二家之文确曾有过深入的研究。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宋濂的古文观念虽在30岁前后就发生了变化,但在40岁以后,他对早年师法迁固的古文观念仍有某种情结。这与他在《赠梁建中序》中所表达的“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正相暗合,该现象也充分说明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自有别于经书的独特魅力。
宋濂古文观念的这一变化与元代科举程式、婺州理学风尚及吴莱、黄等师长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元代进士试把经义与诗赋并为一途。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下诏:“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由于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加上明经、经疑二问采用朱熹的集注,那么朱熹的文道合一观念势必对士子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辞章方面,进士试带有明显的复古特征。延开科采用古赋,元顺帝至正六年更使古赋由选试科目变为必试科目,这在《元史纪事本末》卷二有相关记载:“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关于该问题,时人的文集中也有类似记述,如《吴文正集》卷六三:“次场在通古而善辞。”科举程式的复古倾向必然引起士子习作古赋的风尚,因而它引发了“场屋之士几乎无不学古赋,甚至出现了‘寒窗读赋万山中’的盛况”[2]。宋濂于至元元年第一次参加乡试,这距延开科已有22年之久,因而,他在文学观念上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应注意的是,宋濂所致力的古文辞与科举程式所要求的古文并不完全一致。杨维祯在《潜溪后集序》中指出:“潜溪自弱龄日记书数万言,又工辨裁,尝以《春秋》经术,就程试之文。试不售,则辄弃去,曰:‘吾文师古,则今不协,吾宁不售进士第,毋宁以程试改吾文也。’此其学日古,文日老,非今场屋士之以声貌袭而为者比也。”[1]黄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今人不过剽窃陈腐以应时须,恶足以行远哉?尝谓文章非应用,应用非文章,诚不为过论也。诸作温雅俊逸,然出于时流之外,必如是,庶几无愧于古,斯文为不乏人矣。细玩之余,不胜歆艳。”[1]黄明确强调文章非应用,并赞扬宋濂之文出于时流之外,也说明宋濂之文与时文确有不同之处。即便在辞赋的抒情言志上,宋濂也有迥异于时文的地方,吴莱在与宋濂的书信中就曾指出:“《游仙》等赋妙甚,自时文行而此学几绝,盖皆坐读书不广,故空疏无精采,恹恹如久病人。今吾景濂为之,便自不凡耳。”[1]因而,宋濂文学观念的变化虽受到元代科举程式的影响,但它也并非唯一的因素。
元代婺州理学风尚及诸位老师的教诲对宋濂古文观念的转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婺州有着浓厚的理学氛围,有“小邹鲁”之称。当时的婺州,除了本土以兼容为特征的婺学之外,在朱熹嫡传们的努力下,朱学在婺州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自白云(许谦)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3]。金履祥的义理之学传至义乌诸公时已发生了较大变化,黄、柳贯已“成为辞章之士”[1]。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也指出:“(胡君仲申)每见景濂,辄加奖誉,且谓曰:‘举子业不足烦景濂,曷学古文辞乎?’”[1]郑楷《行状》也有类似之语。可见,在当时的婺州,习作古文辞已成为一种风尚。因而,黄、柳贯等人的文章观念也势必对宋濂古文观念的演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20岁前后,宋濂就开始向婺州著名理学家闻人梦吉、吴莱、黄和柳贯等学习古文辞。《玉龙千户所管民司楼君墓志铭》载:“初,余年十九,负笈入婺城之南,受经于闻人先生。”[1]《浦江戴府君墓志铭》指出:“濂弱龄时,师事渊颖先生吴公于浦阳江上。”[1《]题盛孔昭文稿后》:“余弱龄时,即从黄文献公学为文。”[1《]跋柳先生〈上京纪行诗〉后》④也说:“濂以元统甲戌伏谒先生于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纪行诗》。”[1]闻人梦吉讲学“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而非圣之学不习也。言其攻辞,则以文字从职为载道之用,而斥钩章棘句为非学也”[1]。而黄“所学,推其本根则师群经,扬其波澜则友迁、固”[1]。在《叶夷仲文集序》中宋濂也述及早年跟随黄学习古文的情景:
先师黄文献公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予窃识之不敢忘,于是取一经而次第穷之。有不得者,终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达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晓大旨。[1]
可见,宋濂以六经为本、迁固为辅的文章观念确曾受到过师长的影响,而黄对他的影响尤甚。《〈白云稿〉序》和《华川书舍记》对此也有类似记载。入仕明朝后,宋濂向宗经、征圣方向迈进,主张“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1]。《故新昌杨府君墓铭》也指出:“文者将以载道,道与文非二致也。……殊不知道与文犹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歧而二之乎?”[1]这种文道合一的观念,在《渊颖先生私谥议》中也可找到旁证。这足可说明,诸位师长的教诲,对宋濂向文道合一观念转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仕隐心态的转变及原因
得君行道始终是宋濂的政治理想,他在元朝多次奔赴科场正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做的努力。不幸的是,他却一再地失利。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与科场屡次失利的残酷现实没有让宋濂丧失入仕的热情。作为一个理学家,宋濂恪守了儒家必待君王礼遇才肯出仕的信条。如果说至正九年的他拒绝元王朝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一职是该观念作用下的产物,那么,十年后接受朱元璋之聘则是这一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岁月虚掷、战乱的日益加剧是促成宋濂仕隐观念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
在早年,君主至诚致敬的礼遇是宋濂出仕的前提,科场的屡次失利使他对君臣遇合更为向往。在《论语·八佾》中,孔子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回答鲁定公关于君臣关系的提问,朱熹解释为:“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4]并引尹文氏“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4]之说为证。在孔子、尹氏看来,只有君使臣以礼,臣才事君以忠,二者“义合”才是理想的君臣关系。宋濂早年所固守的即是这一观念。《太白丈人传》是这一心态的集中体现。太白丈人认为君子择主就如同女子择夫一样,“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而后成婚。不然,是奔也,虽国人皆知贱之矣”[1]。“负策而干进”与“不待聘而奔者”一样[1],既不会被君王所采纳,也要为世人所嘲笑。因而,君子不应轻易委身于人,帝王不“北面而事之”[1]或“致敬尽诚”[1],就绝不能出仕。文中的王通正是主动献策,才无功而返。宋濂26岁时所作的《〈太平策〉后题》中“士之遇合”“道之所系于时者”[1]也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科场的屡次失利,似乎使他对科举抱有的幻想也有过动摇,“在前朝(元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甘终老于山林”[1]。《次韵黄侍讲赠陈性初诗韵》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忆昔游虎林,年壮已非冠。……甘从原思贫,耻学毛遂荐。”[1]但他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却没有改变,这从此后所作的《题长春子手帖》中可以看出:“公虽寄迹老子法中,而心实欲匡济斯民,天道好生恶杀之言未尝去口,是以上简帝知。”[1]在对丘处机书法的评赏中,极力称赞对方书法外的用世之心,这不能说完全出于偶然,恐怕他本人没有这种心迹也难以产生共鸣。
至正九年,元廷授予宋濂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但在他看来,元朝之聘还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至诚致敬,因而拒绝了此聘,并于次年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难用于世”[5]为由入仙华山为道。《龙门子凝道记》是宋濂归隐期间的文集,最能反映他入山为道的真正原因。如卷上《终胥符第三》就直接表明他并非“长往山林而不返”[1],而是寻求解脱及等待“上之人致敬而后翩然以起”[1]罢了,“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1]及“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1]才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在《采苓符第一》中,他以独孤氏二女拒绝主动追求西邻之子的故事回答劝他入仕者的质疑,认为“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1]并指出,他不是不愿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而是君王没有以礼相聘,“礼丧则道丧”[1],君子应坚守道义,不能“枉道以殉人”[1]。在该文中,宋濂也明确指出:“君子之任道也,用则行,舍则藏。”[1]并用《易经》困卦之初六、泰卦之初九作为出处的依据。这正是儒家“邦危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观念的体现。在《五矩符第二》中,宋濂以子张见鲁哀公不受礼遇的故事暗示,如果“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1],士将不会受到重用,因而就应该知退。《孔子符第四》闽姝求偶的故事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一福建女子被一外来男子的美貌所倾倒,于是与男子私奔以托终生,一年后却发现该男子竟是遭受“墨刑”[1]的盗贼,闽姝最后也郁郁而终。在宋濂看来,闽姝正是由于“不自重”[1]而导致所托非人,后悔莫及。对于此则寓言,当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部分学者把该寓言归为封建婚姻伦理说教,认为作者旨在警示那些轻佻的女子要洁身自重,择偶时应慎重,不可轻易委身于人;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该寓言以闽姝象征积极投靠元朝统治者、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汉族知识分子,羞斥他们不自重,轻以从人,告诫他们所倾心的不过是盗贼而已,从之终必后悔。其实,只要了解稍晚于《龙门子凝道记》之后的《赠行军镇抚迈里古斯〈平寇诗〉序》,后一种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如果宋濂真要讽刺投靠元朝统治者并甘心为之效劳的知识分子,那何必还要赞扬元朝官员平寇之功?而宋濂本人就曾写过《国朝名臣序颂》,他如果反对汉人仕元,那为何还要为统治者唱颂歌、屡次参加元朝的科举?此外,宋濂在代朱元璋所作的《论中原檄》中也指出:“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1]抛开为朱元璋起义找依据的因素不说,它从侧面也说明了元朝的正统性在当时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对于闽姝求偶是否纯属婚姻伦理之论,从结语“呜呼!岂唯女子然哉”[1]的感叹中便可明白,该寓言的主旨绝不只是阐发女子择夫之事。它与《太白丈人传》及独孤氏二女的故事一样,均以女子择夫喻君子择主,即他要等到明主礼遇才肯出仕。因此,该类寓言正是宋濂不愿出仕的自白,是他仕隐观念的一种反观。值得一提的是,宋濂此次虽然没有接受元朝之聘,但在该年十一月为吴莱作的《渊颖先生碑》中却署名“门人前史官金华宋濂撰”[1],《〈春秋属辞〉序》也署有“前史官金华宋濂谨序”[1]字样⑤。这一细节说明,他仍抱有入仕的情结。他在该年所作的《皇太子入学颂》对皇太子入学之事大加赞赏,也可作为该观点的一个旁证。
事实上,归隐后的宋濂也并未得到解脱,反而更为矛盾、更加痛苦。为了怕别人误解他的“吐纳修养”[5]是为追求“久寿”[5],他请戴良作文为自己归隐辩解,这在戴良《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中有详细叙述。同时期所作的《调息解》⑥也对此再三致意。该文通过作者与玄素先生的对话阐发他的吐纳炼气是为了“拓化原以乘政机,使阴阳和而风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1],可见,他吐纳炼气是有着远大理想的,是为“武功戢而文教施”,并非为个人长寿这一己之私。至正十五年三月,作于46岁时的《白牛生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所谓“常行服气法”[1],只是为了“节宣四时”[1]的理想;至于读“台衡贤守、慈恩诸家书”[1],也不是要皈依佛门,因为“我虽口之,未尝心之也”[1]。以上种种说明,宋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及阅读释家之书,不过是寻求解脱、等待出仕的时机而已。而部分学者认为,宋濂入山为道也有道家情怀在内。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宋濂入仙华山为道实受儒家出处观念的影响,史实证明,入山归隐不失为士子跻身仕途的一条终南捷径,而宋濂本人也正是以此被朱元璋征用的。况且,他对道家的一些学说也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在《说玄凝子》及《诸子辨·抱朴子》中就对长生之术进行了批判,在早年所作的《大还龙虎丹赞·稽曲徵四》结语中也指出:“方知涉有为,不可学长生。”[1]因而,他阅读道家典籍及与道人交往正如他同释氏关系一样,只是他博览百家之言而取其所需这一观念的体现罢了。如果仅凭他在个别篇章中有仰慕道家遗世独立之境的言辞就认为他的归隐与道家情怀有关,则显然欠妥。纵观宋濂存世之作,他对释氏的赞誉、与释门弟子的交往要远远多于他对道家的认知、与道人的往来,这也是全祖望把他视为佞佛之流的主要原因。因而,照上述学者的逻辑,宋濂应对释氏的情怀更深,应成为释门弟子才对,但宋濂为何会选择入山为道而不选择入释氏门墙呢?宋濂入山为道绝不是道家情怀所系,而是想摆脱痛苦、等待出仕时机的不得已之举,他对道家自由之境的仰慕正是用世之志在社会中得不到实现的折射,因而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如《采苓符第一》:“龙门子寝疾,数月不出。”[1]正如闾丘生所言,宋濂之病“非病己也。为斯世病也”[1],“白骨不葬,高如丘陵”[1],“生民流亡,伥伥无所依”[1],“田野荒芜,五谷不生,猫成行,白昼出郊,行人鲜少,腥风秽洒”[1]才是病因,闾丘生欲以“出位之思”[1]使他摆脱痛苦,但宋濂却无法做到,“我非人则已,苟亦人尔,何可不忧世哉”[1]!继《龙门子凝道记》之后,宋濂完成了寓意深刻的《燕书》40篇。“君子怀材抱艺,孰不欲自见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尔”[1]便是暗示统治者要尊重人才、礼遇人才的重要性,而这也正是宋濂仍渴望入仕的一种流露。
宋濂早年期望能遇到刘备式礼贤下士的君主,幻想自己也能像诸葛亮一样得到重用,从而推行大道于天下。但十年归隐,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他,等来的不是圣明君主至诚至敬的邀请,而是满头华发,是社会局势的更为动荡不安,这一情势使他不得不对以往所固守的入仕观念进行调整,以便寻找入仕的时机。朱元璋的征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的。
至正十九年正月,被朱元璋委任为婺州知府的王宗显以婺州郡学五经师征用宋濂。宋濂虽也作了推辞,但在信中表示:“然而兴学在乎明经,明经在乎选傅,得良傅则正鹄设而射志定,土范齐而铸器良,声流教溢,俗转风移。反是则政堕矣,此则执事不可不慎者也。”[1]且不说这种对统治阶层献策不应是真正隐者所关注的问题,而这一才华的展露只能使他更加推脱不掉王宗显的邀请,宋濂不至于不明白这一托辞的客观效果。总之,宋濂这次是接受了聘请。次年,当朱元璋遣使樊观捧书币征用时,宋濂立即“幡然应诏”[1]。而恰恰是在接受婺州郡学五经师的前一年,宋濂的妹妹被朱元璋手下的士兵所执抗节而死。除了家恨,友人戴良也曾暗示宋濂不要答应朱元璋的征用。“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6],这表明戴良已意识到此次入仕前景的危险;“自知羽翮短,不与同奋飞”[6],表明他本人不打算追随朱元璋了,劝宋濂也要“当慎子所之”[6]。但这种家恨与友人的暗示,宋濂都未理会,他出仕的决心是何等坚决就由此可知了。青春易逝,时不我待,之前已错过元朝之征,如果再错失此次良机,恐怕就再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了,正所谓“怀其宝而迷其邦”[4]不仁,“好从事而亟失时”[4]不知。总之,宋濂是下定决心要出仕了。而次年的举动也可作为佐证。当时,他与刘基、章溢、叶琛去南京拜见朱元璋,途经泾县时,刘基作有《泾县柬宋二编修长歌》。“编修”是元朝曾授予宋濂的官职,他虽未接受,但毕竟与元朝也有瓜葛,刘基此称显然是有意提醒,全诗也充斥着悲观情调。但宋濂的酬赠之作并不悲观,尤其是最后几句“肝刿肾竟无益,不如养性祛阴邪。他时紫府或有召,会驾五色麒麟车”[1],宋濂显然是要施展一下抱负了。后来,刘基在《送宋仲珩还金华序》中也曾提及此事,“虽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无芥于心。唯先生泰然耳,日与文彦士相从游不倦,人咸异焉”[7]。与其说“泰然”“从游不倦”反映了宋濂处事不惊的气概,倒不如说此聘正应了他心中所求。对他来说,这一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他足足等了大半生。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宋濂在入仕明朝前逐步完成了从师法迁固到以六经为本、迁固为辅观念的转变,并为他在入仕明朝后向文道合一观念的演进起到了桥梁作用;必待君王礼遇才肯出仕是宋濂早年所固守的入仕观念,拒绝元朝之聘与入仙华山为道正是该观念支配下的举动,随着时光的流逝及战乱的日益加剧,他最终放弃了所固守的观念,而这一观念的转变是在时代大背景下逐步完成的,决非一蹴而就。
注释:
《角端颂》。据同时代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五《角端》篇载,此乃至正十年江浙乡试的题目。那么该信作于是年乡试后或次年无疑,即宋濂41岁或42岁时。
②据《题盛孔昭文稿后》“余弱龄时,即从黄文献公学为文”及
《华川书舍记》“以濂同受经于侍讲黄先生之门也……濂虽稍长于子充……虽然子充弱冠时,濂见其文辄曰……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动荐绅间”,可知该文作于30岁前后。
③据《题盛孔昭文稿后》“余弱龄时,即从黄文献公学为文”及
《太乙玄征记》“窃受教于先生长者,学文二十余年”,可知该文亦为宋濂40岁前后所作。
④元统甲戌年即1334年,即宋濂25岁时。
⑤当然,用此署名可能与求书者请求有关,但如果宋濂真的丝毫不属意于仕进,他完全可以拒绝这样的署名,毕竟他并未担任过此职。
⑥据首句“越西有仙华生”,可知该文是宋濂在入仙华山为道期间所作。
[1]罗月霞.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5.
[3]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六)[M].
[6]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M].
[7]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一五)[M].
I206.2
A
1007-905X(2010)06-0155-04
2010-08-10
王魁星(1979— ),男,河南宝丰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近代(元明清)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