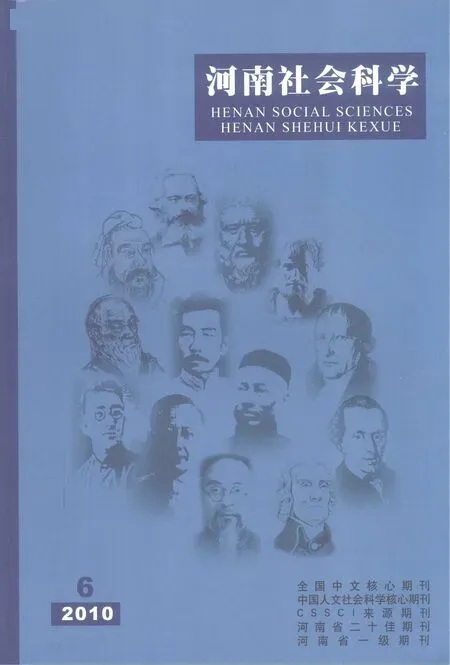“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
——犹太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及其实践意蕴
任东景
(河南大学 犹太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
——犹太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及其实践意蕴
任东景
(河南大学 犹太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当代英国著名的犹太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涵盖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再到“流动现代性”的辩证逻辑,通过作为复杂幸事的解放、对自由的向往与迷惘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清算等加以展开。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理论家的立场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进行深入剖析,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建设精神家园、克服精神生活的物化和虚无主义困境,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鲍曼;生存;发展;解放;自由;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西方世界著名的犹太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以《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等著作闻名于世。他以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历程为背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敏锐洞察,超越对于纳粹和排犹运动的纯情感批判和非理性宣泄,而从现代社会深层发展、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来剖析解放、自由、现代性等背后的“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
一、对解放的追求与拒斥
一般来讲,解放就是从某种阻碍或阻挠运动的羁绊中获取自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冲破各种羁绊、争取自由的过程。人们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足的生活,但并不能满足和沉溺于这种物质的丰裕,要不断地从这个富足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为什么呢?鲍曼现代性反思理论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对解放的重新定位,他把解放界定为一种复杂的幸事,通过对解放的不断追求与拒斥,来展现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辩证法。
当代人的生存状况犹如“笼中人”,生活在现代性中的居民被放置在以人类工程学方法设计好的笼子里。在每个被高科技的锁链束缚在高科技栅栏上的现代笼子里,都有一本生活指南,它向人们解释作为一个现代的笼中人如何过上好的生活。这是一本让人快慰的书,阅读它能使每个笼中人感到十分惬意。……后来一条天堂里的蛇每天夜里潜入城市,打开一些笼门,每天晚上都有一些笼门被打开。笼子里的居住者梦中被钥匙转动的声音所惊醒,带着恐惧和好奇,他们走出笼外,在半明半暗中四处蹒跚而行,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耐心。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世界中,一些人想设法回到笼子里去,却发现门已经从里面被闩上了,已经回不去了,不再有生活指南告诉他们:他们是谁?做些什么?如何感受?如何与他人交往?[1]这突出地反映了人们获得解放之后的无所适从与迷茫,进而可能导致对于这种新生活的拒斥。
鲍曼借助于那些被解放者的话来进行证明:“现在你给我滚,你这个恶棍,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难道你还想纠缠我们?难道你还要将我们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强迫我们的心灵永远去接受新的决定吗?我是如此的快乐,我可以在泥泞中翻滚,在阳光中沐浴,我可以狂饮滥吃,可以鼾声震天,可以龇牙乱叫,我打算做什么,这件事,还是那件事?你为什么来这?!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回到以前我过的可恶的生活?对这些问题,我不用思考,也用不着怀疑。”[2]这使人不由得想起“洞穴假象”中的先知者,他在自己离开了囚禁他们的洞穴,获得了解放之后,在庆幸自己解放的同时,怜悯他的囚徒同胞,为了解放他的同胞,这个解放了的囚徒义无反顾地返回到洞穴里,试图解放他的同胞。但他最后失败了[3]。
解放是一件喜事,还是一次灾祸?是一次伪装成幸事的灾祸,还是一件因为害怕而把它当成灾祸的喜事?由对解放作为一种表象的感知,促使鲍曼去进一步深入对其深层的解读,于是自由被纳入他的视野。
二、对自由的向往和迷惘
对于与解放密切相关的自由,马克思对其褒扬有加,他认为自由是真善美的统一和升华,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马克思结合人的发展的三阶段探讨了解放中所蕴涵的自由问题。第一阶段是人对人的依赖阶段。在这个时期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人格,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人,即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因此,这种独立性又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于是在这种社会中生活,就造成了人的物化,或称为“单向度的人”。只有从这种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只有克服这种物化,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即人的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系列观点被后世理论家所传承。
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至于今天,以及我们自己的境况,我认为我们面临着历史中的新的形势,因为在今天,我们必须从一个相对更好地运转着的、富裕的、有影响力的社会中……解放出来”[2]。“既然富裕社会成了一个为防止毁灭危险而持久动员的社会,既然该社会的商品销售伴随着白痴的产生、辛劳的永久化和挫折的增多,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再能漠然置之”。“在这种情况下,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又回复到健康和强壮的贫穷状况中去,并不意味着又回复到道德纯洁和单纯愚钝的状况中去。相反,根除了有利可图的浪费,将增加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持久动员的结果,将减少克制个人去寻求满足的社会需要”[4]。这就把解放、自由问题与人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
鲍曼认为自由如同空气,只有当失去它时才能感觉到其重要性。解放不仅是指“从某种阻碍或阻挠运动的羁绊中获取自由;是指开始感觉到运动或行动的自由”[2],指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到,不存在蓄意的妨碍、阻挠、抵制或其他任何的阻碍运动的障碍。人们感到是自由的东西有时事实上根本不是自由,人们可能满足于自己的一切现状,即使自己的一切并不令人满意;如生活在奴隶状态下,但是他们仍然感到自由并因而丧失了解放自己的渴望,从而丢弃了使自己变得真正自由的机会,这种可能性的必然结果就是人们没有能力对自己的境遇做出判断,而且必定会遭到强迫或欺骗,甚至怨恨解放所带来的真实的图景,因为这种真实的图景打碎了他们那麻木和虚假的幻象。
鲍曼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揭露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虚假的自由。第一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化培植了娱乐和欢娱引起的集体性的脑损伤,时断时续地激起人们对误入歧途的人们的同情,欺骗人们让其放弃获取自由的机会,责备站立在新的富足门前的不自由的人对不自由状态的明显顺从屈服。第二种情况,鲍曼认为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并不是幸福的保障。他认为个体自由得以存续要依赖于特定类型的社会条件,认为“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5]。在这里鲍曼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对自由进行分析的,只有把自由放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自由本身,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物质动因,才能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自由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鲍曼在批判资本主义虚假解放的同时,试图通过寻找新的政治,建构一个新的共同体来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这种共同体“有赖于agora——这是一个既非私人,亦非公共而同时恰恰又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间。在这空间里,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不仅仅是为自我陶醉之快乐,也不仅仅是为通过公共展示而寻找某种疗治,而是寻找一种集体操纵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一空间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些观念,并形塑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或‘共同价值’”[6]。鲍曼认为,要想超越对于自由追求的歧途,不仅需要用激情去赞扬,更需要用理性去批判,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清算。
三、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清算
鲍曼曾对现代性有过彻底的清算,认为高度发达的“理性”和“人的自我中心”极度膨胀乃是现代性问题的根源[7]。鲍曼认为现代性首先把自己界定为理智与理性的王国,并把理性和理智推向极致,把其他生活方式看做这两种东西的缺乏甚至异端。鲍曼进一步指出大屠杀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和理性精神的极端膨胀。而在大屠杀得以顺利实施中,作为现代性重要成果之一的现代官僚体系进一步使得大屠杀的执行者丧失了作为道德个体的理论关怀,泯灭了他们作为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反对暴行的道德抑制力。“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罪行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被屠杀者的阻力与反抗,屠杀对象几乎是有些主动地与刽子手达成协作,而这种近乎荒诞的情境之所以出现同样是源于被屠杀者自我保存的理性算计能力。经过理性的严密计算和规划,自我保全的冲动成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包括道德冲动、宗教信仰、是非之心在内的所有其他考虑都被贬低到一文不值的程度,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倒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8]。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9]。鲍曼还预言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历史的终结,时间证明,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再次证明了鲍曼当年的预言。
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承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更为美好的世俗社会的存在。后来由于民族国家的萎缩、风险意识的增加、资本的全球化和欧洲帝国主义的衰落,科学已经开始显现其危险性的一面。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臭氧空洞的出现等;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和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理性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再到“流动现代性”理论,鲍曼始终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来探索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
四、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现代性是不可逾越的。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梳理包括鲍曼在内的当代西方理论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透视和反思批判,结合中国国情,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利弊得失,才能积极推动和完善中国现代性的设计和实践,才能更好促进科学发展。
首先,深入理解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有利于把握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化。鲍曼形象地指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已被消费主义所物化,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归于消费,以致陷于消费陷阱的无底深渊。这种貌似富足的社会,也就是当下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借助于传媒,不断煽起人们的消费欲望,而暂时的欲望的满足又导致了更高的欲望,距离人的本真自由状态是愈来愈远,表面上看,人们的自由度是增大了,实质上人们对这样一种畸形状态的依赖性倒是越来越强了,实际上正是由于它的误导才制造了一系列的消费幻象或消费假象。由此可见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它经常允诺它无法给予的东西,它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这种不可实现之梦,并且把自由降格为一种消费,而忽略了其他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路径。所有这些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应该引起高度警觉,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从而超越消费幻象或消费假象,使人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其次,深入理解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有利于应对由于个体化而产生的虚无主义,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科学化。现时代,个体化困境仍在加深,“个体不得不面对稳定的压力,即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10]。个体的生活旨趣消耗或延宕在各种不确定而又充满诱惑的物化世界里,直到完全沉湎于种种形式上开放、实际上封闭的虚拟生活方式中,从而在现实社会中完全封闭了个性,迷失了自我,“今天追求的个性就像更换服装一样可以选取和弃却”[11]。由于工作变得越来越不具有稳定性,所有稳定性的规则、规范都在迅速失控;结构性失业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使人们普遍缺乏对现在的把握;以追求瞬间满足为特征的“瞬时性文明”取代了以连续性和累积性为特征的“持久性文明”;导致了过度的消费、物欲的横流、精神的空虚,人变成了“没有联系的人”,社会也变成了“原子化的社会”。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身之间被撕裂,由过去人们的“我饿”到了今天的“我怕”“我烦”“我活着没意思”等。物质财富并不是万能的,正如金钱可以买到汽车,可以买到别墅,但它买不到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幸福感,人还是应该有点精神追求和精神寄托的。所以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中华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理想归宿和精神家园,更好地应对个体化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困境。
再次,深入理解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有利于消除各阶层之间分裂的风险,促进各阶层之间的融合,实现社会发展的科学化。鲍曼认为当今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层,消费者与有缺陷的消费者,并且导致两者之间的剧烈冲突和彼此仇恨。“按照美国通行的对‘等下阶层’成员的定义,穷困潦倒之人、带孩子的单身妇女、辍学的学生、吸毒者和假释的犯人携手名列其中,而且很难把他们拆开……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的负担’。如果他们以某种方式神奇地消失,那么我们会更加富裕,更加幸福”[11]。正如“全球化”对某些人而言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悲惨的祸根,“一百年之后,现代性的全球化胜利所导致的一个非常致命的(可能也是最为致命的)的结果:随着人类废弃物总量超过现有的处理能力,出现了一种极有可能的前景,即眼下的现代性全球化(资本主义)‘如鲠在喉,窒息而死’”[11]。在当代中国,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穷人”与“富人”之间裂痕加深,“穷是因为你懒”等声不绝于耳,“灭门”、“扎胎”等极端行为也常见报端,仇富与蔑贫两种思想的暗流都在涌动。
地球是个“村庄”,大家都是“老乡”,融则两益,裂则两损。我们可以买到豪华的别墅,但买不到好的治安;可以买到高级的小汽车,但买不到畅通的交通。要关注弱势群体,使各阶层和睦相处,在共建共享中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1]丹尼斯·史密斯,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齐格蒙特·鲍曼.自由[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6]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张曙光.“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J].学习与探索,2006,(1):136—143.
[8]刘新锁.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伦理之可能[J].读书,2006,(3):90—96.
[9]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0]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1]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责任编辑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
B0
A
1007-905X(2010)06-0063-03
2010-09-07
任东景(1974— ),男,河南濮阳人,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马列部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犹太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