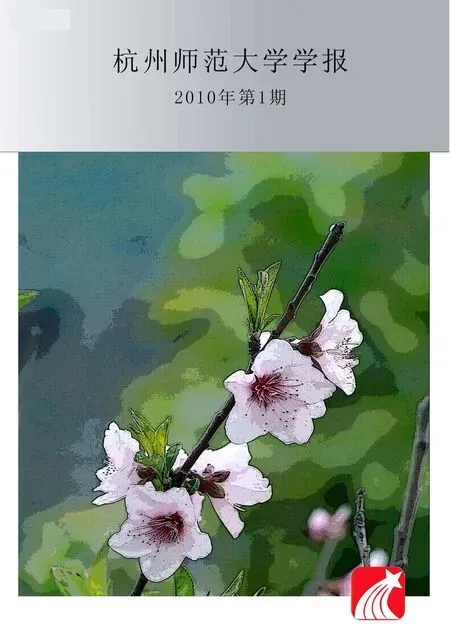王门后学王龙溪与罗念庵工夫论之比较
张卫红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36)
王门后学王龙溪与罗念庵工夫论之比较
张卫红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36)
王龙溪与罗念庵往复多年的思想争议,其分歧在于对良知不同体悟背景下的各说各道,二人分别发挥了阳明致良知教顿悟与渐修的两个方向。同时,随着念庵致知工夫的不断深入,他超出了中期的“主静”说,对阳明学体用一源、即用见体的理路逐步认同,晚年渐趋化境,表明致良知教的顿、渐两大路径殊途同归,通向同一个天德流行之化境。
王龙溪;罗念庵;王阳明;阳明后学;致良知
王龙溪(名畿,号龙溪,1498-1583)与罗念庵(名洪先,号念庵,1504-1564)是两位交往密切而又学术风格对立的王门后学的重要代表。以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学术特征划分法,龙溪属现成派,念庵与聂双江(名豹,号双江,1487-1563)同属于归寂派或归寂主静派。龙溪与念庵关于现成良知说的往复争论长达几十年,构成了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题,也开出了阳明之后良知学开展的不同面向。对于王、罗二人的比较,本文跳出仅从思想义理层面进行概念分析的通常做法,从二人对致良知教的不同“体知”背景入手,厘清双方由此而来的不同的问题意识、工夫路径、理论建构等,以此对阳明之后致良知教的开展有一深入的把握。
一 不同的“体知”背景和问题意识
“体知”一词出自杜维明先生对儒家“德性之知”的诠释,[1]认为“体知”、“体证”是宋明理学建构的真正基础。[2]简言之,道德并非一种经由理性思考获得的概念知识或通过感官从外界获得的经验知识,而是通过身体力行的内在体证获得的体悟之知,是一种内在直观在个体生命中的呈现,具有直接的确定性,是知和行的合一。阳明学*笔者所谓的“阳明学”是指包括阳明及其后学在内的心学一系,行文中兼“王学”、“心学”、“良知学”、“王门后学”等学界通常的用法,与“阳明学”基本上指涉一致。尤其具有强烈的“体知”特色:“心即理”、“知行合一”宗旨的提倡,使得致良知之教要求“体之于身”、“体之于心”,*以上分别见王守仁《答徐成之(二)》(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0页)、《书石川卷》(《王阳明全集》卷8,第808页)。“切实用力”才是进学之方,[3](卷5《与杨仕鸣(一)》,P.185)“实致其良知”才是目的,[3](卷5《答董沄萝石》,P.198)最反对在言语知解上“议拟仿像”、“认虚见为真得”。[3](卷3《年谱一》,P.1232)因此,阳明与门人之间的论学内容基本上都关联着如何致良知的工夫,阳明之后,王门诸子之间的争议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致良知工夫论而展开,学者的思想见解往往关联着各自不同的践履工夫,这是王门后学分化的一大原因。梁漱溟曾云:“盖在前之汉唐人但注疏书文,殊未用功体验于身心间,争论不起。宋明之世,斯学复兴,则学者究当如何用功,在彼此大体相近之中,不免人各有其所取径。朱、陆异同,其明例也。”[4]此语用于形容王门后学之争甚得。并且,学者之间的相互评议也并非只论言说是否动人,而是联系他的实际致良知之践履予以评议。如龙溪对双江归寂说之义理尽管不认同,却能如实肯定其基于实践之“自得”。其谓:“双江公近于寂然处自信真有得力,非从意见解去,亦非从依傍道理得来。”[5](卷9《复刘狮泉》,P.407)以此,对于阳明学的研究,就不能仅从理论见解上论是非,而应当将其理论学说置于体知—工夫的脉络中加以把握,本文对龙溪与念庵致知工夫论的比较也遵循这一脉络展开。
阳明之后,阳明大弟子王龙溪的见在(现成)良知说*需要说明的是,龙溪并未使用“现成良知”一语,然当时以及后世学者多用“现成良知”一语指称,龙溪对此亦未反对。因此在阳明后学的学术语境中,“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的含义基本无别。本文在龙溪的语境中使用“见在”一词,一般语境中则用“现成”一词。此外,龙溪之“良知见在”与心斋之“良知自然现成”的含义及工夫内容并不相同。限于篇幅,本文只论龙溪之说。十分流行。罗念庵未能亲炙阳明,在王门学子“尽以王子(按,指龙溪)之言为言”[6](卷19《赠王龙溪序》,P.11)的背景下,念庵一生的学术思想都是在与龙溪的现成良知说进行对话、交涉中形成和发展的。代表念庵三期思想的著作《冬游记》《(戊申)夏游记》《甲寅夏游记》中的主要思想对话者即是龙溪的现成良知说。从早年的拳拳服膺,到中岁的严厉批判,再到晚年有所修正,诚如福田殖先生所说:“给予念庵影响最大的,并对于念庵的学问形成关键作用的,还是良知现成派的中心人物王龙溪。”[7]他认为念庵与龙溪的共同点是“他们对阳明思想的真正理解以及倾心普及的热情”。[8]尽管二人的学术路径不同,但他们卓然以道自任的共同志向以及互取所长的为学精神使得他们维系了长达32年的高情厚谊,也打下了长期进行思想对话、交锋的基础。
首先,从各自体悟良知的实际境界来看,龙溪“英迈天启,颖悟绝伦”,[9](赵锦《龙溪王先生墓志铭》,P.1)为王门诸子中难得一见的高才。嘉靖二年(1523)龙溪25岁时,“请终身受业于文成,文成为治静室居之”,“逾年遂悟虚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9](徐阶《龙溪王先生传》,P.1)也就是说,龙溪早在嘉靖三年(1524)26岁时即通过短暂的静修而悟得心体。结合天泉证道中阳明告诫龙溪“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工夫”、“正好保任”[5](卷1《天泉证道纪》,P.251)之语,可知阳明对龙溪悟境的肯定。可以说,见在良知说正是来自龙溪自身致知实践的“自得”。而念庵的致知实践可谓历经曲折,晚有所成。念庵早年服膺现成良知说时尚未悟得良知心体,现成良知所要求的“时时致良知,朝乾夕惕,不为欲念所扰、昏气所乘”,[5](卷1《三山丽泽录》,P.259)对龙溪而言并非难事,然对于念庵而言,在多年的“现成良知”实践中,“(良知)倏忽而得之,顾且倏忽而失之,吾之得失相寻于倏忽,而欲求万古不息贞明之体,以为酬酢万变之用,胡可得哉?”[10](内集卷3《熙光楼记》)于龙溪之说始终未能相应。
进而,二人由不同的体悟境界而有不同的关注层面,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意识。阳明学之宗旨,直接针对明代程朱理学走向辞章训诂之支离决裂的弊端而直提本心,所谓“心即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3](卷6《与马子莘》,P.218)学问之目的,“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3](卷2《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P.55)龙溪秉承师旨,论学直指本心:“夫致知之功非有加于性分之外,学者复其不学之体而已,虑者复其不虑之体而已。若外性分而别求物理,务为多学而忘德性之知,是犹病目之人,不务服药条理以复其光明,伥伥然求明于外,只益盲聩而已。”[5](卷5《与阳和张子问答》,P.349)以此,龙溪的问题感在于,批评不能当下安住于良知心体的茫昧支离、帮补凑泊之弊端。尽管他赞赏双江“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于师门大矣”,[5](卷9《答聂双江(一)》,P.405)但同时又批评双江(也包括念庵中期思想)“别求未发之时,故谓之茫昧支离”。[5](卷6《致知议辨》,P.359)然而在双江、念庵这里,这并非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意识。在认同“心即理”的基本前提下,他们所关注的是“当下直指本心”的实际困境,也即在理欲混杂的经验层,欲根“搀入”、“回互”以及“吾人窠臼已在欲中”之吊诡,[11](卷3《答李二守》,P.44)则现成良知说可能导致“以见在之知为事物之则,而不察理欲之混淆……理欲混淆,故多认欲以为理”。[11](卷5《(戊申)夏游记》,P.143)良知如何才能不被欲根、知觉所混同、遮蔽以及不被虚见、情识冒认,是他们的基本问题意识。要言之,龙溪直下从本体用功,发挥了阳明致良知教的“向上一机”,所关注的是不能当下安住于良知心体的茫昧支离之弊,而念庵则代表了绝大多数学子在实际践履中的困惑:在经验层之“当下”难免理欲混淆之弊。故而,以嘉靖二十六年(1547)为标志,念庵摒弃了现成良知说,转而认同聂双江的归寂说,确立了“主静”的工夫论。
二 不同的工夫取径与言说主张
由不同的体悟境界和问题意识,龙溪、念庵之致知实践采取了不同的工夫取径。龙溪早年即证悟心体,发挥其顿悟之长,基于吾人日常的当下一念善端与良知全体具有本体上的同一性,以此为依据,由“真信得及”良知的强大信念而带动起沛然莫之能御的道德主宰力,于日用常行的当下彻底扫荡经验层面欲根习心、知解意识的束缚,把持于心体将动之初的“几微”,当下安立于良知心体并“时时保守此一念”,[5](卷2《桐川会约》,P.291)以此开显良知心体之大用,此即“以良知致良知”[6](卷12《甲寅夏游记》,P.45)的“见在工夫”,*“见在工夫”一语在龙溪文集中有被使用,如龙溪云:“圣学只论见在功夫,以效验求位育,或失则漓。”(《(中庸)首章解义》,《龙溪集》卷8,页391)不过,“见在工夫”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龙溪那里并不多见,而往往体现于龙溪对见在良知的界定中。也即是说,见在良知的内容规定本身就包含着良知如何得以当下呈现在感性经验生活当中的“见在工夫”。也是见在良知说的践履要求。在念庵,尚未能证悟心体,故当下一念是经验层之“随出随泯,特一时之发见”、随时可能被欲根习心所遮蔽的一念善端,因而“一时之发见,未可尽指为本体。则自然之明觉固当反求其根源”。[6](卷12《甲寅夏游记》,P.36)故须“从见在寻源头”,[6](卷12《甲寅夏游记》,P.44)将感性经验层的知是知非之良知向上翻转为超越层之不睹不闻的形上心体,取主静、致虚、归寂、专内之工夫路数,以涵养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心体,取先内后外、立体而后达用的致知取径,以此保证良知不受欲根遮蔽,保证道德实践的纯粹性。之后,念庵在实践中“久而复疑之”,[6](卷12《甲寅夏游记》,P.38)以嘉靖三十三年(1554)作《甲寅夏游记》为标志,完成了为学宗旨的第三变。他认识到归寂说“执寂有处”“指感有时”导致良知由超越层坠落为经验层之“实有可指”的时空规定中,于义理不合,而其“专内”的理论规定本身又使得“内”必然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如此则不自觉地划向“重于为我,疏于应物”,与儒家明明德于天下之本旨不类。于是念庵超出了归寂说,提揭收摄保聚说,主良知为寂感动静合一之本体,以收摄保聚之功保任此寂感合一的良知本体为工夫。在工夫重点上,龙溪不以除欲根为重点,而是安住于心体则自然无欲,所谓“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5](卷1《闻讲书院会语》,P.254)在念庵则始终以欲根为重点,涵养心体与省察欲根同时并重,“诚敬存之”与“入处防闲”并行不悖;在工夫形式上,龙溪主张致知于当下,工夫无分于动静,所谓“心无动静,故学无动静”,[5](卷10《答吴悟斋(二)》,P.440)在念庵,虽然后期认同了寂感合一之旨,但工夫得力处仍在“主静”以“立体”,“收敛”“精神向里”之倾向仍然是首出的。因此,体用关系和工夫样态上,龙溪秉承阳明“因用以求其体”的原则,当下即用见体,所谓“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5](卷7《华阳明伦堂会语》,P.376)呈现为当下立根于心体而向前推展至事事物物的致知样态;念庵后期固然亦认肯了阳明学体用一源、即体即用之学旨,其落实形式则偏重于承体起用,所谓“愈收敛,愈周遍”,[11](卷8《书胡正甫册》,P.172)“十分发挥,乃是十分紧固”,[11](卷3《答唐一庵》,P.77)以向内、向后之收敛心体为向外、向前发用之保证。因此,就工夫之顿渐形态而论,若依阳明天泉证道中之分判,龙溪属于“悟本体即工夫”的顿悟一路,所谓“时时全体放下”,[5](卷16《万履庵谩语》,P.588)“一了百当”,念庵则自称“本是钝根下器,望此殊非易至”,[11](卷3《寄五龙溪》,P.66)走“由工夫以悟本体”的渐修一路,强调研磨习心,存养心体,所谓“夫守是(按,指心体)而存之,人人可以勉进,至日久则可夺旧习。是其进为次序,中人以下皆不至于苦难也……非假存习,断无顿悟超入之理”。[11](卷3《答何吉阳都宪》,P.75)顿渐之分判,在龙溪最后一次会晤念庵时即有总结:
夫圣贤之学,致知虽一,而所入不同。从顿入者,即本体为工夫,天机常运,终日兢业保任,不离性体。虽有欲念,一觉便化,不致为累,所谓性之也。从渐入者,用工夫以复本体,终日扫荡欲根,祛除杂念,以顺其天机,不使为累,所谓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为主,求复其性,则顿与渐未尝异也。[5](卷2《松原晤语》,P.283)
龙溪所谓“性之”、“反之”者,是对自己和念庵的工夫进路总结,判念庵为致良知教之渐修一路。需要说明的是,阳明学中顿渐之别的背景来自佛教的顿渐之分,华严宗五祖宗密将“悟”分为解悟、证悟二义,将“修”分为随相、离相二义,*以上详见宗密《圆觉经大疏》卷2、《圆觉经大疏钞》卷3,《大藏新篡卍续藏经》9册,台北白马精舍印经会印。以此将工夫类型分为顿悟渐修、渐修顿悟、顿修渐悟、渐修渐悟、先悟后修之顿悟顿修、先修后悟之顿悟顿修、修悟一时之顿悟顿修等多种。龙溪曾依“悟”与“修”各有顿渐两种形态而区分致知工夫之类型为:
本体有顿悟,有渐悟;工夫有顿修,有渐修。万握丝头,一齐斩断,此顿法也。芽苗增长,驯至秀实,此渐法也。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顿中有渐,或渐中有顿,存乎根器之有利钝。及其成功一也。[5](卷4《留都会记》,P.318)
龙溪此说显然有取于佛家对工夫类型之划分,儒家工夫内容固然与佛家不同,顿渐形式则类似。就致知工夫而言,“悟”盖指对心体的觉解,“修”则指实证心体的工夫。“悟”与“修”、“顿”与“渐”根据学者的不同资质和各自“自得”而形成不同的组合,构成阳明后学致知工夫分化的多种形态,具有顿悟、渐悟、顿修、渐修等多种形式,这种区分,可谓“天泉证道”中阳明指示的“悟本体即工夫”与“由工夫以悟本体”两大基本工夫类型的进一步细化。如绪山之后天诚意说,东廓早期之“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之工夫并非直接致力于心体的究竟工夫,均为渐悟一路。相比之下,念庵、龙溪均主直接于心体用功,可同属“顿悟”一系,不同者,龙溪以心体直贯当下,所谓“一了百当”,故为“顿修”,或谓“顿中之第一义工夫”;念庵则须先逆觉、涵养心体,继而发为外用,需要一段工夫历程,故为“渐修”,或谓“渐中之第一义工夫”。*林月惠认为,“双江、念庵这种‘立体’工夫,就‘悟心体’当下而言,本质上是顿悟。但从工夫历程来看,却是经长期努力,渐渐入悟,是为‘渐悟’。”见氏著《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594页。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阳明后学之工夫论开展为顿渐之诸多分途,不过,如何“在本体上做工夫”也即“第一义工夫”却是阳明后学共同的追求目标,这一问题可参林月惠《本体与工夫合一——阳明学的开展与转折》,同上书,附录二,第666-667页。因本文对念庵之学的判摄主要以龙溪为参照对比,故而,总体上将念庵之学列为致良知教分化背景中的诸多渐修进路中之一途。
经由实际境界、问题意识、工夫入路之不同,二人的言说层面亦有不同。当龙溪说“只从一念灵明自作主宰”时,[5](卷12《答周居安》,P.495)此一念为立根于本体的一念之微,而念庵则理解为经验层随出随泯的一念善端,故批评现成良知说“认良知大浅”。[11](卷8《另宋阳山语》,P.162)当龙溪说“从一念生生不息,直达流行,常见天则,便是真为性命”[5](卷12《答周居安》,P.495)时,说的是直任心体流行的道德化境,而念庵担心的是“任心之流行以为功”,[11](卷8《垂虹岩说静》,P.179)此“心”非是心体而是感性知觉,如是则造成“一切以知觉簸弄,终日精神随知流转,无复有凝聚纯一之时”。[11](卷3《答陈明水》,P.53)当龙溪说“良知本来是真,不假修证”,[5](卷9《答茅治卿》,P.426)“致知工夫,自然易简省力”[5](卷1《三山丽泽录》,P.257)时,是说良知本体为天然本有、不假后天人为,依此心体则工夫形式简易直截,并非取消了致知工夫本身,而念庵则批评现成良知“言致良知大易”,[11](卷8《别宋阳山语》,P.162)“多忽致知之功而轻于作用”,[11](卷8《示杨生》,P.175)如是等等,二人言说始终不在一个层面。造成言说层面差异的原因在于,王门诸子之间的辩论从来都不是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争辩,他们既没有如现代学术这样在共同界定的种种概念、范畴之内进行纯知识性讨论的“游戏规则”,也反对知解凑泊、言说比拟的知识性求索,所谓“真实受用,非知解意见所能凑泊也”,[5](卷10《答谭二华》,P.453)更重视言说的“切己”性。故而,龙溪“悟本体即工夫”的体悟境界、工夫入路与其言说层面相一致,而念庵也并非在理论上不能理解现成良知说,正如念庵所云:“此其为说,亦何尝不为精义”,问题是,“但不知几微倏忽之际,便落见解”,[6](卷8《答王龙溪(一)》,P.11)乃至“依情识冒认”,这既是他自身实践见在工夫失败的教训,也是基于当时学者以情识冒认良知导致理欲混淆之流弊而引发的忧患。因此,当念庵说“世间哪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11](卷8《松原志晤》,P.182)时,正对应着自身未悟心体、须“由工夫以悟本体”的实际需要。而龙溪遗憾念庵“奈于当下良知,尚信不及耳”[12],仍是关联着自己所得力的见在工夫而发。总之,双方都是在各自“切己”的实践情境中各说各道,这是造成二人关于现成良知的争论长达几十年而未能最终达成一致的一个根本原因。
再从个人各自气质和学术风格来看,龙溪明朗豁达,念庵沉着慎密;龙溪狂放,念庵狷介;龙溪颖悟早发,念庵大器晚成;龙溪洒脱流畅,念庵端严凝重;龙溪之学范围三教、宏阔圆融,念庵之学严守儒宗、深入一路;龙溪之见在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之特色,念庵之收摄保聚证成了渐修而悟得良知之可能。归结到一点,诚如黄梨洲所云:“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13]龙溪与念庵,各自以工夫之得力处为真,从而发挥了阳明致良知教的不同层面。
三 由异趋同
另一方面,二人的差异又不是截然对立、不可泯合的,而具有思想见地上相互借取、工夫进境上渐趋一致之调和。龙溪晚年,看到王门学子误会现成良知说而脱略工夫的情形,亦有强调渐修之主张。万历元年(1573)龙溪76岁时与王门学子会讲于南滁,期间作《渐庵说》赠李世达(号渐庵),其云:“以渐而进,优游以俟其化,非可以躐等而求……理乘顿悟,事属渐修。悟以启修,修乃徵悟。根有利顿,故法有顿渐。要之,顿亦由渐而入,所谓上智兼修中下也”,[5](卷17,PP.616-617)此文反映了龙溪晚年思想的微妙变化,可为龙溪提揭顿悟一路的调和与补充;在念庵,随着工夫践履的不断深入,其晚年的“收摄保聚”说就思想格局而言是一个显著的飞跃,良知本体、工夫内容、工夫形式都超出了中期“偏静”、“专内”的倾向,而具有动静、内外一体的内在一致性,在思维架构上已基本合于阳明学体用一源、内外合一的思路。*林月惠认为,念庵的收摄保聚说对寂感、动静关系的认识“与阳明就良知自身而言‘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见氏著《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第386页。在此大的格局之下,主静以收摄、保任心体的工夫入路当为念庵因病立方的实际需要,此时念庵确信“阳明先生之为圣学无疑矣”,[6](卷12《甲寅夏游记》,P.45)与阳明学之间的张力正在逐步缩短。
至于个人所臻境界,龙溪于80岁时自述云:
思虑未起,不与已起相对。才有起时,便为鬼神觑破,便是修行无力,非退藏密机。不肖于此颇见有用力处,亦见有得力处。日逐应感,只默默理会。当下一念,凝然洒然,无起无不起。时时覩面相呈,时时全体放下。一切称机逆顺,不入于心,所以终日交承,虽冗而不觉劳;终日论说,虽费而不觉扰。直心以动,自见天则。迹虽混于尘世,心若超于太古。[5](卷16《万履庵谩语》,P.588)
彭国翔先生结合这段龙溪自述以及李贽、张阳和、周海门等人的见闻评述,认为以此显示出龙溪通透圆熟的生命境界与人格气象,且无疑是龙溪不断实践其致良知工夫理论的最终结果。[14]在念庵,尽管与龙溪工夫取径不同,其晚年的体悟境界却在向龙溪所说的良知熟化境界不断趋进,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念庵于乡里主持丈田评议时,其修养境界在《松原志晤》中有一段表述:
虽甚纷纷,不觉身倦,一切杂念不入,亦不见动静二境。自谓此即是静定工夫,非止纽定默坐时是静,到动应时便无著静处也。[11](卷8《松原志晤》《P.181)
至此,念庵已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楚山悟道之后兢兢业业葆任心体的工夫阶段迈进到打通动静、依心体而自如发用之境。对此,龙溪打消了对念庵偏于“枯静”的担忧,所谓“是心康济天下可也,尚何枯静之足虑乎?”然同时又指出念庵“终日应酬,终日收敛安静”的工夫“终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无为之旨也。”[5](卷2《松原晤语》,PP.282-283)从此至去世的两年间,念庵学又有进,其去世前两个月,《别周少鲁语》一书云:
落思想者,不思即无;落存守者,不存即无。欲得此理炯然,随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来,此中必有一窍生生,夐然不类者。言此学常存亦得,言此学无存亦得。常存者非执着,无存者非放纵,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幸至也,却从寻求中由人识取。[11](卷8《别周少鲁语》,P.165)
念庵弟子胡直认为这段所述为念庵临终前所臻境界的自道。“不由思得”、“不由存来”,是说致知之功不落入分别知解而能直接安住于良知心体。同时,这种“安住”又是自如无碍的,无须有刻意的收制、存守之功,故云常存、不存而存。此“不存而存”的自如地步,已很少看到“收摄保聚”的工夫痕迹,诚如胡直所论:“读末岁告少鲁之语,则知真得之余,工夫不足言”,[15]此与阳明所臻“开口即得本心”、龙溪所谓“天机盎然出之,不落矜持”[5](卷3《水西精舍会语》,P.297)的道德化境相望,而其“随用具足”亦与阳明学“因用见体”的致思进路颇相一致。故胡直谓其师“已骎骎乎达天德、入圣域,若未见其止也,矧窥其际乎?”[15]可以说,念庵临逝前已基本脱去了工夫痕迹,会得良知化境,进一步泯合了与阳明、龙溪究竟工夫-境界的差距。只惜念庵早逝,似于圆熟境界稍逊一筹,否则,或可消弭与龙溪之争?
嘉靖三十四年(1555),念庵、龙溪同往楚山静修,后龙溪先返。二人临别时,念庵《别龙溪次韵》云:“稽山门下人多少,学术将谁得最真?”[10](内集卷8)的确,几十年往复的学术论辨,背后正寄寓着“谁得良知之真”的扣问。应当说,二人发挥了阳明致良知教“性之”与“反之”的不同层面,诚如龙溪所云:“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故曰:善学者默体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5](卷8《致知难易解》,P.399)毕竟,此心同,此理同,人性的“终极的自我转化”⑧之路通向同一个天德流行之境,念庵与龙溪之学,各依“自得”,殊途同归,两不相妨也。
[1]杜维明.论儒家的“体知”——德性之知的涵义[M].//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14-128.
[2]杜维明.内在经验:宋明儒学思想中的创造性基础[M].//杜维明文集:卷4.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102.
[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梁漱溟.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M].//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4.
[5]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Z].//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98.万历十五年萧良干刻本.
[6]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M].万历四十四年陈于廷序刊本.
[7]福田殖.罗念庵的“学三变”和“三游记”[J].浙江学刊,1989,(4):23.
[8]福田殖.羅念庵の「冬遊記」について——王門における講学活動の一場面[J].(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1994,(第6号):8.
[9]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2[M].万历四十三年丁宾、张汝霖刻本.
[10]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M].隆庆元年胡直序刊本.
[11]罗洪先.念庵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册127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2]耿定向.观生记[Z].//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册50.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6.
[13]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M].//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17.
[14]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5.162-168.
[15]胡直.念庵先生行状[M].//衡庐精舍藏稿: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册1287.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37.
⑧杜维明将宋明理学的宗教性表达为:“不断进行作为一种群体行为的终极的自我转化”。见氏著《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杜维明文集》卷3,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320、325页。
(责任编辑:朱晓江)
AComparativeStudyofthePracticeApproachesoftheYangmingScholarsWangLongxiandLuoNian’an
ZHANG Wei-h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The intellectual disputes between Wang Longxi and Luo Nian’an are studied in the scenario of their different personal “experience” in attaining the innate knowledge, thus to sort out their difference in problem setup, practice approaches, and way of expressions. Their difference is found i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innate conscience that led to their difference in express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same, resulting in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Yangming School by two approaches of practice to attaining innate knowledge, respectively sudden enlightenment (dunwu) and gradual cultivation (jianxiu). On the other hand, with his gradual practice in attaining the innate knowledge, Luo Nian’an went beyond his metaphase inclination of “maintaining quietness” to recognize the approach of unity of innate conscience and practice. Toward the end of his life, Luo Nian’an attained a refined state of innate conscience, implicating the same destination that both sudden enlightenment and gradual cultivation can achieve.
Wang Longxi; Luo Nian’an; Wang Yangming; Yangming School; attaining the innate knowledge
2009-12-10
张卫红(1970-),女,河南三门峡市人,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B248.2
A
1674-2338(2010)01-00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