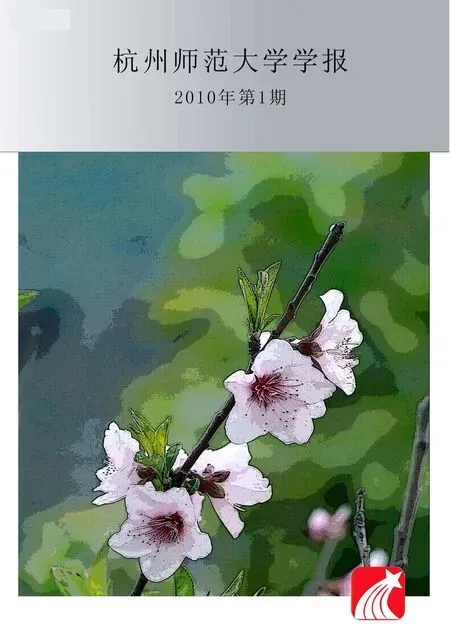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刘半农的通俗小说理论和创作(1913-1917)
姚 涵
(上海政法学院 新闻传播与中文系,上海 201701)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刘半农的通俗小说理论和创作(1913-1917)
姚 涵
(上海政法学院 新闻传播与中文系,上海 201701)
围绕刘半农在民国初年(约为1913-1917年)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可以看出其对通俗文学理论的理解及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的创作特点。刘半农着力从启发民智、提升小说艺术品格等方面展开了他的通俗小说创作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他对文学形式的兴趣及其对通俗文学艺术表达方式的自觉,为他其后转向民间文学寻求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半农;通俗小说;“民初小说”;民间
晚清与五四之间,存在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1912年至1917年,我们姑且将其命名为“民国初年时期”。以往文学史的叙述中,这是一个受到晚清文学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双重挤压的时期。单就“小说”而言,创作和出版数量相当可观,乃继晚清之后的第二个小说繁盛时代。但因前有晚清,民初小说创作又存在混乱芜杂以及创作成就普遍不高的现实,研究者往往将民初小说看作晚清小说的“尾巴”——类似“晚清民初”、“清末民初”的归类法的流行,其实可能正忽略了民初小说的独特之处。理解“民初小说”的环境,是理解刘半农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前提,但对于“民初小说”的理解,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杨义认为:“清末小说是启蒙的,企图参与社会政治的进步,境界开阔而粗豪;民初小说则是媚世的,只求描写生活琐事以博读者的笑谑和伤感,境界狭窄而酸软。”[1]这种看法将民初文学与晚清文学作了区分,但却忽视了“民初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在杨义的论述里,小说由清末到民初,其功用由“启蒙”到“媚世”,几乎就是一个“堕落”的过程。
若遍查当时的各类小说文本,确实参差不齐、良莠共存。一部分创作连同发表的刊物,很大程度上都存在取媚、低俗的倾向,这与民初文学的商品化、市场化特质有密切关联。另外一些小说,则部分接续了晚清小说革命的思想,虽然不是高雅小说,但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所创新,正是这一部分小说创作,为五四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准备。
有学者认为:“以小说界的革命为例,晚清小说界革命一退潮,民初小说就已经明显地向传统回归了。”[2]仅从小说的语言形式看,的确存在这样一种趋向——白话小说的比重在民初小说中逐渐降低,文言小说则越来越多。*参阅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第六章第一节相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曾就此问题作解释,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引起注意:他引用《小说林》徐念慈的报告,认为向“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是民初小说的一个重要任务,“既然小说要面向‘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当然文言就成了时尚。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如办《小说时报》的陈冷血与包天笑等人,他们过去也是在很多场合中使用白话为工具的,今天看到旧学界对小说的青睐,那么通过向士人灌输新知,再通过他们去做更广泛的宣传,也不失为是一条普及的新路,也就自然加大了文言的力量。”[3]由此看来,一部分民初小说的创作,包括刊物的创办,乃是以“回归传统”的方式去实现传播晚清文学革命思想之目的。这种回归实际上成了一种迂回的前进,它在“普及新知”的同时,也为五四新文学革命做了一些铺垫。
刘半农身处特定的文学时期,其文学也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就其早期文学观而言,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重视小说的道德力量和价值,乃是其重要元素。具体来说,他特别重视小说的知识性和认识价值,强调小说对世道人心的有益影响。认为要真正使小说具有影响社会的善的力量,除了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上应有所追求外,重要的是作家应该具有道德完善的人格力量。因此,他之称赞福尔摩斯,乃在于其人的道德人格之功;他之对中国从前的那些小说家痛加挞伐,乃在于责任感的缺失。在这里,我们似乎已能看到刘半农后来转向“新文学”的潜在思想动因。
“启发民智”:小说的功用
刘半农是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由于他早期的小说理论和创作与通俗文学的取向有着密切关系,与鲁迅、胡适、茅盾等的小说理论存在某些差异,迄今为止,其理论、创作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研究。实际上,刘半农早期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对于通俗文学的改良创新及艺术品位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通过他的小说理论,可以发现通俗文学不同于新文学的审美观念及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而他本人,正是在通俗小说写作和理论研究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源。这段时期就其个人而言,或许可以看作五四文学的“准备期”。
1913—1919年,进入文坛伊始,半农发表了40多篇著译小说,创作涉及“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滑稽小说”“哲理小说”“政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多种类型。1915年后,刘半农逐渐向新文化运动靠拢,先后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致钱玄同》《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复王敬轩书》《中国之下等小说》等文,正如后文将要论述的那样,这些文章的理论来源,大致可以推至刘半农创作通俗小说时期。
半农曾与包天笑、张恨水、周瘦鹃等交往甚密,其小说翻译与创作也大多发表在鸳鸯蝴蝶派所主持的刊物上,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这一点不难理解。实际上,鸳鸯蝴蝶派本来就不是《新青年》或《语丝》那样联系紧密的“同人团队”,也没有宣言、声明,但它大体上代表了其时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一派;*由于此派所作也并非单一的言情小说,研究界更倾向于将此派称作“民国旧派”或“《礼拜六》派”。本文沿用“鸳鸯蝴蝶派”之旧称,用意在于以其指代言情乃至哀情一类的小说。而半农的通俗文学创作和翻译,与鸳鸯蝴蝶派“言情”风格存在区别:虽然也创作或翻译了一些哀情小说,但由于对“情”的不同理解,半农的一些小说所写之情并非仅限于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情感。他并没有在“言情”乃至“哀情”的路向上有更多的追求,可以说,他的文学兴趣并不在此。
“鸳蝴派”文学一直被新文学作家批评为消遣、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文学,半农值得注意之处,恰恰在于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特别注重。与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时,他认为,柯南道尔的创作宗旨是“以至精微玄妙之学理,托诸小说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笔而至出。于是乎美具难并,启发民智之宏愿乃得大伸”。[4]与其说这是柯南道尔的创作宗旨,不如说这是刘半农的通俗小说理念。需要强调的是,“启发民智”是刘半农极为重视的文学功能,也是刘半农小说观的核心,这与五四文学的启蒙主潮是相一致的。但刘半农所说的“启发民智”,与鲁迅、陈独秀等人又有所不同:刘半农所说的“启发民智”,更为关注人的知识、理想、人格等层面,虽然这些层面也关乎人的觉悟及个性的精神,但更侧重对“人心”的构建以及对社会、人格的教育作用。
刘半农的文学功用观与通俗小说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他是在通俗小说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来理解“启发民智”的。概括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点。
强调小说的知识性和认识价值。
刘半农在评价福尔摩斯的创作时认为,他的小说虽非正式的教科书,但却隐含着教科书的功能——“即言凡为侦探者,对于政治上之知识,可弱而不可尽无也。言其于植物学则精于辩别各种毒性之植物,于地质学则精于辩别各种泥土之颜色,于化学则精邃,于解剖学则缜密,于记载罪恶之学则博赅,于本国法律则纯熟,即言凡此种知识,无一非为侦探者所可或缺也。”[4]教科书的比喻,源自晚清时期对于侦探小说的广泛定义。袁进将之称为一种“现代科学精神”,认为这“正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刘半农翻译《福尔摩斯探案》的主张说明了他将柯南道尔视为“启蒙小说家”。[5]
翻译《福尔摩斯探案》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之后刘半农很快创作和翻译了很多侦探小说,如《匕首》(《中华小说界》1卷3期,1914年3月1日)、《淡娥》(《中华小说界》2卷11期、2卷12期续载,1915年11月1日)、《一身六表之疑案》(《小说大观》,译自英国柯南达里4集,1915年12月30日)、《铜塔》(译自英国威廉勒苟,《小说大观》6集,1916年6月)、《日光杀人案》(《小说海》2卷12期,1916年12月1日)、《髯侠复仇记》(译自美国Morman Mnnro《小说大观》8集,1916年12月)、《猫探》(译自美国梅丽维勒,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4月版)。
《匕首》主人公老王是一位中国公案小说中的捕快式人物,有着传统的道德与智慧,但是刘半农又赋予了他很多新的精神特质——破案时重视证据、取证确凿、推理严密,俨然将其塑造为类似西方私家侦探式的东方侦探,在曲折、悬疑的情节发展中显示了老王的智慧与果敢;《日光杀人案》中的案子以物理学的原理来侦破,侦探在分析“日光”、“凸透镜”、“火药枪”之间的关系时,层层递进、分析归纳,让罪犯无法反驳,力图显示破案者科学求实的精神。
刘半农之所以喜欢翻译、写作侦探小说,与“科学”精神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些知识既是小说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对科学知识的普及。
同时,刘半农还特别重视小说对社会的认识作用,他认为各就所见的世界,绘一维妙维肖之小影是小说家最大的本领之一。他特别推崇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作品,对下等小说也给予特别的称赞:“你看跑堂的、街流子、买卖人、手艺人,人品多在中流以下,而且全用讥嘲口吻去描写。他能把各人的身份,一一写得适如其量,半点不乱,半点不相混杂,这不是文学上绝大的本领么。所以我要下一句断语,凡要研究中下等社会的实况的,不可不研究这第三类的下等小说。凡是要制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使今后之文学与今后之世界趋于同一之轨道的,尤不可不研究这第三类的下等小说。”[6](《中国之下等小说》,P183)在这里,刘半农提出“制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实际上是将通俗文学当作新文学值得借鉴的文学资源之一。
对世道人心产生有益的影响。
辛亥革命失败、民初政治动荡,很多文人发出时代哀音,其中被反复重复的就是那一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断语,这一时期很多刊物发刊词上都能看到类似“挽回末俗”、“输荡新机”的字样。与其说这是对小说理论的阐发,倒不如说是对小说道德功用的宣扬。然而,小说与道德关系密切,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只有在特定的时代,小说与怎样的道德联系在一起,这一问题才值得深入探讨。
民初时期关于小说道德作用的口号很多,可是这一时期需要“挽回”怎样的“末俗”,“输荡”怎样的“新机”,很多民初刊物和小说都语焉不详。刘半农从传统通俗小说“劝善惩恶”的特征出发,在《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一文中论道:“题中‘教训’二字,是说此项小说出版后,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如何。所谓‘积极教训’,便是纪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羡慕心,摹仿心;‘消极教训’,便是纪述恶事,描摹恶人,使世人生痛恨心,革除之。”[6](PP.137-138)他还认为,要使小说真正能有影响社会的善的力量,除了写作技巧,重要的是要有道德完善的人格力量——他称赞福尔摩斯的,正是他的道德人格之功。他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跋”中认为,侦探应当有人格、有道德、不爱名、不爱钱,而在当时中国的侦探小说中,这样的侦探形象并不多见。因此,他创作的侦探小说就特别注重塑造那种有智慧、有人格的形象。
当然,从小说理论角度来看,这些论述并没有很出众的见解,但可以从中发现,刘半农对于文学的理解始终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因此,其小说理论的关注点自然也落在“人”之上。
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一些缺乏责任感的小说家痛加挞伐,进而指出传统通俗小说的种种流弊。归纳如下:第一,捧皇帝的思想;第二迷信鬼神的思想;第三,崇拜状元的思想;第四,伦理思想;第五,诲淫诲盗的思想;第六,怜悯妓女的思想;第七,厌世思想;第八,革命思想;第九,促动妇女自杀的思想;第十,滑稽思想;第十一,对于贫富不均的思想;第十二,对于外国人的思想。*详见刘半农《中国之下等小说》和《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二文。其中认为,“促动妇女自杀的思想”是下等小说中最为恶劣的思想。
不难发现,这些对通俗小说流弊的认识,也都围绕着“人”来展开,关乎人的思想、精神的方方面面。这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时代命题正是相通的。刘半农从通俗文学中发现了通俗小说不能写什么——那些“非人”的因素,恰恰属于五四文学革命所要摒除的内容。
刘半农重视文学对“人心”的陶冶作用,这一理论主张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和翻译中。
当时的上海文坛,“鸳蝴派”、“黑幕派”盛行,刘半农的小说创作也难免惹了些“才子气”,“时有‘哀艳’和‘滑稽’的成分,不乏笔记小说的俗套,仿佛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就他在《小说海》《小说界》《小说丛报》《小说画报》《小说大观》《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的40多篇著译来说,还是比较注重社会意义和文学意味的。首先,他的作品多以翻译外国名著为主,丹麦安徒生、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美国夸德氏、美国柯南达里的一些作品,都经过他的笔介绍给中国读者。其次,在一些小说中,他也能较为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广大劳动群众的疾苦,具有些许现实主义的因素。”[7]这种现实主义的因素,即使在他的“滑稽小说”和“情感小说”中,也是存在的。*参阅刘氏创作《财奴小影》(《中华小说界》第8期),译作《默然》(《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0期)等作品。
半农早期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强调小说应启发民智、有益人心,这一特点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后来能够转向新文学阵营,思想基础也在这里。
小说艺术品格的提升
受时代责任感的驱使,半农在《通俗小说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一文的结尾处说:“我今天所说的话,自己也知道意思很肤浅,且大有老学究气息;然为目前时势之所需要,不得不如此说。”[6]文体建设的自觉意识,促成了他对于现代小说理论的最初思考。1917—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小说组曾举办过三次关于小说的演讲,即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刘半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以及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三篇演讲被研究者称为“对现代小说理论的最初探讨,也是奠基之作”。[8]显然,胡适的小说理论主要移植西方短篇小说理论,周作人以日本小说为仿效摹本,刘半农的研究强调从本土小说内部发掘资源。关于如何改良中国的“下等小说”,刘半农的论述也是与通俗小说、下等小说的艺术经验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重视下等社会的生活经验。刘氏提出:“我辈要在小说上下功夫,当然非致力于下等社会之实况之描写不可。这下等社会之实况之描写,凡未在做小说时尝过甘苦的,多把它看得很容易,以为下等人之生活思想,异常简单。把我辈文人的思想刻画他,才无不像之理。不知心中有了这含有绅士派臭味的念头,他的著作,便万万不能与下等社会的真相符合,真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今欲采求下等社会之真相,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便是自己混入下等社会,求直接的经验。第二,求之于下等小说,间接的以他人之经验为经验。”[6](《中国之下等小说》,PP.181-182)在半农看来,好的小说创作离不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获取,作家应当重视下等社会的生活经验。这实际上是对本土文化经验的一种强调。
半农还认为,小说家的最大本领“第一是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如施耐庵一部《水浒》,只说了‘做官的逼民为盗’一句话,是当时虽未有‘社会主义’的名目,他心中已有了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托尔斯泰所作社会小说,亦是此旨。……此外如提福之《鲁滨生》一书,则以‘社会不良,吾人是否能避此社会?’及‘吾人脱离社会后,能否独立生活?’两问题,构成‘人有绝对的独立生活力’的新世界……虽各人立说不同,其能发明真理之一部分,以促世人之觉悟则一。”[6]由此,半农阐发出有关小说创作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把下等社会生活经验的真实体验与提炼看作小说生命的根本;二是作家要有独立思考、发现真理的能力。
20世纪初期的小说创作,特别是1919年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主要为两种力量所控制:一是西方翻译小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采用意译方式介绍的西方作品;二是一些“文人”创作的鸳蝴派小说和“黑幕小说”。这两者与中国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均存在很大距离,对此,半农亦有同感。1914年,通过《匕首》的“弁言”,半农阐发了关于“侦探小说”的观点。他认为,中西社会存在很大差异,中国读者阅读西方侦探小说必然存在很深的隔阂。由此小说创作应注重从下等社会中去求直接的经验,或以他人的经验为自己的经验,避免用“文人”的先验观念去描写下等之社会。更进一步来说,这不仅仅是别致的见解,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立场”或者说“知识分子立场”的民间写作立场,即以平民百姓的生活经验和逻辑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逻辑的写作原则。在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中,刘半农同样秉持这样的原则及创作态度,显示出与启蒙文学不同的特点。
刘半农早期小说大多关注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他的大部分作品发现了底层生活的某些真实状态。“吮痈舐痔”的某部次长、“乡曲小皇帝”的县令、“无殊中古时代之教王”的传教士,纷纷出现在他的小说《稗史罪言》中。在关注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中,半农获得了接近“下等社会的真相”的可能性,这对于其后的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积累。
对下等社会生活经验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下等人生活内容的细致观察、精确表现上,同时也表现为对其文学接受经验的重视。夏曾佑曾将“曲本”“弹词”等“与小说合流”的民间艺术形式归为“有韵”之小说,他认为这些小说的弊端就在于必写“君子”“大事”“富贵”“虚无”,他进而将中国小说分为两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9]我们或可从读者接受角度,将夏曾佑此处的分类,理解成精英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分立。在他看来,为了让“妇女和下等人”读懂小说,通俗小说家无法避免运用粗浅笔法,这就体现了其小说理论的局限。刘半农对小说艺术品格提升的有益尝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剔除下等小说的陈腐内容。因此,半农小说几乎很少写“至好之人”成就“平番、救主”的大事,也无“高中状元、拜相封王”的富贵气象,更无“骊山老母、太白金星”等神仙鬼怪。他的早期作品多以较为单纯的结构、明白易懂的语言来写作,既照顾了平民读者的接受水平,同时也尝试着提升他们的阅读品味。
通过刘半农的小说理论和创作,不难看到他后来五四时期诗歌创作所体现的那种明确、自觉的“民间写作立场”。所谓“民间写作立场”,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表达老百姓的思想感情。重视下等人的生活经验,从下等人的生活中发现创作内容,其间包含着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尊重与理解。刘半农自觉地与“绅士”拉开距离——如同他后来写诗却不愿承认自己是“诗人”一样,*半农不屑于为做诗而做诗,他认为“诗人”一旦成为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参见刘半农《〈扬鞭集〉自序》,《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页。有如此的自我认同,才可能与“下层”发生深刻的联系。与底层的隔膜一旦被打破,思想就不再是先验的,也就具有了发现问题和领悟真理的能力,作品也因此具有了鲜活的生命气息:“侦探小说”中的“智慧”与“科学”、“社会小说”中的“现实”与“批判”、“哀情小说”中的“情感”与“体悟”……,这些发现都构成了半农对文学的个性化理解。民初小说创作,是半农理解文学的最初阶段,他从创作和理论探索中获得了什么、如何理解文学的意义,这实际上构成了他对文学整体性理解的起点,并在五四时期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其次,半农的小说理论和创作,特别重视小说情感的自由表达。他认为:“言为心声,文为言之代表。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6](P.117)他进一步说道:“至于吾国旧有之小说文学,程度尤极幼稚,……试观其文言小说,无不以‘某生、某处人’开场。白话小说,无不从‘某朝某府某村某员外’说起。而其结果,又不外‘夫妇团圆’、‘妻妾荣封’、‘白日升天’、‘不知所终’数种。”[6](P.117)其实,在通俗小说创作之初,半农也没有完全摆脱文言小说的影响,一些章回体小说也采用了“某生”体的写法,直到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他才从形式上超越了文言小说的程式。
形式上的改良,一旦付诸创作,就不再仅仅停留于形式层面,它必将与小说所要表达的精神、情感产生互动。半农显然更加看重“真挚自我情感”的表达,试图以此来推翻已模式化的旧有文学传统。他认为:“以古人古事为世间独有之学问的观念,也是人类知识未完备时所共有的……这种好古的心理,就学问与知识的全体上看起来,当然不能消失其存在的地位。若就普遍社会的教育问题上设想,则非用十分坚强的毅力把这种心理完全打破,恐怕思想上物质上的文明断断不能输入,社会断断不能进步,文化断断不能发达。”[6](P.117)那么,在文学观念上如何打破这种好古的心理呢?“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代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6](P.117)
由此可见,打破以往小说的束缚和模式,创造新的文学世界,在刘半农的小说理论和创作中具有实践性的意义。要打破传统的“模式”,必须争取“自我表达的自由”。半农十分重视小说情感的自我表达,其文学实践意义就在于,他的小说往往有多样化的文学情感和多样化的文体表达方式。就多样化的情感表达来说,半农小说中有幽默、机智和诙谐,也有批判、痛苦和哀伤;从小说形式看,他的小说的多样化体现为结构上的多样化及叙述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角度的小说,往往能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情感。对于个人情感自由表达的重视,必然带来小说文体审美形式的变革,这一点构成了刘半农早期小说理论的又一重要方面。而这种自由观的确立,在五四时期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白话诗理念,简单概括就是“真与自然”。
第三,关于文体审美形式的变革。钱乃荣评价20世纪最初20年内短篇小说创作实绩时说:“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刘半侬的作品,刘半侬是很早用白话写了不少短篇,在学习西洋小说的写作手法方面是比较先行的,如《局骗》中对话里插入外貌描写心理描写,倒叙插叙的运用,预设悬念,细节描写等等。”[10]对半农这篇小说有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奇怪,这篇小说不仅有着真切的生活经验的表达,而且呈现出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非常不同的结构形式。叙述者“我”的确立,突破了传统通俗小说一般的“说书人”叙述,文体审美形式的变革影响了他对于中国通俗小说和下层小说的看法。
在半农看来,通俗小说、下等小说有许多有价值的地方,但在“怎么写”即文体的审美形式方面,却存在很多问题。他在谈到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和消极教训时说,做积极小说比做消极小说难百倍,原因如下:1. 我们眼光中所看见的社会,好人少、坏人多;2. 好人是不能单独多的,必须有坏人衬托,然而写坏人易,写好人难;3. 人的性情是喜谈人短,恶说人长的。[6](P.143)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刘半农认为首先应该从“写法”上下功夫,也就是在小说的结构上要有所变化,表达方式上要有所调整。由此,他概括了五种方法。*第一是化消极为积极;第二是以消极打消积极;第三是以积极打消积极;第四是以积极打消消极;第五是消极积极循环打消。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144—145页。
细述这五种方法时,半农大多依照西方小说的表达方法,但他并不主张完全用西方小说的写法来代替中国通俗小说的写法,而是主张在保持中国小说独特优点的同时,用西方小说的方法改良中国小说的弊端。这样的思路在他对中国下等小说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明晰。他认为,中国的下等小说从文体上分类,约有三种:第一种是说白与唱句夹杂。其唱句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长短句,而尤以七字句为多;第二种是俚曲或小调;第三种是近乎韵文的散文。要改良这些小说,当从韵文入手,因为目下爱看这类小说的人都还以韵文为小说的美。他进一步分析这类小说所运用的材料时说,这类小说所用材料大约分三类:第一类是杂凑无理的,全无意识的东西;第二类是有所本的,其来历不外乎经、史、小说、时事、戏剧。这类小说占了下等小说的十分之五六,但好的极少。绝好的材料经不高明的小说家的演绎被糟蹋得污浊不堪。当然其中也有条理井然、秀丽可爱之作;第三类是凭空杜撰的,便是社会的下等小说。刘半农对社会的下等小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类小说对社会、人物的精细描写、下等生活经验的真切表达是所谓“文人”做不出来的。
由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半农对小说的文体形式、表达方法等特别重视。具体地说,他主张小说要有下等社会生活经验的真切表达,要用良好的结构形式处理材料、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文体审美追求在对《海上花列传》一书的分析中体现得更为清楚。他认为《海上花列传》好就好在首先笔法新奇,结构上运用穿插藏闪二法十分神妙;其次是描写事物的手段高明,作者有冷静的头脑,精密周全的观察,能写出社会生活的真相。[11]
半农从以上几个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和下等小说的理论主张。半农早期小说理论内在地包含了与传统亲近的态度,这样自觉的意识使得他在向西方小说学习的过程中保持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传统。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半农的小说理论是如何保持传统的。
半农并不是彻底而极端地反传统,而是在承认传统和现实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良。在这一文学态度的指引下,他保持了对现有文学的某种认知。我们很难对这种改良式的文学观和那种彻底革命的文学观作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但不难想见,“改良”虽没有“革命”那么激烈,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同样十分巨大。这两种文学观念和态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刘半农始终立足本土文学环境,他的小说理论因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对下层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学表达方式的重视。实际上刘半农在早期的小说创作和其后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一直都坚持着这样的立场,他的创作大都以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生活逻辑为主要的创作内容。以这样的写作原则为引领,他特别重视民间文学、传统文学的有益内容,不是用欧化的语言表达舶来西方的思想,力求在对民众生活的认知和表达之中发现某些价值。因此,半农的创作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有很大的区别。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资源持续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打断或改变我们既有的审美经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保持自己的文化、文学个性,刘半农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视点呢?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6.
[2]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M].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18-19.
[3]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2.
[4]半侬.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M].//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上海:中华书局,1916.
[5]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29.
[6]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7]徐瑞岳.刘半农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80-81.
[8]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4.
[9]别士.小说原理[J].绣像小说,1903,(3).
[10]钱乃荣.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前言[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6.
[11]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M].//半农杂文.北京:星云堂书店,1934.227-284.
(责任编辑:朱晓江)
OntheNewStartingPoint:LiuBannong’sPopularFictionTheoryandWritingPracticeduring1913-1917
YAO Han
(Department of News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This paper centers on Liu Bannong's theory and writing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years (1913-1917).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enlighten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iction, Liu began his popular fiction writing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Liu’s interests in literary form and expression approach of popular literature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later creation in folk literature.
Liu Bannong; popular fiction; “novel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years”; folk
2009-06-11
姚 涵(1979-),女,安徽安庆人,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I206.5
A
1674-2338(2010)01-01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