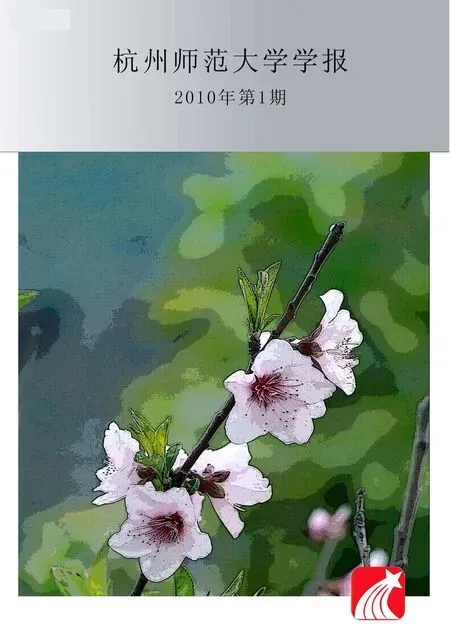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的阐释及其评价
段怀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的阐释及其评价
段怀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尽管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之影响,但他比较自觉地使用“文艺复兴”理念来阐释现代中国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运动,在时间上相对集中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及50年代。在具体内容上,其“文艺复兴”理念一方面是以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现代文艺复兴”,另一方面是从11世纪开始直至现代中国、持续近千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但胡适对五四新文学在理论上的阐释语境,从20年代到50年代,发生了一些位移,就是从绝对的五四新文学中心观,向世界新文学(现代文学)和新文化(现代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扩展,并最终落脚在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本土意义与价值的调适之上,并以新文学与新文化的本土化适应与生成结果作为新的文化理念诉求。
胡适;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学
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或者“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西方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已有不少论述。其中有关《文学改良刍议》与美英20世纪初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主张之间的关系,既有朱自清、梁实秋的说明于前且已广为人知,亦有不赞同的阐释矫正于后,此不赘述。*参阅沈永宝《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文学改良刍议〉探源——胡适与黄远生》,载《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试论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成因》,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而胡适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于胡适白话文学主张、文学改良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启发促进与信念支撑,相较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之于胡适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丰富深沉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味及意义。而检讨胡适在几个不同时期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进行的类比,不仅可以发现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形成过程中西方文学历史语境的“潜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并理解胡适对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所作的历史评价及定位。
一
胡适从来就不忌讳谈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相似,或者干脆就在两者之间进行公开“类比”,相提并论。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二是20世纪50年代。前者以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发表的题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系列演讲为标志,后者则以他50年代从美国来到台湾后所发表的系列公开演讲以及晚年口述自传为标志。
但胡适最早提及文艺复兴,是在1917年6月19日,当时他正在自美返国、途经加拿大“落机山”的旅程中:
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时代》(Renaissance)。“再生时代”者,欧史十五、十六两世纪之总称,旧译“文艺复兴时代”。吾谓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也。[1](P.600-605)
在这段读书札记中,胡适还特意写明“书中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皆足供吾人之参考,故略记之”[1](P.605)。而此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已经发表于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他的另一篇重要的阐明文学改良主张的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也已发表于同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所以当胡适7月6日返国途经日本东京时,听人说此处有《新青年》售卖,遂前往购得一本。“在东京时,虞裳言曾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因同往买得一册。舟中读之。此册有吾之《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本为致陈独秀先生书中一节),及论文学革命一书。”[1](P.614)这也就意味着,胡适在产生并形成最初的文学改良主张之前,或者说在与留美同学、尤其是梅光迪、任叔永辩论中国文学的所谓死文字、活文字时,对于欧洲文学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完整的知识,甚至连最基本的了解都是不足的。但这仅限于《文学改良刍议》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二文。因为在1917年6月19日的日记中(也就是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发表1个多月之后),胡适对所读文艺复兴著作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文学复兴部分作了特别记载:
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学者著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罗马之旧畿,故其语亦最近拉丁,谓之拉丁之“俗语”(Vulgate)。
“俗语”之入文学,自但丁始。……其所著《神圣喜剧》(Divine Comedy)及《新生命》(Vita Nuova),皆以“俗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
……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国之俗语文学,其发生久矣。自宋代之语录,元代之小说,至于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话犹未成为国语。岂不以其无人为之明白主张,无人为国语作辩护,故虽有有价值的著述,不能敌顽固之古文家之潜势力,终不能使白话成为国语也?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阅读“文艺复兴”一书时的读书札记中的观点感想,不仅迅速地落实在他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四卷四号)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更成为他后来将新文学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的思想基础。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就曾经这样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辩护: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能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他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2]
相较于自己在《新青年》上发表探讨文学改良主张的论文,胡适似乎更看重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和思想精神的导师而对于《新潮》知识分子们的影响。所以在毫不吝啬地夸奖《新潮》知识分子群之时,从来没有忘记当初是由他自己将《新潮》的英文译名确定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
在学生办的刊物当中,《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他们那个刊物,中文名字叫做《新潮》,当时他们请我……定一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他们认为这和欧洲在中古时期过去以后,近代时期还未开始,在那个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相同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此为胡适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后收录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台北:台北文艺协会编辑,1961年5月),转引自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0月。
而在其晚年口述自传中,胡适再次提及当初《新潮》杂志编辑者将“新潮”的英文名称确定为“文艺复兴”是受了自己的影响。“他们请我做新潮社的指导员。他们把这整个的运动叫做‘文艺复兴’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他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3](P.185)
胡适有关《新潮》英文译名及与文艺复兴之关联的解释中,至少有两点尚待考证。
其一是《新潮》在发刊词中,并没有将“文艺复兴”作为自己创刊之根本宗旨。其《发刊旨趣书》中有关“文艺复兴”之说明,也看不出《新潮》初创时对于其旨趣的阐明与胡适后来所解释的“文艺复兴”之间在具体内容上有多少共同之处。这篇由傅斯年执笔的发刊旨趣书中关涉“文艺复兴”一段是这样写的:
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而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新潮》1919年1月创刊号发刊词,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
无论是从文字内容中,还是结合上下文之语境,《新潮》发刊旨趣中对于“文艺复兴”的涉及,仅限于此时代学者与世界魔力之无畏之战,并以此来鼓舞砥砺《新潮》同仁以及全国所有有志倡导思想新潮者之意志毅力。
其二是胡适自认为当时在国内学界,自己可能是最早认识到并公开倡导以文艺复兴意识来比拟并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并认为当时Renaissance一词在中国还没有适当的中文翻译,[3](P.186)其实不然。早在1915年1月,也就是胡适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文艺复兴”之前两年多的《吴宓日记》中,就已经数次出现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内容。在《吴宓日记》1915年1月5日中,初次出现关于“文艺复兴”的记载:
历史一课,文艺复兴之大变,极似我国近数十年欧化输入情形。然我之收效,尚难明睹。至于神州古学,发挥而光大之,蔚成千古不磨、赫奕彪炳之国性,为此者尚无其人。[4](P.381)
而在十天之后的日记中,吴宓又记载了一外教就文艺复兴艺术所作的演讲。“历史一课由Starr女士演讲Renaissance Art”。[4](P.388)在同月19日日记中,吴宓还记载了“考历史”试卷情况,其中有三题,均为论文,其一为“中国维新改革之实迹,与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比较”。[4](P.390)而在2月20日的日记中,吴宓更是围绕“文艺复兴”而有大段议论:
近读历史,谓世界所有之巨变,均多年酝酿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无一定之时日,示其起结。若欧洲中世纪之末,文艺复兴Renaissance其显例也。余以文艺复兴,例之中国维新改革,则在中国,又岂仅二三十年以前,新机始发动哉?盖自清中叶以还,或可谓自明末以后,士夫文章言论之间,已渐多新思潮之表见。导源溯极,其由来渐矣。[4](P.407)
而在同年10月5日日记中,吴宓甚至计划将来办一份报纸,其报名即为文艺复兴:“拟他日所办之报,其英文名当定为Renaissance,国粹复光之义,而西史上时代之名词也”。[4](P.504)
但上述两点所能够说明者,就是在胡适之前,国内知识界已经有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一般知识,尤其是当时像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清华学校)这样开设由外籍教师担纲的欧洲史或者欧洲文明史一类课程的学校,但这并不能够否定欧洲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胡适的特殊启发意义,也不能够否定胡适是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中最早将新文学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的人这一事实,尤其是对于两者的评价都是从正面和肯定的角度。
事实上,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之时,一直避免使用一些欧洲的文学史术语来界定这场发生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包括为他所关注并青睐的“文艺复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又是怎样总结这一新文化思想运动的意义的呢?胡适提到了陈独秀1919年初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到了这场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的运动的两大核心观念,即赛因斯(科学)先生和德谟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并为其解释道:因为后者,所以反对儒教,反对旧家庭传统,旧的贞操观念,旧的道德和旧的政治;因为前者,所以提倡新文学、新艺术和新宗教。[3](P.187)胡适自己同年底(1919年11月1日)也写过一篇《新思潮的意义》,将五四新思想运动的“根本意义”定义为一种“新态度”,也就是“评判的态度”。胡适引用了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句话,认为“这句话大概就可包括了我们这个运动的真义”。[3](P.187)但无论是陈独秀的文章,还是胡适自己对于五四新思潮意义的估价,都没有直接出现“文艺复兴”这一概念。
但是,在1926年发表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协会学报(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1月号的一篇英文论文中,胡适第一次将中国所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命名为“文艺复兴”。他的这篇论文的英文标题即为RenaissanceinChina。几年之后,他的另一篇英文论文更是使用了LiteraryRenaissance的标题。1934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有关现代中国文化趋势的系列讲演(此讲座于1933年举行)整理出版,同样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在这用书的自序中,胡适说:
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显地,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渐渐成了一件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The Chinese Renaissance(The Haskell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in 1933),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胡适另外一个比较集中地将新文学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的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学会”发表的演讲中说:
我这几年来,对外讲到这件事,认为这个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前年,……在加州加里佛尼亚大学教了五个月的书;……他们要一个题目: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5](《中国文艺复兴》,P.235)
就在这篇演讲中,胡适提出“我们这个文学的革命运动不算是一个革命运动,实在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阶段”,[5](《中国文艺复兴》,P.245)这是胡适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的评价以及他的“文艺复兴观”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之肇始:即淡化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的革命色彩以及外来色彩,突出它与中国近千年来文学-文化变革的历史连续性。但是,胡适的这一观点上的“转变”并不彻底,也不坚决。就在此前的1954年3月15日于台北省立女子第一中学的讲演中,他从语言的角度解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他说“所有用活的文学的国家都曾经经过这么一个时代。以欧洲来讲,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古文废了。欧洲的古文有两种,最古的是希腊文,其次是拉丁文……所有读书人都是用拉丁文著述、通信”。[5](《白话文的意义》,P.256)胡适旨在通过对于欧洲诸国对于拉丁文统治地位的颠覆和民族语文地位的恢复的解释,来说明五四时期以白话文来替代古文,无异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这都是在强调新文学-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相似性。而在1960年7月10日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所作的“中国传统与将来”的开幕讲演中,他又强调了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说中国传统演进过程中有一大进化时期,这一时期也可以被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或“中国的几种文艺复兴时代”。其中胡适列举了中国的文学复兴(在公元八、九世纪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当代”)、中国哲学的复兴以及中国学术的复兴。而在进一步阐释上述诸种复兴时,胡适说:
到了最后,中国已能做到一串文学的、哲学的、学术的复兴,使自己的文化继续存在,有了新生命。尽管中国不能完全脱掉两千年信佛教与印度化的影响,中国总算能解决自己的文化问题,能继续建设一个在世的文化,一个基本上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与将来》,载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27页。胡适在这段阐述中,强调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国文化本位思想,这与他早年所提倡的西方化思想以及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认识论方面都有些微的改变。
二
由唐德刚整理、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在内容编排上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地方,那就是该自传结束于“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而在此前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部分,也有一节专门内容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后者记述晚年胡适对于五四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类比,而前者则是晚年胡适将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作为近千年来中国文化思想复兴运动之一部分,构建出一个时间长达千年之久的民族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胡适晚年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的最集中、最彻底同时也是最坚决的一种阐述。胡适的这一观点,当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相反,在他晚年的演讲中早已有类似回应或者相近阐发。在1958年5月4日于台北“中国文艺学会”发表的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胡适这样描述40多年前的那场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的一般教授们,在四十多年前——四十多年前,提倡一种所谓中国文艺复兴的运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演,提起这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这个名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个人害病死了 再重新更生。[5](《中国文艺复兴运动》,P.234)
显然胡适在这里是将五四新文学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与当初那些对于这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命名相比,胡适更倾向于使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术语。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说过“我喜欢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而他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3](P.186)而在阐述当初《新潮》杂志之所以选择Renaissance作为它的英文刊名的缘由时,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指《新潮》编辑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3](P.185)那么,40多年前被胡适们所发起的那一场新思潮运动或者文学革命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之间究竟有些什么相同之处呢?胡适所给出的解释是,“我们如果回头试看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就知道,那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因此欧洲文艺复兴之规模与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之处”。[3](P.185)胡适对此进一步的解释是,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思想运动,都是从对“新的自我表达的工具”的需要开始的。这些新工具包括“新语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需要的新工具。而尽管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没有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艺术,但在文学领域,欧洲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极其相同”的。[3](P.186)也就是说,尽管五四初期,文艺的复兴还没有延伸渗透到诸多领域而仅限于文学,但胡适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作为这场文学运动的代名词。
但是,胡适又解释说这只是一种狭义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之间的关系。从第一次读到有关文艺复兴的英文著作开始,胡适对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起始就形成了一个更久远的时间概念。他说,“这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3](P.186)胡适认为,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并非自五四新文学开始,早在中国的元朝,也就是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一个活文学便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不幸的是(在明代)仿古文学再度出现之时,这个文学革命受到了挫折和限制。所以我说,如果这一个趋势未受到人为的故意地限制和压抑的话,一个中国文学革命便可能早已出现了。(其光彩)足以和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但丁(Dante),领导英国文学兴起的乔叟(Chaucer)和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现代德文翻译圣经而开始的现代德国文学等相媲美(亦未可知)”。[3](P.154)
而在初次读到文艺复兴的英文著作的日记中,胡适已经明确地将中国历史上古文与白话之争斗中的此消彼长,看成是为少数人所控制的所谓精英文学与更广大的国民所需要的俗语的、国语的文学之间话语权力的较量。而这样的较量,在胡适看来,已经在中国文学史上持续了千年:
从西历纪元一千年到现在,将近一千年,从北宋开始到现在,这个九百多年,广义的可以叫做文艺复兴。一次文艺复兴又遭遇到一种旁的势力的挫折,又消灭了,又一次文艺复兴,又消灭了。所以我们这个四十年前所提倡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过是这个一千年当中,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当中的一个潮流、一个部分、一个时代,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时代。[5](《中国文艺复兴》,P.235)
三
在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中,将“新文学运动”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有意识地联系起来相提并论,无疑在胡适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中,胡适具有最为强烈的“文艺复兴”意识或者“文艺复兴”情结。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这与胡适从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充分显示出来的世界意识和世界文学意识有关。换言之,胡适很早就在中国文学之外建立起来一个有益而且有效的西方文学史参照体系。在就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所强调的“批判的态度”所作的进一步阐释中,胡适曾经列举了这种态度所包含的四点内容,即其一是研究当前具体和实际的问题;其二是“输入学理”,也就是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我指出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3](P.188)其三是“整理国故”;其四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以及再造文明。[3](P.189)而对于上述四者之间的关系,胡适的解释是:“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的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3](P.189)
在上述四点中,胡适将“研究当前具体和实际的问题”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出发点,而后面的“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均是为解决前一个问题而提供思想理论之材料,即“输入学理”也罢,“整理国故”也罢,都只是手段而已,最终问题之解决,要落实在“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以及再造文明”之上。
其次,很长时间之内,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一直被它的敌人所诟病者,就在于后者认为新文学者们抛弃了中国传统价值和美德,他们所倡导的那些学说和思想,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而上述言论批判,不仅见之于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中国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的清算,亦见之于几乎同时在大陆所发起的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运动之中。也就是说,不能不与上述时代舆论环境相关联的是,从50年代直至去世,胡适是在一种更为小心的严格的历史联系上来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的。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作为传统文化最主要载体的文言抛弃并大量输入西方新学理、新观念和新学说的同时,五四新文学同样也面临着这样一种指控,那就是它的非民族的、非历史的、全盘西化的立场。而对此,实际上胡适早在最初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因此他所强调的,并不是片面的作为中国的他者而存在的西方的新学理、新观念和新学说,而是包括近千年来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当中一直就存在着的白话文学,这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或者中国文学和文化再造的重要语言资源。正如他所言,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为了推动一种用人民的活语言(而不是像那些批评者们所指责的那样只借用其他民族国家的语言)的新文学去取代旧古典文学的有意识的运动”,[5](《中国文艺复兴运动》,P.235)或者说,这场运动只是近千年来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代延续,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这场持续千年的民族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高潮或者尾声。也因此,这一运动根本上讲并非外来的或者否定传统的,而是一场民族文化本位的、通过输入新学和整理国故来对传统进行清算,并在此基础之上达到并实现民族文化之再生和复兴的运动。如果说胡适早年在其《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国与日本的西化》等文中强调了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的话,上述强调并不是以牺牲或者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或者代价的,也不是简单地通过古老文明的再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来实现的。而可供创造这种新文明的思想资源,不仅存在于异域文明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古老传统之中,忽略其中任何一个资源,这样的新文明创造无疑都是存在缺陷的。而胡适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观或者文艺复兴观,不过是“依据”时代语境,在上述两种语言资源之间进行微调互动而已。
[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卷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胡适.逼上梁山[M].//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6-147.
[3]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4]吴宓.吴宓日记:卷一[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姚鹏,范桥.胡适讲演[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朱晓江)
HuShih’sNewInterpretationof“TheRenaissanceofModernChina”
DUAN Huai-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lthough Hu Shih’s ideas on literary reform were affe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by the ideas of the Western “Renaissance”, he, comparatively and consciously, used the ideas of “Renaissance” to interpret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reform and literar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uring the twenties, thirties and fif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for the content, for one thing, his ideas on “Renaissance” were “modern renaissance” centered around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ry and new cultural movement; for another, it was renaissance which lasted for about one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modern China. However, Hu Shih’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had change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fifties, namely, from the absolute focus on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to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ew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a result of combination between alien culture and the local meaning and local worth of Chinese culture. Then, he resorted to new cultural ideas resulting from the adapt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literature and new culture.
Hu Shih; Renaissance;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2009-04-28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B104)的成果之一。
段怀清(1966-),男,湖北随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著作有《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等。
I206.6
A
1674-2338(2010)01-006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