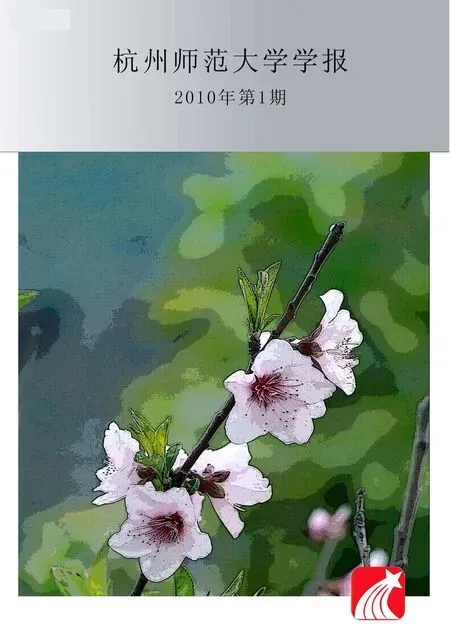民国文艺副刊合订本的出现及其文化意义
——以《京报副刊》为例
陈 捷
(复旦大学 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民国文艺副刊合订本的出现及其文化意义
——以《京报副刊》为例
陈 捷
(复旦大学 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民国时期文艺副刊合订本在五四时期就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媒介属性,完成了向杂志化、书籍化发展的转变,从而在副刊内容上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而且通过自身的广告宣传,尤其是通过与现代书局的合作并借助其完善的销售网络,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基于此,孙伏园在编辑《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过程中,始终大力推动副刊合订本的发行与营销,尤其是通过《京报副刊》合订本与北新书局的业务合作,在扩大副刊影响的同时,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深入开展。
《京报副刊》;副刊合订本;孙伏园;五四
民国时期报纸副刊的版式是研究现代文艺副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由此视角切入来看看关于副刊合订本这个以前无人关注的文化对象。副刊合订本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人们传统阅读副刊的习惯,完成了从读报到看杂志的转变,而且在扩大副刊的销售渠道、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副刊本身文化品格的再次构建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晨报副镌》开始发行副刊合订本到孙伏园在《京报副刊》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副刊合订本并与现代书局合作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在还原历史文化生态的“现场”中开拓一个副刊研究的新视角。
四大副刊中出合订本最早的是《民国日报》的《觉悟》,然后是《晨报副镌》,再是《时事新报》之《学灯》,最后才是《京报副刊》。在1922年4月27日《晨报副镌》的第四版中就有《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合订本的广告,“本刊每日一张,按日随时事新报发行,不另收费。自二月起,装订成册,每册零售小洋三角,外埠邮寄费三十五分,即可寄奉。”1922年5月10日《晨报副镌》第四版广告栏内又有《觉悟汇刊》的广告,“从一九二零年七月起,每月汇订成册。每册内容三十余万字,定价三角。前年七八九十十一及去年一月的已卖完,今年三月的已订好,欲购的从速。”从这些交换广告中可见当时的文艺副刊都十分重视副刊合订本的发行工作。
作为《京报副刊》的创办者,孙伏园十分注意读者对合订本的意见。在1925年2月27日《京报副刊》的《编余闲谈》中,他特意提到了有关合订本目录的印刷:“自上月起,本刊目录另页印刷。上月目录也经随报分送,但颇有几位来函竟云尚未收到者。特此奉告未收到上月目录诸君,请赐函本刊编辑部,以便补奉。”[1]其实,早在《京报副刊》第17号中就有读者给孙伏园来信,信中说:“……及至《京副》出世时,我因为别的缘故,没有即刻和她会面。后来,过了七八天以后,我才订了一份京报,才和她会面。可是,以前的没有,简直把我急坏!……现在对她有几句话说:……2,爱读‘京副’者,都要合订。但是自己订既不美,又不便,而且没有印的封面。因为这个缘故,我希望京报馆承订,办法如次:A爱读者,每月终,将至本馆代订。B并付代价若干,寄费若干,务廉为要!C注明人名地址。3,每月终,另印目录一张,订于卷首以便查阅。”孙伏园在信后回复说:“‘京副’合订本是有的,托本馆代订一层大约也可以办到,现在已向经理处商议手续了。”而之后的第47号也就是1925年1月31日的《京报副刊》上也有记者特意加上的大号字体说明:“自本月起,本刊目录另页印刷,仍夹入副刊附送,附送时另有布告。”《京报副刊》第二册合订本就采用了“目录另页印刷”的方式。合订本目录的出现,就是《京报副刊》从报纸到杂志媒介性质转换的标志性象征。
日报副刊合订本较之于日报副刊的优势在于,副刊是以随报纸附送的形式每天与读者见面的,这一媒介形式具有不容易保存、发行空间范围有地域限制,尤其是在刊发长篇文章时受到信息承载量的限制等缺点,而对于副刊合订本来说,这些问题完全不存在,正如孙伏园所说:“……(副刊)所述文艺学术两项,自然不能全是短篇。如果把合订本当作杂志看,那么,一月登完的作品并不算长,只要每天自为起讫,而内容不与日常生活相差太远,虽长也是不甚觉得的;因为有许多思想学术或人情世态,决不是短篇所能尽,而在人们的心理,看厌了短篇以后,一定有对于包罗的更丰富,描写的更详尽的长篇的要求的。”[2]这是孙伏园从人们的阅读心理出发来讨论副刊登载长篇文章和副刊合订本出现的必然性。日刊不适合刊载长篇文章。早在1922年11月11日的《晨报副镌》中,孙伏园就敏锐地指出:“本刊的长篇太多,久已为人诟病,记者自己也知道的。有许多读者,一看见‘续’与‘未完’两字,那便题目无论如何动人,也没有看他的勇气了。不过讨论学问的文章,即问题极其狭小,也不能只用数百字乃至千数字便说得圆满。……究竟副刊的读者不是天天更换,不是今天看了副刊明天就不看了,那么如果希望著作者把文中意义说得格外丰富圆满,自非让他多做长篇不可,读者何妨稍微耐点性子,一天天的往下看去。”[3]报纸副刊合订本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媒体属性,完成了从报刊向杂志的媒介转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矛盾。从读者方面说,不必再像孙伏园说的那样“耐着性子,一天天的往下看去”了,带给读者的不光是实物保存上的方便,更是阅读上的便利。从此,有系统的、连续性的、大容量的学术、文艺作品以及时间跨度较大的相互辩驳的杂感类文字在副刊日刊上发表时,人们可以得由报刊合订本而满足阅读欲望,不至于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正是这样,孙伏园早在《晨报副镌》时就注重合订本的发行工作。《晨报副镌》自独立刊行后就出合订本了。在1921年10月31日附页广告的显目位置上就有“一九二一年十月份晨报附刊合订本 第一册 订价二十枚 晨报发行部发行”的广告。1921年12月14日的中缝广告内第一次说明《晨报副镌》第一册合订本已经销售完毕,第二册仍然有售。而在1921年12月12日的中缝广告上还第一次出现了邮购的说明:“……二册邮票二十三分,寄费在内”,此后12月20日的中缝广告中又有“外埠函购,请寄邮票二十五分,寄费在内”的信息。这类广告消息很是重要,因为通过邮购的方式,副刊合订本可以像书籍一样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得以销售。
《晨报副镌》的广告发行人员显然也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1921年12月30日的第二三版中缝广告以及12月31日的附页广告中说:“本京阅者,可嘱本报送报人代买;外埠函购,请示详细地址,并封邮票二十五分,寄费在内,本馆即当将书寄奉”。从“将书寄奉”四字可见,此时副刊合订本已被当作书籍在晨报发行部售卖了。而为了扩大合订本作为书刊销售的业务渠道,1922年2月3日,在《晨报副镌》的中缝合订本广告内除了以前的内容外又出现了“……外埠代派,不折不扣,零售时准其酌加邮费”的内容,这就已经是在外埠寻找代售处了。这之后几乎每天的第二第三版中缝广告栏内都有关于合订本的销售广告。在1922年6月的副刊合订本,也就是《晨报副镌》合订本第九册的附页上定价发生了变化,“(一)本京 三十枚 (二)外埠 (1)国内与日本 邮票二十五分(2)欧美各国 本国邮票三十五分 发行者 北京晨报社 印刷者 明明印刷局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发行”。从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出,由于副刊合订本相对报纸日刊的媒介优势,它的售卖范围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已经扩展到了日本和欧美。而对日报副刊来说,是不可能有如此广大的发行面和影响力的。同时,副刊合订本的印刷工作一般是在下一个月5号完成并开始发行工作,这也保证了副刊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到1922年8月份的《晨报副镌》合订本价格又发生变化,本京从三十枚变成了大洋二毛;而到1924年1月,副刊合订本的价格上升到每册定价三角,为了推销,六册一元六角,十二册是三元整,并规定“外埠订购三册以内可用三分以下邮票代价九五折算三册以上均收现款”,邮费也相应地变更为每册“本京二分,国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另算)及日本是三分,其他各国是一角二分”。*由于篇幅和读者群大体相同而为了争夺文化市场,后来的《京报副刊》也把合订本的价格定为三角。《晨报副镌》合订本的中缝广告一直延续到1922年10月9日,此后中缝里就没有关于副刊合订本的广告了,可见这个时候,《晨报副镌》合订本的品牌推广工作已经初步完成。
孙伏园推销副刊合订本广告策略十分高明,在他主持《晨报副镌》阶段,就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读者迫切要求购买副刊合订本的信件,或是发布一些极力营造“卖方市场”广告效力的“副刊部启事”,比如在1922年6月15日《晨报副镌》第四版中有“本刊特别启事”,其中说到:“(一)一二三月份的副刊合订本均已售完。对于购阅诸君,除将邮票寄还以外,特此通告。(二)二三月份,不知有肯割爱者否,托本社代为征求者甚多,如愿出让,请交送报人带回,至发行部领取原价。(三)四五月份尚有数本余存,购者请从速。”这样的启事,显然具有两方面作用,其一是传递了有关副刊合订本发行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在无形中给副刊合订本的销售增加了“卖方市场”的优势心理,这也是孙伏园为副刊合订本可以在更广大地域范围和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好的销售成绩和更深入的品牌声誉所进行的“造势”宣传。
《京报副刊》由于是随《京报》免费奉送的,所以,对于那些没有订《京报》的人,孙伏园更是大力推荐合订本。在《京报副刊》第35号上,有孙伏园答读者的一封信,其中提到:“杨文蔚等诸先生:副刊不能单定,但每月底有合订本,即全份京报定价亦甚廉,殊无单定副刊之必要,委问图画周刊可以单定与否一节亦恕不转问了。”从信件的抬头称呼就可以看出,孙伏园并不是对单个读者发言的,一定是他同时还接到了很多类似的疑问,因此一并答复。这里孙伏园不但替他的老板邵飘萍的《京报》做了广告,更为关键的是借此推销了《京报副刊》的合订本。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候,都有对上个月合订本销售的广告,比如在第43号的《京报副刊》上就有用二号黑体字显目地标出“本刊合订本去年十二月的已发行”,而在第85号上面又有记者颇为自豪的声明:“本刊合订本第一册早经售完,连日尚有纷纷来社购买者,特此通告,并且道歉。”之后又连续三天登出了同样的广告。在1925年3月30日,孙伏园又用二号大字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本刊特别启事,其中说到:“二月份本刊合本,已经装成发售,购者务请从速。一二册均售完,印刷部方面一时无暇再版,不胜歉疚。”即使到了后来五卅惨案发生后,《京报副刊》的篇幅让给清华学生会去编时,孙伏园也没有忘记在第八版上给合订本做广告,可见他对合订本工作的重视是一贯的。
在副刊合订本的业务运作上,孙伏园完全是把合订本当作书刊杂志来进行销售的。合订本既然单独从报纸副刊日刊中独立出来而具有了杂志的品性,那么对合订本的运作也就要按照杂志来进行。而这种影响力大、覆盖面广的刊物有一个相对报纸副刊很显著的区别,就是广告的增多。早在1923年7月份的《晨报副镌》合订本首页上就刊登了两则广告,都是晨报副刊社自己给自己做的广告,其中“招登插页广告”一栏下这样说:“全国最大之定期出版物,销行最广——最多——最速——刊费极廉——效力极大——又可保存久远——实在是登广告之绝好机会!!!晨报自创办以来,销数日涨,信用日厚,已为北方言论界之中心。去年所刊行之《晨报副镌合订本》,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爱读。现时每月销数,竟达一万份之多,实为我国出版界空前之盛。近因商界诸君来函商请登载广告者甚多,本报为应社会上之需要起见,特自本年七月起,在《晨报副镌合订本》上,另加篇幅,刊登广告。”同时另外一则“副镌部启事”的广告内这样说:“……此后本刊一切无条件的交换广告,应暂停止。此启。再者本刊合订本销数飞涨,广告效力甚大,自下月起,拟在合订本中增加广告数页。上述章程,只限于出版品,但如有各大商铺,以及一切文具服食器用等等,欲登本刊合订本广告者,亦请直接向本报广告部接洽,创办伊始,价目自当格外优待也。”而在具体的发行渠道的扩张方面,也借鉴了书籍的销售经验,在1923年7月份的《晨报副镌》合订本末页上刊登了副刊合订本广告价目表以及发行渠道,总发行所是晨报社发行部,外埠分售处则分布在11个省14个城市,具体则是天津、保定、直隶顺德、太原、开封、济南、成都、重庆、武昌、长沙、南昌、南京、广州和昆明。*后来南昌没有另设,到1924年2月增加了河南信阳,同年5月,分售处又增加了直隶深泽、山西闻喜、陕西西安、上海、绍兴、潮州、长春。1923年底在北京分代售处有:东城的新智书社、瀛贤书社,南城的福生祥纸庄、京华教育用品公司、高师工读贩卖部和养拙斋,西直门外的清华学校书报社,共7处,到1924年2月,又增加一个东亚书社。而在孙伏园去了《京报副刊》之后,在京的《晨报副镌》的分代售处减少为6家(福生祥纸庄和养拙斋退出)。
在书局对副刊合订本销售的推动方面,与《京报副刊》关系最大的就是成立于1925年3月的北新书局。《京报副刊》1925年9月12日第三版和第六版中缝上刊登了“北新书局廉价书目”,其中关于刊物总共有三个:立达季刊(刘大白等主撰)、法院季刊(广东大学出版)和京报副刊月订本(孙伏园主编),从中不难看出北新书局与《京报副刊》的密切关系。北新书局作为新文化运动中与周氏兄弟来往密切的书局,李小峰作为鲁迅的学生,通过书局的发行渠道来扩大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作家作品的影响力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是作为报纸日刊的合订本,《京报副刊》合订本也作为北新书局廉价销售的书目以北新的名义来售卖,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北新书局是《京报副刊》合订本的总代售处,到1925年10月份,在26个大中城市有了《京报副刊》合订本的分代售处,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保定、大名、邢台、开封、南昌、杭州、济南、沁阳、汲县、太原、西安、南京、芜湖、武昌、宁波、广州、潮州、长沙、成都、昆明、绍兴、涪州(涪陵)和重庆,外埠的分代售处更是达到了45家之多。在北京的分代
售处除了北新书局以外,还有:北大出版部、北大一二三院号房、中大出版部、师大号房、大东书局、晨报社、青云阁富文斋、市场新华书局、市场佩文斋、劝业场东亚书局和中央公园大东书局,共12家。书局在其中大约只占一半左右,这是因为北京的一部分高校利用地域上、服务上的便利而获得了销售上的优势;但是在外地,《京报副刊》合订本的发行工作几乎都是书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天津共有4处分代售处:大胡同中华书局、南开华英书局、西开世界图书局和西北城角博古书局,全是由书局来推进副刊合订本的发行工作。因此,在政局不稳定的社会背景以及通讯和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环境限制下,报纸征订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影响面因此也不可能太大。但是副刊合订本的出现改变了这个面貌,通过以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书局为发行网络,副刊合订本借助于新的销售渠道很快地得以发挥自身的媒介优势,并影响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阅读群体。
总之,副刊合订本的出现是副刊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副刊合订本改变了副刊日刊原有的报纸属性而变更为杂志、书籍属性,极大地改变了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和认知方式,并且借助于现代书局较完善的销售渠道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民众思想启蒙、现代观念建构过程中更完善地发挥了文艺副刊的作用。
[1]孙伏园.编余闲谈[N].京报副刊,1925-2-27.
[2]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N].京报副刊,1924-12-5.
[3]孙伏园.编辑闲话三则[N].京报副刊,1922-11-11.
(责任编辑:朱晓江)
AStudyoftheEmergenceofBoundVolumeofLiteratureandArtSupplementintheRepublicanPeriod.——TakingJingbaoSupplementasanExample
CHEN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The intellectual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bound volume of literature suppl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an years. Because of its emergence, the supplement not only changed its media property, in other words, it completed the conversion from a supplement to a book or a journal, while still possessing more flexibility to contain more content. Through advertisements, 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with modern press, the bound volumes of literature supplements expanded the coverage and impact area in the modern culture movement. In view of this, Sun Fuyuan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issuing and editing of the bound volumes ofChenbaoSupplementandJingbaoSupplement. 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JingbaoSupplementand Beixin Book Company, Sun Fuyua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JingbaoSupplement; bound volume; Sun Fuyuan; May Fourth
2009-11-15
第四十四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时事新报·学灯〉研究》(20080440593)的研究成果之一。
陈 捷(1977-),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I206.6
A
1674-2338(2010)01-01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