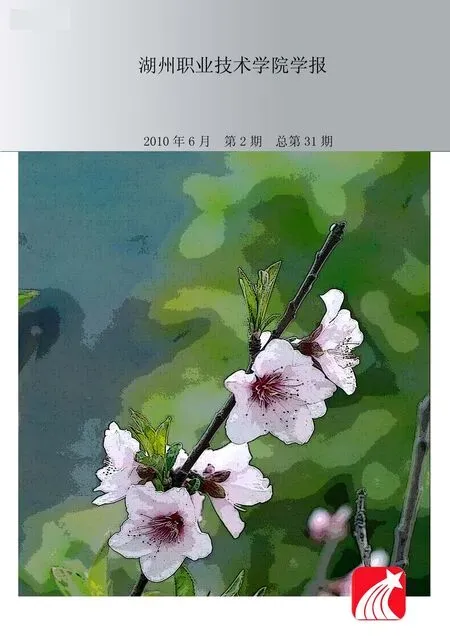略论李贽的“童心说”与文学观*
陆 涛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今福建晋江人,明代后期杰出的思想家。出生在一个回教徒的市民家族。原籍河南,原姓林,名载贽,元朝以后迁来福建。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他一生矢志不移地以反对封建虚假礼教为己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本质上说,李贽更多的是一位思想家而非文学家,但李贽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以“童心说”为基础的文学观。本文拟就从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三个方面来论述李贽以“童心”为基础的文学观。
一、童心:李贽的文学本体论
李贽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但其提倡的“童心说”无疑和文学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童心说”就是其文学观的基石。简单地说,李贽的“童心说”就是要求人们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体现在文学观念上,就是要求文学必须是出自童心。“童心”也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情感。所以,李贽主张,文学要抒发人的真实情感,不得有半点的矫揉造作的虚假成分。《童心说》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1](P98)显然,李贽认,为童心、真心是文学的第一生命,没有童心、真心就没有文学作品。这样,他把童心提高到了文学本体的地位上。关于文学的产生,李贽是这样说的: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文也。其胸中如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1](P97)
这说明文学创作是真情实感的不得不发,不像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以歌功颂德为能事,抑或是一些文人墨客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这都显示出李贽对于文学之真的追求。我们应注意的是,李贽的这种真是一种主观的真,是感情抒发的自然而然,如他在《读律肤说》中所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1](P132)这里的自然显然是一种主观的真,同现实之真是有区别的。
关于文学(古时主要是诗歌)本体,自古就有“诗言志”之说。《尚书》云:“诗言志,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注]《尚书·尧典》,郭绍虞编《历代文论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意思是诗是表达人的情志的,认为文学的本体是志,志也是人的情感。但是,志所包含的情感已被后人理解为被礼义所过滤过的个人情感,并不是人的自然本真性情,这是与李贽的童心相背的。晋人陆机提出了诗歌的“缘情说”,对于文学抒发个人情感的作用予以重视。而李贽的文学本体论显然是沿着缘情的路线发展下去的,并着重强调感情的真。关于文学的主观之真,以前的历代文论家也有所论及,李贽显然不能不受到前人影响。庄子认为,艺术创作要浑然天成,返璞归真,从而视真为艺术的第一境界。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夫篇》)汉代的王充也曾从实用的角度提出文学创作要“疾虚妄”;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说:“为情者要约而写真。”金代王若虚将感情的真诚作为艺术之根本,说:“哀乐之真,发乎性情,此诗之正理也。”(《滹南诗话》)。虽然,历来的文论家都倡导作家真性情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但却因为受到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审美准则的束缚而无法自由地抒发自己的真性情。李贽提出的文学“童心说”则是对儒家审美理想的冲击,也是对传统文学之真的复归,且姿态更加激进,把“童心说”所包含的真性情上升到了文学本体的地位。在这种文学观之下,李贽发现了通俗文学主要是小说、戏曲等的价值。在李贽看来,这些被儒家士大夫所不屑的俗文学恰恰表达了人的真性情,从而比儒家的诗文更有价值。
二、自适与教化:李贽的文学价值论
李贽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人的真性情。那么,这种出自童心的文学究竟有什么价值呢?用李贽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自适。由于李贽倡导主体的童心,认为文学的决定因素是自我,最佳的作品也就是自我个性的表现,这样,李贽在文学作品里一味地追求自我的人生之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李贽看来,读书或创作的目的乃是求乐,是人的怡情养性的精神享受。这里的乐包括歌与哭的双重内涵,歌是指自我愉悦,哭则是自我宣泄。李贽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功能古而有之,就是认为文学一方面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宣泄的功能。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对于悲剧功能的描述就涉及到这两个方面,认为悲剧具有陶冶和净化作用。在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也是把文学作为自我抒发闲情逸致的玩物;也有落魄不得志的文人把文学作为自我宣泄的工具。李贽在《读书乐》中写到: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1](P226)
显然,李贽认为,在歌与哭的阅读效果中,作者可以获得精神之不朽。在李贽看来,读书不仅是人生之手段,更成为人生之目的。通过读书陶冶感情已经成为李贽生命形式的一种,无此便不以自乐。李贽说:“大凡我书,皆以求快乐自己,非人为也。”如果说这是在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带来的乐的话,那么李贽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感到了创造之乐,如其在对《西厢记》、《拜月亭》和《琵琶记》的评点中,每当读到兴起之时,则挥笔泼墨,写下自己的一时感受。更有甚者,则对原文加以篡改,“涂抹改窜,更觉畅快。”
李贽之所以看重文学的自我愉悦作用,乃是其认识到文学对个体的人的陶冶作用。李贽虽然是个重哲学思考的思想家,但却没像宋时的道学家那样倡导以文害道或文以载道。这主要是因为他把文学的功能看作是人生之自适,从而与其人生自我解脱的哲学追求取得了一致的价值取向。因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并没有轻视被大多道学家所不屑的文学。
与文学的自我愉悦功能相比,李贽论述更多的还是自适中的宣泄功能。传统儒家文论就有“诗可以怨”的说话,向上则可以讽刺时政,向下则可以疏导民情,而疏导民情就指的是文学的宣泄功能。所以,在文学史上,可以经常发现不满时政而抒发自己心中不平的文人的存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对此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注]司马迁《报任安书》,郭绍虞编《历代文论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这都说明,人在悲愤时易于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心中的苦闷。李贽自然知道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其自适的宣泄说显然是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作了发挥,道:“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栗,不疾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1](P108)由此可见,李贽关于文学的宣泄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进一步发挥。后来,钟嵘在《诗品·序》中也对文学的宣泄说有所论述,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唐时韩愈则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认为“有不得已而后言”和“郁于中而泄于外”,也认为人们是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要有所宣泄。李贽在继承了上述宣泄、怨愤的观点后提出了自己的宣泄说。如在论述其文学本体论时,他认为,文学产自于强烈的感情。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学产自于悲愤,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学可以发泄心中的苦闷,如李贽所说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甚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再如他在《读书乐》中所说的恸哭呼呵,涕泗磅礴。当李贽遇到了愤懑之事,便通过文学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当读到书中感人至深之处,则不免大喊大叫,甚至失声痛哭。这无疑是李贽自我个性的真实表现,与其“童心说”是一致的。李贽的这种文学价值论,无疑也是对儒家中和之美的一种挑战。与儒家压制人的真性情相比,李贽的文学宣泄说则是个人情感的真实表现,是童心的自然流露。
不得不提的是,李贽对于文学的价值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他曾注意到文学教化世人的作用,这同儒家的诗教是毫无二致的。如他在《拜月》中写到:“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兰比崔垂名,尤为闲雅,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也。”[1](P192)在《红拂》里,他也论述:“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起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诗可发,可敬可羡。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关,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1](P193)显然,李贽这里所说的“兄兄妹妹、义夫节妇”的礼义教化以及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与其上述所说的自适是相背的,是向儒家诗教传统的复归。这显然是李贽的一个矛盾之处:他一方面激进地反传统;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打上儒家传统的烙印。这种局限的存在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李贽根据其人性论的观点,把社会群体作了上士与下士、凡人与圣人的区分。对于圣人而言,为了超越世俗而达到自由境界,可自我适意,但凡人则必须服从教化而识礼。显然,这里,在李贽的思想中精英主义思想在作祟,从而造成了其文学价值论的双重标准。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不同的文体造成的。我们发现,李贽所重视的文学自适的价值,更多的是指向诗文,而诗文的创作大多是精英文人,追求自我超越者往往是这类人;戏曲小说面对的接受者则是下层人民,李贽认为应对这些人进行教化。就是从这种人群分类和文体的不同,李贽采取了文学价值的双重标准。当然,在评论戏曲小说时,他虽然重视教化作用,但也不排除愉悦、宣泄作用。但是,在李贽的整个文学价值论中,文学的自适始终是占主要地位的。
三、革新:李贽的文学发展论
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文学,且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从孔子开始,已有尊古卑今之说。孔子也曾梦想回到周代,因为那时的礼乐是他理想的礼乐形式。所以,崇古思想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准则。在文学史上,也有多次文学复古运动:唐朝有陈子昂、韩愈的复古运动。明代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率先掀起了文学复古的高潮,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形成了广泛的复古运动。一时之间,复古成为社会风气,复古也走向了拟古。嘉靖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次提出了复古的主张。
在这样的复古大风气下,李贽对复古则不以为然,并不认为古代的文学就优于今天的文学。他对于文学是持发展的眼光的,正如他所说: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1](P98)
显然,李贽对于文学上的复古运动是反对的。他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和其“童心说”仍是分不开的。在李贽看来,世间一切文学都出于童心,都是童心的表现。只要文学作品表达出了作者的童心,那么这就是一部好作品。依据这个标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就无所谓优劣了,即是李贽所说的“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所以,也不必从古文里去寻求诗歌创作的标准抑或从先秦去寻找作文的标准了,更无需从《六经》和《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里去寻求范例了。因为,各个时代都有出自童心的文学,而童心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所以,古今文学也无优劣之分。就文学自身体裁来说,文学体裁也是不断变化的,各个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由先秦的文到六朝的近体,进而为传奇、院本、杂剧等。如果一味复古,那么这些新的作品如何复古呢?李贽不仅反对崇古抑今,相反还认为今胜于古,特别是当时的戏曲、小说等新兴的文体。戏曲、小说相比于诗文来说,更有效地表现出了人的童心,人的真性情。因此,李贽对这些通俗文学是持肯定态度的。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李贽的文学观念做了简要的论述,无论文学的本体论、价值论,还是文学的发展论,都与其所提倡的“童心说”不无相关。作为反对封建虚假礼教的斗士,李贽所提倡的“童心说”对反对封建虚假礼教的思想运动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而李贽以“童心说”为基础提出的文学要表达真性情、要有感而发,文学要有自适与教化功能,以及文学不应崇尚复古而需要不断更新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更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些观点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公安派,如“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和文学发展论都是对李贽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因此,“童心说”的提出,使李贽无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宋]李 贽.焚书·续焚书[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8.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