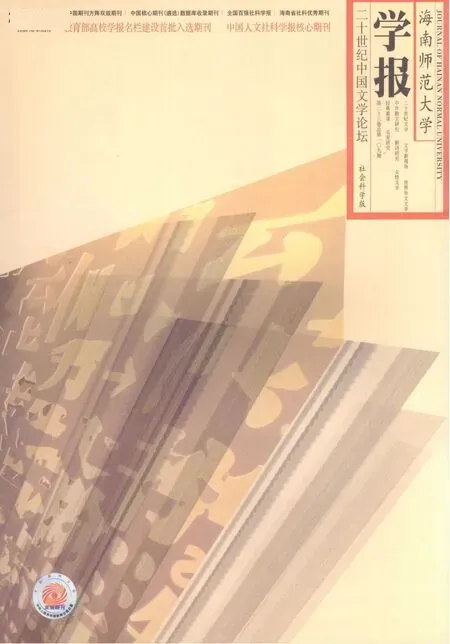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黄维樑
(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台湾宜兰)
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
——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黄维樑
(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台湾宜兰)
论文比较的对象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钱氏1946年36岁或以前完成的其它文学论著。文章依据《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从“原道”到“隐秀”,作刘、钱文论的比较,对二人论比喻和论言外之意着墨较多。二人“打通”复“圆览”,直探文学的核心。论文通过对若干文论概念(或范畴)的比较,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可以成立。有论者谓钱氏的《谈艺录》(以及《管锥编》)都属札记式书写,缺乏体系,而有微词。论文指出,钱氏固然有其具备体系的文论篇章,其《谈艺录》(以及《管锥编》)自有其“潜”体系或“钱”体系;钱学学者就钱著作内容加以分类、整理、建构,当可形成“显”体系。
刘勰;钱钟书;《文心雕龙》;《谈艺录》;文学理论;大同诗学
一 引言:比较刘勰和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学问渊博,著述宏富,这已是中华学术界的公论。知钱深者、尊钱重者如汤晏更誉他为“民国第一才子”,舒展誉他为“文化昆仑”,汪荣祖誉他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①对钱氏的称誉请参阅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台北,时报文化,2001年);舒展《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随笔》1986年第5期;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页169。阅读这位文化英雄、文学大师的著述,我想起另一位文学大师、“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约公元465-520)。钱出生长大于无锡,刘出生长大于镇江,二者地理上相距只有约一百公里。两人年代上则相差近一千五百年。时代远隔,历史文化背景殊异,年寿也大别,我们怎样拿他们俩人来做比较呢?钱钟书是文史哲通人,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涵盖了文史哲,也是通人。两位通人论述的重心都是文学,我们就来一次“比较”文学吧。20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相当蓬勃,号称龙学;二十多年来钱钟书研究颇盛,号称钱学。学术界似乎还没有人作过刘、钱的专题比较,笔者不避浅陋,这里做个尝试。
二人的时代、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可有心同理同处?在探索他们的文心异同之前,我们先说其生平经历的异同。钱钟书自幼聪颖好读书,抓周时抓的就是书;我们相信刘勰也聪颖好读书,有没有抓周,如有,抓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钱钟书大学毕业后;留学英、法3年;刘勰青壮年时期在南京的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佛经十多年。钱钟书年轻时恋爱结婚,与夫人杨绛女士一生恩爱,且两人一生爱书,在国难时期生活虽受困扰,其它岁月钱氏却不必因家务事或其它事而对读书著书心有旁骛;史书说刘勰因家贫而不婚娶,我们相信他生平中也是与书为伍的日子居多。中文之外,钱钟书通晓英、法、德、意、西和拉丁文,三十多岁时担任过英文刊物《书林》的主编,又当过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刘勰懂不懂梵文,我们不得而知;他长期整理编修佛经,则是史籍所记述的。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记忆力强如照相机,而他仍勤于做读书笔记。他自己的藏书据说不多,但身边周遭的河图洛书、中典西籍甚为丰富。留学牛津大学时,他在著名的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如蠹虫般饱蛀馆藏;29岁至31岁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日后所写长篇小说《围城》那所三闾大学以蓝田这学校为蓝本——虽处僻地,学校又属初办,却是出乎意料地藏书甚富,《四部丛刊》等大部头书籍俱备。刘勰的学术资源也不匮乏。龙学学者指出,刘勰待了十多年的定林寺,除佛教经籍外,儒家以至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很多。定林寺在南京城外,刘勰要进城读寺藏之外的书籍相当方便。①史 书对刘勰生平记载简略。关于定林寺地位之重要和藏书之丰富,可参看孙蓉蓉《刘勰与〈文心雕龙〉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32、33;牟世金《雕龙后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78。坊间已有钱氏传记多种,包括钱夫人杨绛女士的记述;本文提及蓝田师范学院藏书多,可参看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台北,时报文化,2001年)页225。我们相信刘勰和钱钟书一样,也是“蠹虫”。《文心雕龙·知音》说“圆照之象,务先博观”;②本文所引《文心雕龙》文句,主要根据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一书;引述时注明篇名,不逐一注明出处。据《文心雕龙·知音》推论,刘勰博观了经史子集各类的书(经史子集自然是后世才有的分类)。
刘勰处身分裂动荡的南北朝,是儒释道多元文化交锋、交融的时代。好学深思的刘勰,思想受到冲击,探索怎样择善固执,怎样在文学文化上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钱钟书大半生中国家同样动荡不安,思想文化有中土的也有西方的,因此更为复杂多元。《谈艺录·序》自言此书“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③本文所据《谈艺录》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本(准确地说,是1984年9月第1版1993年3月第5次印刷)。此为“补订本”,全书逾650页。本文所论,乃据《谈艺录》初版(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内容,所以只包括1984年中华版的前半部,即页1-312。他之读书写书,本于兴趣,也寻求寄托,以期安身立命。中国弱而西方强,说不定他在中西的比较中更想为中西文化异同问题探索究竟,以认定中国文化的特色与发展方向。
无论生平与时代文化有何异同,两人博学、“积学以储宝”是一致的。学问愈渊博的人,往往态度愈谦虚。钱钟书名其书为《管锥编》,取管窥锥指之意;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谦称“识在瓶管”即见识狭窄。这“管”正是《管锥编》“以管窥天”的管,然则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可名为《管锥编》。
钱钟书的《管锥编》有上百万言,其《谈艺录》等专书或论文,加起来约有《管锥编》一半的篇幅;他还有长、短篇小说,还有杂文集,还有用英文写作的多篇论文。刘勰流传下来与文学有关的著作,就只有三万多字的《文心雕龙》一书。二人著作篇幅悬殊,这又怎样比较呢?龙学学者普遍地认为《文心雕龙》在刘勰三十五六岁时成书,笔者据此决定,本文拿来相比的钱钟书著作,只计其文学论述,而且只限于1946年或以前完成的作品。1946年钱钟书36岁,约略与刘勰完成《文心雕龙》时同一年纪。根据这个年限,本文比较的对象为:刘勰的《文心雕龙》;钱钟书的《谈艺录》(完稿于1942年,时钱氏32岁④《谈艺录》在1942年初稿既就,钱氏“时时笔削之”,后于1948年出版;参见1948年《谈艺录》的《序》。),以及《钱钟书散文》中1946年或以前写成的文学论文,主要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33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1937年)、《中国诗与中国画》(1939年)、《小说识小》(1945年)、《谈中国诗》(1945年)。(其巨著《管锥编》在六十多岁时写作、出版,不在本文探讨范围。⑤本文所据《钱钟书散文》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钱氏1946年或以前完成的文学论评还有用英文写成发表的“On Old Chinese Poetry”,“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等等,阴差阳错,本文未能列入讨论,以后当补充之。)
二 据《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作刘、钱比较
刘钱二人论述的范围,都极广阔。刘通论古今文学的各种体裁各个方面,钱更是古今中西兼论。《文心雕龙》论述先秦至南北朝千多年间35种文体、两百多个作家的种种,有理论阐释,有实际评论;此书有组织有条理,成一体系,是文学理论、实际批评、文学史的综合体。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不在本文范围的《管锥编》)是札记式文字,论者或视为诗话、文话之类,而评之为不具体系,甚至有论者批钱著只是罗列数据,不成一家之言。笔者在此郑重指出:《谈艺录》(以及不在本文范围的《管锥编》)确属札记形式,各则札记长短不等,长者固然可视作文学论文,短者也可称为文论小品。《谈艺录》(以及不在本文范围的《管锥编》)的片片段段,加以分类、排比、建构,当可成为具系统的论述。
至于《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国诗与中国画》、《小说识小》、《谈中国诗》诸文,其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层次井然、逻辑严谨,与现代一般学术论文并无差别。其中《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是钱氏拟撰写的“中国文学小史”的纲要,体系性明显。不过,在钱氏已发表的著述里,向来没有《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小史》一类专著,这可能因为他在《序论》后没有写这本专著,或曾动笔而没有完成,或写作了而没有发表。学术体系有大中小各种规模,正如佛教所说有小中大千各种世界,《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至少已成为一个小体系。其它单篇论文或《谈艺录》较长的片段,至少可成为小小体系。他的所有文学论著的内容,分类之、排比之,而建构成“中体系”、“大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只是钱氏最感兴趣的是实际作品的鉴赏;①参阅郑朝宗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虽然他胸有成竹,竹且成林(体系),却不把竹林绘画出来。
两位博学的通人如何通论文学,古刘与今钱两位文化英雄所见的异同如何,下面加以探究。《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向来学者公认。我们不妨先标出其体系,并以此为准,就其中项目,作刘、钱的比较。刘勰在《序志》篇中这样说明《文心雕龙》全书的纲领、体系: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我们可以根据《序志》篇的纲领来建立一个《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作为下文的依据;我们也可换个方式,“西化”一点,例如根据面世逾60年、影响很大的韦礼克、华伦(Rene Wellek&Austin Warren)合着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纲领,重新组织《文心雕龙》的论点,作为它的体系。《文学理论》把文学研究分为三个范畴。(一)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原理、类别、标准等; (二)文学批评:对具体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 (三)文学史: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有不同时代的演变。韦、华两氏从另一个角度,再把文学研究分为二类。(A)外延研究:研究文学与传记、心理学、社会、理念的关系,以及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关系;(B)内在研究:研究文学的节奏、风格、比喻、叙述模式、体裁、评价等等。笔者认为更可以中西合璧地(即兼用《文心雕龙》和西方的术语、概念)建立的“情采通变”《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作为下文讨论的依据。②关于这个体系的解说,参看拙文《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刊于《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又:这一段所说Rene Wellek& 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乃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Inc.1956年版本。这个体系主要由“情釆(情志、主题;辞釆、技巧)”、“剖情析釆(对作品的实际批评)、批评的态度及批评的方法”、“通变(通过比较,实际析评不同作家作品的情采)”、“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学的功用)”构成。
三 文学通论:从“原道”到“隐秀”
论及文学的本质和功用,刘勰在《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开宗明义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钱钟书在《谈艺录》说:“艺之极至,必归道原,上诉真宰,而与造物者游。”[1]269同书另处论及性灵与创作的关系时,直接用了“心生言立,言立文明”[1]205这《原道》篇的话语而不加引号。
作品显现作者的情志、风格,而情志、风格受各种因素影响。《物色》篇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时序》篇则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此外,《体性》篇指出作者“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这些也都是因素。钱钟书也认为影响作者风格的因素众多,“同时同地,往往有风格绝然不同之文学”;“时地之外,必有无量影响势力,为一人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2]483
现代人把文学界定为语言的艺术,刘勰在《情采》篇早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采就是文采,就是艺术,就是各种修辞技巧。《情采》篇虽然指出“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繁采寡情,味之必厌”;龙学学者都知道,刘勰对文采十分重视,《文心雕龙》用了四分之一篇幅阐述镕裁、比兴、夸饰、丽辞、声律等技巧。③龙学学者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论《文心雕龙》的“文术”甚善,可参看。刘勰崇奉儒家思想,主张“征圣”“宗经”;不过他对文学的内容思想并没有集中而详尽的说明。钱钟书对技巧的强调,绝不逊于刘勰。钱氏认为作者的“感遇发为文章,才力定其造诣”;他构想中的《中国文学小史》,其旨归“乃在考论行文之美,与夫立言之妙,题材之大小新陈,非所思存”。在论及作者诚伪及修辞时,他强调必须“精于修辞”,“舍修辞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说“至精文艺,至高之美”,要那些好学深思者才能心领神会。他说,谈艺者定“文章之美恶”,这包括“布置镕裁”种种技巧的考虑。[2]486
作家须具想象力。刘勰《神思》篇对神思(包括想象力)有生动的描述: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神思蹁跹飞舞,要把神思凝定、转化为文字,却并不容易。刘勰跟着又有一番生动而中肯的记述: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为什么呢?“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钱钟书的看法与刘勰殊无二致。他引述《神思》篇的话,再引西方几个作家的言论,添趣添色地说:
Lessing剧本Emilia Galotti第一幕第四场有曰:“目成即为图画,不须手绘,岂非美事。惜自眼中至腕下,自腕下至毫颠,距离甚远,沿途走漏不少。”……
后来Friedrich Schlegel亦言“男女爱悦,始于接吻,终于免身,其间相去,尚不如自诗兴忽发以至诗成问世之远。”
嗜好比喻、本身是比喻大师的钱钟书,在征引二说之后,不忘赞曰:“尝叹两言,以为罕譬。”两言还不够,他要三言:
Balzac小说La Cousine Bette论造作云:“设想命意,厥事最乐。如荡妇贪欢,从心纵欲,无罣碍,无责任。成艺造器,则譬之慈母恩勤顾育,其贤劳盖非外人所能梦见矣。”
一次拍案之后,钱氏真要二拍惊奇了。他总结说:“此皆谓非得心之难,而应手之难也。”①上述诸引文见《谈艺录》页209、210;钱氏原书这几则所附外文,这里为省篇幅,从略。创作时得心非难,应手难。为此,《文心雕龙·神思》主张向经典学习,“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钱钟书赞成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说法,认为学问不是一切;然而,在论及性灵与学问时,他说:“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1]206钱钟书又引《沧浪诗话》“诗有别材……而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之语,加评曰:沧浪这样说“周匝无病”。[1]207
风格的区分,更再三论及。《谈艺录》第一则论的就是唐宋诗之分,钱钟书说: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想见胜。[1]2
俗语说一样米食百样人,文学的风格自有多种;钱氏这里的二分法,就和君子小人之别、雄浑秀美(the sublime and the graceful)之分一样,属于大而化之的分类。顺便一提:上引“体格性分”四个字,使人想起刘勰《体性》篇的“体性”。钱氏是否受《文心雕龙》影响,其用词已“化而相忘”? 钱氏又说“格调之别,正本性情”,[1]5这又与《体性》篇所说的无异:八体虽然不同但“莫非情性”的表现。当然我们可以说“文如其人”的见解大概是文学常识。
作品的风格应该怎样分类,难有定论;要形容风格,则较为容易。而作品的评价,向来是难题;《文心雕龙·知音》以“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为戒。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可能很主观,跟别的读者很不一样。刘勰在《知音》篇列举了四种气质品味不同的读者:“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差不多就是20世纪西方读者反应论(theory of reader’s response)的说法。钱钟书也认为读者“嗜好不同,各如其面”。[2]491刘勰在承认读者气质品味不同、反应不同之余,认为: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器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意即博观圆照之士乃能评断作品的美丑优劣。博观圆照者是谈文者中不可多得的品类,钱钟书的看法也颇为“贵族”,他说:
窃谓至精文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素人(amateur)俗子(philistine),均不足与于此事,各何有于“平民”(the court chaplains of king Demos)。[2]491
不过,我们要指出,即使是文评的精英、贵族,其个别的气质品味仍有不同,还是会影响到对作家作品的不同评价的。《诗品》的作者钟嵘,应该是“博观”的、“好学深思”的人了,但他在评价陶渊明时,只把他列为中品,称其篇章“文体省净,殆无长语”。文学史上为陶渊明抱不平的极多。钱钟书认为钟嵘的作法,有其原因,即钟嵘评诗——
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高奇”、“词彩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1]93
拘于口味之外,还“囿于时习”。钱钟书对钟嵘个人更有这样的贬抑:“眼力初不甚高”。[1]93这是一个文评家对另一个文评家的批评,评价的问题太复杂了。评价包括对“文情”的鉴识。《情采》篇认为就情而言,作品有两类:有“为情而造文”的作品,即作者先有感动然后抒情成文;也有“为文而造情”的作品,即作者为了写作文章可以虚述感情。刘勰贵真,反对“为文而造情”。王充《论衡》斥“虚妄”的写作,钱钟书在评论其立场时,指出“文艺取材有虚实之分,而无真妄之别”。他连带论及近人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言之有物”等说法,指出这些说法与“作者之修养”有关,而与“读者之评赏”无涉。这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他接着说:
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词立诚”(sincerity)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非必“诚”而后能使人信也,能使人信,则为“诚”矣。[2]489
他还认为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读者分辨不出来。[1]163比较两人观点,当以钱说中肯、周全,因为作者有病与否,不识作者、只读作品的读者,实在无从得知。钱钟书这种说法,与新批评学派(The New Criticism)的“作者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说互相发明。
钱氏拈出“善于呻吟”4字,这就关乎写作技巧了。上面说刘勰重视写作技巧,《文心雕龙》有四分之一篇幅都在论述修辞。《知音》篇举出衡文的六观,涉及的主要是技巧:“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笔者根据《文心雕龙》所述,对六观作如下的解释。这里对原来六观的先后次序,稍微做了调整。第一观位体,就是观作品的主题、体裁、形式、结构、风格;第二观事义,就是观作品的题材,所写的人、事、物等种种的内容,包括用事、用典等;第三观置辞,就是观作品的用字修辞;第四观宫商,就是观作品的音乐性,如声调、押韵、节奏等;第五观奇正,就是通过与其它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整体手法和风格,是正统的,还是新奇的;第六观通变,就是通过与其它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整体表现,如何继承与创新。
六观中的第二、三、四观,可合成一大项目,以与第一观比照。这个大项目就是20世纪新批评学派所说的局部、组成部分、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以与第一观的全体、整体大观、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比照。刘勰论文,非常重视局部细节与整体全部的有机性配合;事实上,“置辞”与“事义”息息相关,而此二者,加上“宫商”,乃构成整篇作品的“位体”,或者说这三者都为“位体”服务。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位体”决定了“事义”、“置辞”和“宫商”。第一至第四观,乃就作品本身立论;第五观“奇正”,第六观“通变”,则通过比较来评论该作品,用的是文学史的角度了。①关于六观法,可参阅拙著《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一文(写于1992年),以及《〈文心雕龙〉“六观”法和文学作品的评析》一文(写于1995年)的有关说法。
《谈艺录》对诗文的修辞有极具体极细致的评论,如指出李贺诗好用“金石硬性物做比喻”,以其“昆山玉碎凤凰叫”、“羲和敲日玻璃声”等诗句为例;又说“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刚刚引的“羲和”句就是;又说李贺好用“啼”、“泣”等字,如“芙蓉泣露香兰笑”等。[1]51钱钟书所重视于文学的,是“行文之美”、“立言之妙”,对比喻的论述尤多(后来《管锥编》更有喻之二柄、喻之多边等说)。美妙的“置辞”,包括一种含蓄的手法。《文心雕龙·隐秀》解释何为隐、何为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秀”的手法包括用比喻,“隐”则是含蓄。《隐秀》篇还这样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隐文深蔚,余味曲包。”言外之意为中国古今诗学一大论题。钱钟书在析评《沧浪诗话》和王士祯神韵说时,都曾论及,他的要点是:“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1]42不过,和刘勰不同,他向来没有对文学的修辞之美作系统的述说。
上面钱氏说钟嵘眼力不甚高。眼力不高是个缺点,虽然眼力高与低的评价有相当的主观性,不像运动会跳高比赛可以尺寸为准。刘勰对历来作家的“瑕病”常常指出来,《文心雕龙》有《指瑕》篇。他说:“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跟着举了很多实例。他对历来的论文者也有颇多不满,《序志》篇历数曹丕、曹植、应玚、陆机等等的不是或不足;正因为如此,他“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而有《文心雕龙》。
在钱钟书眼中,“虑动难圆,鲜无瑕病”的人,到处可见。他古今中西兼评,对外国谈艺之士往往很不客气。20世纪中华知识分子崇洋的极多,抑洋的甚少。钱钟书则不同,他的刀笔这样削下来:法国神甫白瑞蒙《诗醇》一书,发挥瓦勒利(Paul Valery)重视“文外有意”的思想;英国人李特著书批评白氏,谓英美文人已先有这样的观点。钱钟书评李特说:白氏“原未自矜创见”,“李特穷气尽力,无补毫末”。他对白氏也不放过。白氏《诗醇》虽然“繁征广引”,但对同属旧教的名诗人柏德穆的相关见解欠征引,觉得可惜;总之,白氏的书“考镜源流,殊未详核”。②关于对白氏的评论,见《谈艺录》页268-270。钱氏英法同批,男女都评。英国女诗人薛德蕙(Edith Sitwell)——
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在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文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2]392
“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这一个大英的光荣,经中华学者钱钟书的评隲而逊色了。不过,这实在难怪,薛女士又不是博学的汉学家,她怎样知道远在东亚的翁方纲已有“肌理”的宏论。
四 “打通”和“圆览”
中西兼采、中西兼评正是钱钟书过人的优势和成就。这种作法,是他所说的一种“打通”。他的“打通”有好几种,曲文军归纳为三种:(一)在横向上将中西文化思想打通;(二)在纵向上将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打通;(三)在不同学科上打通观照。[3]我们还可在曲氏的“三部曲”之外加上第四种,即:(四)事物内里和外表打通。我们可以说,就文学研究而言,则为(一)中西文学理论、现象打通; (二)不同时代的文学理论、现象打通;(三)不同文学类型(genre)打通观照;(四)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内里和外表打通。
夏志清196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度评价钱氏小说《围城》,钱氏在欧美汉学界自此受瞩目;1979年钱著《管锥编》面世,周振甫、郑朝宗等以它为研究对象,钱学跟着兴起。周、郑等对钱氏的“打通”说法、做法加以标榜。其实钱氏在早期的著作中,已有“打通”之用意和用词。1933年钱氏23岁时写成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对谈艺者视“诗文词曲,壁垒森然,不相呼应”表示不满。他认为不同文体“观乎其迹,虽复殊途”,然而细究其理,“则又同归”;他强调谈艺者要“沟通综合”。[2]4801937年钱氏27岁时发表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他引述黑格尔“表里神体的调融”论点和章实斋本末内外道德文章“而一”之说后,加评道:这是“人化文评打通内容外表的好注脚”。[2]406从这里所述,我们知道钱氏并举黑格尔和章实斋之说,是上面说的第一种打通(即中西文学理论、现象打通);钱氏认为不同文体的森然壁垒可以拆除,是第三种打通(即不同文学类型打通观照);钱氏《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所揭示的“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现象(如钱氏所引《文心雕龙·附会》说的“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即刚才征引黑、章说然后指出的“人化文评”,是第一种也是第四种(即内容外表的)打通。至于第二种打通(即不同时代的文学理论、现象打通),则前面钱氏并引《文心雕龙》“隐”说和王世祯“神韵说”属之。钱钟书打通,刘勰也打通。《文心雕龙》上半部有20篇分论各种文体,“囿别区分”,“释名以彰义”。到了下半部,近半篇幅都用于论述各种不同文体的修辞技巧,论述时把各种不同文体合而析之,通而论之,这正是“打通”。做法一如其书名,刘勰探讨的是“文心”: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的核“心”。
具备聪明智慧,加上对文学有深入通透的认识,才能发出通达之论。博观之后才能贯通、通达,刘勰说“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正是此意。太史公司马迁游历四方,广博地阅览分析史料文献,乃能“通古今之变”,其理相同。“博”与“通”与“圆”关系密切。刘、钱两位渊博的文论家,著述里博字、通字还有圆字,经常出现,如《文心雕龙》的博观、通变、圆备、圆合、圆照、圆该、圆通等,圆通且出现了三次。钱钟书在论“人化文评”时,提到《文心雕龙·比兴》的“触物圆览”说,认为刘勰对圆字“体会得无比精当”。[2]398《谈艺录》有一则钱氏花了近3千字说“圆”,引述西方“形体以圆为贵”说法,表示对此有同感:“窃常谓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西方从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英国、德国、法国,中土从《论语》到汉译佛典到唐诗到清代散文,语语都是圆形、圆觉、圆智、圆通,思转都圆,“乃知‘圆’者,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1]111因为博观圆览,刘勰深谙衡文不能只观一面之理,而有其六观说(见上文介绍)。因为博观圆览,在《辨骚》篇中,刘勰对屈原作品乃能兼顾多方,指出其“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面,而总体评为“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钱钟书对时人单方面的文学反映时代精神说不以为然,认为“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因世以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他的圆说是:
鄙见以为不如以文学之风格,思想之型式,与夫政治制度,社会状态,皆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之表现,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初无先因后果之连谊,而相为映射阐发,正可由以窥见此种时代精神之特征;较之社会造因之说,似稍谨慎。[2]483-484
五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
博观圆览的刘勰,立论时必详举例证,这一点上文略为提过。这里试举其文才的“迟速异分”说:
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掇翰而惊梦,桓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迟速各举6例,够丰富了。钱钟书的旁征博引远远超过刘勰,甚至在中外学者里前无古人,而可名登“健力士纪录”(又称坚尼斯纪录、金氏纪录)或“健笔士纪录”。例如,他议论诗歌的神、韵、言外之意时征引之繁,诚为观止:
“白瑞蒙(Henri Bremond)《诗醇》一书”发挥瓦勒利(Valery)之绪言,贵文外有独绝之旨,诗中蕴难传之妙(l’expression de l’neffable);……《碎金集》第一千八百八十七则谓“诗之为诗,不可传不可说 unbeschreiblich undindefinissabe)”亦远在兰波(Rimbaud)《文字点金》(Alchimie du verbe)自诩“诗不可言传”(Je notais l’inexprimable)以前。……《沧浪诗话》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唱三叹之音。”[1]268-275
比喻大师钱钟书论比喻,《谈艺录》自然更非獭祭前人种种比喻不可。《谈艺录》的獭祭略引如下:
《大般涅盘经》卷五《如来性品》第四之二论“分喻”云:“面貌端正,如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满月不可即同于面,雪山不可即是白象。”《翻译名义集》卷五第五十三篇申言之曰:“雪山比象,安责尾牙;满月况面,岂有眉目。”即前引《抱朴子》、《金楼子》论“锯齿箕舌”之旨。慎思明辨,说理宜然。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妆成眉目。英国玄学诗派 (Metaphysical Poets)之曲喻(conceits)多属此体。吾国昌黎门下颇喜为之。……浪仙《客喜》之“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玉川《月蚀》之“吾恐天如人,好色即丧明”。而要以玉溪为最擅此,着墨无多,神韵特远。如《天涯》曰:“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认真“啼”字,双关出“泪湿”也;《病中游曲江》曰:“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坐实“渴”字,双关出沱江水竭也。《春光》曰:“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执着“绪”字,双关出“百尺长”丝也。[1]22
非议钱钟书者说他只会罗列资料,只会抄书。这样评说极不公平。钱氏若不充分以至“过分”地把证据一一罗列出来,他的论点就欠缺说服力了。钱氏“炫”学因为他“实”学,这是“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没有东海西海“海量”式的征引罗列,他怎能让人信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个学说?这个学说是钱钟书在完成《谈艺录》时建立的;这以后,他继续在著述中用大量的例证去支持。刚才说的言外之意和比喻,正是中外古今心同理同的文论核心。上述《文心雕龙·隐秀》的“隐”正属言外之意的范畴。刘勰之后,从唐代皎然、宋代梅尧臣到清代陈廷焯,重视言外之意的说法极多。①参看拙著《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中《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一文。西方亦然。上面钱钟书所引言论之外,20世纪名诗人佛洛斯德(Robert Frost)说的ulteriority正是此意——言外之意。艾略特(T.S.Eliot)的objective correlative(笔者译为意之象)亦是,艾略特说:
表达情意的唯一艺术方式,便是找出“意之象”,即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些都会是表达该特别情意的公式。如此一来,这些诉诸感官经验的外在事象出现时,该特别情意便马上给唤引出来。②参看拙著《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页140。
20世纪新批评学派喜用的象征(symbol)一词,也与言外之意密切相关。涵义丰富、以少言多是文学语言的核心艺术,这正是言外之意的诗学价值。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怎样发挥最小资源的最大效能;文学语言之精美者,则能以最少的语言涵蕴最多的意义。就此而言,笔者可以这样“打通”:这就是文学的经济学。
刘勰重视比喻,与钱钟书不相上下。二人笔下比喻纷纷、对仗纭纭、典故频频,更可作一专题论述。③刘 、钱二人笔下辞釆斐然。其不同点为:刘较严肃而钱常见机智幽默。钱对诙谐文字常感兴趣。《钱钟 书散文》中的《小说识小》一文所引笑话提神醒脑,此处聊举一二,以博此处拙文读者诸君一粲,也可见东方西方心同笑同。《笑林广记》谓南北二人均惯说谎,一次二人相遇,南人谓北人曰:“闻得贵处极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时,道中小遗者需带棒,随溺随冻,随冻随击,不然《人与墙冻在一处。闻尊处极热,不知其热何如?”南人曰:“南方热时,有赶猪道行者,行稍迟,猪成烧烤,人化灰尘。”钱氏又引英诗人罗杰士语录》(Table Talk of Samuel Rogers,ed.by A.Dyce)第135页记印度天热而人化灰尘之事(pulverised by a coup de soleil),略谓一印度人请客,骄阳如灼,主妇渴甚,中席忽化为焦灰一堆;主人司空见惯,声色不动,呼侍者曰:“取箕帚来,将太太扫去(Sweep up the mistress)。”钱氏曰:较之《广记》云云,似更诙谐。《文心雕龙·比兴》篇论比(即比喻)和兴(相当于象征),所说的“物虽胡越,合则肝胆”那样的比喻,更与上述的“曲喻”相通。《毛诗序》言诗艺,早就标举赋比兴三者;宋代陈骙在其《文则》宣称:“文之作也,可无喻乎?”近人秦牧则谓比喻是文学语言这只孔雀的彩屏。刘勰重视文采,钱钟书认为佳作必“精于修辞”。中外同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定义,在强调其情感作用之际,即指出悲剧所用的是“装饰”的语言(英译本相关语句中连用embellished和artistic二词④S.H.Butcher tr.(with Introduction by Francis Fergusson),Poetics(N.Y.,Hill and Wang,1961),p.61.)。比喻是语言艺术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比喻是修辞的三大技巧之一;其它重视比喻的言论,如“诗是韵语与比喻(Poetry is meter and metaphor)”之说,举不胜举。正因为如此,大作家通常也是创造比喻的大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李白、苏轼、余光中。文学中的比与兴、秀与隐,相当于比喻与象征,有如宗教伦理中儒家的仁、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
人类数千年历史中,各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百家百花以至万家万花,多采多姿。愈是近代愈多样多元,简直千家争鸣、众声喧哗,心异理异者不能胜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从变者和不变者两个角度看宇宙人生,我们也可从异者和同者两个角度看宇宙、人生、文学。刘勰和钱钟书从异者也从同者看,而他们在“打通”之后,看到同心。刘勰之生也早,未接触西方(佛教所说的西天仍在东方),但他在博观圆览之后,发现“文心”就是“道心”。他在《灭惑论》一文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又说:“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是刘勰“打通”后发现的核心、圆心,也正是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那个核心、圆心。《谈艺录·序》在“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两句之后是“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们也可以说“古学今学,道术未裂”。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有“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East is East,and West is West,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的“名言”;钱钟书把它彻底颠覆了。
近日辞世的法国人类学者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1908至2009-10-30)在其1955年出版的名著《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指出亚马逊雨林印第安部族的不同部落,骨子里有相同的深层结构;而原始部族的深层思想体系,跟文明的西方社会并无分别。①"Claude Lévi-Strauss dies at 100".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nytimes.com/2009/11/04/world/europe/04levistrauss.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1957年出版的名著《批评的剖析》(The Anatomy of Criticism)②此书在1957年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中,指出不同国家语言的文学中有其普遍存在的各种原型(或译为基型archetype)。史陀和弗莱之说也就是“心同理同”之意。二人的学说获普世重视,影响深远。钱钟书的《谈艺录》在1948年出版(其伸延性巨着《管锥编》则在1979年),钱钟书视野之阔大,大概超过史陀和弗莱二人。中华学者中仰钱、迷钱者众,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说深得张隆溪等的认同,③张隆溪在其《同工异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的序中,说此书“强调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在各方面的契合与类同,而不是专注于极端的区别或根本的差异”,见页3;张氏又说“本书中有很多想法,都是受钱钟书先生著作典范的启廸”,见页5。钱学且已建立起来,但可惜的是其学说尚未有国际性地位。心同理同,中西大同;人类应有民胞物与的心情,应尽量消弭争端,促进和谐。当然,中西文化的异同是个极大的议题,涉及诸种学科诸多个角度既深且广的研探,议论纷纷是必然的。笔者绝无才学独力作全面的研讨与判断,对此所能说的只是比管更狭窄、比锥更尖小的一得之浅见而已,只是震服于钱钟书的海量式论据进而折服于他之高见而已,只是凭数十年的阅读、观察、体会认为东海西海事事物物的基本性质或核心价值相同而已。
六 结语:“潜”体系或“钱”体系;龙学和钱学
本文对刘、钱两人文学见解的介绍与比较,并不完整;即使如此,我门已发现刘、钱通论文学,虑周思精,多有心同理同处。一古一今二人都是文论大师。刘勰在中国文论史上,享誉最隆;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钱钟书。刘勰其生也早,历史与地域视野远不及钱钟书广阔,学科知识也不及钱氏丰富多元,所以《文心雕龙》的广度不及钱氏,对很多议题的析论也不及钱氏深入细致。不过,高明而中庸的种种见解,使刘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文心雕龙》还胜在有明显的体系。钱钟书自有其“隐”体系,这需要钟钱钟书的学者努力把钱氏著述内容加以分析、分类、整理后建构了。《谈艺录》等论著的点点滴滴、片片段段、则则篇篇,有如“理格高”(Lego)积木块,有耐心的钱学学者可把这些片片篇篇堆砌成理论格局高华的体系——可以是参照上述韦礼克、华伦《文学理论》纲领而成的体系,可以是参照上述“情采通变”《文心雕龙》架构而成的体系,也可以是参照钱学学者如蔡田明的《管锥编述说》纲目而成的体系(我初步的看法是:《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基本思想和写作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在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正如笔者上面所说,钱氏已建立了一个体系。该文一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体制;二论文章体制;三论体制与品类——体制定文学的得失,品类辨其尊卑;四论文学史之区划时期;五论文学与时代精神之表现;六论文学之价值端在其“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七论文学狭义说之不当;八论虚实真伪之分辨与文学之评赏;九论由行文语体区分雅俗之理,十论文学佳作应有之功用,文末附论兼及八股文之理由。
在1945年发表的讲稿《谈中国诗》,是一篇中西诗歌比较的论文。钱氏层次井然地指出:(一)西方先有史诗,中国不然,先有抒情诗。(二)与西洋诗相比,中国的诗短小,“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两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钱氏以诗为论,在论文中常用比喻,这里提供了例证);诗短,所以诗贵有“悠远的意味”。(三)“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四)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中国的旧诗词,因为诗意往往包含“浑沌含融的心理格式(Gestalt)”。(五)“西洋读者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orchestral),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六)“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vers d’occasion)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钱氏继续指出:
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品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质量,西洋诗哩,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2]532-539
在这里,钱钟书再一次表明他“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思想。
刘勰与钱钟书学博思精,文心共通,且通于东海西海,其论点尽管有岐异之处(如上面论及的“为情造文”),基本上可构成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钱著之有异于刘书的,主要是所谓“缺乏”体系。笔者在上面指出,钱氏的一些论文,已呈现了体系,而他“不成体系”的“隐”体系则可以转变成为“理格高”的“显”体系。明显可见、纲张目举的体系,便于阅读、认识,且予人自成一家、自成格局的感觉。钱钟书的“隐”体系也许应称为“潜”体系,或者“钱”体系。钟钱钟书者不断研究,尝试建构其宏大的文论体系,从“潜”到“显”,而钱学更是显学了。龙学与钱学,并为当世显学。
[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3]曲文军.试论钱锺书“打通”的思维模式[J].理论学刊,1999(2).
Liu Xie and Qian Zhongshu:Common Poetics
HUANG Wei-lia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Taiwan Fuguang University,Yulan,China)
Literary theorists Liu Xie and Qian Zhongshu,with an age gap of almost fifteen centuries apart,are brought together for comparison in this article probably for the first time.Liu’s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Wenxin Diaolong)and Qian’sOn Literature(Tanyi Lu)as well as his other works of literary criticism written when he was 36 years old or younger,are compared.With references to the systematic framework provided by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Wenxin Diaolong),both theorists’ideas ranging from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to its rhetoric skills are juxtaposed;and we discover that they have tremendous commonness.Their discourses on metaphor and on ulteriority,among others,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universal or common poetics.Qian is famous for his super-erudition and his abundance in citing evidences to support his claims.Critics of Qian have harsh words for this“excesses”in citation.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is exactly the way for Qian to build solid foundations for his theories.Illustrating with massive quotations from various cultural traditions that“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a common heart and mind,”Qian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ity and thus would probably promote harmony in the world.He deserves an internationally highest prize for peace.There is criticism that Qian’s literary discourses are just notes-like writings,without an apparent systematic framework.The author argues that by reorganizing and categorizing the contents of Qian’s critical writings,a grand systematic framework would emerge from these.
Liu Xie;Qian Zhongshu;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Wenxin Diaolong);On Literature(Tanyi Lu);literary theory;common poetics
I 0
A
1674-5310(2010)-05-0092-09
2010-08-18
黄维樑(1947-),男,广东澄海人,香港中文大学一级荣誉学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历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美国、台湾、大陆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或客座讲座教授。现任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