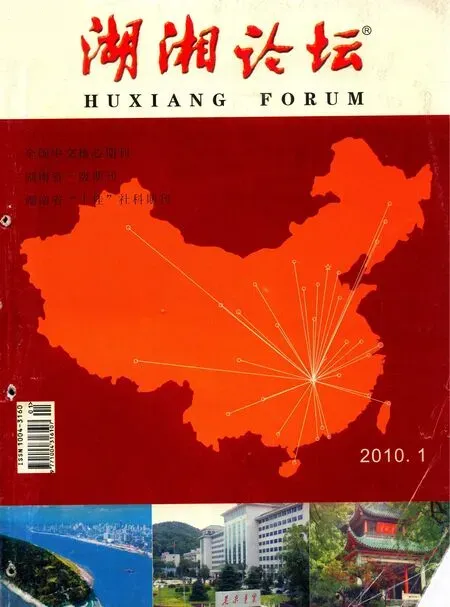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从王维对闲适的吟咏看“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胡遂,曹梦晶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2)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从王维对闲适的吟咏看“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胡遂1,曹梦晶2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2)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佛”,其一生的文学作品中,对闲适生活的吟咏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其独有的恬淡空灵的特色,究其缘由,与其对佛教的深刻造诣分不开。本文试从其闲适诗与佛教的交汇之处,浅谈王维的“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王维;闲适诗;禅宗
被后世称作“诗佛”的王维,以其杰出的艺术才能与高深的佛学修养,成为盛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珠。尤其是他的山水田园诗,独有一种空灵、澄澈、悠远之美,唐代殷评王维诗云:“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极言王维诗歌意境之独绝。的确,盛唐时代,山水田园诗自成一派,虽俱绘山水,却各有特色:孟浩然之平淡,韦应物之清新,柳宗元之冷峭,刘长卿之苍凉,裴迪之幽寂……然王维能独绝其间,因其“以禅入诗”,在对山水自然的审美观照中,融入佛禅之道,体悟宁静的真谛,使他笔下的山水诗,不仅空灵静美,意境悠远,更禅意盎然,因此在山水诗苑中独具魅力。尤其是王维晚年的隐居生活里,一心习佛,写下了大量以禅入诗的闲适诗,在云水自然中吟咏情性,这些诗作处处闪现着若有若无的禅意,如佛光影现,引人入胜。
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无论是北宗禅之“渐悟”,还是南宗禅之“顿悟”“,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悟”是三昧之别称,所谓“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坛经》),慧能认为“人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一任主体心性的坦然呈现,“即心即佛”,当下即能妙悟成佛,而若要达到“明心见性”,则需“一行三昧”,无论是闲居净坐,入定冥想,还是悠游山林,兴致所往,只要能够杜绝心间杂念,抛却俗世束缚,往往就会在一刹那间,妄念俱灭,物我皆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自已仿佛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心里会产生一种奇妙又愉悦的感受,静谧的自然里流动着盎然生气,这就是“禅悟”。而严羽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禅与诗的相通之处,或在此间。
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论王维闲适诗中的“无念”思想
王维大半生生活在辉煌灿烂的盛唐时代,盛世年华,气象宏大,政治开明,国家繁荣。这也是古代诗歌发展到极致的一个时代,诗人们赋诗表怀,漫游励志,游侠赴边,一首首意兴盎然的诗歌,犹如一个个昂扬的灵魂,落魄也洒脱,率真也不羁,积极也超然,他们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情怀,渴望“达则兼济天下”,所作诗歌“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扫齐梁五代空有繁丽之表而无兴寄之志的靡靡之音,傲然如原野上最辉煌的红日,即使仕途受挫,诗人们也不哀怨泄气,或是“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养性,或如庄子般逍遥天地间,不问功名事,或在深山古刹里,林木溪涧边参禅观心,证得吾身。
王维早期诗歌亦多反映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如“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燕支行》)、“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树功勋”(《老将行》)、“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从军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陇西行》)、“慷概倚长剑,高歌一送君”(《送张判官赴河西》)等等,这些诗作充满了英雄气概,寄寓了诗人立功报国的政治思想。然而,安史之乱前后,政治上的腐败黑暗,战乱的动荡不安,被叛军俘后的监禁生涯,平乱后因被授伪职而定罪……人生境遇如海浪沉浮,困境挫折不断,使诗人对于政治以及个人前途渐渐失望,“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诗人在《叹白发》中发出感慨,又在《饭覆釜山僧》中自言:“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可以看出,王维看淡了名利,选择在孤独与寂寞中,以禅悟为人生之乐趣。
综观王维的山水诗作,诗中最常出现的便是“空”、“寂”二字,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酬张少府》)……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足可见佛禅之“空寂”观对他的影响。王维一生,半官半隐,尤其是晚年时居于辋川别墅,终日与友泛舟往来,共赏烟霞,吟咏山水,弹琴落画,如此生活,怎一个“闲”字了得。《全唐诗》上载:“……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笃于奉佛,晚年长斋禅诵。”晚年清净悠闲的隐居生活,使诗人拥有一颗宁静安闲的心,忘却尘世喧哗,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中,明心净性,胸无杂虑,于山林间悠游,感悟自然,进而将这种领悟转移到人生的体悟。
王维的闲适诗大多为隐居于终南别业和蓝田辋川时所作,其时身闲心亦闲,一首首空明澄净的山水诗,如一幅幅淡雅宁秀的水墨画,读之可品其清芬,赏之可观其神韵,悟之可觉其禅意。何谓“闲”?有首很出名的禅诗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闲,是为无事,无牵挂,身无束缚,悠游自在,清净的生活,空旷的心境,方可称之为“闲”,心闲之人观物,物皆著“闲”之色彩,淙淙清溪,漾漾菱荇,澄澄葭苇,脉脉斜晖,淡淡月光,亭亭新荷,青青绿竹……莫不因诗人之眼观之,而体现出自在写意,随性自然的风貌。
观乎前代田园山水诗家,恬淡莫过于陶渊明,清新莫过于谢灵运。前者以其整个人生经历,开拓出了一片田园隐逸的天地,东篱与菊花,南山与酒,成为后代诗人心里无法割舍的世外桃源。后者则将笔触转向山水,另辟蹊径,扭转了一代诗风,“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沈德潜《说诗晬语》),在对自然山水的描摹刻画中,暗用匠心,使之既有“出水芙蓉”之清新,又有“错彩镂金”之绮丽。渊明的归隐田园与大谢的纵情山水,一个在出仕与归隐中,决然地择其后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更道出了他对归隐后的自在生活感到无比愉悦。可以说渊明之“闲”,在于心,“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金人元好问此句评点,深得陶诗之旨趣。而大谢因仕途受挫,转而将审美情趣移向自然,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徜徉山水,肆意遨游,不言心累,借山水清音抚去心中不平,可以说大谢之“闲”,在身不在心,与陶诗相比,谢诗难以达到陶诗那样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常常是有句无篇,或许是因其未能将俗事纷扰放开,无法将本心真正完全地投射到自然山水之中吧,董其川说,“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若无一颗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无念”之心,又怎能体会那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自在气韵?
王维也有过追求功名的时候,但是“浮名寄缨珮,空性无羁鞅”(《谒睿上人》),他不甘也不愿在官场里沉浮,也不愿身心被束缚,不只一次地,诗人在诗作里表达了愿挂冠而去,隐居山野的愿望。他寄情山水,专注诗画,渴望如飞鸟般回归本心自然,那“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的宁静生活,“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的安闲心境,如何不令仕途受挫的诗人心向往之?“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送张五归山》),因朋友的不幸遭遇,引发了诗人的愤懑与无奈,王维并非没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勇气,也并非没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实在是家境所迫,责任使然——“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偶然作》之四),做为家中长兄,实在是出于无奈。直到晚年,王维过上了“半官半隐”的生活,终得身闲,一心向佛,“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以“寂悟”为乐,在王维安闲的生活里,成了他最为倾心的事情。
再看王维诗中之“闲”,从初时的渴望闲逸——“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认识到自己身闲而心不闲——“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闲”(《留别丘为》),有与僧、友相交之闲——“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秋色有佳兴,况君池上闲”(《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有体观物相之闲——“澄波澹将夕,清月皓方闲”(《泛前陂》)、“闲花落岩谷,瀑水映杉松”(《韦侍郎山居》)、“圆光含万象,碎影入闲流”(《赋得秋日悬清光》),最终求得心闲自在——“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答张五弟》)。王维从休官罢职的身闲,逐渐上升到萧散平淡的心闲,从逐渐离开官场,抽身红尘俗世,到最终达到心无挂碍,随缘自适的超然心境。
王维虔心修禅,晚年生活萧散平淡,离开官场后,诗人终得心闲且无挂碍、随缘自适的心境,且看下面一系列的五言绝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如此之类的小诗,在王维诗集里有许多,意境空明朗净,给人以空幽静寂之美感,春山绝人迹,明月照溪水,花落无声息,红叶日见稀,或有斜阳映青苔,或有竹风送琴韵……一切自然景象在诗人笔下,缓缓铺开,如挥就一幅春山图,却可听见鸟鸣、人语、琴声,静中有动,在这静寂之中有着勃勃的生机:鸟语花香、诗情画意,令人读之如临其景、如感其境,在这虚融清静中又分明感到一种淡淡的生命的喜悦。诗人心无杂念,所写之物也是如此清淡,恰是这颗清净无染的真心,无执无求,无束无缚,才能放任心神,一任本然,才能以清澈之眼观之,清净之心写之,最后达到纯粹自然空灵静美的境界,诗与境偕。
二、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王维闲适诗中的“无相”思想
唐朝禅师青原惟信云:“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是参禅的三种境界,也是人生行路的三种不同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还停留在事物的表象阶段,通过身体感官来认识客观世界,而不知山水所蕴含的“意”;当其学参禅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知山水是“法身”的显现,渐渐融合了自我意识,将主观心灵情感投射到客观事物上,类似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体现了自我生命的传达;当其大彻大悟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认识到“色空如一”,则是自由地观照,自由地出入于客观与主观之间,没有束缚,自我已经成熟,身体与灵魂已拥有宁静、独立,一切无可无不可,山水与我无妨,与王国维“无我无物之境”相似,已达到了最高妙境。为诗也是如此,唯有识遍世间纷繁复杂的种种色相之美,加以自身的审美体验,才能最终到达妙空无我的宗教或哲学层次。
就诗人自身而言,以“兴趣”所观照之外物,无论是青青翠竹,郁郁黄花,还是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尽管各具不同的相状,但全都是真如佛性之体现,所谓“月白风恬,山青水绿。法法现前,头头具足”。在大自然面前,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切都是现成,一切都是圆满自足,一切都是“真空”随缘显现的大千世界之“妙有”。“无相”即“离相”,于一切相,离一切相,是为无相。当诗人看遍种种纷纭色相,真正沉浸入无边山水自然中时,会将心中的妄念放下,一切来自心灵的束缚都会杳然无存,心中唯有畅适,唯有惬意,这就是涅磐,就是解脱,就是超越,就是自在。
王维称自已“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有着高超的绘画技艺,极能捕捉大自然种种光影变幻间的美景,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充分说明了王维诗充满诗情画意的特点,王维以其画家的敏感与诗人的兴致,描绘了自然之景在时空流转过程中的种种瞬间流变,展现了山水清音的气韵,也体现了世间万物的无常之态,更因诗人禅学修养深厚,使他诗中的画意多有自然天趣,宛若天成,诗境与禅境相得益彰,心境与自然契合无间。如《田园乐》其六: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活脱脱的一幅闲逸春眠图。桃花,多艳丽美好而又易于凋零的事物,犹带宿雨,更显其鲜红娇艳;柔绿的柳枝在远处摇,似笼一层薄雾,更添了几分浓绿。在大自然无比惬意舒适的春光里,花落满庄,家僮未扫。黄莺轻啼,山庄的主人却犹自沉睡,睡意酣然。真不知是这融融春光赐予了诗人如此闲散清净之心,还是诗人澄澈安闲的心境方观到宁静的春意。所谓“一切诸法本性皆空,一切诸法自性无性。若空无性,彼则一相,所谓无相。以无相故,彼得清净。”随意自然,离却万相,才能摆脱尘世的种种俗念,恬然澄明,达到“本来无一物”的清净之域。
还有这首《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秋雨之夜,给人以悲凉难以自处的情素,更深人寂,诗人独坐空堂,想到岁月无情逝去,还有生老病死的无奈,“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山果可知自己落去的韶华,草虫可知自己渐渐的离逝,自然之物也是悄悄地被时间无情地带走,而犹不知。诗人顿然开悟:人与自然万物一样,有生必有死,短暂的生命,如有刹那的光彩,也是永恒,“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身心超脱,物我两忘,才能真正地领悟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再有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瞑》)的清幽明静,“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的若有还无,“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的波澜阔大,“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的婉转明丽……皆体现出了诗人闲逸超脱的品性与外物和谐圆满、宁静生机的风神合一。诚如李泽厚评《鹿柴》、《鸟鸣涧》、《辛夷坞》三首诗时所说:“一切都是动的,非常平凡,非常写实,非常自然。但它所传达出来的意味却是永恒的静,本体的静……自然是多么美啊,它似乎与人世毫不相干,花开花落,鸟鸣春涧,然而就在这对自然的片刻直观中,你却感到了那不朽者的存在。”王维诗超越了外象的沉静而达到了富有生命力的扶摇而上之美,在闲适生活状态下,大自然给予诗人的启迪,使诗人创造宁静幽寂的诗境中,焕发着生命的律动,“那不朽者的存在”恰是禅在诗人参阅水山过程中的灵感启发。
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闲适诗中的“无住”思想
“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已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禅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产物,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心灵的体认与外界的流逝感悟如此之深,才能将禅发挥到极致。而禅诗,也是独有中国特色,饶富深趣。禅家所倡导的“顿悟”、“明心见性”、“即心即佛”等思维方式推及至诗歌创作,直接给予了诗人在观象体物,参照山水自然的过程中灵感的启发,“一花一世界,一砂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佛典》),最是这样难以言说的刹那心会,深得佛家诗家深味,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如同疏林斜斜投射下来的阳光,空中浮动的微尘,某个午后时光的凝结,却有风细细吹过诗人的心怀,静止与灵动,瞬间与流逝,悠然神会,妙处难与君说。
王维诗中多次提到自己爱闲居净坐,在坐禅中体悟。《旧唐诗·王维传》中也曾提到王维“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闲居净坐”,参禅悟道,“禅定”就是“安静而止息杂虑”,要求专、空、无、静,要“离一切色相”而入“虚空处”,唯有得到“虚空处”才算是到“实有处”——幻化了一切,才能拥有一切,空下心,才能有心去体察万物,这也是庄学中无与有的辩证法,庄子也曾提出的“虚静”、“坐忘”,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已身存在,达到虚静的状态,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才能创作出与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禅悟”之道,与此相似,王维对此亦是了然,如这首《书事》: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清淡淡的一首小诗,恰如诗人清闲的心境,缓缓冥冥,微雨深院,泯于无形。这是幅静寂的画面,万物皆慵懒自如,闲适随意,连时光仿佛都停止了脚步,而诗人却瞥见那雨后愈加鲜绿的苍苔,好像要从地上跃起,亲昵地依上诗人的衣裳来,这样的幽静深院,却有着这样灵动的生机,细微的禅机,借着诗人从容和谐的心境,与细致敏锐观察,被点现出来。苏轼诗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诗》)。“空静”之中,包领含着生命无限的可能性,犹如平静的湖泊,水里暗流涌动,鱼儿轻灵游弋,静中有动,动中寓静。若诗人满怀愁绪,又怎能看到如此细微的物色之动,若诗人心绪迷离,又怎能抓住大自然赋予的瞬间契机,“欲上人衣来”实是神来之笔,方得此怡然之妙趣。
再有这首被胡应麟誉为“五言绝之入禅者”的《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花开花落,如美人迟暮,最是令人黯然神伤,后主一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传达室了多少幽恨。古时之人写落花,无不洋溢着浓浓的忧伤与惋惜。但在王维诗笔下,却是另一番景象:空寂无人的深山流涧边,鲜艳的芙蓉花生机勃勃地开放着,如此灿烂,如此幽雅,落蕊纷纷,自开自落,这是一场无人打扰的盛宴,开也罢,落也罢,不求人欣赏,也不需要人怜悯,诗人只是恰巧见证了这一幕的华美,蓬勃的生命,寂静的山坞,采采的流水,刹那的生灭,整个世界莫不如这芙蓉花一样,“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泰戈尔《飞鸟集》)。胡应麟言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真是不着禅语,尽显禅心。唯有舍弃对“相”的执着追求,看清这世间万物——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种种纷纭变幻之色相,都处于生灭无常的状态中。诗人不因其生而狂喜,不因其死而悲痛,这并不是漠视生命在此间的刹那生灭,而是以一颗恒心观之,生命的存在只是刹那生灭的连续显现;人与一切有情众生,都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自我,即是佛家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除去“坐禅”,王维还采取一种“山林悠游禅”的修习方式,“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永嘉玄觉(《证道歌》),在悠游山林的过程中,遍看万物诸相,秉持着“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习禅理念,在自然山川、泉源溪涧、草木丛林中体悟禅机。“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木兰柴》)、“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瞑》)……诗人以清净无染之诗心观物,周遭事物都是如此明净、闲逸、澄澈、悠然,不着意去寻禅,不刻意去描写,语淡而自然,清新而持久。有一首禅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禅,就像雪后初蕊一枝的冷梅,淡香萦人,不作言语,不需刻意去寻,在某个蓦然回首的瞬间,拈花微笑,了悟禅意,如这首《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如。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南山”,隐逸之别称,在中晚年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中,诗人常常乘兴独自闲游,淡然世外。“胜事空自知”,更道出了自己洞悉尘世,怡然自得的情怀,最令人称道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一联,姿态翩然,风神清朗。诗人心思闲逸,随心行走,待到水穷处,未有阮籍哭穷途之举,而是拂地南坐,静观云起,并不因行路岐岖而悲观着怒,并不因末途而惊慌绝望,不刻意寻求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宁心静性,不烦不恼,看云生云起,别有一番风味。六祖慧能说:“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行云流水,不住无碍,任心飞扬。
恰是“不住”,才是任兴使然,无拘无缚。如诗人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蓝田山石门精舍》),凌波微笑,随任风神,表现出了诗人无比恬适与散淡的心境。
禅,并不等于寂灭,在禅宗看来,佛性遍于有性,宋朝洪寿禅诗有诗云:“朴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充分道出了世间万物皆显佛性。清朝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云:“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迦叶见花,因为能与世尊心心相印,体悟“真如”无限生机自由流动的精神境界,所以“破颜微笑”。王维在遍看周身般若实相的过程中,看到了大自然里活泼的生命流动,广褒天地间流转的勃勃生机,都在诗人宁心静性的观照中展现着最自然最纯粹的本来面目,“拈花微笑”,心领神会。
综上所论,王维“空观”世间万物,其笔下的林泉山石、月夜花溪,都与诗人心境相偕,达到淡泊恬淡,空灵澄静的艺术境界。当诗人在山水景物中感悟禅理、证悟禅理的同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与自由,也使诗与禅相合要契,获得了审美与心灵上的愉悦,王维通过禅宗“一行三昧”禅来进行审美观照,使其笔下的诗歌,极富禅意,不仅是山水田园自然美的纯粹体现,更是空静超俗心境美的清净再现。
I1206
A
1004-3160(2010)01-0082-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佛教与中国文人心路历程》[编号:04BZW034]的阶段性成果。
2009-11-27
1.胡遂,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国古代文学;2.曹梦晶,女,湖北大治人,湖南大学赴泰国支教志愿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叶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