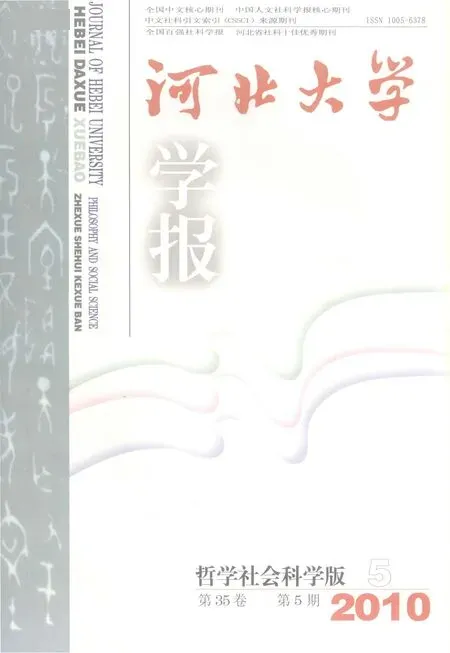王阳明“龙场悟道”之三时论
王路平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 550002)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三时论
王路平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 550002)
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这是他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在500年前的这个同一时空中,浓缩了阳明悟道境况的三个时段,即前悟道之苦难时、悟道之体悟时和悟后起修之受用时。公元1508年阳明龙场悟道的这三个时段,不仅是阳明个人生命心路历程重大转折性的人生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思想性事件。深入考察分析这一大事因缘,对我们理解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启发我们的生命觉悟,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阳明;龙场悟道;三时论;体悟;悟后起修
王阳明最终归本孔孟,悟得圣人之道,是缘之于龙场悟道。黄宗羲云:“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1]181阳明之学,凡三变:始泛滥于词章,继学朱子之书,又出入于佛老,最终龙场悟道而始得其入圣之门。因此正德三年(1508)37岁的阳明在龙场悟道,这是他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在500年前的这个同一时空中,浓缩了阳明悟道境况的三个时段,即前悟道之苦难时、悟道之体悟时和悟后起修之受用时。公元1508年阳明龙场悟道的这三个时段,不仅是阳明个人生命心路历程重大转折性的人生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思想性事件。深入考察分析这一大事因缘,对我们理解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启发我们的生命觉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前悟道之苦难时
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死,明武宗继位,时年仅15岁,因年幼昏庸无能,不理朝政,以太监刘瑾为首的“八虎”(即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八个太监)专权,朝政紊乱。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十月,明孝宗的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谢迁等联合上疏,请诛“八虎”,却被刘瑾矫旨罢职。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四川道监察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要求起复刘健等,又被刘瑾矫旨将他们解京入狱。是时阳明任兵部主事,面对这种黑白颠倒的严峻形势,他没有像其他一些朝臣那样望而却步,明哲保身,而是冒死救援。十一月他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将矛头直接针对刘瑾,结果被刘瑾矫旨将他廷杖四十后系狱,十二月谪为贵州龙场驿丞。谪官龙场,是阳明坎坷人生的最大一次灾难,也是促成他悟入圣人之道的大因缘。在贵州的三个年头里,阳明遍历种种苦难,受到无尽的折磨,但却在贵州悟道成道,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心学体系。
正德三年(1508)三月,阳明抵达龙场。当即面对五大苦难:一是环境艰险。龙场在今贵阳西北40公里的修文,当时“处于万山丛棘之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2]1228,外来之人,水土不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二是居无定所。阳明来到龙场,并无居所,只好自己在境内小孤山下结草庵居之,其后阳明又移居龙场境内龙冈山(又名栖霞山)的“东洞”中,改其名为“阳明小洞天”,以此寄托对故乡浙江绍兴会稽山阳明洞的思念之情;三是生活无着。在上述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阳明的生活也没有保障,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世界:无米、无菜、无盐、无油、无火、无水……,为维持生计,存活下来,阳明以一介文弱书生亲自去砍柴、挑水、采蕨、摘菜、煮饭、浇园,直至请学于农,种田南山;四是疾病缠身。环境艰险,居无定所,生活无着,穷途潦倒,使阳明多次旧病复发,加之当地缺医少药,瘴疠侵之于外,忧郁攻之其中,随时都有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可能;五是官吏迫害。先是阳明为救戴铣等言官,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被刘瑾矫旨下诏狱,受廷杖四十之刑,一度死而复苏,大难不死,寻贬谪龙场。在赴谪途中,阳明曾被刘瑾的刺客追杀,至龙场刘瑾对阳明的威胁并未解除。是时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府,遣人至龙场凌侮阳明,不料却引起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公愤,他们把差人围困起来羞辱并痛打之,最后将差人赶出龙场。差人向王质告状,王质大怒,要阳明认错谢罪,阳明不畏强权,拒不谢罪,后赖阳明同乡、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从中调解方罢。
面对这五大苦难,阳明怎么办?这五大苦难的折磨,超过了一般人所能忍受的限度,而他却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龙场这种出生入死的临界境况下,长期困绕阳明心中的生命精神归宿问题再次空前大爆发。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3]告子下德国存在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认为,大病、生死是人实存的“临界境况”或“边缘处境”,它能促使人突然觉悟,发现日常世俗生活的虚幻和无聊,大病、死亡迫使人们重新检视生命存在的本真价值,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阳明从京城到龙场,已经在长期的思索和生命的实践中,超越了得失荣辱,惟生死尚未了断。到达龙场面临五大苦难,促使他作出最后的了断。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要向生中活,便向死中求;大死一番而后大活,置诸死地而后生;若要人不死,除非死个人;凤凰涅槃重获新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等道门中语,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皆即此之谓也。阳明后来曾说:“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2]154
前悟道时,龙场五大苦难的境遇,使阳明“百难备尝”,这为阳明龙场悟道准备了外部条件。可以说阳明龙场悟道,既是他先天条件(生长于三代书香世家,聪明绝伦,12岁即有为圣之志)发展的趋势,又是他早期思想演变的产物(未至龙场前已饱读各家论典,出入儒佛道),更是他处于龙场这个特定环境(五大苦难)中产生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而以后者为悟道的契机。
二、悟道之体悟时
面对龙场这种凄凉困苦的境遇,阳明反复设想“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在境遇险恶和死亡逼迫的生命极限体验中,阳明依次采取了最为本真的五大人生态度,即接受、承受、忍受、抗争和超克。第一,阳明必须接受现实。阳明谪居万里绝域,只身面对五大苦难,去之不可,忘之不能,内外交困,百难备尝,只能挺直脊梁,接受苦难,先活下来。第二,阳明必须承受。在五大苦难的生存环境中,阳明承受着肉体的痛苦,内心的煎熬,常常处于彷徨、焦虑、恐慌、绝望之中,时时在生命的紧张里苦苦支撑,以至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不仅经世济民之志成为泡影,而且恬静清静的生活也无从谈起,唯一的就是“吾惟俟命!”第三,阳明必须忍受。五大苦难如魔鬼似的撕裂着他的神经,啃噬着他的意志,使他遭受炼狱般的痛苦却无法解脱,承受惨烈的折磨却无法逃遁,唯一的只能是在其中忍受!在其中挣扎!在其中奋然前行!在其中动心忍性!这无法排解的大痛苦、大困惑,最终促使他大抗争、大觉悟!阳明十年后回忆说:“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2]159第四,抗争。有了抗争,阳明虽然谪居龙场,日有瘴疠、盅毒和魑魅魍魉“三死焉”,而“未尝一日之戚戚也”,王质的加害,阳明视之为“三死”而已尔,决心置生死于度外,拒不向权贵屈服,坚持抗争到底,这充分表现了阳明刚正不阿、坚持大义的大无畏精神!阳明的抗争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无怨无悔,真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第五,超克。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一切有无、爱憎、善恶、是非、名利、贵贱、得失、荣辱,总之一切的一切,对阳明来说都无所谓了,“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惟生死一念尚存于心,“而后如大梦之醒”,必须刻期证道,超克生死,使自己的身心不再流浪!
于是阳明“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象山语),他抛开一切得失荣辱、生死之念,藐视困难,开始静坐沉思,以求静一。他终日默坐“玩易窝”中,冥思苦想,反复诵读《周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后经思索再三,认识到“精粗一,内外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的道理[2]897,终于悟出“心即理”之道,“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龙场悟道”。《年谱》对阳明龙场悟道作了如下描述:
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误也。[2]1228
阳明日夜于玩易窝洞中端居澄默,以求静一,这是阳明悟道的最为关键的过程。在中国文化中,所谓“端居”“澄默”“静一”就是静坐。静坐就是一种如实体悟而自我觉悟的修行工夫。体悟心体亦即寻求真实的自我以获得自我觉悟,然后即依此真实自我参与历史文化活动,成己成物,自救救人。在世俗日常生活中,人们由于种种计较和私欲,而将本真本善、纯一澄明的心体遮蔽,从而使世界和人生丧失价值和意义,疏离了真实的存在,使人的存在异化为物的存在。为此中国儒佛道三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静坐的方法,以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根本,以促使人找到自我,自我觉悟,从而使人的生命真正成为具有本源的活动和有意义的存在。因而静坐是中国儒佛道三家悟道的共法,即通常道门中修行所说的“趺坐”或“跏趺静坐”。所谓“趺坐”,就是悟道者把两脚背置于两腿股之上的盘坐方法,有圆满安坐之意。道家讲守静、心斋、坐忘,佛教讲禅定、止观,儒家讲静坐,都是讲的这种工夫。
儒家经典《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静、安既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悟道工夫。宋代程颐提出静坐,有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说。陆象山弟子杨慈湖常拱坐达旦,有静坐反观之说。明代陈白沙提出静坐见体之说。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终而归本儒学,对三家静坐之法应相当熟悉,他所采取的工夫应是佛道儒三家的静坐共法,最终归于儒学的静坐体悟。龙场悟道从静坐体悟而来,以至阳明悟道后将静坐体悟作为教门的重要方法。黄宗羲云:“自此(龙场悟道)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1]181阳明过常德、辰州专教人静坐,自云:“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2]1230阳明至滁州督马政,“见学者往往口耳异同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2]1575。后来阳明释《大学》定、静、安云:“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2]25
阳明在玩易窝洞中,端居趺坐以求静一,体悟到在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中,不仅一切贵贱、荣辱、是非、得失、成败等皆可舍之,甚至连生死都可舍之,置生死于度外,而一切舍之所剩下的则唯“吾心”而已,因为吾心良知是舍无可舍、损无可损者,是念兹在兹者,“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2]1342阳明悟此,心灵震憾,激动万分,故“不觉呼跃”。澄心久之就感到胸中“洒洒”。“洒洒”者,内心喜乐,言行洒脱之谓也,佛门中人达到二禅即会有此体验。二禅,有内净、喜、乐、定四种功德,因为它已经断灭了一切生死之念,心无挂碍,心中呈现明净、喜悦、快乐、安定四种状态,非常爽快、自由。阳明的“洒洒”境界,表明他已超克生死一念,面对“居夷”的一切苦难处境都能谈笑处之。于是他又是做歌诗,又是调越曲,又是杂谈笑,竟然“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阳明龙场悟道,在静坐过程中对世界和人生的观察获得重大突破,了悟了心性本体,开辟了自己崭新的人生境界。
阳明龙场所悟之道是什么?这个“道”主要并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然事物的一般规律、法则、条理,而主要是人的道德伦理、道德原则、道德意义,它关乎人的终极依据、终极理想和终极意义,一句话即道德的终极关怀。道德的终极关怀,是指存在世界之中的人,他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什么才是最值得为之终身追求的理想?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解答就形成了人生的价值观。一旦树立了人生价值观,就为人遭遇到的生活提供了自由选择的行为指导,为事物的价值判断提供了应然性依据。阳明龙场所悟之道,从直接的内容看,不外是对格物致知之说的重新理解,而其深层的内涵则颇为复杂,主要包括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和致知格物三个内容(另撰文论述)。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自觉得失荣辱、生死之念皆已超脱,他的疑问全部得到解决。接着他以自己的体悟印证于五经,无不契合。之后便提出了他的“知行合一”之说,并奠定“致良知”的理论基础,后来进而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心学理论体系。
三、悟后起修之受用时
阳明弟子王畿总结师门三种入悟教法云:“从知解而得者,谓之解悟,未离言诠;从静中而得者,谓之证悟,犹有待于境;从人事练习而得者,忘言忘境,触处逢源,愈摇荡愈凝寂,始为彻悟。”[1]253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在京师时,求之周敦颐、程颢之学,与湛若水相互切磋,即对心学有所解悟,然仅是从知解而得,“纸上得来终觉浅”(陆游诗);龙场悟道之体悟时是从静坐中而得证悟,尚离不开当下之境遇;悟后起修,受用心学,事上磨练,触处逢源,方谓之彻悟。对于已经体悟到本心良知的人来说,应该时时“必有事焉”,日日“提撕警觉”,要注意不间断地进行精神修炼和实践工夫,存养良知,扩充良知,发用良知。“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之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则知致其良知矣。”[2]267在良知的召唤和运作下,阳明就从本体世界进入存在世界,将自然生命、道德生命和文化生命合并归一,通化为一个生命,使他的人生开始具有真正的意义,将他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到无限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之中。龙场悟道,不仅使阳明的心学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而且也使他达到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阳明在此境界中,不异旧时人,只异旧时行履处;高高山顶坐,深深海底行。阳明《玩易窝记》云:
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联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内外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呼!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亡拘幽,而不知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2]897
君子悟道后,则知其所以终其之身,如周文王被囚拘而演《周易》,孔子遭厄运而作《春秋》等,悟道而成道,而不知老之将至。同样,阳明遭遇龙场五大苦难,经过悟道之艰难,终获得道之喜悦,成就了心学的大受用。儒家从孔子时就提倡“为己之学”,其学不是为了自己获取功利,而是为了成长自己、充实自己、修养自己,发展自己,完成自己的人格,圆满自己的道德,因而它是生命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是安身立命之学,是成己成物之学,是体验之学,是意义之学,是受用之学。阳明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找到了自己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找到了自己的为己之学,因而他得到了大智慧、大受用。何为受用?受用是身心修养的实证自得,是生命气质的变化,是精神状态的转化,是人生境界的提升,是转识成智。得大智慧而享大受用,阳明从澄明的本体即本心良知而展开发用的人生新境界,是一种艺术人生、快乐人生、自由人生。晚年阳明的《中秋》诗适可说明阳明此时的心境:“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2]793
阳明龙场悟道后,精神生命得到终极安顿,心中充满光明,万缘都已放下: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朝已悟道,夕死可矣。阳明寻找光明,得到了光明,最终心中充满光明,由此死不足畏、死无所憾、死而瞑目矣!由此知所以终吾身矣!由此至大至刚之气得以养成!由此遇生死而解生死,解生死而了生死,了生死而超生死,超生死而任生死!故其临终“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之语,盖早出之于龙场悟道之时也。有了龙场悟道的这一大事因缘,以后使他在酬酢万变时能够排除任何困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不勉而中,当下即是;斟酌调停,纵横自在,阳明的人生之舟开始扬帆入海,破浪前行!后人有联赞阳明龙场悟道云:“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光绪二十八年贵州布政使罗绕典撰于龙场阳明洞王文成公祠正门石柱)悟后起修,受用心学,阳明一扫郁闷阴霾,心情感到轻松自如,这从其《居夷诗》中的“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梦魂兼喜无余事,只在耶溪舜水湾”“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渐觉形骸逃物外,未妨游乐在天涯”“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2]702-713等诗句即可见之。这时阳明已有预感,他的人生已否极泰来,阴极阳回,他将会出山弘道,并且不久将会离开龙场,这从其《居夷诗》中的“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阴极阳回知不远,兰芽行见发春尖”[2]703-707等诗句中即可见之。
阳明悟后起修,修以证悟,一心开二门,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2]31。一方面他要置身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创造活动之中,振人心,砺风气,对人生和宇宙承担责任,完成使命,使万物得其理,万事得其位,这体现了阳明之“仁”,此即本体即工夫也;另一方面,在世上做事功的同时,他又能超越于一切贵贱、荣辱、是非、得失、成败之外,一切尘染皆不足以累其心,情顺万物而无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微近纤曲而盛德存焉。诚如阳明所说:“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故凡有道之士,其于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而取舍爱憎也,若洗目中之尘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相,值若飘风浮霭之往来变化于太虚,而太虚之体,固常廓然其无碍也。”[2]211阳明遭受“百死千难”而龙场悟道,最终觉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其后虽经宁濠之乱,张、许之难而毫不动摇,反而在艰难困苦之际,生死存亡之间,更加体验到自己的本心良知这个本体,从而能主宰万物,不惧权势,不为富贵名利、贫贱得失所动,这体现了阳明之“智”,此即工夫即本体也。
阳明悟后起修而落实于事,归位儒者而尽其心,“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2]257。是时阳明未在政位,只能做“礼乐教化之施”,故虽冒天下之非难而遑遑然不忘讲学弘道,以使龙场乡民复归心体之同然。阳明《何陋轩记》云:
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2]891
阳明在龙场从其儒家心学“性善论”出发,在《象祠记》中提出“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2]894的观点。他认为“心即理”,人之本心即是至善,此心此理人人皆有,故圣贤与凡夫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区别仅在于修炼程度和本心复明程度的不同,只要“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因此他在《何陋轩记》中,深刻剖析了龙场少数民族的内在本质,批驳了那种“居夷鄙陋”和“蛮夷不可化”的谬论,认为对苗彝诸少数民族只要通过教化,诱导他们认识本心,都可以成圣成贤。所以他并不因为龙场苗彝诸土民“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而有所嫌弃,而认为他们“犹淳庞质素之遗焉”“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阳明“居夷”三年,龙场少数民族在食、住、行等方面给予他无私的援助,他们内心的朴实善良和嫉恶如仇的耿直性格,给阳明留下深刻印象。龙场“夷民”这种淳朴善良的民风,与朝中士大夫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习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龙场“夷民”有此“淳庞质素”,所以如果对他们施以教化,“其化之也盖易”。后来阳明回忆说:“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大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2]1574-1575中原士大夫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意见”、成见、思想观念,反而遮蔽了他们的良知,而黔中龙场乡民之心并无乱七八糟先入为主的“意见”,反而容易教化,能得到心学真谛。基于以上观点,阳明对龙场少数民族抱以亲善友好、诱导教化的态度,并不因来自“上国”(京城)而自以为是,也不因身为朝廷命官而傲视龙场乡民,更不因是大汉民族而轻视黔中少数民族,相反,他与龙场苗、彝诸少数民族朝夕相处而不以为陋。阳明500年前的这一观点对于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群众解放思想,使之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确是起到了巨大的鼓动和催化作用。
果然阳明弘道的因缘很快就来到了。为报达当地苗彝乡民对他生活上的帮助和照顾,阳明在龙场创建龙冈书院,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深得当地“夷民”及诸生的敬服,一时各地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苗彝乡民环聚而观如堵,遂使落后闭塞的龙场书声朗朗,礼仪顿开,成为士人诸生向往的儒学圣地。阳明龙场讲学,声名大振。贵州按察司宪副兼提学副使毛科书请阳明至府城贵阳讲学,他以病婉辞。正德四年(1509)四月,毛科致仕归里,席书调任贵州提学副使,再次恳请阳明出山来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阳明见席书敦请恳切,乃欣然应聘,于正德四年暮春来到贵阳,主讲于文明书院,首倡“知行合一”之说,“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4]卷五孟子云:“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3]尽心上圣人所经过的地方无人不教化,心所主处,神妙莫测,其功德可与天地之化共同运行,此是圣人的功业与境界,此语正可誉之于阳明黔中弘道也。
纵观阳明龙场悟道之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悟道之苦难时是阳明悟道的外部条件;悟道之体悟时,是阳明悟道的关键时段,此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因而在龙场悟道之三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悟后起修之受用时,则既是阳明悟道后的结果,又是阳明弘道的开始。总而言之,前悟道之苦难时、悟道之体悟时和悟后起修之受用时这三个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由此构成了阳明龙场悟道全部完整的过程。
[1]黄宗羲.明儒学案[M].上海:中华书局,1985.
[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孟子.孟子[M].线装古旧书.
[4]道光贵阳府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The Three Periods Theory of Wang Yangming’s Enlightenment in Longchang
WANGLu-ping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iyang,Guizhou 550002,China)
Wang Yangming had enlightened in Guizhou Longchang in Zhengde third year of Ming dynasty(1508),which is a dividing range of his thought.In this same space time 500 years ago,it is an enrichment of his three periods enlightenment condition.They are the suffering time before enlightenment,the enlightening time,the application time after enlightenment.In 1508 AC,the three periods of Wang Yangming’s enlightenment in Longchang,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of Yangming’s life matter,but also a shocking matter in Chinese philosophy.It is significant to analyze this great karma indepth for us to understand Yangming’s mind confusion and to enlighten our consciousness.
Wang Yang-ming;enlightenment in Longchang;the three periods theory;realization;practice after enlightenment
王路平(1956—),男,湖南湘潭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贵州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和佛教文化。
B248.2
A
1005—6378(2010)05—0023—06
2010—03—12
[责任编辑 侯翠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