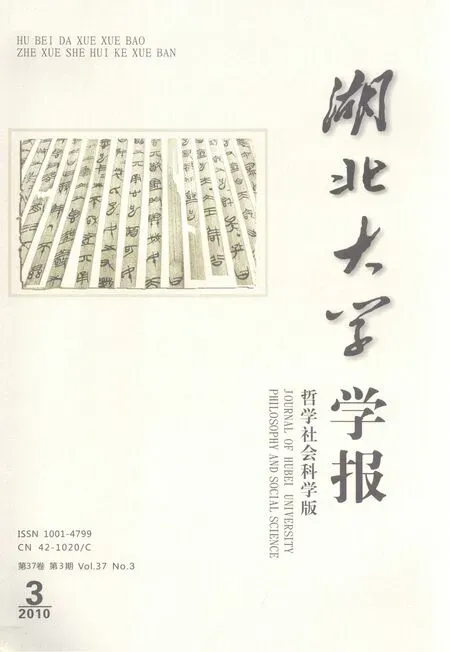论“五四”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沉沦》
李 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论“五四”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沉沦》
李 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郁达夫《沉沦》中的“身体叙事”在五四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这是为过去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可以从对文本内外所存在的三方面问题的分析得到揭示:第一,“灵肉冲突”的主题认定反映了作者和研究者们对主流话语认同的心态,而文本自身所展示的普遍的人性问题却被遮蔽。第二,身体叙事作为一种“私人叙事”,其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作用是思想言论的直接影响无法替代的,但在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成熟的时期,它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和难以避免的尴尬。第三,“国家之爱”使得《沉沦》获得了更高的价值,但这种“国家之爱”却具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它由怨恨心理转换而来,而文本对个人欲望和国家话语的嫁接存在明显的裂隙。
五四;郁达夫;《沉沦》;身体;公共空间
郁达夫的《沉沦》以其对性行为和性心理的大胆裸呈而构成了对封建伦理的巨大挑战,成为五四时期轰动一时的作品。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面对《沉沦》,不仅是面对一个经典的文学文本,也是面对一个典型的文学事件。围绕《沉沦》,笔者将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希望以此对《沉沦》进行重新审视,进而研究“身体叙事”在五四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意义和局限。
一、“灵肉冲突”与主流认同
对性心理和性行为的真实展示是郁达夫小说的重要特征,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沉醉在肉欲之中不能自拔但又有着强烈的自责心理,夏志清所说的“一般人通常都把郁达夫自传式的主角看做颓废人物。不过此人颓废只是表面的,道德方面的考虑照样很多”[1]76,指的就是这类作品;与此构成对立的是郁达夫另一类追求情欲升华的作品,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这类小说可以说是前类小说的一个自然延伸,正是因为有了对沉醉放纵于肉欲的自责和否定态度,才会有对纯洁、唯美的精神之恋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郁达夫表现“性”的这两类小说实际上是居于肉欲与精神的两端的,前者倾向于肉欲,后者倾向于精神,这两类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其实都是一种灵肉分离的生活。
《沉沦》作为郁达夫的代表作,集中讲述了在他前期大量小说中反复讲述的故事——性的苦闷和变态的故事。在《〈沉沦〉自序》中,郁达夫这样介绍这篇小说:“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de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2]185对于郁达夫自道的“灵肉的冲突”,成仿吾很怀疑,他在仔细分析了小说后认为并不存在“灵肉的冲突”:“《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描写灵肉冲突的作品,那不过是把我们这世界里的所谓灵的观念,与这作品的世界里面的肉的观念混在一处的结果。”[3]6~7成仿吾认为,正是在理想的“灵肉一致”的爱情不能实现的背景下,主人公才转向性的变态,因此,“灵肉一致”实际上只能算是文本外的一个观念前提。成仿吾还说在东京时他就与郁达夫谈过这个想法,郁达夫当时也首肯,但“后来出这本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在序文上又说是描写灵肉的冲突与性的要求了”[3]10。苏雪林更是对郁达夫的这种自我认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作品“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3]73。不过,除了郁达夫本人外,后来的人们也都仍倾向于用“灵肉冲突”的主题概括郁达夫及创造社的作品[4]73,事实上,这种“灵肉冲突”的文学史认定是事出有因的。
五四时期反封建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是西方的“自然人性论”,周作人作为“自然人性论”最热情的提倡者和最权威的阐释者,在《人的文学》一文中阐释了这一观念:人是灵与肉的统一体,一方面“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另一方面“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因此,兽性与人性,这两方面都是自然的人性,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5]32~33。周作人特别强调“肉”和“灵”一样具有同等的价值,这种强调是以传统文化对肉体的歧视和压制为背景的。在周作人的理论中,“灵肉和谐”或“灵肉一致”是作为人的一种自然需求提出来的。然而,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这种“自然”的人性却逐渐成为了一种“理想”,当“灵”或者“肉”受到压制不能健全发展时,就会在人的心理上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文学表现“灵肉冲突”的主题才应运而生。不过,由于“灵肉冲突”的具体情况充满着复杂性,所以五四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它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
在《沉沦》遭到封建卫道士们的围攻后,周作人站出来为《沉沦》辩护,他说:“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压迫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3]3周作人并不愿意对作品的“灵肉冲突”作出具体的分析,而认为作品真正的意义在于其真实性,这样含糊其词的赞扬显然不太具有说服力。
《沉沦》的主人公渴求的是灵肉一致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然而这种爱情在小说中是没有实现的,因此主人公才会耽于一种单纯肉欲的发泄。成仿吾认为,如果只有“肉”没有“灵”的话,又何来“灵”与“肉”的冲突?不过,这种判断也失公允,如果说对灵的要求也是生命的一种本能,那么动物性的甚至变态的肉欲发泄当然会产生内心的冲突和对自我的否定,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对自己小说“灵肉冲突”的认定,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的,不管周作人、成仿吾所理解的“灵肉冲突”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都不能否认郁达夫本人所理解的“灵肉冲突”的存在。当然,郁达夫对成仿吾的意见出尔反尔,说明他自己也存在疑虑,而最后他仍执意于这一“灵肉冲突”的认定,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为了呼应“当下”流行话题,这包括五四关于“灵肉一致”的人性讨论的主流话语、日本“私小说”和西欧浪漫主义所推崇的“灵肉冲突”的文学主题等,从这一意义上说,郁达夫的这种认定是对时代话语和世界文学潮流的自觉回应。
当然,《沉沦》在当时的成功显然不取决于作者的这种认定,也并不取决于后来一些研究者所说的具有“反封建”的精神,而是取决于它的“真实”。对于《沉沦》来说,它在五四那样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带给人们这样一个真实的私人空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沉沦》以“真率”为旗帜来反抗传统的假道学,通过对主人公性压抑下的心理和行为的大胆直露的描写,表现了非常真实的个人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高尚的还是卑下的,是精神的还是肉欲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世人若骂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认的,世人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内心的苦闷就对了。”[2]188作品所表现的主人公的“沉沦”,是非常真实的个人身体的“沉沦”,“真实”正是郁达夫能够走向公共空间并让读者认同他的原因。所以,若说人物本身具有多少反传统道德的意识,或者说在主人公身上有多少时代的典型特征,都未免失之牵强。研究者对郁达夫本人的“灵肉冲突”论的认定显然是为了使小说更符合反封建话语的阐释模式。
无论作者和研究者如何试图使作品的阐释获得一种更高的主流价值,都没有作品自身的身体言说更具说服力。如果我们不把身体看作一个被作者和研究者的理性意识指挥的机器,那么我们就会在文本中发现身体的主动言说。
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主人公对身体的态度来说明这一问题。由于周作人等五四思想家对传统文化赋予身体的“不净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此这里人们很容易就把《沉沦》中主人公的“洁净观”和五四主流话语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小说本身所表现的却不完全如此。笔者认为,主人公自渎后的负罪感除了来自传统的养身之道外,也来自于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和普通的性科学常识。小说写道:“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爱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主人公的“爱高尚爱洁净”不能只理解为受封建“不净观”的影响,从普遍的人性来说,人都有一种离弃形而下的肉欲冲动和追求更高境界的爱欲冲动的品质,而主人公的这种行为恰恰与人性的本然追求相悖,因而身体的沉沦自然会遭到心灵的抵抗,也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意识。
同时,这种罪恶感还来自于对这种“非自然”的行为将造成的对身体的伤害的忧虑。小说写道:“所以他每天总要去洗澡一次,因为他是非常爱惜身体的,所以他每天总要去吃几个生鸡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鸡子的时候,他总觉得惭愧得很,因为这都是他的犯罪的证据。”主人公对犯罪感的认定不仅来自于传统教育,还来自于现代医学书籍:“他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代表着科学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主人公对自己行为的否定和负罪感因此而进一步加深了。然而,不仅封建的性学观有可能以现代医学的面目出现,按照话语建构理论,就连现代医学所提供的“知识”本身也只是一种代表权力的话语方式,如对手淫的否定就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话语方式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卢梭的《爱弥儿》对手淫大加讨伐,而在卢梭之后,“当卫生学家们集伦理与医学、宗教告诫与罪恶感之大成,创立了手淫病理学时,他们延续了卢梭的观点。手淫者的形象确立起来。这个形象与哲学家卢梭所描绘的那个流浪城市街头的放荡者一模一样:身体佝偻,四肢战抖,神情冷漠,满面愁容,神志恍惚,步履蹒跚,面如死人,双目惊恐,眼球发红,眼圈深陷,眼皮泡肿,面色蜡黄,一脸憔悴,还有自杀倾向”[6]212。在《沉沦》中,正是这种让主人公感到信赖的性科学话语更加在“伤害身体”的意义上增加了他的恐惧,但自然的本能又总是促使主人公暂时丢弃一切顾虑再一次“犯罪”。
因此,与其说主人公得的是“时代病”,还不如说主人公病态的心理和行为体现的是人的理性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反映的是一种普遍人性的问题。尼采曾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分析了自我发泄与内疚产生的心理机制,他说:“这种被迫潜匿的自由本能,这种被挤压回去的、返回内在的、最终只有向自身发泄的自由本能,只有它才是内疚滋生地。”[7]63因此,主人公无以发泄的生理和心理情绪才是内疚、自责产生的根源,一些研究者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沉沦》中的主人公所患的是“时代病”,表现了当时青年的时代苦闷,具有反封建道德的作用。他们把主人公内心的自卑感和罪恶感完全归于传统儒家道德对人性的压制[2]188,笔者认为这是把文本简单化、模式化了。
无论是作者有意识的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的自我认同,还是研究者对其符合主流话语的文本阐释,都是把文本及文本中的身体看成了一个被动的客体的结果。实质上,文本在脱离了作者以后就有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使被赋予某种意义,它也可以通过返回现场的方式使被遮蔽的那一面浮现出来。因此,在对个人真实身体的寻找中,一扇新的阐释作品的窗口被开启了。
二、私人叙事与公共空间
《沉沦》在当时的“热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是否就意味着郁达夫所表达的身体体验获得了公共空间的认同呢?如果说存在认同的话,那么公共空间对于这样一种私语性质的文学作品又是在何种层次上予以认同的呢?
实际上,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平台上,公众对思想家和文学家认同的层次是存在差异的。思想家的言论即使关涉个人问题,但因为这些问题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且思想家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学理性”的,所以公众会对思想家的言论持一种有距离的观照的心态,而思想家们也会强调学者身份的重要性,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等文章中,反复强调“研究”的态度。从谈论这些问题的姿态来看,周作人是以一个思想家、学者的身份进入公共平台的,这使他在表述这些观念时不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色彩。胡适也是如此[8]517。这种科学、客观的立场是周作人、胡适等思想家进入公共空间的基本姿态,而相应的,读者也会以一种对待“公共话语”的心态对待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读者在潜意识中会以一种“这是一件与我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共的事情”的心态看待他们提出的问题。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有当新的思想和观念最后形成一种社会潮流和风尚时才能触及到个人,因此,倘若从个性解放中许多与身体相关的话题来说,虽然思想家对个人身体的言说从一开始就拥有“公共话语”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也限制了人们接受它的心态,即人们会以一种“距离化”的心态对待之,这也决定了思想家在公共平台上影响普通人的限度。
对于思想表达与身体的唯一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赵汀阳认为:“身体性的唯一性是个体自身认同的真正根据,而思想性的自我只有在以身体性的唯一性作为根据时才能够连带地具有唯一性。心灵和思想当然有着个性,但心灵或思想在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它的来源和所表达的东西都是公共可理解并且可分享的。如果自我要独自占有某种思想的话,除非这种思想能够成为私人的,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思想是非常可疑的,因为缺乏专门用来表达私人思想的语言(维特根斯坦曾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私人语言不可能因此私人思想其实也是不可能的)。”[9]61因此,从文学是对个人身体唯一性的表达来说,身体的文学叙事在反传统道德的功能方面有着与思想观念的宣传相异的作用。同样是个性解放的问题,当以文学的方式表述时,就会还原出这一问题对于作家和读者的私人性质。李欧梵认为:“尽管五四文学具有公众意识形态,但很独特的一点是,一些作家仍然能够将他们的自我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10]61特别是像郁达夫《沉沦》这样的自传体小说,可以说把文学的私人性质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对私密的个人心理包括潜意识的表现,使郁达夫的小说大大超过了此前文学的私人性的一般尺度。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2]203将个人真实的身体推向公共空间,这无异于在中国这种总是把身体欲望隐藏在黑暗角落的文化氛围中丢下了一颗惊雷,其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性和颠覆性显然是空前的。
对于文学的私人性及其在建构公共空间上的功能,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论述道:“一方面,满腔热情的读者重温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私人关系;他们根据实际经验来充实虚构的私人空间,并且用虚构的私人空间来检验实际经验。另一方面,最初靠文学传达的私人空间,亦即具有文学表现能力的主体性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拥有广泛读者的文学;同时,组成公众的私人就所读内容一同展开讨论,把它带进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过程当中”,由此,“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11]54~55。从哈贝马斯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作品的私人空间为读者的私人空间的建构创造了条件,而随着读者的私人空间的扩大,一种积极的代表着社会建构力量的公共空间就会逐渐形成。
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所展示的私人空间在进入公共空间之后对公众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事实上,当面对郁达夫这种由小说所营造的“私人空间”时,普通读者大都会从个人经验出发寻求与文本的交流,似曾相识却未曾得到表达的心理体验就会在这种交流中得到释放。在这种交流中,尽管传统道德的约束还在,但因为读者阅读文本时等于是两个隐秘的个人世界在进行交流,这时传统道德观的约束就会相对减弱,人们更容易在内心深处从个人经验出发体味它、想象它,并且读者可以由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反观自己的生活,从而建构起哈贝马斯说的“虚构的私人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意识形态话语进入公众内心世界的困难而言,文学“私人”性质的定位却使它言说的各种具有时代意义的话题对读者更具亲和力。因此,郁达夫“私小说”在公共空间的建构上所具有的功能是突出的,它是身体从传统的私人空间走向现代的公共空间的一次颇具成效的尝试。但是,在成熟的现代文化空间还未建立起来以前,这种对私人空间的展示也意味着它给人们提供了一次“窥淫”的机会,也正是因此而使这一身体叙事面临着难以逃避的尴尬。苏雪林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她说:“郁达夫的作品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3]67因此,如果读者仅仅把小说对“性”的描写看作是一种对“私人空间”的展示,那么小说的意义当然也就只能在由作者的私人空间走向了读者的私人空间之后就画上了句号。
对于郁达夫把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通过文学的形式抛露给公众的做法,李欧梵分析说:“郁达夫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驱妖,通过向想象中的听众揭露的办法来赶走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恶魔。忏悔是他净化自己感情的手法;当他把所有的弱点都暴露以后,他会感到好过的。”[3]580而王富仁则说:“我们读郁达夫的小说总能感到他在自我暴露中也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快感,并且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夸张了自己的丑恶。”[12]391~392他还指出:“在郁达夫的小说里我们则听到了一个上帝之子的啼哭,人类那不得满足时的啼哭,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不得满足时的啼哭。”[12]395总之,公开个人的隐私成为郁达夫为心灵寻找支撑的渠道。除了他的小说,郁达夫对待个人生活的方式也可以用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把与王映霞的纠纷公之于众这一事件就是郁达夫的一种类似于儿童的依附心理的体现,反映了郁达夫在心理上对公众的依赖。
公共空间已经成为现代人寻求自我认同的一个场所,尽管郁达夫在《沉沦》中所表现的是个人化的身体体验,但这仍然是一种寻求公共认同的个人身体体验。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的进入寄寓着现代人对新的文化空间的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即希望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的绝对拥有,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重合中,私人空间也化为公共空间。这实际也是一种古典的文化空间心理的现代变种,“中国古代关于性知识的指南和政治力量的动力的本文是一致的,天文图同医学药理逻辑也是等同的。西方的两种原则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与私(政治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在古代中国被否定了”[13]237~238。按照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理论,成熟而合理的社会空间关系是:个人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相互独立而又彼此交融的,它们不应是一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覆盖的关系,而应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对话和交流的关系,这样才能保持个人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活力。从这一意义来说,郁达夫表面激进的姿态中,仍带有传统文化对于“公”与“私”的关系的理解。
三、身体欲望与国家话语
郁达夫借助文学走向公共空间的动机在《沉沦》中还有另一种呈现方式。一句“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了!”喊出了个人欲望与国家、民族话语之间关系的所有内涵。它表明,个人是软弱无力的,个人的自我认同只有在国家、民族解放这样的宏大叙事的保护下,才能得以完成。同时,国家、民族也提升了个人的悲剧,从而使个人悲剧获得了一种崇高感。表面上看,这样一种写作策略是为了附和被广泛认同的国家、民族话语,但实际上,从文本的逻辑线索出发,个人与国家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可以连接的心理机制,这样一种合乎常情的国家认同在文本中只是由于作家的忽略才表现出分裂的痕迹。
从郁达夫1934年至1936年在《人间世》、《宇宙风》上发表的自传性文字来看,国家、民族意识是贯穿于郁达夫的整个人生经历之中的。有趣的是,尽管国家、民族意识早已萌生在郁达夫的心中,但在《沉沦》中这种情绪却是由性的挫折引发的。在自传性散文《雪夜》中,他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明确的说明,他说:“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剑的一刹那。”[2]58也就是说,正是个人欲望的欠缺使得郁达夫真正理解了国家、民族的含义,在这里,两性关系成了衡量政治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两性关系成了观察政治的一个窗口。这也说明,对于一些“大概念”,人们往往是通过个体体验而使之变得真切、清晰起来的。
在《沉沦》中,作者把个人“性”的苦闷与国力的衰弱联系起来,这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常识来看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国家的兴衰荣辱是与个体的幸福紧密相联的,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不过,这只是文本外的一个简单预设前提,在文本中,主人公的国家认同更有内在的心理动因。
对于《沉沦》主人公的心理特征,小说一开始便介绍道:“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作者在《〈沉沦〉自序》中说:“《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2]185这里的“病”指的是主人公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或者说是心理障碍。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因“狂想症”而处处疑惑有人在迫害他,与此相同,《沉沦》中的主人公则因为内心的极度自卑而产生了一连串反常的心理反应:在学校里,“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尽管他也有与人交流的愿望,但却常常陷入无人理解的“空虚”,偶尔与人交流、被人理解,他却又“自悔失言”。而实际上他也承认,即使“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因为他的孤僻,而“不得不同他疏远了”。忧郁症、自闭症的人是害怕进入公共空间的,公共空间对他而言充满着压迫感。一方面,强烈的自卑心理使他对外界有一种恐惧,但因为不被认同才更增强了他心中渴望被认同的期待。对于《沉沦》的主人公来说,无论是“性”的压抑还是弱国子民的悲哀,抑或是落魄文人的处境,都是寻找自我认同而不能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肉体的极度宣泄就成为他情绪释放的方式。
《沉沦》中主人公在单纯肉欲的极度宣泄中身体堕落成了肉体,在爱情缺失的情况下,找任何一个对象发泄他的肉欲和压抑的情绪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主人公发泄方式的“单向性”决定了主人公的性欲和情绪的发泄对象是“虚化”的、可以随意更换的。这种“单向性”的情绪发泄在他对国家的情绪发泄上也得到了体现,因为国家是个抽象的存在物,对它的情感表达也只能是单方面的,因此,“国家”也是一个“虚化”的对象。从这一意义来说,“国家认同”就成为主人公发泄情绪的一种选择。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和情绪发泄对象的“非实在化”,所以,主人公的自我认同总是难以真正完成。
不仅如此,主人公寻求国家认同的心理机制还可以从他与国家都有相同的怨恨心理上得到解释。中国自近代以来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下有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心理。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封闭、保守的状况,与这种状况相一致的是极端自负的“中国中心”思维方式和相应的心理特征。但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强力改变这种封闭、自我中心的状况后,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极端的自负滑向了极度的自卑,出现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西方,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融合着怨恨和羡慕的感情。“怨恨就是怨贫恨弱,羡慕就是羡富慕强。这可以说是两种基本的现代性体验心态”[14]75。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实际上一直在中与西、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等价值的较量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坐标。
就心理特征来说,与当时这种怨恨的民族情绪相似,在《沉沦》中,贯穿整个小说的也是这样一种无所不在的怨恨情绪:从对日本学生的怨恨到对中国同学的怨恨,从对长兄的怨恨再到对妓女的怨恨,以及在这些怨恨中生长出来的对祖国的爱恨交织的情感。这种种怨恨都可以归纳为由身体欲望的欠缺所导致的怨恨。舍勒认为,怨恨心理是现代人处世态度的情感根源,怨恨涉及到一种生存的软弱感和无能感,它来自于在一种“价值平等”的原则下把自己与别人进行的比较,如《沉沦》中就写道:“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跑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但是,由于比较者“又无能力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去获取被比较者的价值,被比较者的存在对他形成一种生存性压抑”[15]363,所以,《沉沦》中主人公的怨恨情绪就由此而生。
个人怨恨与民族怨恨都来自于生存空间遭受挤压后的欠缺感,它们在心理上具有同源性和同质性,因此,“国家”在这里就不仅可以看作主人公寻求精神支撑、发泄情感的对象,也可以看作一个可以与其同病相怜的对象,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小说把国家话语和个人欲望连接起来就有充分的理由。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从小说中我们看到,由于《沉沦》中这种有意识的国家认同脱离了整个小说的语言环境,所以小说中主人公临死前的这句“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了!”的呼喊就显得特别生硬,而这种突兀感还可以从小说人物的心理层面作进一步分析。
小说中主人公对祖国的爱是发生在“性”的挫折之后,从性爱之恨到祖国之爱的转移隐含着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舍勒认为:“怨恨之爱的含义是,一切如此被‘爱’的东西只是作为另一种曾经被恨的东西的对立面被爱。这种怨恨之爱之所以产生的规律也仅仅涉及一种假爱的形成,而不是涉及一种真爱的形成。就连怨恨之人本来也爱他在自己的情状中所恨的事物——只是由于不曾占有它们或无力获取它们,恨才发泄到这些事物上。”[16]767根据舍勒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出,《沉沦》中“我”对祖国的爱并不是一种本源性的真爱,而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异性的爱情,这时一切使“我”得不到爱情的因素都是“我”怨恨的对象。由于“我”在真正爱的对象身上得不到所想要的,因而“我”就把爱转嫁到另一个对象上去,而这个转嫁的对象在当时最合适的莫过于“国家”了:“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对国家的热爱和肯定并非是因为其内在的价值和品质,而是为了贬低、否定那些怨恨的对象,因此作者在文本中只是把国家作为自己转嫁情感的一个对象,这就造成了“国家之爱”某种程度上的虚伪性。因此我们可以说,郁达夫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明显是由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而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不过,即使这种“爱”包含着虚伪性,也并不排除其转换成功的可能。转换的过程只要天衣无缝就能掩饰对象嫁接的虚伪。对于《沉沦》来说,也就是要在转嫁以前,对“国家”也应该有足够多的情感投入和表现。但是,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丝毫没有这种“努力”,“国家”只是在个人怨恨心理产生的时候才出现。如对日本同学,他想:“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见到女同学,他觉得她们的秋波是送给日本同学的,就想:“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他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如果说祖国的贫弱与被日本同学欺辱和漠视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的话,那么小说主人公与他的中国同学的关系的不融洽则与“国家”没有丝毫关系,这也正说明了“国家”在这里是一个可以替换的能指:“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复仇的心。”“他同他的几个同胞,竟宛然成了两家仇敌。”主人公的这种“不能用行动作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的复仇获得补偿”[7]20的心理特征,正是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的人的心理特征。主人公往往在性受挫后,才想起他的祖国,想起他的弱国子民的身份,并马上把这种挫败感、自卑感归咎于祖国的弱小。因此,“国家之爱”本来就存在的虚伪性由于作家在文本技术层面的草率而显得更加明显,以致使身体欲望与国家话语的连接出现了裂缝,并最终导致了文本在个人欲望与国家话语的连接上给人以生硬造作的感觉。
郁达夫的小说有意识地将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纳入个人身体叙事之中,其效果是,个人通过民族、国家话语而获得了更大的认同空间。这也说明,有关民族、国家的体验最终必须通过个人的真实体验获得认同。同时,尽管郁达夫有一种自觉的民族、国家意识,但由于小说主要是以个人的身体和心理为书写对象,因此,在小说中,民族、国家话语的指向仍是个人。在这一问题上,把鲁迅和郁达夫作一个比较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在鲁迅的作品中,因为个人和国家两种力量都非常强大,并且激烈地冲突,所以他的作品有一种分裂的痛苦和张力。而在郁达夫的作品中,个人话语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国家话语的力量,所以他的作品是单纯而透明的,即使有痛苦,也只是一种单一的个人痛苦。
由以上对《沉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身体叙事与公共空间的认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社会培养了作家的公共认同意识,但文学特别是私人性较强的一类作品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运作上又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微妙而复杂的因素。身体叙事在社会转型期作为一种反叛性力量出现的时候,由于一个成熟的话语空间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种身体叙事就会暂时获得某种优先权,它可以逃离传统道德的约束,并对新的公共空间的建构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沉沦》所叙述的关于个人的身体欲望被压抑的故事重合了五四的个性解放和民族、国家的话语,它兼具个人和公共的双重指向。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郁达夫在文本中对后者是弱化的,这似乎暗示着他在潜意识里更希望个人话语能够挣脱各种限制,从依附走向自主。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4]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本色:3[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米歇尔·昂弗莱.享乐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2003.
[7]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8]胡适.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2000.
[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2]王富仁.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M]//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13]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4]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16]舍勒.爱的秩序[M]//刘小枫.舍勒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9.
I206.6
A
1001-4799(2010)03-0034-07
2009-01-03
李蓉(1969-),女,湖北江陵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