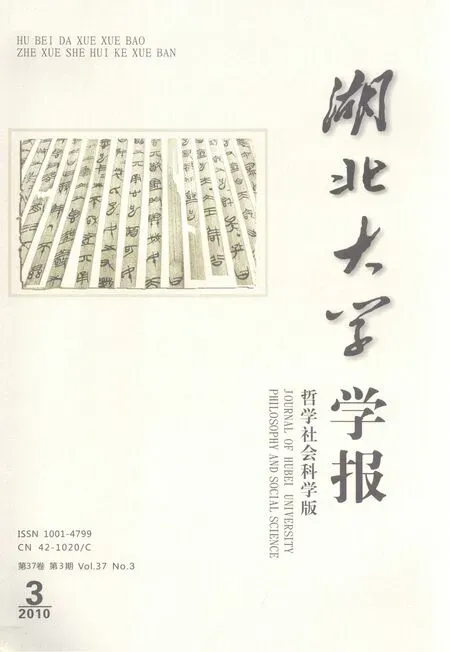企业社会责任跨国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曾丽洁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企业社会责任跨国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曾丽洁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目前,各国在涉及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诉讼中,主要有针对企业违反国际法的诉讼和针对企业违反母国国内法的诉讼。这些新的实践有法制创新和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也存在管辖权、权利的可诉性、法律适用、母子公司责任的承担等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和实践上的障碍。要使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则需要跨国诉讼中的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共同努力。而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实践也为该领域国际法的形成提供了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跨国诉讼;国际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营活动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出。在目前国际法还未能直接适用于企业的有限性的条件下,通过国内法对企业跨国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规制已成为现实的需要。从能力上讲,母国管制跨国公司的域外经营行为是最可行的。母国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法律规制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规制,二是以母公司为对象对其海外子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规制。第一种途径由于域外管辖权的限制而缺乏实践。实践中采取的多为第二种途径。一些投资母国的法院已趋于受理以跨国公司为被告、以其境外附属公司的行为为诉由的案件。原告也多利用企业母国的法院寻求救济,所依据的具体法律也不同。目前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针对企业违反国际法的诉讼;另一类是针对企业违反母国国内法的诉讼。这些保障域外劳工权利、人权、环境权等的做法有法制创新的作用,也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和实践上的障碍。
一、针对企业违反国际法的跨国诉讼
针对企业违反国际法的跨国诉讼主要是依据1789年美国联邦法律《外国人侵权诉求法》(ATCA)。该法规定:对于外国人提出的违反美国所参加或缔结的条约的侵权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具有初审管辖权。该法最初是针对公海海盗的罪行,之后近200年基本上被弃用。1980年,第二巡回法院对Filartiga v.Pena-Irala案的管辖为ATCA用于解决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开了先河。美国劳动和雇佣法并不保护海外非美国工人的权利,也不能直接适用其他国家的劳动法,而大多数国际劳工公约又缺乏约束力或执行机制。所以,对海外劳动侵权进行救济时将国际劳动侵权界定为对国际人权法的违反,一些与劳动有关的侵权行为被提升到了ATCA的规制对象层面,对跨国企业海外劳动侵权行为在美国提起的诉讼频繁发生。
除了美国之外,只有一个国家的法院曾允许非居民为人权受侵犯而起诉企业。1999年,比利时提出了《关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惩罚的法案》。该法案将三类对人道主义法的严重违反(酷刑、反人类罪、对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第一、第二议定书的严重违反)并入国内法。该法案最特别之处是承认比利时法院可以不论罪行发生的地点、被指控方的国籍、受害者的国籍,只要存在对该法案的违反,都可行使“普遍管辖权”,即,法案不要求被控罪行和比利时之间有联系[1]。这一法案被用来作为对一家被指控涉及强迫缅甸工人劳动的法国公司Totalfinaelf进行调查的依据。后来,出于压力,比利时修改了该法案,使之只对比利时公民和长期居民行使管辖权。于是,比利时法院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权力被取消了。ATCA仍是对以违反国际法为诉因的诉讼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唯一国内法依据。
二、针对企业违反母国国内法的跨国诉讼
(一)民事诉讼
这类诉讼的特点是并不以直接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为依据。
1.根据商业和消费者保护法起诉。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相关行政规则的规定,跨国公司制定和公布保障劳工权益的行为准则,等于向消费者做出表示意思,而在其违反公司准则的情况下,就是对消费者作了重大误导。非政府组织兼具消费者及劳工代表的身份,具有以欺诈性广告为由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资格。1998年,Kasky v.Nike案的原告指控Nike公司在为了应对社会对其劳工问题的指控而进行的公共关系活动中,商业性质的虚假和误导性陈述误导了消费者,违反了加州商业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案所针对的不是发生在Nike工厂的劳动侵权行为,而是Nike否认存在劳动侵权的陈述。Nike主张其作为公关活动的“非商业性质的”陈述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不产生法律责任。考虑到Nike所作陈述的公共性质、保持和增加销量及利润的意图、主要受众为消费者及陈述中包含Nike商业经营实际内容的事实,很可能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2002年加州最高法院认定Nike的陈述属商业性陈述,应受法律约束。
2.违约之诉。加州法院受理的Doe v.Wal-Mart案中的原告沃尔玛工人对该企业拒绝支付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强迫劳动、否定自由结社权的行为提起违约之诉。该诉因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原告声称,沃尔玛将其行为守则并入供货协议,工人就是协议中劳动条款的第三方受益人。而沃尔玛未能采取适当的监督措施以确保供货商遵守标准,未能履行供货协议,因而违反了合同义务,对原告造成了直接损害。一般认为,企业行为守则是自愿的。如果法院认定守则在法律上可以执行,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3.一般侵权之诉。将侵权法归责原则引入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侵权责任承担者不仅包括直接侵害工人权利的实施者,也包括主观上存在过错而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侵权行为人。因此,当跨国公司供应链上的某一供应商侵害工人权利时,受害者既可以要求该供应商承担法律责任,也可因供应链上家的跨国公司在该侵权行为中存在主观上的过错而直接要求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承担形式突破了公司内部界限的限制,使得跨国公司更加严格地执行生产守则,实现对工人权利的最大保护。Doe v.Wal-Mart案的原告提出侵权之诉时,认为沃尔玛本应对供货商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有所知晓,却在选择并与之缔结合同时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知道或应该知道如不适当监督,供货商有可能将之理解为批准,而侵害原告的权利;要求供货商短时间送货和给予低于市场价格的货价,也应该知道它无法适当地补偿工人合法的利益;未对供货商进行适当监督及要求他们遵守其行为守则、当地法和国际标准;违反了加州商业和消费者法、行为发生地的劳动和雇佣法、国际劳工标准以及沃尔玛的行为守则,不符合理性人不会违反促进安全的法律的推定过失(negligence per se)的法律原则。故沃尔玛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以确保其行为守则得到遵守,存在过失。
美国还以追身侵权法规(the rubrics of transitory torts)为受害人提供保护。对于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当侵权人的不法行为使他负有跨国界的责任时,就被认为是可转换审判地的侵权民事责任,州法院有权对追身侵权扩大其管辖权。如果在行为实施地国是“不可裁判的”,就应该适用法院地法。原告可以运用追身侵权对企业引起的倾倒危险物、环境损害、杀虫剂污染等提出索赔。另外,《酷刑受害者保护法》(TVPA)为美国公民和外国人对个人在外国政府实际的和明显的权力下实施的酷刑和非法谋杀提供了民事诉因。一般认为,TVPA针对的对象包括企业,认为企业也是可以实施酷刑或谋杀行为的“个人”。然而,由于它要求个人的行为要与政府有联系,就排除了没有国家支助的企业行为。
加拿大仍然只以传统侵权作为诉讼的依据。在Tolofson v.Jensen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对侵权行为的认定,依侵权行为地法。虽然最高法院注意到了可以运用侵权的冲突规范的例外以避免不公平,但还是声明这种例外应限制在关于企业的特殊诉讼中,而侵权行为地法仍是一般的、不具特殊性的企业侵权的准据法。Tolofson案设定了企业域外侵权行为诉讼的一个极为有限的前提: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不认为该行为构成侵权,就不做侵权行为处理。该企业就可以逃避责任[1]。
英国与加拿大和美国都不一样。英国对解决发生在海外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诉讼经验有限,只经历过一些在非洲的工人试图对英国公司课以责任的争端。原告一般依据作为英国普通法的一部分的习惯国际法,或1995年英国国会通过的规制跨国侵权案件的《国际私法(杂项条款)》。
4.特殊侵权之诉。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环境侵权这一特殊侵权。大部分跨国公司的母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了严密的行政监管法规,同时在污染者与污染受害人的民事冲突中建立了有利于受害者的侵权责任制度。这些法规规定了跨国公司的诸多义务。更特别的是,美国1980年《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对危险物质的泄漏尤其是危险废物倾倒建立了特殊的连带责任制度,包括设施的所有人或营运人、处置危险废物时的所有人或营运人、运输者、危险废物产生者等相关主体间为清除和处置危险废物泄漏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责任不以泄漏的主要原因是否因为违反安全标准而取消,是一种法定的民事严格责任[2]161。根据这部法律,美国许多法院基于母公司作为其子公司的危险废料设备的所有者或经营者的身份判决母公司应该承担环境侵权责任。这一制度显然加重了美国母公司的环境侵权法律责任风险。
5.产品责任之诉。由于企业的行为而遭受损害的人也可以利用产品责任起诉企业对职业安全和健康标准的不适当执行。香蕉工人案的原告——香蕉农场工人,因在工作过程中使用一种称为DBCP的化学物品而健康严重受损,根据州法院的侵权法提起产品责任之诉,主张缺陷或危险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和分销商对产品损害负责。产品责任是严格责任,只要产品缺陷给原告造成损害,即使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注意措施,仍应对产品缺陷负责。即使损害发生在其他国家,产品责任可以适用于源自美国的生产和销售。原告可以要求生产商、销售商或分销商中的任何一方赔偿损失。
6.不当得利之诉。Kasky v.Nike案和Doe v.Wal-Mart案的原告均主张:被告Nike和Wal-Mart从对劳动和供货的虚假陈述创造的积极品牌形象和与消费者的良好关系中非法获利,带来了超过竞争者的不公平商业优势,构成不当得利。另一项美国法律——《联邦防止诈骗及反黑法》(RICO)也可使企业行为受害人据以寻求企业不法行为的救济。RICO对“诈骗”的定义很宽,还规定犯罪行为受害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民事讼诉因常被称为“民事RICO”,可用于针对企业的人权诉讼。为使RICO域外适用于发生在美国之外的行为,原告必须确定通过某企业进行的不当得利行为与美国有足够的联系。法院主要考虑美国境内的行为是否直接引发了在外的损害,或在外国发生的行为在美国境内有实质性的影响。
(二)刑事诉讼
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对企业提出刑事诉讼,但管辖范围大多限于在该国领域内实施的罪行。然而,发生在域外的暴行如果是由在域内的管理机构策划或指挥的,只要策划和指挥的机构或雇主代表了该企业的指导思想或是为企业的利益而做出该行为,就可能被纳入一国的刑事管辖下。
大多数国家允许对严重的罪行行使域外管辖权。比如澳大利亚法院对涉入域外买卖奴隶的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加拿大将刑事管辖权扩大到在域外实施的灭种罪、反人道罪、战争罪。英国法院受理英国公民在国外犯下的灭种罪和反人道罪。美国TVPA要求原告用尽行为发生地当地的适当救济,也允许酷刑和法外死刑的受害人或其代理人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要求被告必须是州或是以州的名义行事。美国RICO规定利用企业实体进行犯罪活动,包括违反移民法律以及各种诈欺、贿赂、谋杀和勒索的,构成联邦犯罪。
在国内法院对跨国公司参与在境外发生的酷刑、谋杀、绑架行为展开刑事诉讼程序是一种对企业实施境外暴行课以责任的法律途径。而且,刑事诉讼为受害人提供了其他国内法律解决途径所无法实施的监禁的救济,是使从事不法行为的人承担责任的最强方式。当然,监禁的惩罚针对企业是无法执行的。
三、企业社会责任跨国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管辖权问题
当案件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地国提起诉讼时,原告要说服法院对案件可以并应该行使管辖权,除了满足在该国提起民事诉讼的一般管辖权要求外,还可能面临其他管辖权问题。
1.对跨国公司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国际法基础。国际法上,对跨国公司的域外管辖主要有:一是国籍管辖;二是客观领域管辖,依据的是发生或始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完成或终止于特定国家领域内或对该国领域内的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后果;三是保护性管辖,以侵害的利益为根据。几乎各国都承认国家有权管辖在域外实施并对该国重大利益有影响的行为。传统域外管辖的最主要依据是因国籍管辖,主要有:(1)公司所属国对域外子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其中多为母公司所属国国籍)可因国籍而进行域外管辖。(2)如果在外国子公司的董事会没有外国国民,或仅为少数,那么母公司所属国可要求母公司对子公司做指令,使之服从于该国法律。这种机制不是由国家进行直接管辖,但可以起到域外管辖的实质效果。(3)当本国公司在外国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从事民事活动时,则这种域外行为仍为本国公司所为,可根据国籍管辖原则直接行使管辖权。
而在国际法上,跨国公司的国籍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多数国家一般还是通过传统国籍标准来确定: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取法人的成立地,只要成立地与该法人有足够的联系;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经营中心地或住所地,但也往往要求该法人组建于该国。如果以成立地来决定公司的国籍,那么,设立在外国的子公司就有外国国籍,而不具有母公司的国籍,母公司国籍国就不能根据传统的国籍原则对其外国子公司行使管辖权。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在采用传统的以公司设立地为其国籍国及国籍管辖原则的同时,运用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原则:“跨国企业并不完全适应传统的国籍和领域概念”,它承认国内公司或个人对外国公司的控制可以作为类似于国籍的联系,并支持国内对外国子公司的管辖权[3]292~293。
2.可诉性。第一,美国法院对受理违反国际强行法的侵权之诉的管辖权的解释很狭窄,只有很少的权利被承认具有强行法的地位。美国法院如何发展有关的法律、确定其适用范围、并构建其适用于跨国公司的基础,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国家行为要求进一步限制了ATCA对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企业行使管辖权的诉因。依国家行为要求,除了个别的例外,国际法只能对国家有约束力,侵权必须归因于国家行为,个人必须是为国家利益而做出受指控的行为。大多数法理认为,企业的责任不是直接的,而是依赖于与国家共谋的责任,如果指控企业违反了国际法,原告必须证明企业是与国家行为者共同从事被控行为或获得国家的支助,或因过度行使政府的指令而造成该违法行为,或表明是在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范围内从事。这种举证很难,因此,没有国家成分的企业人权侵犯行为将不大可能依照ATCA而具有可诉性。
并且,即便满足了国家行为要求,依国际法上传统的国家行为理论或豁免理论,一国法院不对外国政府以其领土内主权者身份所作行为进行裁判。法院在确定管辖权的时候,会更为谨慎,要顾忌国家政府行为的不可裁决性,如果它对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进行审理,可能会干预本国外交政策。这种审慎考虑,使得依据ATCA具有可诉性的有国家成分的企业侵权诉讼障碍重重。
第三,美国法院也可能考虑争议问题是否更具政治性而非法律性。若属于不可裁决的政治问题,出于宪法性考虑,法院将会以案件由政治机构解决更加适宜的理由驳回诉讼。跨国劳动权利诉讼涉及美国对外政策,如布什政府已对依据ATCA提起的几乎所有诉讼表示反对,法院也已经在某些场合表达了接受行政机构建议的意愿。
3.非方便法院原则。原告在跨国公司母国提出诉讼常常会因被告提出非方便法院的主张而被驳回。该原则的运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美国方式。美国法院通常首先考虑可替代的法院是否与案件具有充足的联系,如果是,再考虑是否行使该案应由可替代法院管辖而驳回诉讼请求的自由裁量权。通常,法院会假设原告选择本法院是认为其为最方便的法院。如果由替代法院管辖有充足的公共(诉因所涉及的特定公共利益)或私人(证据的取得、证人、相关的费用)利益考虑,则本法院将不被视为最方便的法院。比如,ATCA只用于美国法院能够对被告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情况,而法院通常只会在被告与法院之间具有“充足的联系”的情况下行使属人管辖权。如果在侵犯行为地可以获得充分的救助,美国对于针对一家美国企业违反国际法的诉讼又没有特殊的公共利益,被告关于非方便法院的主张往往使其得以脱离管辖。实践中大多数追身侵权诉讼主张也都被以非方便法院为由而驳回。加拿大在扩大域外管辖权的方法上极为限制,要求必须具有与法院地“真实的实质的联系”,一些企业跨国侵权的案件常被以非方便法院为由而驳回。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出于公平的考虑很少以非方便法院拒绝受理。这主要发生在以另一种方式运用非方便法院原则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这种方式与美国方式的最大区别就是考虑“实质正义”而不包括“公共利益”。澳大利亚对与之有某种联系的境外行为行使管辖权。而且,只要外国公司在澳大利亚从事业务,就容许法院行使属人管辖权。在非方便法院的问题上,尊重原告对法院的选择,除非原告以令人不能忍受的、令人可恶的方式提起诉讼,或如果允许在被挑选的法院受理案件对被告是不公平的且可替代法院对原告来说不会造成不公平。因此在澳大利亚,被告很难使对他的诉讼以非方便法院为由被驳回。
如果没有另外的合适的法院,英国法院也愿意对企业海外暴行行使管辖权。对合适法院的判断依据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因的性质和在其他法院获得实质正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其他的法院明显是更为合适的选择,英国法院也曾声明,出于正义的要求,会保留将诉讼在英国国内解决的自由裁量权。但英国是否行使运用非方便法院原则终止诉讼的裁量权受到了欧盟理事会2000年12月22日通过的《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第44/2001号(欧共体)条例》(简称《布鲁塞尔条例Ⅰ》)的约束。但过去一般认为,依《布鲁塞尔条例Ⅰ》,当可替代法院也是欧盟法院时,成员国法院不能以非方便法院为由驳回诉讼,可替代法院是非欧盟成员国时应采取的立场并不明确。因此,受英国在南非的矿业公司伤害的南非工人、在纳米比亚工作中受伤的英国工人、英国在南非的矿业公司附近的南非居民都成功地在英国法院对英国公司提起了诉讼。虽然在上述案件中,由于正好处在位于伤害发生及证人和证据能获取的地方,境外的这家法院明显是更合适的法院,但在侵权事件发生的那些国家不能获得法律援助。出于经济的考虑和实质正义的要求,法院决定选择将英国法院作为合适的法院。当然,在欧洲法院通过Owusu v.Jackson案对《布鲁塞尔条例Ⅰ》作出解释后,英国对非方便法院原则的运用将走向终结。根据欧洲法院在该案中确定的原则,《布鲁塞尔条例Ⅰ》第二条实际上是不允许成员国法院运用非方便法院原则终止诉讼,不论原告的住所在哪里,也不论可替代法院是否是欧盟成员国的法院。这为原告在英国起诉英国籍的跨国公司母公司扫除了障碍。
(二)被告资格的问题
首先,企业可否成为违反国际法之诉的被告?一般以为,跨国公司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得到肯定,不能成为国际法约束的对象。传统国际法可以适用于以国家名义行为的企业。关于海盗、奴役和强迫劳动的诉求没有国家行为要求。虽然Doe v.Unocal案法院对原告的支持表明,即使没有以国家机构的名义行为,私人部门也应该依照ATCA承担责任。一般而言,ATCA诉求如酷刑或法外死刑仍然要求针对的是国家的行为,使这些行为区别于一般的袭击和谋杀而提升到违反国际人权法的高度。
其次,被告的确定还要考虑责任理论和因果关系:应先看被告之行为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再证明被告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在Sinaltrainal and Gil v.The Coca-Cola Company案中,谋杀是由哥伦比亚武装人员在Bebidas厂经理的协助下完成的。而Sinaltrainal案的原告却提出一系列被告:作为雇主的Bebidas工厂、Bebidas工厂的厂主、可口可乐美国和哥伦比亚公司。不过,佛罗里达联邦地区法院并没有接受原告的所有诉求。
(三)诉因问题
1.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的高标准。美国最高法院并未明确说明哪些属于可依ATCA提出违反国际法的诉由。自Filartiga案,法院不断阐释何种规范属于“国际法”而纳入ATCA的诉由范围。美国最高法院在2004年的Sosa v.Alvarez-Machain案中重申了Filartiga案的标准,认为依ATCA可诉的侵犯人权行为必须是违反了普遍的、义务性的和明确的国际规范,一般包括:蓄意的灭种族屠杀、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奴役、强迫人口迁移、谋杀、法外死刑、强奸和海盗。在Sosa案后,美国法院继续对可依照ATCA提起的诉由范围进行界定。第九巡回法院在2006年的Sarei v.Rio Tinto,PLC案中裁定,原告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指控一国际采矿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铜矿经营中的侵犯人权行为,构成依照ATCA的诉由:战争罪,违反战争法,种族歧视和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的高标准使很多最普通的国际劳动侵害行为如最低工资、超时工作、危险工作条件和工伤,还无法成为可依照ATCA提起的诉由。
2.“协助和鼓动”责任。美国第九巡回法院2003年对Doe v.Unocal的判决注意到原告关于Unocal与缅甸军队共用照片、测量和地图的主张,裁定此种行为属于“有意识地实际协助或鼓动”,无论被告是否控制或参与该行为,都足以产生责任。该案不仅确立了国际法同样适用于企业等私人部门,还确立了像跨国企业这样的私人实体应为帮助和鼓动人权侵害承担责任,即使其本身并未直接实施侵害行为。
自Doe v.Unocal案后,此类案件的原告主要以“协助和鼓动”责任为理论基础对企业提起ATCA诉由。但该案是唯一支持“协助和鼓动”责任的,它受到要缩小依ATCA追究“协助和鼓动”责任之范围的挑战。尤其是,2004年Sosa v.Alvarez-Machaim案的被告辩护说,Filartiga案中确立的普遍性、义务性和明确的标准必须适用于ATCA诉求的每个要素,包括“协助和鼓动”责任,而民法中的“协助和鼓动”责任并未获得世界认同,国际法上不存在对“协助和鼓动”人权侵害行为的普遍的、义务性的和明确的禁止,因此它不属于ATCA诉由。可见,ATCA下的“协助和鼓动”责任是否成立还没有确切答案。
这还涉及“公司同谋”的概念。这一源于刑法的概念最早在企业的运用是由人权观察在1999年关于跨国公司投资活动与侵犯人权关系的报告中提出的[4]。1999年联合国《全球契约》要求企业应当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200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也在一般义务中明确提及公司同谋的问题。公司同谋责任可分为四种情况:(1)企业积极地直接或间接协助他人的侵犯人权行为;(2)企业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可合理地预见或最终获悉政府在履行协议时可能侵犯人权;(3)企业受益于侵犯人权行为,即使它没有积极协助或造成侵犯人权行为;(4)企业对侵犯人权行为保持沉默或不作为[5]125~136。第一种情况属于直接同谋,这种明知是一种有意识的参与,但不一定是为了引起损害结果,只是知晓该行为可能会带来损害结果。第二、三种情况属于间接同谋,尽管公司并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授权、指挥或预先知悉该侵权行为,但它却继续维持与政府的伙伴关系,从他人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中获取利益。第四种情况属于保持沉默的同谋,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判断时需要考虑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使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公司是否有实力影响或能否通过撤离市场的方式来减少或根除侵犯人权的行为等[6]41。但以上都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因此,公司同谋责任是否可以作为诉因还没有国际法的依据。
(四)法律适用问题
对企业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美国各州的法律选择方法不一,一般是适用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英国对于涉外侵权诉讼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95年《国际私法(杂项条款)》,该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是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即该人或物受到伤害或损害时其所在地,其他侵权案件则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2007年7月11日通过、2009年1月1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第864/2007号条例》(简称《罗马条例Ⅱ》)包括了产品责任、环境损害、劳工行为等问题,确立了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规则,除非案件明显地与另一国家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则适用另一国家的法律。
对企业跨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是适用国际法、侵权行为地法,还是法院地法?从实践来看,加拿大依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美国及英国基本上适用法院地法。ATCA的目的是对违反国际法进行救济,国际人权法应该得到适用。但美国法院不会自动适用国际法,即使要适用国际法,也是作为国内法解释的工具。而且,Unocal案的判决称:只有在被指控的侵权构成了对强行法的违反时才应适用国际法。其他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律适用规则也不相同。且同一性质的诉因,不同法域对准据法的确定也存在不同方法。英国在少数侵权案中以“公共政策保留”拒绝适用外国法,依此,如果适用外国法将使被告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脱逃法律责任,那么外国法将不予适用。
实践中,针对企业的跨国诉讼都是在跨国公司母国法院提起,这往往是出于母国能更好地控制跨国公司、更易于司法救济等方面的考虑。但是,如果实施违法行为的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的法院被认为是合适的法院并且实际行使了管辖权,确定母公司的法律责任也存在法律适用的问题。位于不同国家的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关系,一般由子公司的属人法支配。东道国法院依子公司的属人法作出让外国母公司对该内国子公司的行为负责的判决,是符合一般国际私法原则的对母公司法律责任的追究,但是,只有当有关母公司法律责任的规定能域外适用,才有实际意义。所以,可能引起的问题是,母公司所在国(投资母国)对子公司所在国(东道国)法院的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7]48~49。
(五)跨国企业为其子公司或商业伙伴承担责任的问题
跨国公司一般采用母子公司的组织结构,而全球化生产链或供应链的经营状态、现代公司结构中的多层承包以及现代雇佣制度,使跨国公司结构日益复杂,很多大型跨国企业实际上不从事生产,只是居于多层承包结构或供应链的最高层。不履行社会责任的常是独立于跨国企业的另一个企业,而跨国企业可能是唯一有足够实力阻止侵害发生的实体,也往往是母国法院可以有效行使管辖权并执行裁决的唯一实体。可以参照公司法上跨国公司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原则确定跨国企业对其子公司和商业伙伴的行为应承担的责任。
著名的印度“博帕尔案”表明,在东道国发生的侵权由于存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而可能在母国法庭被诉,母国的法律可能被适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当地化和分权化,可能降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能力,传统的以控制理论为基础的母、子公司责任原则是否适用?精确区分控制程度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经合组织曾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区分:一是跨国公司整体的经营方式与地点的影响。在这方面,子公司基本上没有自主权。二是特定决策中母公司影响力的程度。集中于母公司的决策属于“被视为与文化差异无关的决策,以及由母公司来制定更有效率的决策。”而与特定子公司相关的决策、必须保持对东道国环境高度敏感的决策(诸如人事安排、劳资关系、产品促销等)则是相对分权的领域[8]60。但集权与分权只是因理论分析的需要而设置的,子公司完全独立或母公司绝对控制的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分权或集权的确定只能与具体的母子公司关系和子公司的特定商业决策相联系,才是可行的[9]115~116。有学者建议,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应当与子公司所享有的自主程度相联系,视自主权被剥夺的程度让母公司负部分或全部责任。
各国让跨国公司承担子公司责任的做法各不相同。有的以传统的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为根据来揭开法人面纱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如美国);有的通过专门的公司集团法做出直接规定(如德国)。美国法使跨国企业为子公司或商业伙伴承担责任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考虑它们之间关系的类型。原告不需要证明跨国企业知道、帮助或默许另一实体的任何非法行为,关系的性质足以使跨国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种方式通过证明跨国企业明知、协助、参与、甚至鼓励另一实体的侵害行为对跨国企业追究所谓“帮助和教唆责任”,认为同谋者与主犯承担同等责任。从实践来看,即使跨国企业对其承包商拥有明显的权力和控制,受害人主张此种关系也是很困难的。
如前所述,跨国诉讼也可以通过直接针对跨国企业本身的行为和未尽义务,而非引入某种责任理论使跨国企业对另一实体的劳动侵害行为负责。如Nike对其工厂的劳动条件、对劳动侵害做虚假陈述;沃尔玛没能依照劳动条款监管其供货商的劳动条件的违约行为。但一般而言,这些只限于与劳动侵害有关的行为,而且也不具有普遍性。
四、结语
目前,就企业社会责任跨国诉讼中权利的可诉性来说,许多国家已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的健康权、环境权、劳动权、结社权等规定为可诉的权利,并出现了许多案例。然而,针对违反国际法提起的诉讼需国内法院的法官解释国际法以识别原告的请求,受到法官经验的限制。而且,大多数国内法只为与国内具有联系的原告提供救济,使很多非母国公民受害人及针对在母国域外发生的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都不能在母国法院求得救济。另外,与企业社会责任跨国诉讼相关的国内法还面临非法律性的挑战。ATCA虽然是目前最能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跨国诉讼的法律,也面临着美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限制,以及在石油工业等的游说与抵制下美国政府的反对。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诉讼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地方。尽管这些跨国诉讼的实践还不太普遍,而且遇到很多理论难题和现实挑战,但这些实践是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法律规制的新趋势,其意义在于:一是逐渐形成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法律规制的机制,二是作为国际法形成的证据,有利于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法的发展。
[1]Barnali Choudhury.Beyond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ttributing Liability to Corporations for Extraterritorial Abuses[J].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Business,2005,(Fall).
[2]肖剑鸣.比较环境法[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3]李金泽.公司法律冲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Anita Ramasastry.Corporate Complicity:From Nuremberg to Rangoon-an Examination of Forced Labor Cas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Lia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2,(Vol120).
[5]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Policy.Beyond Voluntarism:Human Rights and the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of Companies[M].Geneva: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Policy,2002.
[6]Anthony P.Ewing.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Compact Human Rights Principles,in a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Office and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Embedding Human Rights in Business Practice[M].New York:UN Global Compact Office,2004.
[7]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8]P.Muchlinski.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Law[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1995.
[9]陈东.跨国公司治理中的责任承担机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D996
A
1001-4799(2010)03-0086-06
2009-10-08
曾丽洁(1971-),女,湖南邵东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法研究。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