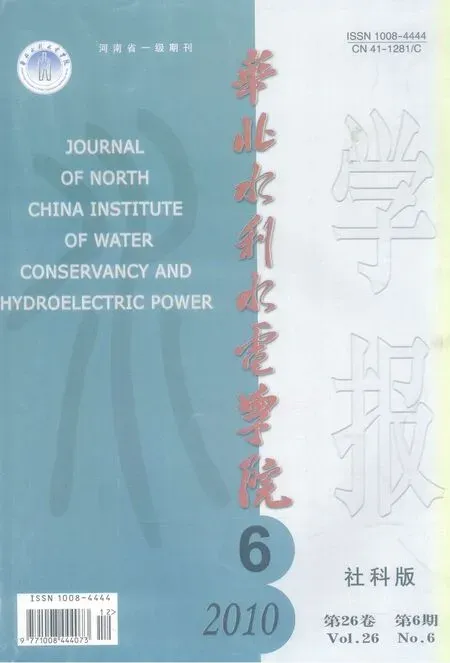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张自然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1)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张自然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1)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宋明时期;笔记;《史记》;文学成就
《史记》作为史学著作,一问世就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对其文学作品性质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魏晋以前,人们在评价《史记》时,多注意其史学成就。如西汉的刘向、扬雄称《史记》为“实录”,“服其善序事理”[1](卷六二);班彪称《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2](卷四○上);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语中谈及武帝时人才之盛时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1](P2634),算是最早称赞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了,但对《史记》的评价仍然是在史学方面。魏晋以后,《史记》成为正史之首,因此也较少有人从文学角度去关注《史记》。晋张辅称“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他认识到《史记》“逞辞流离”、“辞藻华靡”等今天我们认为是文学方面的特点,但仍然是从史的角度着眼的,即其所谓“此所以迁称良史也”[3](卷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曾谈到司马迁的文章,但是没有突出《史记》作为文学作品的成就①《才略》、《时序》、《史传》等篇均有涉及。。此期重要的文学选本——《文选》,因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也没能选录《史记》之文[4]。可以说,在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挖掘。
真正认识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并从文学角度去研读《史记》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为反对骈文、扫除浮靡之风、整饬世风、挽救社会危机而掀起的古文运动,把《史记》作为学习的典范。韩愈、柳宗元等古文作家不仅对《史记》的文学成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在创作实践中也学习《史记》的章法、句法,《史记》作为汉代散文典范的文学史地位得以确立。此后,在宋代的古文运动、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中,许多文学家如欧阳修、曾巩、“三苏”、黄庭坚、洪迈、刘辰翁、朱熹、吕祖谦、黄震,明代的前后七子、茅坤、归有光等人都对《史记》极为推崇,并对《史记》的艺术特色诸如文章结构、转折波澜、人物刻画等作了积极的探研和发掘。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成就的评论除了出现在诸种《史记》评点本、文人别集之中外,笔记著作中也多有涉及。这一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评论是多方面的,包括叙事特色、艺术风格、语言技巧等,笔者仅对其中有关《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进行简要述评。
一
今人论《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指传记文学领域方面,宋明时期的笔记中对此多有论及。宋宋祁云:“老子《道德篇》为玄言之祖,屈、宋《离骚》为辞赋之祖,司马迁《史记》为纪传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5]宋祁把《史记》看作“纪传之祖”,看作“规”、“矩”,充分肯定了《史记》在纪传文学中的地位。宋陈善对宋祁的看法也持肯定的态度:“宋尚书云:老子《道德经》为至言之宗,屈平《离骚经》为词赋之宗,司马迁《史记》为纪传之宗。”[6]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更多地是从《史记》的史学性质中看其文学特点,指出《史记》与众多史学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文学特色浓郁,是史、文结合的佳作。明胡应麟云:“《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7]①明张存绅《雅俗稽言》卷二六“史说”部分亦有此条。正是认识到了《史记》、《汉书》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明戴君恩云:“六经而下,事与文兼该者,马《史》、班《书》、《左传》而已。”又云:“诸史之文,马迁为冠。”[8]戴氏不仅指出《史记》“事与文兼该”,而且还指出《史记》在诸史之中文学成就最高。
有一些笔记著作还把司马迁及其《史记》与同期的其他文学家或文学作品对比,以此来揭示《史记》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杨慎把司马迁《史记》这种“纪事之文”与“游说之文”、“政事之文”、“谲谏之文”、“说理之文”、“术数之文”等并称,来描述汉代文章之盛[9]。明于慎行在言及两汉文章之盛时,将《史记》这种“记事之文”与枚、邹、相如、庄助、吾丘之流的“词赋之文”、淮南宾客的“著述之文”并举,说“此三种文章至今为世所宗”,并特别指出“《史记》不号为文,而其文之妙为千古绝唱”[10],对《史记》的文学成就可谓推崇备至。明屠隆《鸿苞》卷一七“文章”条把司马迁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刘向等文学家并称,把《史记》与当时的射策之文、词赋以及诗歌等今天我们所说的纯文学并论,亦可见其对《史记》文学特色的认识[11]。
还有一些笔记把司马迁及其《史记》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对其文学成就作出评判。《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云:“自昔博学而擅文辞者,公孙侨、左丘明、东方朔、司马迁、刘向、扬雄、曹植、王勃、杜甫、韩愈十数人耳。”[7]②明张存绅《雅俗稽言》卷二六“史说”中亦有此条。明詹景凤对司马迁在汉代文学中的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汉之文无如子长者”[12](卷三〇)。其《詹氏性理小辨》(卷三七)又言:“文导源于左氏,澒洞于二马,而流沫于班、扬。譬之兵家,左氏夹谷之会乎?马氏巨鹿之战乎?班、扬则细柳矣。”詹氏指出,二马(当然包括司马迁)之文胜过其前的左氏,也优于其后的?
二
《史记》作为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宋至明,笔记著作对《史记》在文学史上产生的影响作了很多论述。班固、扬雄辈。然而,这一评价的时间范围还仅限于汉代以前,于是詹氏在同书卷三八“摛藻下”中说:“千古文章鸿藻,予所惊心动骨,蒲伏称臣而不敢仰视者三人:前惟庄生,中则司马龙门,后惟苏长公。”又说:“子长滉洋自恣,笼罩上下,千古文章家一大英雄也。”这一次则把对司马迁的评价放到整个文学史框架之内,其对司马迁及《史记》文学性的推崇可见一斑。明冯时可云:“屈原之骚,庄生之书,司马子长之史,相如之赋,李、杜之诗,韩、苏之序记,驰骋纵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13]与司马迁并提者,皆为历代文学大家。明杨继益把《史记》与六经、《左传》及韩、柳诸大家等比较,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虽不如六经、《左传》,但优于韩、柳等大家文字,其《澹斋内言》云:“韩、柳诸大家以篇为文,必读完篇,其意旨乃见;《庄子》、马迁以句为文,盖虽一句中便极其工而意足也;《左传》以字为文,盖虽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如六经,则无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14]
也有一些笔记作者从阅读的角度来认识《史记》的文学特色,认为《史记》之文具有可读性。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五)“史记撷语”摘录《史记》精美语句数十条,并认为《史记》不仅文句优美,“平顺可读”,而且议论精当[1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史书占毕》)中提到“相如窃女,曼倩滑稽”时,说“其文瑰伟可喜”[7]。诸如此类尤多,不赘。
此期笔记著作还分析了《史记》在文学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杨慎云:“《史记》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为独冠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笔力,亦由其书会辑《左氏》、《国语》、《战国策》、《世本》及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辈诸名人文章以为桢干也。”[16](卷一二)明支允坚所云与杨氏略同:“欧阳公《五代史》,非其得意之文,其叙事劣于史迁,其持论则正于史迁。然史迁会萃《左》、《国》及西京名家文章以为桢干,而公独掇拾残文断简于兵戈煨烬之余,其为力固有难易也。”[17](卷九)他们认为《史记》能成为诸史之冠,不仅在于司马迁之笔力,而且在于司马迁吸取先秦及同代文学之精华。
(一)《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有“杨恽有外祖风”一条,云:
杨恽以口语坐废,其友人孙会宗与书,戒以大臣废退阖门惶惧之意。恽报书,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气宛然有外祖风致。盖其平日读外祖《太史公记》,故发于词旨,不期而然。[18]
这里王楙指出,杨恽《报孙会宗书》之所以表现出怏怏不平之气,与其平日读外祖《太史公记》有重要关系。《史记》一书是司马迁去世后由其外孙杨恽祖述,“遂宣布焉”[1](卷六二)。完整阅读《史记》的第一人是杨恽,在创作上受《史记》影响的第一人也是杨恽,王楙之说甚是。
《史记》流传以后至六朝,在文学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再加上其散文体与六朝崇尚骈丽文风相对立,文人对其学习和模仿就更少,成就不高,影响不大。王楙曾指出:“梁江淹狱中一书(笔者按:指《狱中上建平王书》),情词凄惋,亦放迁作,惜笔力不能及之。”[18](卷二)
《史记》的文学价值真正被发掘是在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史记》倍加推崇,也最早主动地在创作上学习、模仿《史记》,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成为宋明时期笔记评论的话题。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七“韩柳为文之旨”条曾以韩、柳之语来阐明二人为文之旨[19]。韩、柳二人当时互评对方之文,也指出对方对《史记》的学习及文学风格与《史记》的近似①韩评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之流不足多也。”柳论韩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分别见刘禹锡《柳河东集序》及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但两人之论都非有意吹捧。宋李如箎《东园丛说》云:“详究其作,二公之论,皆非溢美”[20]。如果“详究其作”,确实能够看到《史记》对韩、柳的影响,此期其他笔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具体分析。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韩柳文法祖史记”条云,《获麟解》中“角者吾知其为牛,……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孔子谓弟子曰”云云,《游黄溪记》“北之晋,……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21]。这是从具体文章指出韩、柳在创作上对《史记》文法、句法的学习。详论韩愈学习《史记》文法、句法者还有很多,试看几例:
《史记·张释之传》云:“吏不当如此耶!”《薛广德传》云:“晓人不当如是耶!”……皆有味也。[22]
《史记》:张仪论韩地险恶曰:“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羮。”此倒句也。昌黎文:“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亦此类。[23](卷一)
(韩文)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史记》云“胜不敢复相士”云云“胜不敢复相士”,韩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记》荆轲云“轲真倾危之士哉”,韩《毛颖传》云“秦真少恩哉”。……若此者殆不胜纪。[15](卷一八)
太史公《管仲传》内云:“天下不称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及作《季布传》亦云:“人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而朱家亦用此名闻天下。”……韩退之效之云:“诵文武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盖文少变而意同,乃是善学。[24](卷上)
亦有从具体篇章来论韩愈学习《史记》叙事方法、形式、风格等的。论学习叙事方法的如:李耆卿认为“《圬者王承福传》叙事论议相间,颇有太史公《伯夷传》之风”[25];王鏊认为《何蕃传》仿太史公《伯夷》、《屈原传》“时出议论”、“自发其感愤”之意[26](卷下);方以智认为《张中丞传后叙》中“叙睢阳,述南八”仿《史记·荆轲传》叙鲁句践、高渐离事,并指出:“此善请客之妙也。妙高峰七日不见,而见之别峰,道寓于器,正意寓于旁意,何往不然”[27](卷首三)。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则指出韩愈论在行文形式方面对《史记》的学习,认为《原鬼篇》、《送窦平序》之结语均祖法《史记·河渠书》,并指出“后人沿袭者甚多”,如李习之《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卫》、贾同《责荀》、孙复《儒辱》、王安石《闵习》等[21](卷一)。戴君恩以为韩《毛颖传》的风格“直欲与七十二传争雄”,《徐偃王碑》、《平淮西碑》、《曹孝成王碑》风格“方之十表,真堪伯仲以敌矣”[8](卷一四)。
宋明笔记作者也认识到《史记》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宋龚颐正《芥隐笔记》有论:“老杜《瘦马行》‘此岂有意仍腾骧’,盖用《史记》邹衍‘此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意,最为奇。”[22]元刘埙《隐居通议》卷六“李杜苏黄”条亦云“少陵诗似《史记》”。前者是从形式上论,后者盖从内容上言,均看到了《史记》对杜甫的影响。
宋代古文家对《史记》的学习在宋明笔记著作中也有述评。宋王正德《余师录》记载一逸事:“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28](卷一)此事既可见散文家对《史记》的重视,也说明熟读《史记》确实能提高写作水平。明焦竑《焦氏笔乘》卷二有“荆公学史记”一条,言王安石的短文可与《史记》的论赞“相颉颃”,并举《读刺客传》与《伍子胥庙铭》为例,认为“此等文,观其笔力曲折,真脱胎换骨手也”[29]。
相传苏轼不喜《史记》。宋袁文云“苏东坡喜《汉书》,而独不喜《史记》”[30],宋周密云“坡翁不喜《史记》”[31]。其实并非如此。明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记载一轶事:“坡公作《表忠观碑》成,客见之,皆谓古无此体,王介甫笑曰:‘诸公未之知,此司马迁《二王世家》(笔者按:当作三王)体’。”可见,苏轼还是受到《史记》影响的。宋明笔记著作论宋代文学家学习《史记》的条目中,与苏轼有关的最多。罗大经认为:“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23](卷六)。周密也认为“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32](卷上)。刘埙则说苏轼《韩文公庙碑》“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使其身一日自安于朝廷之上”句与《史记·龟策列传》“神至能见梦于元王,……而不能令卫平无言”“文法正似相同”[15](卷一八)。盛如梓认为《扶苏论》“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积威信之剧”与《史记·吴王濞列传》“恐上诛之,计乃无聊”、“积威约之渐”“句法同而意殊”[33](卷中上)。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引朱凌溪言:“康对山谓《范增论》后数句忙杀东坡,盖以峻快斩截为著忙也。此亦有见,但不免溺于一偏。缘康之文全学《史记》纡徐委曲重复典厚,而不知峻快斩绝亦《史记》之所不废,如《韩信传》‘任天下武勇’以下载‘我以其车’一节,可见东坡于此等得之,康见之熟,遂以为忙,不知《史记》为文如右军作字,欧师其劲,颜师其肥,虞师其匀圆,各成一体,皆可取法,不可以己好典重纡徐而遂轻峻快斩截也。”并认为“凌溪此言可谓善求古人之文”[34](卷二三)。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字法、句法,还是结构体式、艺术风格,苏轼都从《史记》中受益不浅。
以上这些宋明时期笔记著作在分析论述时,多从大家入手,细处着眼,涉及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基本可以说明《史记》对后世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的影响。
(二)《史记》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由于自唐代古文运动起,广大文人开始重视《史记》,从中汲取营养,使得许多文学作品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都带有《史记》的印记。因此,人们在评论文学家或文学作品时不由自主地就会把司马迁或《史记》作为标准,如唐李肇说“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髙,不下史迁”[35](卷下),就是以《史记》为标准评论韩愈《毛颖传》的。宋明时期笔记著作中此类评论甚多:
东光张预作《百将传》甚有旨趣,文落落不拘,翦殊得太史公笔法,但太史公篇篇有主意,而张预或有泛而无统者也。[36](卷下)
晁以道之文雅健,却少太史公气概。[36](卷下)
东坡《表忠观碑》,介甫以为序似太史公《诸侯王表》。[36](卷下)
韩退之文绝似马迁,苏长公文绝似孟子。[8](卷一四)
苏明允作《成都府张公安道画像记》,鲁直读之,云:“司马子长复出也。”[37](卷三)
巩丰仲至言:“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37](卷下)
夫子长而后,至唐而有李太白,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维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将进酒、问月诸篇,天才跌宕,差可与子长比肩。[38](卷七)
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39](卷二)
他们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评论他人文章优劣的标准与参照,充分说明他们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肯定。
三
宋明笔记中对《史记》的文学性评论之所以条目众多,与宋代古文运动与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分是不开的。宋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的散文创作,无不受到《史记》的影响。尤其是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明确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史记》作为古文创作的典范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与秦汉派相抗衡的唐宋派所推崇的唐宋古文如韩、柳、王、苏等文亦与《史记》等秦汉古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唐宋派古文家代表茅坤、归有光等人还有评点《史记》的专著。当然,由于笔记的随录性质及篇幅限制,其评论大部分没能展开,大多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部分,甚至是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单独一条来看,大都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又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显得过于空泛而缺少说服力。但是,这些评论大都把《史记》与世人公认的文学大家及其名篇名作相联系,而这些古文大家多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中坚力量或文学复古运动中所师法的典范,因此,其评论的代表性勿庸置疑。我们如果把这些不同著作中的不同评论互相结合,无疑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并且能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萧统.文选序[A].文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宋祁.宋景文笔记[M].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刻学海类编本.
[6]陈善.扪虱新话[M].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十一年(1922).
[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64.
[8]戴君恩.剩言[M].明刻本.
[9]杨慎.丹铅续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于慎行.山谷笔尘[M].明万历于纬刻本.
[11]屠隆.鸿苞[M].明万历三十八年茅元仪刻本.
[12]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M].明万历间刻本.
[13]冯时可.雨航杂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
[14]杨继益.澹斋内言[M].涵芬楼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学海类编本.
[15]刘埙.隐居通议[M].丛书集成初编本.
[16]杨慎.丹铅余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支允坚.梅花渡异林[M].明崇祯间刻本.
[18]王楙.野客丛书[M].丛书集成初编本.
[19]洪迈.容斋随笔[M].四部丛刊本.
[20]李如箎.东园丛说[M].丛书集成初编本.
[21]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M].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十一年(1922).
[22]龚颐正.芥隐笔记[M].丛书集成初编本.
[23]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张凤翼.谭辂[M].明万历刻本.
[25]李耆卿.文章精义[M].上海:有正书局,1918.
[26]王鏊.震泽长语[M].丛书集成初编本.
[27]方以智.通雅[M].清康熙五年龙眠姚氏刻本.
[28]王正德.余师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
[29]焦竑.焦氏笔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0]袁文.瓮牖闲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1]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2]周密撰,邓子勉校点.浩然斋雅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3]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M].丛书集成初编本.
[3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明万历七年龚元成等刻本.
[35]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6]韩淲.涧泉日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8]李豫亨.推蓬寤语[M].明隆庆五年李氏思敬堂刻本.
[39]杨慎.诗话补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in Respect of Literary Achievements in the Pen Jottings of the Dynasties from Song to Ming
ZHANG Zi-ran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in respect of literary achievements in the pen jottings of the dynasties from Song to Ming mainly includes the epistemology of its literary nature as a historical work,the epistemology of its literary nature as a biography,its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reasons for its literary achievements,its influence on the later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s,and so forth.These comments can deepen our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its literary value,and from them the relation of succession can be discovered as well of China’s classical prose compositions.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Literary achievements;Pen jottings;Dynasties from Song to Ming
I206.2
A
1008—4444(2010)06—0044—05
2010-08-21
张自然(1970—),男,河南禹州人,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讲师。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