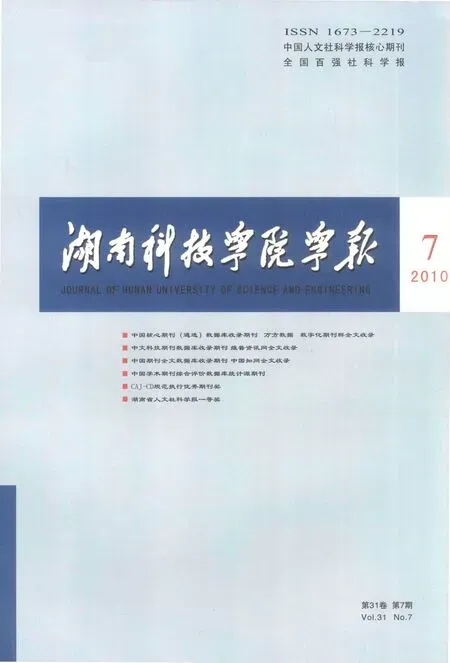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从以旧换新案例看共同诈骗的刑法适用
邓中文
(宜宾学院 法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
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从以旧换新案例看共同诈骗的刑法适用
邓中文
(宜宾学院 法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
行为人伪造其他单位印章,篡改发动机编号,贿买非国有公司主管工作人员,里应外合,以废旧发动机换取新发动机,从而骗取公司巨额财物,行为人构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诈骗罪,应择一重罪处罚。非国有公司工作人员构成诈骗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应择一重罪处罚。
以旧换新;伪造印章;行贿;受贿;诈骗
一 案 情
某摩托车集团公司规定:凡是符合产品“三包”规定的发动机,在规定期限内指定的经销商可以免费以旧换新。2006年8月以来,陈某伪造龙衡摩托车厂和天合摩托车有限公司的印章,对超过退机时限的发动机进行改号后,以上述二公司的名义到摩托车集团公司以旧发动机换取新发动机。为了胜利地换到新机器,陈某先后7次向集团公司的主管工作人员陈某某、金某某、颜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彭某某、周某某等人行贿,数额达8.21万元。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收取贿赂后,相互串通,明知陈某不符合退机条件而仍然让其换取新发动机。2005年5月以来,徐某伪造双狮摩托车配件厂的印章,同时以不具备退机资格的雄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到集团公司以旧换新。徐某采取与陈某相同的方式先后向集团公司
中的上述主管工作人员多次行贿,数额达5.21万元。集团公司中上述多名主管工作人员均承认先后从陈某、徐某处收取过1万余元的好处费。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均认为集团公司中的主管工作人员陈某某、金某某、颜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彭某某、周某某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安机关认为陈某、徐某二人构成诈骗罪,检察院认为陈某、徐某二人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
二 研 讨
(一)陈某、徐某分别与集团公司中的几名工作人员共同构成诈骗罪
按照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具有犯意沟通和联系,均明知共同犯罪行为必然或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都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在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中,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至关重要。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共犯的主观要件是意思联络。由于甲的意思与乙的意思互相联络,其两者的行为,才产生法律上同意观察的结果。”[1]前苏联刑法学家特拉依宁指出:“不要求各共犯之间有一定的主观联系,就必然把刑事责任建立在几个人的不同的行为客观巧合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然会导致所发生结果的客观犯罪。”[2]共同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二人以上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共同实施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这些共同犯罪行为既可以是共同的作为,也可以是共同的不作为。当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时,如果有身份者的身份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身份特征,即没有法定性和特定性时,就只能作为一般主体对待,全案按照共同实施一般主体犯罪处理。[3]
在本案中,陈某事先分别与集团公司中的几名主管工作人员协商好,由陈某给付每名工作人员一定的好处费或按每台发动机支付相应的费用。当陈某把不符合退机条件的发动机拿到集团公司后,集团公司中的几名工作人员就会不予检查即让陈某退到新发动机。陈某与集团公司中的几名工作人员在主观上具有犯意联络,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单独犯罪,而是有其他人在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陈某与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陈某提供不合格的发生动机,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故意不予检查或检查不认真。陈某是作为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在能够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故意不履行职责,是不作为犯罪。虽然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具有特定的身份,属于公司内部的员工,不同于陈某这个普通的个体,但由于此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身份特征,也就是没有法定性和特定性,因此对陈某与集团公司所构成的共同犯罪就只能按照一般主体所实施的犯罪来处理。陈某与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共同构成什么犯罪呢?
根据刑法第266条对诈骗罪的规定,要构成诈骗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认识到自己所采取的是欺骗手段,必须意识到在用诈骗手段非法骗取他人财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持有人陷于认识上的错误,从而“自愿”将财物交给行骗人。所谓虚构事实,既可以是虚构全部事实,也可以是虚构部分事实,总的来讲就是捏造客观上不存在的事实以骗取他人的财物。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只有当骗取财物数额达到较大时,才能构成诈骗罪,这也是区分一般欺诈行为和诈骗罪的界限。在共同诈骗犯罪中,对各共同犯罪人分别以什么数额作为定罪依据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款规定:“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据此司法解释,有专家认为,在共同诈骗犯罪中,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的诈骗数额,应以集团诈骗的总数额认定;对共同诈骗犯罪中的其它主犯,应按照其参与共同诈骗的总额处罚;对共同诈骗犯罪中的从犯,则按照其参与诈骗的总数额决定其应当使用的刑罚。[4]
计算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时,是只计算被骗财物的价值呢还是应该除去犯罪成本的费用呢?本案中陈某、徐某为了能够获得新发动机,必须要向集团公司提供旧发动机。计算诈骗罪的数额时,是否应该用新发动机的价格来减去旧发动机的价格呢?显然不能。首先,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不应当除去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中用于作案的犯罪工具的价值。只把犯罪的“净收益”、“净利润”作为犯罪数额是不恰当的,比如小偷为了偷东西而买了很贵的盗窃工具、诈骗犯为了骗取他人的财物而买了很贵的“诱饵”工具,虽然这些作案工具仿真程度高,价值本身也不低,但绝不能将作案工具的价值从所骗财物价值中减去。其次,社会危害性是应受刑罚处罚的原因和前提,而社会危害性应当以被害人所遭受财产损失来作为衡量非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依据和标准,不应当以行为人所实际获取的利益作为定罪量刑依据。再次,从刑法条文的表述来看,“数额较大”作为“诈骗公私财物”的结果,“数额较大”一词所指向的应当是被骗取的公私财物本身的数额,而对罪犯的作案成本、作案工具等费用显然并未提到。
在本案中,陈某伙同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采用伪造有退机资格的单位印章,篡改超过退机时限的发动机上的编号等手段,使集团公司基于错误认识从而“自愿”地将新发动机予以发放。陈某与集团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集团公司中新发动机的犯罪目的,在客观上虚构了事实,使集团公司在不知道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处分了自己的财产。由于诈骗罪是结果犯,诈骗财物的数额大小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查清集团公司被骗发动机的价值大小对于本案的正确处理至关重要。如果集团公司的帐上能够反映出陈某退了多少台新发动机,公司帐上有陈某的签名且陈某对此也予承认的话,那么陈某所退新发动机的价值大小便可轻易地算出。如果找不到以旧换新的账目,要直接计算出集团公司被骗新发动机的价值就会比较困难,此时也许只能根据现有证据进行推定。推定作为一种新颖的证据规则,可以满足严厉打击某些特殊类型犯罪的需要,同时可以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推定是一种认证方式,依据推定得出的事实结论如无相反的证据推翻,就可以定案。当然,运用刑事推定时,要求推定所依赖的基础事实必须确实可靠,否则就容易导致所推出的结论错误。其次,要注意把握在基础事实和应证事实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常态联系,只有在无任何相反证据动摇推定结论的前提下,推定得出的结论才能最终被用于定案。
由于陈某自认向集团公司中的几名工作人员行贿了8.21万元,且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也承认收过陈某的好处费,这就是本案的基础事实。根据基础事实便完全可以推定陈某从集团公司所骗新发动机的价值至少应该在8.21万元以上。因为按照常理,陈某骗取新发动机的价值肯定超过陈某的行贿款项,否则如果没有利润可赚的话,陈某就不会冒着风险去骗取新的发动机。至于废旧发动机的价值,则不应除去,况且本案中废旧发动机已被处理,其价值也不好确定。认定陈某与集团公司中几名工作人员共同骗取集团公司8.21万元的财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于陈某在共同诈骗中,所起作用大,可定为主犯,诈骗数额为8.21万元,集团公司中的几名工作人员在共同诈骗中,所起作用小,可定为从犯,在处罚时应当比照主犯陈某从轻、减轻处罚。本案中另一行为人徐某的作案方法与陈某如出一辙。徐某与集团公司中的几名工作人员一起共同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可推定为行贿数额即5.21万元。其中徐某系主犯,对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作为从犯对待,应当比照主犯徐某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陈某、徐某除了构成诈骗罪外,还构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处理时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在本案中,陈某、徐某为了非法占有集团公司的新发动机,通过采取伪造有退机资格的企业印章,贿买集团公司中主管工作人员的方法,里应外合,顺利骗取集团公司的财物。陈某、徐某在构成诈骗罪的同时,还构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牵连犯。
陈某、徐某为了达到非法占有集团公司新发动机的犯罪目的,实施了三个相对独立的犯罪行为即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诈骗罪。陈某、徐某在主观认识上,对伪造印章行为、行贿行为和诈骗行为均有认识,在客观上这三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性。陈某、徐某的目的行为是骗取他人财物,因而构成诈骗罪;陈某、徐某的方法或手段行为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的行为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诈骗罪与后面两种罪之间就形成了目的行为与方法行为的牵连关系。在陈某、徐某所触犯的三个罪名中,由于刑法分则条款上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处刑方式,所以就应当适用牵连犯的通说理论即择一重罪处断解决陈某、徐某的定罪处罚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中陈某、徐某诈骗集团公司的财物数额显然属于数额巨大,如果按诈骗罪处理,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来量刑。由于《刑法》第164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均没有规定数额巨大的标准,所以不好认定陈某、徐某的行贿数额属于数额巨大,只能按照数额较大的标准,对陈某、徐某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刑法》第280条第2款之规定,本案中陈某、徐某伪造有退机资格的企业印章,构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如果按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对陈某、徐某处理的话,最多只能判其3年有期徒刑。
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应当符合的处刑幅度来看,对陈某、徐某应当适用诈骗罪来定罪处罚方能体现牵连犯的通说理论,即择一重罪处断。由此看来,对陈某、徐某二人认定为犯诈骗罪,并在3年以上10以下的幅度内判处有期徒刑,不仅符合法律规定,而且符合刑法理论,是一种可行的处理方式。
(三)集团公司中的七名工作人员除了构成诈骗罪外,还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时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集团公司中的七名工作人员为了从陈某、徐某处获取好处费(收受贿赂)而不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他们与陈某、徐某里应外合共同骗取了集团公司中数额巨大的财物。集团公司中七名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是原因行为,他们与陈某、徐某共同骗取集团公司中财物的行为是结果行为,这里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具有牵连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集团公司中的七名工作人员在构成诈骗罪的同时,又因收受陈某、徐某的贿赂而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应择一重罪处断。
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构成诈骗罪时,因诈骗财物数额达到“数额巨大”应在有期徒刑3年至10年的量刑幅度内处刑。根据刑法第163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刑法及司法解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仅规定了数额较大的起限标准,但未明确数额巨大的标准。本案中集团公司的7名工作人员收受贿赂都不到2万元,显然不能认定为数额巨大。若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最高只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倘若按诈骗罪来处理,则最高刑期可达10年。两罪相比,本案中的重罪显然是诈骗罪了。因此对集团公司中的7名工作人员按诈骗罪处理比较恰当。
(四)全案按诈骗罪处理,既符合法律规定,又有利于打击“以旧换新”中的犯罪行为
综合全案来看,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里应外合的共同犯罪。陈某、徐某二人通过贿赂厂方工作人员的方法,共同骗取了集团公司数额巨大的财物。陈某、徐某在触犯诈骗罪的过程中,显然还构成了其它犯罪,但由于这些其它的犯罪行为与诈骗罪之间具有牵连关系,适用重罪(本案中的诈骗罪)来定罪处罚陈某、徐某及集团公司中的7名工作人员,完全符合刑法规定、刑法理论,能使犯罪分子判处更重的刑罚。由于诈骗罪是一种财产犯罪,刑法还为其设置了罚金刑、没收财产刑。本案在处理时,法院应充分考虑犯罪分子贪利的特点,在对罪犯判处主刑的同时,还应当附加判处罚金,以使罪犯在经济上占不到任何便宜。
以旧换新本来是厂家的一项营销手段,既有利于厂方,又有利于顾客,厂家和顾客皆能从中获利。陈某、徐某与集团公司中的工作人员勾结起来共同骗取厂家的财物,严重地扰乱了经济秩序。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行为,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关注。只有严惩类似本案中的犯罪行为,方能有效维护“以旧换新”活动的持续开展。
[1]牧野英一.法学研究[M].东京:有斐阁,1928.
[2]特拉依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3]马晶.共同犯罪身份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6,(10).
[4]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责任编校:周 欣)
D924
A
1673-2219(2010)07-0110-03
2010-03-01
邓中文(1968-),男,四川岳池人,宜宾学院法学副教授、法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