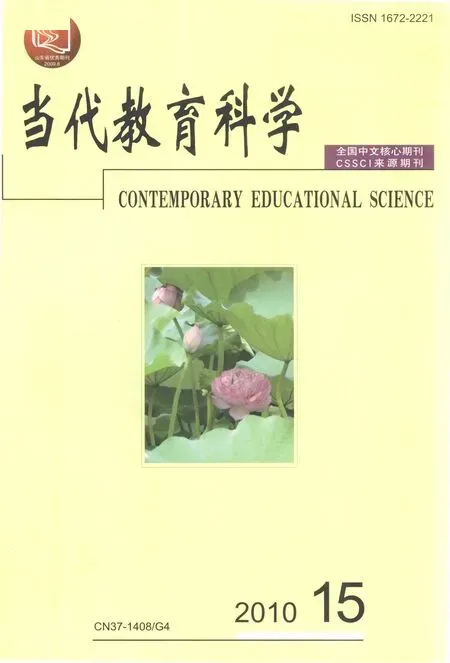“游戏人”理论与“游戏课程观”
● 王宜鹏 夏如波
“游戏人”理论与“游戏课程观”
● 王宜鹏 夏如波
游戏与教育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长期以来,游戏往往只是作为推进教育的手段,作为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活动方式。“游戏人”理论则认为人人都喜欢游戏且生活在游戏之中,人人都是“游戏者”。在这种理论观照下,我们可以宣称:课程即游戏。
“游戏人”理论;游戏;课程
一、“游戏人”理论
(一)游戏与教育关系的一般考察
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游戏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希腊语中,“游戏 (paidia)”和 “教育(paideia)”只有一个字母之差,都与“儿童(pais)”的成长相关。英语中的“学校(Schoo1)”源于拉丁语“Schhola”,而“Schhola”又源于意为“闲暇”、“休息”的希腊语“Skhole”。[1]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从柏拉图到杜威,教育家们一直非常关注“游戏”与“教育”二者关系的研究。柏拉图主张“教师应通过娱乐游戏的帮助,努力把儿童的爱好和乐趣到生活的最终目的上去”;[2]亚里士多德认为游戏是学习闲暇学科和发展理性的重要方法,对于七岁以前儿童尤具意义。正因如此,英国教育史学家威廉·博伊德才说“我们平常的大多数游戏,雅典人都搞过。希腊教育家们对游戏的教育价值有相当正确的认识”;[3]夸美纽斯重视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意义,指出游戏可以使儿童“自寻其乐,并可锻炼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活泼和各种肢体的敏捷”;[4]福禄倍尔以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基础,认为游戏是一种创造性的自我活动和本能的自我教育方式,是儿童“整个未来生活的胚芽,因为整个人的最纯洁的素质和最内在的思想就是在游戏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的”;[5]杜威更是认为如果“没有一些游戏和工作,就不可能有正常的有效的学习”。[6]看起来,教育家们对于“教育”中“游戏”的重要性都是非常强调的,但对各家的游戏观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游戏当成推进教育的手段,把游戏看作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于游戏对教育的促进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在幼儿阶段。这种仅把游戏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或仅在学前教育阶段围绕游戏组织课程的观点一直持续到当下。
(二)“游戏人”理论及其理论观照下的教育
自康德以后,人们对游戏研究的力度不断加大,形成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格局。康德首次在美学的意义上使用“游戏”这一概念,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从正面将艺术与游戏联系在一起的人,这种联系在他看来,就是自由。席勒继承了康德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只要是艺术,就必须同时称为游戏,因为游戏代表着艺术的“最高审美作用”,没有这种“最高审美作用”,艺术便不能称为艺术。他进而宣称:“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7]从康德到席勒,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家们的一种努力,即赋予游戏以生命本体论的意义。于是,“游戏人”理论于二十世纪初应运而生。
1938年,荷兰学者胡伊青加(John Huizingga,或译赫伊津哈)出版了专门研究人类游戏的专著《人:游戏者》,把人们对于游戏的认识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胡伊青加系统考察了游戏在各种文化形态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地观点:“人是游戏者。”在胡伊青加看来,游戏比文化更为古老,因为文化总是以人类社会的存在为前提,而动物则无需人教它们也会游戏。也就是说,胡伊青加认为游戏乃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天性,人天生地就需要游戏也会游戏。不是文化产生了游戏,而恰恰相反,是游戏产生了文化。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仪式,还是音乐、舞蹈、狩猎、竞技,所有人类社会中那些伟大的原型活动,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游戏。接着,胡伊青加通过对古希腊到18世纪这一历史过程的纵深考察,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始终都活跃着游戏的因素,正是由于这种游戏因素的存在,才产生了后来社会文化生活的很多重要形式。但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崛起,胡氏发现文化中许多原有的游戏因素正处于衰退之中。胡伊青加认为,19世纪以来,“理性人”和“制造人”理论的肆虐导致人们游戏精神的淡化,但即便如此,“游戏”依然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范畴”,而文明恰恰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真正的文明离开游戏乃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将总是根据某些规则来游戏,而真正的文明将总是需要公平游戏的。欺骗和破坏游戏就是摧毁文明本身”。[8]由此,胡伊青加得出结论:人不仅是“理性人”和“制造人”,人的最本源的存在方式乃是“游戏人”。我们强调游戏的本体性意义,目的即在于召回全人类的正在渐行渐远的游戏精神,寻求人类游戏真正而纯粹的游戏因素,重新寻回那种失却已久的自足而自恰的人类生活。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胡伊青加“游戏人”理论的基本观点:第一,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冲动,人人都喜爱游戏,游戏的冲动不仅表现于人类的儿童时期,而且贯穿于人的一生;第二,生活就是由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游戏构成,人人都生活在游戏之中,“理性人”、“制造人”等也只不过是人类为自己在不同时期、不同活动中所设计的不同角色而已;第三,人人都是“游戏者”,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成为”和“看到”自己以及他人。第四,游戏是人类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各种文化的“母体”。[9]从“游戏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活动,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既然人人都是“游戏者”,人人都生活在游戏之中,教育当然也是游戏之一种。人们“在教育中游戏”、“通过教育游戏”、“为了教育而游戏”,参与教育这种“游戏”,享受教育这种“游戏”的愉悦,应该是超越其他目的的更为重要的目的,所以,所有的教育都应该充满“游戏精神”。可以说,当前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对“教”和“学”的普遍厌倦正是因为这种“游戏精神”缺乏所导致的恶果。同时,既然教育活动究其实质也是一种游戏,那么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就是游戏者与游戏者之间的关系,双方必须共同营造一种游戏的氛围,承担游戏中各自应该承担的角色,共同制定并遵守游戏中的若干规则,并根据各方的需要共同商定对规则的修改。
二、“游戏课程观”:“游戏人”理论视野下的课程
(一)“游戏课程观”中的师生——“游戏者”
平等精神是游戏的基本精神之一。游戏者间的博奕,彼此地位平等,机会均等,无长幼尊卑之分,正如中国一句俗语所言:“牌桌上无父子。”不仅如此,游戏规则还是人为规定的,同一游戏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规则,就是同一地域、同一伙人的游戏,其规则也可以有多种解释。在课程与教学中,权威意味着控制。传统课程观看来,对教师而言,没有比权威和控制更重要的了。而在“游戏课程观”这里,教师的作用是“平等者中的首席”,即师生之间不存在教导与接受、先知者与后知者的必然鸿沟,而是作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知识领域的过程中相互对话、相互合作。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学生可能对教师的权威构成不信任,但通过共同探究和沟通却能向教师开放信任。
“游戏课程观”中的师生走出了传统的“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之争,他们都是“游戏者”。既然人人都是游戏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是一种游戏者与游戏者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在这场游戏中,他们都将尝试某种意义上的“偏离”:教师自专门知识的占有者和自成人权威者偏离,这意谓着他不再是控制者和命令的发布者;而学生则是实现从“自我跛足”(self-handicapping)的一种偏离。有了这两种偏离,师生作为共同游戏的参与者就有了合作和商谈的可能,课堂也就有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验的学生也才有了得到理解的可能。这样,才能保证师生取得主体间的一致,并从而不至于仅让学习经验多一些的教师和少数学生留在活动中而其他人则游离于活动之外。只有通过与学生的互动,商谈出一种新的共享的意义,教师才能确认学习已经成功发生了。
(二)“游戏课程观”中的创新——“自由书写”
在汉字中,“游”的本义是饰于旗帜上下垂的飘带。《说文解字》释“游”曰:“游,旌旗之流也。”可见,正是从旌旗下垂缨带的飘动感出发,人们赋予了“游”字悠闲从容、无拘无束的含义。可见,从一开始,人们所理解的游戏便具有了一种从容不迫、悠闲自得的内涵,近乎一种自由的状态。胡伊青加对于游戏的自由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首先,一切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遵照命令的游戏已不再是游戏,它至多是对游戏的强制性模仿。……儿童和动物之所以游戏,是因为它们喜欢玩耍,在这种‘喜欢’中就有它们的自愿。……游戏的最主要的特征,即游戏是自愿的,是事实上的自由。”[10]与“游戏人理论”对于自由的强调相背的是,当前的课程行为中充斥着大量的强力控制的痕迹。首先,“学什么”的自由本是学习者最基本的自由,但伯恩斯坦所说的“强分类”和“强架构”的“集合编码型”教材[11]则彻底剥夺了学生“学什么”的自由:不管愿意与否,所有教育者选定的知识,学生必须面对,而选定范围以外的知识,则被粗暴地排除在学生的视野之外;其次,对于课程知识的解释具有独断性的特征。“独断性解释”是一种客观主义的、一义化的解释,它否定理解的历史性和个人性,从而也扼杀了学习者的创造性。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提出“书写”的概念向这种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挑战。在他看来,“言说”主体在场的缺失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意义的确定性,故“言说”也从根本上失去了对“书写”的优越性。[12]在“游戏课程观”看来,课程文本不再是终极教学素材,不是金科玉律,而只是游戏的材料,游戏者可以面对这样的材料去“自由书写”。这是因为课程文本与特定时空、历史中的全体等相连并表现为一个开放的结构,从而召唤当下时空、当下历史中的游戏者“书写”文本中所没有的东西,创生新的共享意义。
课程作为一个系统,存在一种自组织的过程,特别是当教学过程从教导式转向自主式、对话式、探究式的游戏活动,教师、学生、文本之间就会发生碰撞,这不是一种对概念、命题或观念的认同,而是一个教师、学生与文本三者之间的一个饶有兴致的游戏过程,是对概念、命题和观念的主动消解、转化和升华的过程,是通过自主参与对话和探究活动而扩展自我实践、促进生命成长的方式。“游戏课程观”倡导课程的学习者不仅要能 “对所研究的材料有足够的理解,并有足够的信心既能解决、解释、分析和表达所呈现有材料,又能以富有想像力的和离奇的方式与那些材料游戏”。[13]这种自由游戏的过程也就是自由书写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当课程表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时,其丰富的多样性、疑问性和启发性以及“游戏”必然具有的结构“松散性”和“多余度”使得多种用途、解释和观点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才会发生。
(三)“游戏课程观”的目的——游戏过程
康德曾将游戏与劳动加以,认为劳动是为了获得劳动之外的结果,是被迫的;游戏是为了体验活动本身的乐趣,是自由的。同样的一个活动,如果有了功利性的“外在于”活动的目的,那它就不能称为游戏,而只能是一种劳动。很多研究游戏的文章都喜欢引用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孩子在院子里滚一个破铁桶,铁桶滚动的响声十分讨厌,吵得周围的人无法休息、工作。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是不听,而且兴趣非常浓。有位老人走了过去,悄悄告诉他,你干得不错,这次你滚一个来回我给你一元钱。孩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完成之后,老人果真给了他一元钱。然后又对他说,你再滚一次我给你五毛钱,孩子还是很高兴,没想到自己这么容易就得到了报酬。又玩了一次,老人给了他五毛钱。这次老人说:“我只有一毛钱了,你再玩一次就给你”,孩子听了有点不乐意,但想想还有一毛钱呢,勉强又重复了一次。最后老人说:“没钱了,你再玩一次好吗?”孩子兴趣全无地扔下铁桶走了。
故事中的老人很“高明”地把孩子的有趣的游戏转化成了让其厌烦的工作,它形象而生动地告诉我们:如果在教学中我们只让儿童去追求外在的名利或奖赏而不在乎过程的话,任何有趣的事情都会变得异常乏味。对于游戏来说,目的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游戏除了过程没有目的。游戏者只为自己游戏,不为外在于游戏的任何其它人游戏。当然,游戏往往都有观众(在场的或不在场的),但对于游戏者而言,游戏时眼中应没有观众,只有游戏本身。游戏的目的就是游戏。
“游戏课程观”认为课程的目的即在于过程。我们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的课程概念重建运动中看出对于改变传统的课程目的观的努力。作为该运动的始作俑者,皮纳在《课程理论化:概念重建主义者》一书中指出了美国现代主义课程所带来的诸多弊端,提出要根据“课程”这一概念的原意,并结合最新的哲学、心理学思想来对课程进行“概念重建”。皮纳认为,传统课程的误区在于曲解了课程的意思,必须根据“课程(curriculum)”这个概念的词源“currere”来重新界定课程。“Currere”的原意是“在跑道上奔跑(to run the racecourse)”,是一个动词,一种活动,一种旅行。而现代课程观则断章取义,只注重其同源词中的名词“racecourse”,而忽视了其最重要的本质“run”。[14]很显然,以“奔跑”为重点的课程的意思是强调游戏过程中的游戏而不是最终的游戏结果。只把课程作为教学过程之前和教学过程之外设定的目标、计划和预期结果,必然会导致把教育教学过程本身的非预期性因素排斥于课程之外。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之一是人是创造的主体。当特定的教学情境中教师和学生(游戏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这种教学的进程将是富有创造性的,其间也必然存在诸多非预期性因素,而正是这种非预期性因素才拥有无穷的教育价值。“游戏课程观”开始走出预期目标和计划的限制,关注教学进程本身的教育价值,强调“过程课程(currere)”。
(四)“游戏课程观”的内容——回归生活
与“理性人”理论和“制造人”理论关注理性世界、科学世界不同,“游戏人”理论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认为普通生活具有丰富的可描述性,所以它代表了对崇高理论、尤其是对企图进行概括的归纳理论的一次背叛。在这种理论观照下,足球场上和厨房里的事情同伊拉克战场上和白宫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具有同样的历史重要性。按照“游戏人”理论的理解,现代社会显然低估了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纵观20世纪,对课程内容选择起支配作用的是主要是科学世界,课程的改革主要也是为了适应科学世界的变化。唯科学主义因而成为支配 20世纪课程的主要价值观。受科学世界支配的课程体系越来越脱离生活世界。在“游戏课程观”看来,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课程观当然是极其错误的,他们不证自明地认为科学世界高于生活世界,认为科学知识高于其它知识。“游戏课程观”认为生活世界才是科学世界的基础,是科学世界的意义之源。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着生动而丰富的交往,这种交往是主体间的交往,是充满“人格主义态度”的交往。同时,休闲化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劳动已不再是人们的主要活动方式,甚至劳动本身也越来越休闲化:人们不再围着机器转,工作时间越来越灵活,甚至昔日的休闲活动如读报、上网等也成为劳动。社会的休闲化必然带来休闲文化的兴起。人们对日常生活将越来越关注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游戏课程的内容也必将回归生活,现实的生活世界就是“教育”与“游戏”最内在和本质的联结点,师生都在游戏中生活,理想的教学也就成为了“师生作为‘游戏的人’的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师生不再作为教学的主体,教学的主体成了教学本身,师生双方完全沉浸于当下的教学愉悦之境”,[15]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课程即游戏”才成为可能。
[1]吴航.教育与游戏——兼论教育的游戏性[D].华中师范大学,2001:71.
[2][英]伊丽莎白·劳伦斯.纪晓林译.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8.
[3][英]威廉·博伊德、埃德蒙·金.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9.
[4]任钟印.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42.
[5][德]福禄倍尔.孙祖复译.人的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4.
[6][美]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08.
[7][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冯至,范大烂译.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80.
[8][10][荷]胡伊青加.成穷译.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70,9-10.
[9]石中英.重塑教育知识中“人的形象”[J].教育研究,2002,(6):16.
[11][英]伯恩斯坦,论教育知识的分类和架构[A].[英]麦克·F·D·扬.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C].谢维和,朱旭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1-89.
[12]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87.
[13][美]多尔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4.
[14]张文军.后现代课程观初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4):12-13.
[15]刘铁芳.教学——一个可能的价值世界[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4):9.
王宜鹏/淮阴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夏如波/淮阴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和课程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