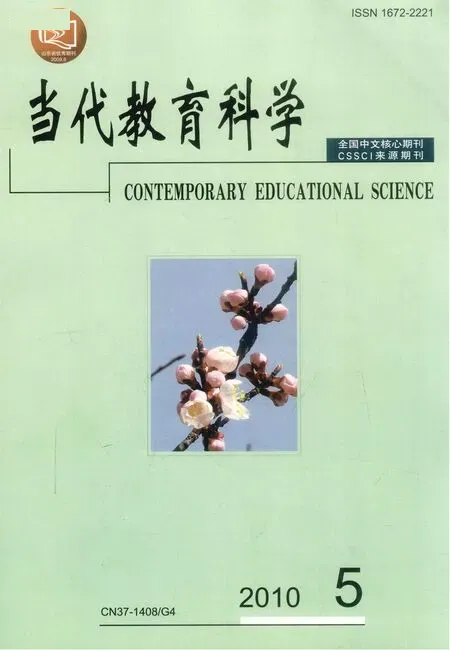解读“课程”:从既定的跑道到权力的竞技场
● 彭彩霞
现代西方很多学术用语,最初大抵是近代学者参照古拉丁语或古希腊语词根构建的新词,“课程”一词亦如此。 “课程”(curriculum),源于古拉丁语“currere”,意即“跑道”(racecourse),转义为“学习之道”。依据这个词源,最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或“学习的路线”(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既可以指一门学程,也可指学校提供的所有学程。但由“跑道”自然易衍生赛马(跑)者、跑、裁判、观众、终点等相关意象。课程的拉丁词源其具有的丰富意象为后世的解读者提供了充裕的空间。从将其阐释为名词形式的“跑道”,重在静态的、预设的轨“道”,到其动词形式“在跑道上跑”,重在动态的“跑”的过程与体验,再到认为是描绘了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竞相在课程中激动地争夺权力的图景,凸显课程的政治性格——侧重点各异的解读并非浅薄的文字游戏,其背后涵蕴的是不同的课程思想,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并捕捉了不同的时代主题。
本文梳理和勾勒了这一历史的转换与演进轨迹,希望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课程的涵义,从多维的视角审视课程的发展。
一、课程——既定的跑道
在西方,时至19世纪60年代初,课程(curriculum)一词才最先出现在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他所用的“curriculum”一词指向学科内容的“跑道”,强调课程作为静态的、外在于学习者的教育内容的系统组织。
1918年美国课程理论家博比特(F.Bobbitt)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书——《课程》,在此书中,他根据课程的拉丁词源“跑道”,解释课程是行为和经验的跑道,通过这一跑道,儿童变为他们应然的、能在成人社会获得成功的成人。
这些课程理论先驱的思想对于尔后的课程工作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课程的“跑道”观都处于未被挑战或难于撼动的地位。这一观念对于课程及课程发展的影响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首先,跑道的特点之一是:固定的和标准的。这导致了学校课程的缓慢发展。如克斯特 (Kirst)和沃克(Walker)所提到的,“很多世纪以来,欧洲的课程是固定的,以(中世纪)的三学科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边界。而且,最近的这300年来,西方学校的课程变化很缓慢……”
其二,“跑道”也意含着课程是按既定顺序行进的、可控的体系,有着清晰的起点、明确的终点,不可偏离和逃逸,是了解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有效捷径,交织着“强制”、“控制”、“规范”、“有序”、“效率”等语感。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后,这些语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最典型的阶段是在20世纪前期,工业领域追求“效率”和“唯科学主义”的潮流催生了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相应的 “教育效率增进运动”(the efficiency movement in education)和 “教育科学化运动”(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education),并很快推衍至课程领域。令人瞩目的博比特课程思想,尤其使“效率”“目标”等词成为美国课程思索中较为持久的论调。
第三,课程是学科内容的“跑道”,不同的学科也就有不同的“跑道”,由此,分门别立的“跑道”愈来愈多。这种分科设置适应了社会分工的需要,按照知识的纵向发展来编制课程,有利于各科知识的系统学习,强化了学科内部的逻辑组织,尤其是凸显了知识的内聚性、递进性,缩短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距离。但是,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曾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将科学划分为若干不同领域,这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其实,从物理学和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直到社会科学,这中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环节。”[1]分立的“跑道”导致了知识学习的孤立化,牺牲了知识的相关、融合和广域化,形成割裂学生理解力的“破碎课程”(Fragmented curriculum)。
二、课程——跑的过程与体验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课程的“跑道”观开始受到冲击与挑战,在经历60年代课程领域新旧范式的碰撞与转换时期之后,传统课程研究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正如课程史学家克利巴德(H.Kliebard)所指出的:“课程领域接下来 50年的工作必然是发展一些可供选择的方式,来取代已支配了前50年课程领域的思维模式和框架。”[2]如其所言,70年代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概念重建运动,矛头直指向博比特、泰勒以来的所谓主流课程理论,呼吁超越传统的课程发展和设计。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蕴涵,其频度、力度和强度之大,历史罕见。他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1],这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热潮。国内学术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何形成、为何必要、如何理解、何以实现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引向深入,需要在梳理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注重关键大国的态度、把握“五个世界”总路径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关系、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知行合一”问题。
作为当前课程领域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并作为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派纳认为,传统课程发展的问题是误解了“课程”的含义。“Currere”应是指“跑”(to run),在跑道上跑(running of the race),而不是指(racecourse)本身,课程因此是一个动词词组,一种活动——或者派纳所说的,一种内在的旅程;课程远不是静态的、预设或规定的,而是被“不可预料的、模糊的、复杂的、奇怪的、可疑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激发出来的。[3]
后现代课程理论者代表之一的斯拉特瑞亦批驳,“现代课程的基本原理已截去了‘课程’的‘跑’的意义,将它变为一个对象名词,跑道自身。因此,一代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被教导成相信:课程是一个有形的对象——我们所实施的教案或我们所遵循的课程指南——而不是在跑道上跑的过程。”他倡导转向学习的一种更积极的过程,“这一转向从未否定文本、材料、教案、考试和教室是重要的,只是它们不是课程的本质或教育的意图。”[4]
舒伯特(W.H.Schubert)也主张“跑道的含义,不应该被认为是必须遵循的预先确定的轨道;它可以比喻成有意识地发展的学习和成长的旅程。”[5]
从“跑道”到“在跑道上跑”,也即从“文本课程”转向“体验课程”,昭示着对课程理解的深刻转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
当课程的内涵等同于学科内容,等同于由教科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文本组成的、内容稳定不变的知识体系时,它就排斥了学习者现实的活生生的经验和体验,使它从作为学习者的发展资源而转变为规训和控制的工具,消解人的主体性,泯灭人的个性,这一愈演愈烈的态势也正是重建论者所声讨的。他们呼吁联系个人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来寻找课程的意义,珍视个体经验的独特性,课程因此是自我的“履历情境”(biographic situation),是主体性生活经验的改造、重组和建构。
根据舒伯特对课程重建立场的总结,对“跑”的关注,强调了课程是给个体提供持续的个人意义的过程,强调了个体参与和再概念化生活经验的能力,本质上,它表征着学习及至课程的一种经验观——课程是生活经验的解读。在当前的事件中寻找意义,回溯自我的历史,想象未来的可能方向,课程因此成为对生活的重新认知,同时,与其他同伴的经验分享,又使课程成为一个社会的过程,由此,个体达成对自身、他者和世界的更好理解。[6]
其二,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凸显课程的生成性。
其三,它有利于达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
课程强调“跑”的过程和体验,强调解脱固定目标的桎梏,也就有利于超越上施下效的纵向注输,营造平等对话、民主交往的师生关系。
多尔在其教育信条中表述了这种师生关系,“在教师与学生的反思性关系中,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求学生延缓对那一权威的不信任,与教师共同参与探究,探究那些学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教师同意帮助学生理解所给出建议的意义,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并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所获得的默契和理解。”[8]师生之间不再是知识的占有者和无知者之间的传递与接受的关系,教师的位置 “从外在于学生情境到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9]而加拿大的后现代教育学者史密斯也认为,新型的师生关系将是一种教师和学生之间互惠式而不是从前那种传授式和控制式逻辑衍生的教学关系。这是一种在师生一起跑步、共同建构经验、获得成长和意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系。
总之,强调“跑”的课程观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眼光,有益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课程目标、内容、评价等课程范畴的重要问题。当然,它也并非完美无缺,有其局限性,其本身也受到诸多理论学派的批判和质疑,仍需要时间来发展和完善。
三、课程——权力的竞技场
“课程来于拉丁词‘跑道’……但是,跑道这一词不能准确反映17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学校课程,而‘赛跑’倒能更为准确地描绘这三百年以来人们渐增的在课程中激动地争夺地位的图景。”[10]克斯特和沃克从另一视角诠释了课程的这一拉丁词根,而事实上这也代表了70年代以来课程领域部分学者的研究取向,即从政治视域中来审视课程,认为课程是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政治竞技场、是各权力团体争取自身知识合法化的角斗场,其间充满了矛盾与妥协,现行的课程政策和课程实践都是各权力团体间暂时力量平衡的结果。这一取向与知识社会学、课程社会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随着课程决策渐增的复杂性凸显,使课程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愈加质疑,其政治性开始受到很大关注。从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到阿普尔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则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这一历史变迁。但是,在70年代以前的课程视域中,根据克斯特和沃克的梳理,“专业的教育者在课程著述和研究中,很少意识到其主题的政治性。‘政策’、‘政治’和‘政治的’这些词甚至没有出现在这个领域任何主要教材的索引中。”[11]其指向的主要教材包括从40年代末泰勒的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50年代史密斯(Smith,B.0.)、斯坦利(Stanley,W.O)和肖尔斯(Shores,J.H.)合著的 《课程编制的基本原理》,60年代格温(Gwynn,0.M)的《课程原理与社会趋势》,塔巴 (Taba,H)的《课程发展:理论与实践》,谢勒 (Saylor,J.G)和亚历山大(Alexander,W.M.)的《现代学校的课程规划》等。这些作者将课程领域的冲突仅仅视为观点之间的分歧,而不是个体、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或学校体制内官僚的派系斗争;将国家、州、和地方的政治人物,以及家长、纳税人和其它对课程感兴趣的团体或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均视之为仅是课程决策上的“影响”,回避了谁在课程决策上的发言权、在什么阶段、在哪些方面等问题。
随着课程决策的复杂性逐渐可见,研究者认识到这一“科学”诉求的缺陷和无力,尤其在美国,课程决策的政治情境的复杂性变得更为明显。因为,对于课程,从国家评审委员会、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基金会、教材出版商到各种专业协会,人们都不再安分于作为比赛的观众,而是纷纷走进比赛场地,试图占据有利位置。其全国教育研究所的课程开发工作组(1976年)的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人们参与决策的热忱,使关于应该教什么和如何组织课程这些经典的课程问题都黯然失色。[12]课程必须满足“不同的族群、阶层和性别,保守派和自由派,老年人和青年人,穷人和富人,市区、郊区和农村利益。”[13]不同群体和个人所持的不同价值观和哲学,使课程决策变得棘手。由此,随着参与者名单的拉长,课程决策否决某项议案的阶段增多,分工更繁琐,过程更合法化,也就比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出某项决策。
在理论领域,作为当代美国批判教育学派主将的阿普尔的言论则使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成为课程研究的核心话语。除其鲜明的民主进步性和批判斗争性之外,强烈的政治取向是其思想的重要特征,在其1979年的代表作 《意识形态与课程》及随后的著述中,他揭示了课程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认为课程是主流阶层的权力、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现和象征,它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知识,是一种法定文化,现行政策和实践都是权力集团间斗争、妥协的产物,但是这种妥协只是暂时的,只要一有机会,社会各权力集团就会竭尽全力地使自己的知识合法化,保护自己的社会活动模式以及增强它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力量。
从政治学视域中研究课程,尽管面临一些危机,遭受到批判与争论,尤其是其观点的偏激性、过于用知识的主观性取代知识的相对客观性和真理性、某种泛政治化倾向等。但是,它将课程放回至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社会大语境中来探析,有利于从一种整体视角思考课程,有利于人们认识课程所蕴含的政治意蕴,其理论价值值得继续挖掘和研究。
结语
“课程”的一个简单的拉丁词根,却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在新的情境、从新的角度不断得到阐发,历久而弥新,这应是词根的始创者所未能预见的,而在未来的无数世纪里可能仍会持续我们当前所不能预知的诸多解读。这一演变轨迹标记了人们认识和理解课程的重要阶段,每一阶段对于课程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一过程记录了课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变迁,从工业科学管理理论到现象学、自传、解释学等,再到知识社会学、批判理论等,理论基础在不断充实和多元;其次,这也是逐渐在一个更开放的体系、更广泛的背景中来理解课程的过程,从强调学科内容、学习者再到考察课程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语境之间的关系;从关注课程的目标及其实现,到探析学习过程中个人发展的过程,再到课程与权力等的关系,即从透过课程表面所见的风平浪静到窥见下面翻动的暗涌,这是一个不断拓深的过程;同时,历史是由人来推动的,不同阶段的领军人物从斯宾塞、泰勒、博比特,到多尔、史密斯、斯拉特瑞,再到阿普尔,以其敏锐的思索或针锋相对的论争推进了这一过程。
[1]戈特等.科学知识整体化的基本方向、因素和手段[J].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软科学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H.Kliebard.Persistent issu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Educational Comment,1970,40.
[3]Pinar,W.F.Curriculum: Toward new identites[M].New York:Garland.1998,84.
[4]Slattery,P.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odern Era(2nd edition)[M].New York: Routledge/Taylor and Francis,2006,62.
[5][6]Schubert,W.H.Curriculum:Perspective,paradigm and possibility[M].New York: Macmillan.1986,6,33.
[7][8][9]Doll,W.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on Curriculum[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3,13.160.167.
[10][11]Kirst,M.W.,&Wallker,D.F.An analysis of curriculum policy-making[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971,41(5),479-509.
[12][13]Unruh,A.Unruh,G..Curriculum development:problems,processesand progress.Berkeley,California:McCutchan Publishing Corp[M].198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