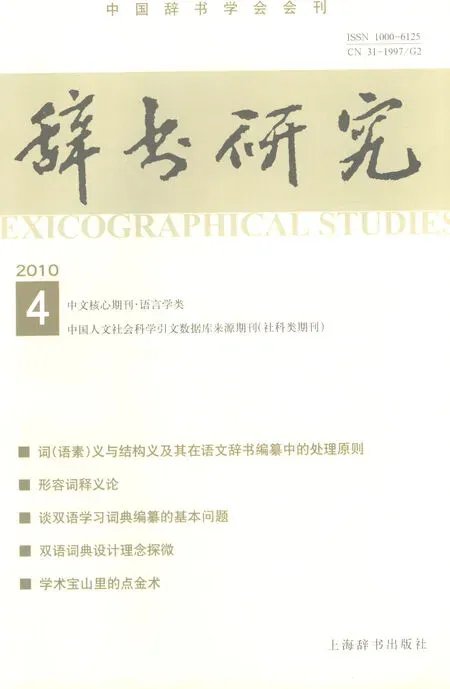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智初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00710)
2010年4月9日,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礼堂召开,会议议题为“辞书中的语言文字协调”。这次会议由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主办,商务印书馆承办。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主任、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王铁琨,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韩敬体、雷华、徐宗文、潘涛,全国科技名词委语言文字协调委员会主任董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等出席。来自28家出版社、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编辑、学者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一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着重介绍了全国名词委和国家语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像”和“象”的用法的研制过程。20世纪末,“像”和“象”的用法在科技界、辞书界、编辑界出现了比较大的混乱,全国名词委组织科技专家和语言学专家共同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操作上作了明确的界定,两家联合发布了“象”和“像”的用法的研讨结果。经过十来年的推广使用,现已比较规范和稳定,成为语言文字研究和协调的成功范例。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指出,语言文字中混乱和区分不清的情况是实际存在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不可能涵盖所有方面,辞书界、编辑界、科技界应该对容易出现混乱和区分不清的情况进行协调,取得共识,引导社会使用。比如:“堰塞湖”的“塞”怎么读?“嫦娥奔月”的“奔”怎么读?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李宇明建议,像这样的会议,要有纪要,会后可以通过政府向社会各界转发,这是我们规范化工作的重要途径。
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主任、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强调,语言文字规范,是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的冲突,是用理性原则来规范习性原则。应该既要尊重群众的约定俗成,又要进行必要的因势利导,引导语言的使用向规范和健康的方向发展。近些年来语言中出现了很多字母词,它的出现必然有它的合理因素,对于这样一些有利于语言发展和使用的现象,我们应该予以承认,并在使用中加以规范和引导。至于异形词,有些是冗余的,可以把它规范掉,有些异形词之间不是完全等同的关系,存在使用范围、感情色彩等非常细微的区别,我们不要过多地合并,那样会影响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二
开幕式后,会议进行大会主题报告。
全国科技名词委语言文字协调委员会课题组代表李志江向大会作了题为《“做”和“作”的使用》的主题报告。近几年来,课题组对“做”和“作”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学理分析,最后得出六条倾向性意见,分别为:1.“做”主要用于造句,“作”主要用于构词。2.首字是zuò的动宾词组,全用“做”。3.首字是zuò的双音节词,按习惯用法。4.末字是zuò的双音节词或三音节词语,全用“作”。5.成语或四字格等固定结构中有“做”或“作”的 ,按习惯用法。6.在用“做”、“作”两可的情况下,要做到局部一致。
“做”和“作”的分辨及其使用,是辞书界、出版界、教育界和广大读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学界、辞书界、出版界、教育界的问题。大家围绕着主题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董琨认为,“做”和“作”的区分不能搞得太复杂,要具有可操作性。江蓝生说,要区分这两个字是在句子的层面还是在词的层面,这有利于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歧义问题。徐祖友说,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去作界定,比如说“zuò戏”一词中的zuò一般用“做”,但是在“逢场作戏”里面用的是“作”,我们怎么协调,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假如一刀切,按照抽象和具体的标准,可以大体区分开来,但如果按照原来习惯的用法,尊重语言的习惯,这个标准是不是违背了简单化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雷华提出,如果按照是名词还是动名词的标准来判断,有一些可能区分起来更难,可能会引起内部的不协调,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江蓝生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建议把动名词作宾语这一标准吸纳进来,二是建议和台湾地区的辞书作一个比较,如果台湾地区的处理凡是抽象的都用“作”的话,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调整。这两个方案拿出来之后还应该开一次专家论证会,听取语言文字专家的意见。做决定不能草率,一旦草率地做了决定就更被动了。
有的代表提出在“做/作”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怎么区分这一问题。也有代表提出,从方言的角度考虑,南方人很容易通过方言对这两个字做出区分,而在北方方言中,这两个字的读音无任何区别,所以北方人无法通过方言区分二者;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个简单的便于操作的方法,凡是两个字后面的都用“作”,不用再考虑其他了?
在会议后半段,李志江作了关于《264组异形词整理表》的报告。报告首先提出《现代汉语词典》在对有些异形词的处理上不尽合理,建议在修订的时候进行调整,比如“菜子”与“菜籽”、“答理”与“搭理”、“得意扬扬”与“得意洋洋”等,这类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原来的主条应改作副条处理,原来的副条应改作主条处理。报告第二部分提出《264组异形词整理表》中需要商榷的异形词,要注意异形词取舍时的理据性、相关性,注意异形词分化的趋势,注意异形词规范与《规范汉字表》的关系以及异形词的界定。报告最后提出了需要讨论的几组异形词,如“拉拉队”与“啦啦队”,有人认为,lālāduì是用“呐喊”来给运动员助威的,因此用“啦啦队”更能使词义外现,不妨以“啦啦队”为推荐词形。此外还有“标志”与“标识”、“执著”与“执着”、“密室”与“秘室”等。
在对这一主题报告的讨论中,江蓝生指出,不是说异形词整理得越多,成绩就越大。异形词问题不是一对一错的问题,只有那些确实是冗余的东西,我们才能去整理,不太成熟的,可以等一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去整理它。董琨强调,异形词整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个绝对错,那个绝对正确。晁继周还专门介绍了自己对“执着”与“执著”的思考,他认为在这一对异形词中,应该推荐“执着”的写法。
王铁琨对上午的会议进行总结。认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大家的讨论也是非常务实和深入的,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肯定。其次是此次讨论的这些问题,反映出语言文字的复杂性,有很多不是标准和规范能解决的,但辞书的规范又非常必要,因为辞书对读者来说是有引导性和方向性的,所以要做好出版社之间的协调工作。最后建议,会上的讨论可以由中国辞书学会和其他民间团体发布,等将来成熟了再由有关机构正式发布。
下午,与会代表对主题报告的内容继续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结束前,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辑专业委员会根据民主协商的原则进行了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周洪波继任主任委员,陈崎、顾青、亢世勇、李尔钢、刘玲、马汝军、彭东林、王祝英任副主任委员,委员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