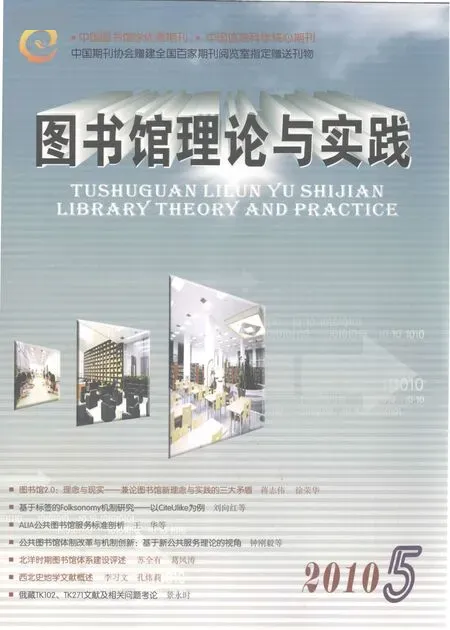《吕氏春秋》明宋邦乂刻本辨识
●杨居让(陕西省图书馆,西安 710061)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韦令其门客编著,《四库全书》著录为吕不韦撰。《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录《吕氏春秋》不著撰者,自元至清,包括同一刻本的不同批校题跋者在内,共计48种。其中元刻本5种,明刻本34种,清刻本7种,清稿本2种。在34种明刻本中,宋邦乂刻本有4种。《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只对宋邦乂刻本中的第一种,著录了行款和版式,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收藏单位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18家单位。其余3种,未著录行款、版式,应为同一版本、不同的批校题跋者。该版本笔者未见,笔者所见的其他几种版本:《四部丛刊》初编本所选《吕氏春秋》宋邦乂刻本、2008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选本,以及笔者在2009年古籍普查中,所见到的陕西李先生私藏宋邦乂刻本,比较之下,发现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些情况表明,《吕氏春秋》明宋邦乂刻本存在一些未明之处,笔者对这几种刻本进行了详细查检比对,将其不同之处客观叙述并试图澄清,以求教于方家。
1 不同的宋邦乂刻本
《吕氏春秋》明宋邦乂刻本,至少有3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为了便于说明,现将各种刻本情况分述如下。
第一种刻本:2008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选《吕氏春秋》宋邦乂刻本(以下简称“《图录》选本”)。此刻本收藏单位是,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图录》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汉)高诱注,明宋邦乂等刻本。框高29厘米,宽19.5厘米。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1]卷端校订者题名“明云间宋邦乂、男宋启明校”。此刻本应着重注意的是,版框尺寸和校订者题名。
第二种刻本:《四部丛刊》所选之涵芬楼藏《吕氏春秋》宋邦乂刻本(以下简称“《四部丛刊》选本”)。此本“原书板框高营造尺六寸二分,宽四寸六分”。[2]按营造尺计算,一寸等于3.2厘米,版框应为高21.2厘米,宽18.8厘米(整版宽度)。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每卷卷端校订者题:“云间宋邦乂、张邦莹、徐益孙、何玉畏校”;而在卷五、卷八题:“云间宋邦乂、范廷启、徐益孙、何玉畏校”;在卷七、卷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六题:“云间宋邦乂、范廷启、徐益孙、张邦莹校”;在卷九、卷十五、卷二十一、卷二十三题:“云间宋邦乂、范廷启、张邦莹、何玉畏校”。此刻本应着重注意的是,卷端校订者有“何玉畏”、诸多卷端校订者不同、版框尺寸与“《图录》选本”差别较大。
第三种刻本:陕西李先生收藏的《吕氏春秋》宋邦乂刻本(以下简称“李先生藏本”)。此本版框高19.2厘米,宽14.5厘米。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所有卷端校订者题名与“《四部丛刊》选本”同,只是《四部丛刊》选本校订者中的“何玉畏”在此全都变成了“何三畏”。此刻本应着重注意的是,校订者“何玉畏”变成了“何三畏”。
另外还有一种刻本,即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所记《吕氏春秋》宋邦乂本。此本与杜信孚先生《明代版刻综录》选本相同。[3]因此刻本的校订者著录“明云间宋邦乂、男宋启明校”,类归于《图录》选本以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所载,在此不单列。且王利器先生在《吕氏春秋注疏》中注释宋邦乂此刻本时,引用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云:“《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明刊本,高诱《训解》,明云间宋邦乂、男宋启明校。前有琅邪王世贞撰《序》,又华亭宋启明重刻《序》及高诱原《序》。”[4]王利器先生认为:“宋邦乂原有是刻,范廷启、徐益孙、何玉畏同校。此皆删去,仅列男宋启明一名耳。”[4]按王利器先生此说,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所记《吕氏春秋》宋邦乂本,应是“《四部丛刊》选本”的重修本。
2 宋邦乂刻本的相同与不同
将以上客观信息进行比对得知,宋邦乂《吕氏春秋》3种版本存在着相同与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一样,行款版式均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但3种版本也存在着不同。不同之一是,版框尺寸相差悬殊;不同之二是,校订者不一样;不同之三是书中的其他细节有差异。差异一,“《四部丛刊》选本”,只有高诱原《吕氏春秋序》;而“李先生藏本”,除高诱原《吕氏春秋序》外,还有琅邪王世贞撰、云间莫是龙书《重刻吕氏春秋序》和方孝孺《读吕氏春秋》序。差异二,“《四部丛刊》选本”,在高诱原《吕氏春秋序》的第二页书口下方有“长洲张楩刻”;而“李先生藏本”,在琅邪王世贞撰、云间莫是龙书《重刻吕氏春秋序》的第一页、高诱原《吕氏春秋序》的第二页版心下方,均有“长洲张楩刻”。对于张楩其人,《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记载:“张楩或署张便,明嘉靖间长洲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春秋四传》(吉澄本)。万历间参加刻过《文心雕龙》《史通》(皆猗兰堂本)、《欣赏编》(文霞阁本)”。[5]差异三,在“李先生藏本”中,琅邪王世贞撰、云间莫是龙书《重刻吕氏春秋序》后,有两方镌刻印章:“王氏元美”“弇州山叟”,在第二十六卷卷末有“宋邦乂印”小方镌刻印章;“《四部丛刊》选本”“《图录》选本”却没有。
3 宋邦乂刻本不同情况分析
上述情况和客观信息说明,宋邦乂《吕氏春秋》3种版本很可能是同一刻本,因为3种版本的行款版式完全相同。但各版本的不同点也说明其复杂纷繁,让人眼花缭乱。要弄清楚这些不同情况形成的原因,必须从各自的不同点入手。第一个不同是,版框尺寸大小不一,特别是“《图录》选本”。“《图录》选本”框高29厘米,宽19.5厘米;“《四部丛刊》选本”版框高21.2厘米,宽18.8厘米(应该是整版宽度);“李先生藏本”框高19.2厘米,宽14.5厘米。我们知道,古籍版框尺寸大小,直接决定着行格款式变化。而出现版框尺寸大小不同的最可能的原因是,是否选择了同一版面,以及虽是同一版面但内框、外框选择是否同一。如果考虑到上述版框尺寸所取不同的页面以及内、外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四部丛刊》选本”与“李先生藏本”,版框尺寸,差别不大。但“《图录》选本”,则相差甚远。也就是说,若以版框尺寸来判断,“《图录》选本”肯定是另一刻本。但仔细观察比对“《图录》选本”、书影与“《四部丛刊》选本”以及“李先生藏本”,结果发现:这3种版本的行款、版式、字体风格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字体风格、版式,特别是行格款式完全一样,而版框尺寸相差悬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认为“《图录》选本”版框尺寸著录可能有误,而不是不同刻本。第二个不同是,卷端校订者题名,以及序和镌刻印章。将3种刻本不同之处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3种刻本的不同点,都出现在卷端校订者题名以及序和镌刻印章上。“《图录》选本”卷端校订者题名为“明云间宋邦乂、男宋启明校”;而“《四部丛刊》选本”卷端校订者题名为:“云间宋邦乂、张邦莹、徐益孙、何玉畏校”;“李先生藏本”卷端校订者题名为:“明云间宋邦乂、张邦莹、徐益孙、何三畏校”。另外是如前所述,各刻本存在序文多少和有无镌刻印章之不同。这些地方和内容所出现的差异,是重修本最方便、最容易实施的地方,也是重修本的重修范围。《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对“重修本”的定义是:“保持原书正文,仅增补或改动原书附录。若同时修补更换原书残损模糊的版片,仍属重修”。[6]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白,《吕氏春秋》明宋邦乂刻本,不存在诸多刻本的情况,但存在着重修本的问题。既然是重修,弄清楚哪一种是原刻本,哪一种是重修本,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4 原刻本和重修本之辨
一般说来,原版初刻,镌印上版,增辉传播,这是文人酷爱文化的典籍确证,也是原刻本的重要特征。作为原版初刻,为了彰显知名的写序大家和表明版权所有,除了将牌记和封面作为署名标识处以外,刊刻者还常常将作序者的名字和校刊者自己的名字,以印章形式镌刻上版,或在序后,或在卷末,以传扬功业。
如前所述,“李先生藏本”,在书前琅邪王世贞撰、云间莫是龙书《重刻吕氏春秋序》之落款处,镌刻有两方印章“王氏元美”“弇州山叟”,这是在作“序”者之后;在第二十六卷卷末镌刻有“宋邦乂印”,这是在卷末。“王氏元美”“弇州山叟”,均是王世贞的藏书印章。王世贞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好为古诗文。始与李攀龙主文坛,以复古号召一世。攀龙死,独主文坛二十余年,操文章之柄。而宋邦乂是此书之校刊者。这两处镌刻着两人的印章,是“李先生藏本”作为原刻本的第一个依据。
第二个依据是,“李先生藏本”和“《四部丛刊》选本”的校订者中,“何三畏”与“何玉畏”的一字之差,也显露出了原刻本和重修本的端倪。“李先生藏本”卷端题名的最后一位校订者是“何三畏”,“《四部丛刊》选本”卷端题名的最后一位校订者是“何玉畏”。关于“何玉畏”,王利器先生在《吕氏春秋注疏》中引用《天禄琳琅书目·后集》著录《四部丛刊》选本云:“玉畏字士柳,华亭人,万历壬午举人,官绍兴府推官。余无考。”[4]除此之外,史无记载。也就是说,“何玉畏”仅出现在“《四部丛刊》选本”卷端校订者题名处。关于何三畏,瞿冕良先生在《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云:“何三畏,明隆庆间松江华亭人,字士柳,曾任绍兴府推官。有《欶六斋集》。万历间刻印过自撰《新刻何氏类镕》三十五卷,又《何氏芝园集》 二十五卷。”[5]
将这两条资料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天禄琳琅书目·后集》所注的万历朝的“何玉畏”很可能就是瞿冕良先生所说的隆庆朝的“何三畏”,即同一人。只是将“三”字误刻为“玉”字。
需要纠正的是:何三畏,其字为“士抑”,而不是“士柳”;何三畏不只经历隆庆、万历两朝。
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何三畏刻自撰《新刻何氏类镕》三十五卷(中国科学图书馆收藏此版本),其卷端著者题名是,“皇明云间何三畏士抑父撰”。在此书卷前胡继升所写的序中有:“士抑以七十岁作《类镕》。”[7]在《新刻何氏类镕》其他几个序文中,陈继儒及何三畏的门人,均称何三畏为何士抑。因此,何三畏字为“士抑”而不是“士柳”。又因为《类镕》刊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根据胡继升在该刻本序中所说“士抑以七十岁作《类镕》”推算,何三畏大概出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天启四年(1624年)何三畏又刻印过自己纂修的《云间志略》二十四卷,《志余》一卷。显然,何三畏至少经历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与王世贞(1526—1590)为同一时期人。
何三畏的资料详细确凿,其真实程度应该确信无疑。反过来说,“何玉畏”却有重修版时刻字错讹、造成张冠李戴之嫌。这是因为,原刻本的刊刻者,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印错误。而重修本重修时,或因时过境迁,对校订者不熟悉不了解,出错也就难免了。因此说,“李先生藏本”,因其卷端校订者题名有何三畏,应为原刻本。“《四部丛刊》选本”则为依之重修本,重修时,有可能将何三畏误刻成“何玉畏”。
第三个依据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何三畏刻印的《新刻何氏类镕》三十五卷,与《吕氏春秋》选本,字体风格一样。而所有《吕氏春秋》宋邦乂等刻本,字体风格、行款版式完全一致。这条附加佐证说明,署“何三畏”校订者的《吕氏春秋》宋邦乂等刻本,和《新刻何氏类镕》刻本,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何三畏之手。也就是说,署“何三畏”校订者的《吕氏春秋》宋邦乂等刻本,是原刻本。
综上所述,虽然《吕氏春秋》明宋邦乂刻本,复杂多样,存在许多差异。但经过笔者仔细查检比对和分析研究,澄清了其版本差异原委,理清了头绪:陕西李先生收藏的明宋邦乂刻本是原刻本,《四部丛刊》所选涵芬楼藏宋邦乂刻本为依之重修。《图录》所选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藏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所记《吕氏春秋》宋邦乂本、杜信孚先生《明代版刻综录》选本,应同为《四部丛刊》涵芬楼藏宋邦乂刻本之重修本。
[1]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O].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75.
[2]吕氏春秋[M]//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3]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4]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M].成都:巴蜀书社,2002.
[5]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K].济南:齐鲁书社,1999:309.
[6]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撰小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S].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胡继升.何氏类镕叙[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