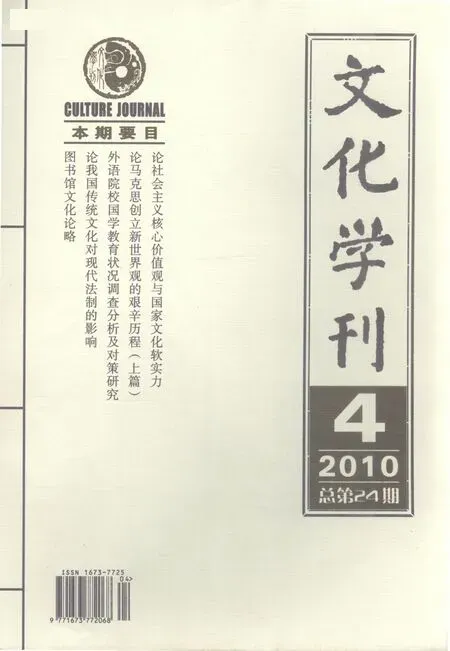这里有个小山村
王充闾
一
一阵清脆的鸟啼,把我从梦中唤醒,揉了揉眼睛,一时竟忘记了身在何处。这时,表针刚好指向六点。
推开窗扇,几棵高大的芒果树立刻把遮天的浓绿罩在了我的眼前,上面有几只鸽子般大小,却是花脖彩尾的大鸟,在悦耳地欢叫着,像是相互对歌,又像是呼唤着远方来客。一些在屋脊上、草坪上、卵石小径上啄食、跳跃的山雀自是不甘寂寞,也在那里“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
山村,醒了。
我信步徜徉在村路上,无论把目光扫视到哪里,都会有鲜花映眼。许多院落里盛开着大丽花、芍药花、月季花。还有一些花木我不认识,很遗憾,没有办法记下它们的名字。比如,眼前这株几丈高的大树,漂亮至极,整个树冠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像是我国南方的木棉,可是,木棉是先花后叶,花朵洒洒落落,而这棵树却是花团锦簇,宛如火炬、赤霞,真正称得上是“枝头春意闹”了。当然,“春意”也并不确切,因为此时这里正是道道地地的冬天。
村民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有的穿着长布袍,有的披着深色的沙丽,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赭红的脸膛,深陷的目睛上闪现着宁静的、友善的神色。小学生穿民族服装的倒不多,大都是一身袄裤,戴着有遮檐的便帽,背上双挎着书包,完全是城里孩子的打扮,想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这个名叫桑地尼克坦的小山村,“世外桃源”一般,静处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鸟去鸟来山色里,人哭人歌水声中”,千百年来,寂然无闻。只是由于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在这里定居过,才使它声噪全球,名垂典籍。1861年,诗人出生于加尔各答,1901年迁居到这里,以此为分界线,前后恰好都是40年。就是说,诗人的一半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过去,我就常常设问:那个桑地尼克坦是个怎样的所在呢?为什么竟有那么大的魅力,吸引诗人与它相伴了那么多年?
二
中国作家访问团昨天晚上抵达这里。从加尔各答乘火车,走了四个多小时,在博尔普尔站停下。——啊,这里插上一节,泰戈尔当年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我们抵达博尔普尔时,已是黄昏时分。我坐进轿子,眼就闭上了。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象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前。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破坏。”此刻,我的心情也正是这样。时间都是在冬季,不同的是,我们进村是乘坐轿车,而在130多年前,他坐的是轿子。那一年他的父亲曾有喜马拉雅山之行,12岁的小泰戈尔,跟随着父亲,在这里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快活的几天。
诗人的童年时代,是在加尔各答的老宅里度过的。负责照管他的仆人,为着自己可以四处闲逛,把他圈在一个大屋子里。仆人用粉笔在他的周围画了一个圈儿,然后以恐吓的口吻警告说,如果随便走出去,就会惹来可怕的灾祸。小泰戈尔早就听说过《罗摩衍那》中的故事,熟知女主人悉多越过圆圈之后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因此,他就整天坐在原地不动,不敢越雷池一步。
来到这个小山村,他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大了,身心彻底解放了,一时福至心灵,竟然趴在一棵小枣树下,在笔记本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剧。回去以后,他还想象着要变成一朵金色的小花,与大自然结为奇特的伙伴,想象着“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去寻找我前生的爱”。甚至在一首诗中,直呼桑地尼克坦为他“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
漫步在山村的小路上,我想到印度的诗翁泰戈尔与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诞生于19世纪的世界一流的伟大作家;都出生于名门望族,家庭里都出了几位文学家、艺术家;本人都享有80岁以上的高寿;特别是他们都曾长期居住在寂静的乡村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当时,我记起了一句清人的诗:“万花如海一身藏。”托翁如此,泰翁更是这样。
“藏身”原有二义,这里应作安身解释,而不应理解为藏锋、避世。20世纪第一年,泰戈尔是为了进行一项伟大的尝试而前来桑地尼克坦的。他痛感于英国殖民奴役下的人民觉悟亟待提高,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移植到印度国土上的那种机械死板、毫无生气的教育方式亟须改革。为了要在新的世纪伊始探索一条培育人才的新的途径,他想创办一所由自己直接管理的学校。他认为,这所学校和自己的定居地必须选择一个安静、幽雅的环境,而且必须贴近大自然。这样,诗人就选定了桑地尼克坦——这个童年曾为之无限神往的地方。
自幼,泰戈尔就热爱神奇的大自然,习惯于过简朴的生活,他也希望子弟在这样理想的学园中健康成长。他设想把古代教育环境和现代教育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古代印度哲人在森林中静修的理想画面,一直浮现在诗人的脑海中:在乔木参天、幽深静穆的环境中,那些哲人智者教育他们的门徒,在简朴的生活条件下,培植崇高的理想和精深的学识。印度的传统经典著作《奥义书》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形成文字的。
三
吃过早饭,我们就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了这所以泰戈尔的名字命名的驰誉世界的国际大学。校园环境幽雅、宁静,而又十分宽阔,一条乡村的土路把它同居民住宅隔开。1901年学校创办之时,只有包括泰戈尔的长子在内的5个学生和5名教师,今天,已经扩展到十几个院系,拥有来自26个国家的5000名学生和620位教师。
这座学校经历了20世纪的全部历程,即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但据校方介绍,它在办学思想、教学方式上,基本上还是坚持当日泰翁确定的原则,没有多少改变。上课时,师生仍然像当年一样,团团围坐在大树之下。我们走在广阔的草坪上,看到许多师生坐在亭亭如盖的大树下面,热烈地研习课业,讨论问题。学生穿戴朴素,有一些还打着赤脚,然而,心态却是健康、活泼的。学校负责人介绍说,这种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环境,有助于学生接受纯洁、清新的心灵陶冶,在感受世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激发出好奇心、想象力,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
从1902年到1907年,死神似乎一直住在泰戈尔的家里,短短5年间,夺走了他的4个亲人,他温暖的爱巢已经被冲击得摇摇欲坠。先是相伴二十余年的爱妻撒手尘寰,使他经历了“中年丧偶”的苦境;9个月后,13岁的二女儿又凄然惨别人世;尔后,病魔又吞噬了他敬爱的父亲;紧接着,最小的儿子死于霍乱,也只有13岁。悲痛与枯寂愈发加重了诗人的沉郁和苦闷,但也深刻地启悟了伟大的诗人,使他透过死亡的阴影,更加体味到爱之深沉,生之可贵,因而,格外地热爱蓝天、大地,珍视广阔而绚丽的生活。特别是,从聚集到桑地尼克坦的天真无邪的青少年身上,他似乎找到了亲子之爱的快乐与真情,他从那些清纯似水的童稚心灵中得到了慰藉,汲取了力量,从而逐渐平复了心中的创痛。
素有“世界公民”之美誉的泰戈尔,一向主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要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他曾把一行古老的梵文诗选作座右铭:“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坚信人类的思想是通过一种深奥的媒介联系着的,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变革必然会影响到另一方面。他通过多维的视野,努力探寻着印度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多层次联系,希望在各民族之间架设起金色的桥梁。而泰戈尔国际大学的创建,正是这种伟大设想的成功实践。
到19世纪末,泰戈尔即已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取得了早期创作的辉煌成果。但是,作为伟大的诗人,一生中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诸如对于自然、生命、艺术与宗教的深入思索,则是在移居桑地尼克坦之后日益走向成熟的。他的几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期间相继问世。特别是《戈拉》,评论界把它比之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说它同样深刻分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及其复杂矛盾,因而在印度文学史上成为光辉的史诗。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举世闻名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所追求的深邃、神秘的“梵我一体”的理想境界,所表现的和谐、安宁的美好气氛,以及“天然去雕饰”的清淳的艺术风格,使得蜗居尘壤之中,深为生存烦扰、都市喧哗、商品化的人际关系所苦的现实世界的人们,有一种清风拂面、如饮醇醪的解脱感和舒适感。这一时期,泰戈尔的重要诗集《园丁集》、《新月集》也都相继面世。如果说,前者是爱的颂歌,那么,后者则是诗人献给孩子们的深情的小夜曲。而格言诗集《飞鸟集》,则是诗人情感顿悟时迸射出的点点火花,在这里,诗人通过他的灵心慧眼,从大自然那些表面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中发掘出深邃的意蕴,并且采用喻义、象征的手法,以形形色色的客体对象生动、形象地喻示了主体意识,从而收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
四
对我们中国作家来说,泰戈尔国际大学最具吸引力的还是它的中国学院。这是一幢掩映于花光树影之间的米黄色的两层楼房。楼内陈设着一些红木雕花家具,还有许多古瓷、字画和匾额,使人一眼就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国的特色。
中国作家的来访,给师生们带来了节日般的欢快。他们满怀着亲切而自豪的神情,导引我们参观了楼上的图书馆,这里的二十几个书架,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五列,里面按照类书、经籍、史书、佛典、诗文专著等内容,陈列着十分丰富的线装中国典籍,巡行其间,一股淡淡的纸香扑鼻而来。他们告诉客人,这些典籍是上世纪40年代初从中国运过来的,一直完好无损地珍藏在这里。尔后,他们又带领我们参观了陈列中国现、当代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名著和学术著作的书房。座谈中,我们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国学院的师生都能用中文会话,尽管有的讲得还不够熟练,但在我们听起来,还是感到亲切异常。出访十多天来,除了在中国大使馆,就是在这里听到了异国乡音。临别时,师生们热情地同我们合影留念,并且主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大家完全沉浸在浓郁的友情之中。
像泰翁这样,在自己国家里专门建立一座学院来研究中国,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足见其对中国的前途、命运的关注之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深,向往之殷了。1924年,他曾访问过中国,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等七八个大城市,做过数十次演讲。后来,亲自主持建立了中国学院,并在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著名演说。
他对中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在20岁时,他就曾对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此毒害人民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日本侵略中国,他不顾年老体衰,以电报、信件、演讲和诗歌等各种形式进行声讨。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抗战,他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资助战。在生命垂危时,他还口述了一首诗,追忆他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称中国是“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那里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五
告别了中国学院,我们又来到坐落在校园对面的泰戈尔纪念馆。一条穿过椰林和乔木的林阴大道,把游人引向一组欧式的建筑群,纪念馆设在一座两层的楼房里。一楼以大量的照片和实物,展示了诗人八十载的壮丽人生;二楼为诗人作品展览和图书馆。旁边还有一座四层楼房,为诗人的故居。
展览内容颇为丰富,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泰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他热爱中国,中国也同样尊崇和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照片中展现了他在访问中国时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场面。从展览中得知,泰翁挚友徐悲鸿访问国际大学时,曾为诗人画过肖像,并留赠了两幅奔马的国画。其中一幅题了杜甫的诗句:“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分明是诗人的真实写照。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周恩来总理于1957年访问印度时,不辞旅途辛苦,在百忙中,专程赶到桑地尼克坦,瞻仰泰戈尔的故居,参观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并和师生们一起歌舞联欢,临别时在纪念馆题词,给予泰戈尔崇高的评价。其实,一年前,周总理就曾真诚地赞扬过:“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这番话切切实实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1961年泰翁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泰翁的作品选入了中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即将离开桑地尼克坦了,我满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感受着诗人的遗爱,心中时时涌荡着一种深沉的崇敬之情。在这里,古榕是随处可见的,这是泰戈尔诗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他曾在诗中深情地写道:
呵,大树,人类的手足,
我向你走来。
作为人类的使者,
——受到你的精神的激励,享受过你的浓荫的凉意——得到了你的力量的鼓舞。……
想做风,
吹过你的萧萧的树杈;
想做你的影子,
在水面上随阳光俱长;
想做一只鸟儿,
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
此刻,面对着这一株株参天拔地、郁郁森森的大榕树,我却想到了我们心仪已久的泰翁。那有着蓬勃、持久的生命力,枝条牵连交错、气根丝丝下垂的银榕,多么像鹤发飘逸、银须冉冉的长寿诗翁啊!你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呀,泰翁!你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中。
再见了,桑地尼克坦,这静美的小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