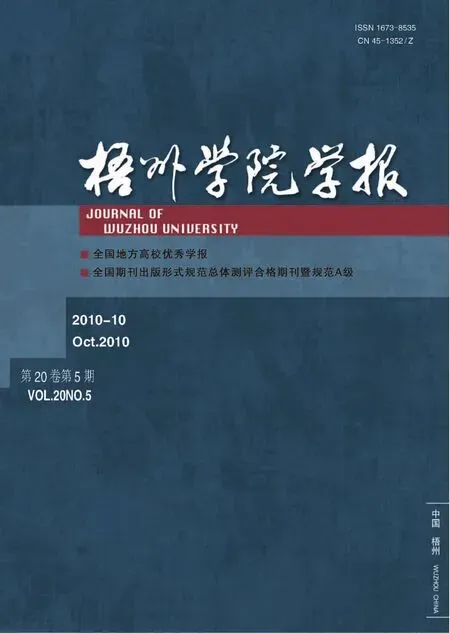也谈散文诗的可能性——不仅仅只是与余光中前辈的偏见商榷
林美茂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10000)
也谈散文诗的可能性
——不仅仅只是与余光中前辈的偏见商榷
林美茂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10000)
余光中先生认为散文诗属于一种 “非驴非马”般的存在,这种观点几十年来成为许多人对于散文诗偏见的代名词。通过对中国和日本文学界存在的几种正面肯定散文诗的观点以及散文诗产生与发展历史的考察,分析回应了余先生的偏颇以及这种言论产生的背景,指出这种文体不仅属于诗歌文学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更进一步展望了散文诗由于其美学特质超越了简单的自由诗与散文的结合,必将发展成为聚各种文学、艺术的表现精华于一身,具有立体审美可能性的 “大诗歌”文学。
非驴非马;散文诗;独立文体;立体审美;大诗歌
“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 ‘散文诗’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往往,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1]157
这是余光中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散文诗所表达的观点。之所以笔者要在今天重提这个观点,原因有二:一是时间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在今天的大陆文学界,一谈到散文诗,仍然有不少人以 “非驴非马”来界说它的文体特征,余光中先生的肤浅和偏见至今阴魂未散;二是从近几年中国的散文诗创作现状来看,许多作品的美学与思想高度已经向新诗趋近,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散文诗的美学特质越来越明显,谁也无法否定它与新诗、散文并存发展了。是时候了,散文诗可以理直气壮地矫正余光中先生曾经的偏执与轻狂了。
不管当时余先生出此言论时台湾文坛的现实背景如何,我们仍然可以说不知道是谁给予了这位诗人这种权利,可以如此狂妄地认为散文诗不值得存在,其言辞达到了对于散文诗的存在几近侮辱的程度。正如玉米不能说水稻长得矮小,南瓜不能嘲笑红薯不够肥大一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学名:庄稼。它们都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其不同只是味道相异而已。新诗作为现代汉诗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秉承了古典汉语文学中骈赋诗词等韵文学的一条支脉向现代延伸。而散文诗同样属于中国古典韵文学向现代汉诗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条矿脉,其存在的独立性早已有许多文论家述及,它的存在与新诗一起构成现代汉诗的左右两翼,只有这样才能让现代汉诗展翅,实现中国韵文学从古典向现代健全地滑翔着陆,怎能说 “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呢?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余光中先生的这段轻言,谈一谈散文诗的存在理由以及其作为一种文体所蕴含的巨大发展可能性。
一、无论散文诗是什么,它的存在无法否定
从中国的新诗与散文诗的诞生来看,它们几乎同时出现,第一本新诗 《尝试集》 (1920年)和第一本散文诗集 《野草》 (1927年)的出版时期前后相距不到十年。更不用说 《野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一部不朽的名著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当然,究竟散文诗是一种怎样的文体至今尚无法给予明确的定论,而对于新诗不也是如此吗?除了在形式上采用分行写作,在语言上主要运用意象的表现技巧、情感节奏的紧凑简洁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多的关于新诗的特点吗?这一点余光中先生在他的上述那篇文章中似乎也同样遭遇到新诗无法明确界定的问题。所以,他除了以 “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1]来强调新诗的优越性之外,也无法更多地为其所推崇的现代诗进行自身优越性的炫耀。
笔者相信至今为止还无人敢说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比其 《恶之花》逊色。也没有人说过泰戈尔的 《吉檀迦利》比不上他的其他诗歌作品 (当然诺贝尔奖只是把这部作品当作诗集颁奖,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散文诗集来读,其分行形式和对节奏的把握已经超越了一般我们所熟悉的自由诗)。而圣琼佩斯、纪伯伦、屠格涅夫、鲁迅和萩原溯太郎等大师所留下的散文诗名著,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在中外文学界被广泛运用,并留下了宝贵的创作遗产,这些是谁也无法否定的。纵观中外文学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诗人年轻的时候,一开始写过散文诗,后来才放弃了这种文体转向只写新诗。而有的文学大师却是在其艺术技巧和思想深度达到极其圆熟的时候才写开始散文诗。这种现象究其原因,应该是这种文体难以驾驭的缘故,因为它对作者的学识、修养、审美境界、人生境界等要求都极高。[2]
对于散文诗的难写,自从这个文体被引进中国以来就被人们论及。到了20世纪70年代,林以亮先生也在 《论散文诗》的文章中谈到: “散文诗是一种极难应用到恰到好处的形式,要写好散文诗,非要自己先是一个一流的诗人或散文家,或二者都是不可”。所以他认为: “散文诗并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尝试”,并进一步强调: “写散文诗时,几乎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内在的需要才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写诗或写不好散文,才采取这种取巧的办法”。[3]当然,笔者引用这个观点,并没有狂妄自大到认为写散文诗的人都是一流的诗人或散文家,只是想指出一点,散文诗绝非一种可以轻视的文体,那是写作者 “几乎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内在的需要才这么做”的文体,所以,王光明先生认为: “散文诗绝不是为了自由解放而自由解放的,是诗的内容就不该为了追求自由而写成散文诗-诗不应该有这种毁灭性……所以散文诗不是诗意的散文,也不是散文化的诗,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个完整特殊的性格”。[4]
从笔者多年来的散文诗创作经验以及一些散文诗作者的创作经验出发,大家一般都会对上述的这些评论家精辟的观点产生共鸣。散文诗写作者之所以写散文诗,那是来自于自己生命律动的本能需要,需要通过这种文体才足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推演到极致。如果用新诗来表现,会感到其不能完全地触及到自己生命的底色,不能淋漓尽致地敞开自己,完成自己的生命绽放。当然这只是从笔者个人以及一些散文诗写作者的创作感受而言,绝非含有否定新诗的意义。
二、散文诗与新诗在表现特征上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来说,新诗是一种可以隐藏的艺术,通过意象之间的组合、跳跃、张力等作用,把一些应该表现的东西为了追求精炼而隐藏起来,让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去完成。这是新诗的长处,然而也是它一种软肋,因为这样容易造成一些本来并不具备一流素质的诗人,在表面上看来却好像是那么一回事,而其自身究竟在写什么根本就不明确,甚至不知道,许多思想只是后来的评论家们过度阐释所赋予的。而散文诗则不同,它像一面镜子,可以让作者的学识、修养、审美高度、思想深度,以及情感的起伏、节奏的舒缓、内在韵律的颤动一览无余。好的散文诗作者自己在写什么,要写什么,其中的思想、情感、审美、场景与意象的指向极其明确,不然根本无法自然而自如地展开生命的律动细节,写出来的作品就会捉襟见肘,根本无法游刃有余,写不出好的散文诗。所以,与新诗可以隐藏相比,散文诗是一种暴露的艺术,所以,郭沫若先生称之为 “裸体的美人”。[5]
是的,散文诗需要裸体才能呈现其美,不能有任何遮掩。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现代诗奠基者原溯太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不无感慨地说: “在我国一般被称为自由诗的文学中,特别优秀的、比较上乘的作品才称得上是散文诗”[6]。后来,他又在另一篇题为 《超越散文诗时代的思想》文章中强调指出: “我当然承认散文诗的艺术意义,并相信其在未来将取得更大的发展。毕竟散文诗作为散文诗的原因,以其艺术的意义是不可能被纯粹意义的诗歌所取代的。我绝不否定散文诗。……换一种看法,实际上也可以说现代是散文诗时代”[7]。有识者都知道,萩原溯太郎的一生主要成就在于现代诗的创作,而他最晚年的作品集 《宿命》却采用了散文诗这种表现形式,他不但没有排斥散文诗,相反,他更把散文诗置于新诗之上。他认为散文诗与抒情诗相比,内容上的观念性、思想性因素更多,所以,可以把散文诗当作音乐节奏强、艺术香气浓厚的思想诗。笔者在这里虽然引用萩原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主要是不同意他简单地把散文诗放在新诗之上来认识。我们必须肯定几十年来新诗的辉煌成就,新诗的探索与发展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繁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那是散文诗无法替代的。
余光中先生作为现代诗的前辈,他在新诗方面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的贡献才极其敬重。由于他的巨大成就和对于现代诗创作上的贡献,也许有资格认为新诗君临于其他文体之上。但是,即使如此,他也完全没有权利否定散文诗。更可悲的是,我国还有许多自己只能写出小学生诗歌水平的所谓诗人,他们也在附和余先生,认为散文诗是一种 “非驴非马”的存在,这些人好像自己这么一说就可以跟余先生的艺术与审美高度相提并论了,这种浅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三、余光中发言的历史背景
跟余光中先生学舌的那些肤浅之辈当然无心深入了解,余先生当年发表这种言论时台湾文坛的现实背景。其实当时的台湾现代诗坛正在为了是 “横的移植”还是 “纵的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最初在50年代中叶,针对纪弦先生强调新诗横的移植,提倡包容自波特莱尔以来一切新兴诗派精神与要素作为 “现代派”诗群的美学主张。而余光中先生则代表 “蓝星”诗社明确表明反对这种主张,表示不愿贸然作 “横的移植”[8]。而到了60年代初,经历50年代的那场被称为“现代诗保卫战”的关于现代诗路线和倾向的论争之后,台湾诗坛又出现了在诗人之间展开的关于如何面对新诗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余先生与 “创世纪”的洛夫先生之间的论争。以洛夫先生为代表的一群诗人选择了对于传统更为彻底的反叛,而以余光中先生为代表的另一群现代派诗人则转向对于传统的重新体认。本文开头引用的 《剪掉散文的辫子》中的那段话,其写作背景即在此后不久的时期。我们无法进一步探知余先生当时说此话有没有现实的具体所指,如果仅从认为散文诗起源于西方,以波特莱尔作为最初的代表性作家的情形来看,反对 “横向移植”的他发此言论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更何况当时属于 “现代派”成员的纪弦、羊令野等诗人都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然而,我们如果更进一步审视中国的古典文学,可以视为散文诗源头的辞赋诗文等亦大量存在,郭沫若先生甚至把屈原的《卜居》、 《渔父》,庄子的 《南华经》中的一些文字等也当作散文诗。[5]那么,余先生即使再反对“横的移植”,而他既然认同了传统的价值,强调重新认识传统,那就不该持有如此偏执的观点,更何况余先生的诗歌作品中,有许多篇章基本都可以当作散文诗来读。当我们纵观这些,余先生的这种发言不免会让人感到与他在现代诗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极其不和谐。
从文字的表现上看,前面引述的那段余先生的关于散文诗的看法,措辞过于激烈,过于武断与轻狂,这一点是否与台湾文坛争论时的措辞习惯有关呢?笔者不得而知。不过,这种倾向我们似乎可以从其他人的文章中窥之一斑。比如,苏雪林在一篇题为 《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文章中,痛斥台湾的现代诗 “更像是……匪盗的切口”。甚至有的诗人谩骂台湾的现代诗是 “可羞”的 “李金发的尾巴”。而余先生似乎偶尔也有这种措辞倾向,他在与洛夫的论争中,说自己已经 “生完了现代诗的麻疹”。此处的 “匪盗”、“尾巴”、 “麻疹”等都是粗俗的谩骂用语。如此看来,我们也许对余先生关于散文诗观点的那段话的措辞也不应该愤慨,因为这是他们争论时的用语习惯,不值得放在心上。
然而,问题是余光中先生属于台湾现代诗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应该十分明白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对于社会的舆论界、读者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就决定了余先生作为个体存在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自己所应该具备怎样的良知的问题是需要思考的。我想这一点余先生不会不明白。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也许他就是要凭着自己影响大,偏偏就不想顾及这些。然而,我们即使承认余先生在现代诗创作上的成就,可他的这些成就也无法否定鲁迅先生的散文诗著作 《野草》的存在。如此等等,笔者不想再就此深究。
总之,我们即使可以从余光中先生的上述发言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以及其言说方式的地域性特点出发,从而做到心平气和地笑对其狂言,不计较他那与其身份不相匹配的肤浅与偏见,但也不能忽视他的这种言论对于当代文坛人们认识散文诗所造成的误导和伤害。笔者之所以要把余先生的这段话揪出来说事,并非针对余光中先生本人。2009年,中国大陆文坛崛起了一群以“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为核心的散文诗探索者,在他们所追求的 “大诗歌”创作情怀面前,余光中先生的这种观点只是一颗小石子激发的浪花。 “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的引领者周庆荣先生读了余先生的这段话,说了一段很能体现 “我们”态度的感受: “余光中曾经把乡愁写到了乡愁之外,我们有过经典的感动,对他四十多年前的轻言我只选择抖一抖肩膀,不会去介意,这进一步说明我们必须让散文诗有意义,让我们的写作与当下的生活有关,我相信,我们是有自己的信念的人,余光中先生动摇不了,比他更强大的人也同样动摇不了”。
四、余光中言论的滋生与存活的土壤
在我们检阅当代散文诗的创作成就时,重提人们对于散文诗偏见的言论,并非像以往那样,总是纠缠着散文诗究竟是什么身份确认,散文诗发展到今天早已超越了它是什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该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担心当下文坛上还存在的一些有关歪曲散文诗的言论会动摇我们探索散文诗巨大的美学可能性的认识。问题是我们在面对这种言论的时候,必须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言论?其获得人们共鸣的原因何在?所以,我们有必要检讨当代散文诗的历史,其自身发展过程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一些问题来源于何处?明确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散文诗发展是极其必要的。
其实,造成人们对于散文诗这一文体美学偏见的责任不能全部都推到余光中先生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几十年来中国散文诗发展自身存在的一些模糊的、不自信的、不明智的言论为余先生的言论提供了获得受众的土壤。更具体地说,造成这种局面与一些前辈散文诗人对于散文诗认识的模糊与不自信有关。且不说鲁迅先生对于 《野草》写作的感受: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 《野草》。”[10]这段话我们无论怎么看都可以理解为鲁迅先生自谦的表现,但同时也不能否定鲁迅先生在这里对于散文诗这种文体自觉依然模糊不清。当然即使这样,并不会影响到 《野草》作为中国散文诗之里程碑的存在意义。问题是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只抓住 “小感触”说事,却忘记了其中承载着时代大悲痛是鲁迅先生 “小感触”背后巨大的叙事背景。这就造成了几十年来散文诗创作在继承和断裂上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该继承的没有得到继承,该断裂的没有被扬弃。比如,郭风在 《叶笛集·后记》中写道: “写作时,有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起初把它写成 ‘诗’说得明白一点,起初还是分行写的;看看实在不像诗,索性把句子连接起来,按文章分段,成为散文”[11]。而柯蓝则企图创建他所认定的散文诗美学特征:以小见大,短小精美。[11]鲁迅对于 《野草》文体的模糊、以及 “小感触”之“小”的谦虚表达,这些表面上的东西被放大到作为散文诗的写作态度和美学特征被言说或者提倡。几十年来,作为散文诗坛代表性作家都如此不明确自己要写什么、在写什么,或者都如此不自信、或者那么缺少自知,散文诗还能期望得到别人公正的评价吗?
不过,有关散文诗文体认识的问题,不仅仅中国的现状这样,在我们的邻邦日本也存在相同的现象。日本著名散文诗人粕谷荣市先生在散文诗的创作谈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长期以来写散文诗,近四十年了。然而,没有一次想到是在写 ‘散文诗’。是想写诗的,自然地成为那样(散文诗)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不中用吧!为了自由,至少可以说,写作的时候我希望是自由的。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采用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我的理由”。[12]而在这章散文诗刊载的同一期杂志上,另一位散文诗人高桥淳四先生也同样拒绝承认自己是在写散文诗,他说自己只是根据内在节奏而需要句子的长短表现,所以,自己的作品被当作散文诗,而自己没有打算写散文诗,而是在写诗,[14]等等。看来,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对于散文诗的写作,都存在着不自觉的、模糊的认识倾向。就是作者自身的这种非自觉写作,为那些否定散文诗的观点提供了滋生与存活的土壤。
然而,从中国当代的散文诗创作情况来看,这种非自觉的散文诗创作历史应该可以划上句号了。许多作者不再是想写新诗而写成了散文诗,而是自觉地、明确地要创作散文诗。特别是一些两栖性的作者,他们一方面从事新诗写作,另一方面明确地以区别于新诗创作的情感、思维驾驭方式、有意识地要写散文诗,并且能够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采用的两种体裁在表现手法上是不一样的。这应该就是林以亮先生所说的 “一种不可避免的内在的需要”,或者王光明先生所谈到的那样,应该写成新诗的内容,就不会为了追求自由而写成了散文诗的形式。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说,应该是散文诗就不可以采用新诗的写法,所以,像上述那些非自觉写作者那样写自由诗因为不像成了散文诗,不可能从自由诗变成了散文诗。
总之,那些对于散文诗认识模糊的作者,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的散文诗。也许,这是散文诗这种体裁处于萌芽阶段所要走的一段必然的摸索路程。而在当今的中国文坛,这个阶段应该可以宣告结束了。散文诗的文体美学确立、创作繁荣的时代正静悄悄地开始了。
五、散文诗的可能性
所以,作为散文诗这种文体的探索者、实践者,我们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绝不赞同散文诗像余光中先生所说的那样: “兼具两者的弱点”,恰恰相反,它可以兼具两者、甚至所有文学艺术的优点。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有必要替余先生纠正他的偏执,让他在现代中国诗坛更能显示出其存在的从容与大气。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历史来看,余先生所追求的如何处理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的关系,寻求中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的过度的探索都值得我们借鉴。恰恰因为我们敬重他的贡献,才需要纠正他的这种极其肤浅的认识,把他的观点提出来进行商榷。那么,笔者的结论是:散文诗不仅可以兼具散文和诗的优点、甚至可以吸收所有文学艺术中的精华元素来发展自己。
笔者的这种观点,不仅只是许多创作实践者来自于创作过程的切身感受,对于散文诗潜在的美学可能性,著名文学理论家谢冕先生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85年写的一篇题为 《散文诗的世界》文章中精辟地指出: “散文诗的‘两栖性’便成了它在文学体系中的特殊的一种身份。它的 ‘双重性格’使它有可能兼采诗和散文之所长 (如:诗对对象表达的精粹和飞腾的幻想性,以及散文的流动、潇洒等),摒除诗和散文之所短 (如:诗的过于追求精炼而不能自如地表达以及诗律的约束,散文一般易于产生的散漫和松弛等)。在诗歌的较为严谨的格式面前,散文诗以无拘束的自由感而呈现为优越;在散文的 ‘散’前面,它又以特有的精炼和充分诗意的表达而呈现为优越。在全部文学艺术品类中,像散文诗这样同时受到两种文体的承认和 ‘钟爱’、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环境中而又回避了它们各自局限的现象,大概是罕有的。这一特殊的地位,无疑为散文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14]笔者认为这是一位文学理论大家令人信服的敏锐眼光。
不过,笔者觉得还应该补充一些谢冕先生未曾论及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总是把散文诗当作散文和诗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有些前辈就认为它是 “美丽的混血儿” (王幅明)。笔者认为散文诗不是两者的结合,散文诗完全超越了这两者的存在,它是一个可以包容所有文学艺术中精华的元素来铸就自己的美学品格的文体。如戏剧一样,音乐、美术、诗歌、散文、小说等要素融为一体成就了戏剧这门艺术。所以,说散文诗 “非驴非马”也许对,但它本来并非驴 (散文)和马(诗)的杂交而诞生的骡子这一点必须明确。我们如果把文学进行大的分类的话,传统的看法无非只有诗歌 (有韵文学)、散文 (无韵文学)、小说(故事文学)三种。笔者认为散文诗的内在情绪节奏接近于传统的韵律,这就决定了它应该归入传统意义上的诗歌范畴,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新诗,也不是散文,更不是诗和散文结合的产物,为了区别这些, “我们”散文诗群使用了 “大诗歌”的概念。因为它作为一种具备内在情绪节奏特质的文体,其本质上完全可以在创作中吸收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散文的自由与从容,诗歌的意象与象征,小说的叙事与细节,戏剧的场景设置与情节安排,美术的构图、图像与色彩,光与影、泼墨与留白等手法,尽可能以精炼的文字,自由地绽放生命的展开机制,通过场景、细节、象征、情绪浓淡、节奏的舒缓等有机的诗化结构处理等,创造出一种既超越于单纯地为追求精炼而隐藏,为了分行而跳跃的新诗,又区别于松散、冗长、拖泥带水的叙事散文以及浅白直抒、单纯平面的抒情散文,使散文诗展现出具备立体审美可能性的、全新的、综合现代各种艺术技巧于一身的、属于现代意义的、具有内在韵律节奏的 “大诗歌”范畴中的一种文体。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快餐文化的普及和流行,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时间的因素所左右,那么,长篇大论的大部头小说将越来越被拒绝,而散文诗恰恰可以把一些生命的具体场景和细节进行诗化的处理,浓缩成一篇精美的生命与情感律动的文字。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社会里她将被更为广泛地接受。
所以,笔者一方面认同谢冕先生的观点,那是来自于自己创作经验所带来的强烈共鸣。同时,也承认中国散文诗90多年来发展滞后于新诗的创作成就,散文诗的探索还远远不够,自身的突破尚且远远不足,谢冕先生为散文诗所作的美学定位还远远没有抵达,更不用说已经抵达聚各种文学艺术精华于一身的、具备立体审美可能性的“大诗歌”了。然而,笔者坚信谢冕先生的观点是对的,当代的散文诗创作,正在通过各种探索逐渐趋近这种美学高度。这种高度的抵达需要生命与审美的极致飞翔,并且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更进一步,笔者甚至大胆展望,今天中国文坛关于散文诗这种文体的一切美学探索实践,在将来的文学历史中,将有可能会绽放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意义。因为据笔者所知,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人把散文诗这种体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有许多人正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1]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M]//余光中.寂寞的人坐着看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5.
[2]林美茂.散文诗,作为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被历史传承的可能性[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4).
[3] 林以亮.论散文诗[J].文学杂志, 1956(1).
[4] 王光明.关于散文诗的特征[J].福建文学,1983(2).
[5]郭沫若.论诗三札[M]//郭沫若选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01.
[6] 原溯太郎.关于散文诗[J].现代诗手帖,1993(10).
[7]原溯太郎.超越散文诗时代的思想[J].现代诗手帖,1993(10).
[8]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M]//余光中.余光中散文选集:第2辑·听听那冷雨·焚鹤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339-358.
[9]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M]//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6.
[10]郭风.叶笛集·后记[M]//叶笛.叶笛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11] 柯蓝.散文诗杂感[N].文汇报,1981-02-21(3).
[12] 粕谷荣市.月明·散文诗观[J].现代诗手帖,1993(10).
[13] 高桥淳四.天使·散文诗观[J].现代诗手帖,1993(10).
[14] 谢冕.散文诗的世界[J].散文世界,1985(10).
On the Feasibility of Prose Poetry——beyond a Discussion about Mr.Yu Guangzhong's Prejudice
Lin Meimao
(Philosophy Colleg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10000,China)
Mr.Yu Guangzhong thought that prose poetry is a being of“neither a donkey nor a horse”.This viewpoint has been a substitution of many people's prejudice over prose poetry.In this paper,after analyzing some affirmative viewpoint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circle about prose poetry,the history of prose poetry,Mr.Yu Guangzhong' prejudice and its background,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is style is not merely an inevit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The author predicts that because the literature features of prose poetry surpasses surpass the combination of simple poetry and prose,prose poetry will inevitably develop into a“great poetry” literature containing ful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ombining the cream of all kinds of literatures and arts,because the literature features of prose poetry surpasses surpass the combination of simple poetry and prose.
neither a donkey nor a horse;prose poetry;independent style;full aesthetic appreciation;great poetry
I207.25
A
1673-8535(2010)05-0083-07
2010-07-01
林美茂 (1961-),男,福建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柏拉图哲学、公共哲学、日本思想史、散文诗。
覃华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