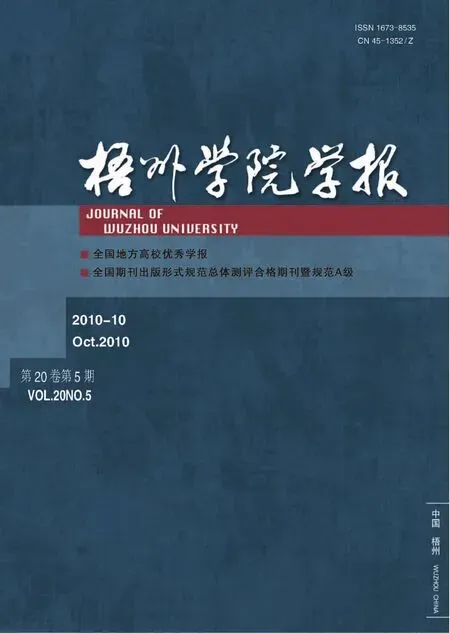早期中国散文诗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创新
黄永健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早期中国散文诗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创新
黄永健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20世纪20年代,高长虹、郭沫若、滕固、郑振铎对散文诗的文体特性进行了独特的解会,而其中以高长虹的见解颇具说服力,郭沫若对于散文诗文体的界定过于宽泛,论说且有相互龃龉之处;许地山的散文诗相对来说,具有艺术创新意义。
散文诗;散文诗理论;艺术创新
一、高长虹的散文诗理论探索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初步讨论了散文诗的文体问题,郑振铎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组织了3次讨论散文诗的专辑。郭沫若、滕固、高长虹等都对散文诗的文体特性进行了探讨,如滕固认为新诗是黄色,散文是绿色,由新诗配合散文,而成了散文诗的蓝色。这十分具体的比喻,道出了散文诗既不同于新诗又不同于散文的文体特性。今天看来,早期中国散文诗的作者们不仅取得了崇高的创作成就,而且在散文诗的理论问题上,他们的探讨也是追根探源的,具有相当深遂的想象力和思辨力。
高长虹在《什么是诗》和《诗和韵》这两篇并不太长的论文中,集中探讨了新诗和散文诗的问题。[1]他认为诗不能没有形式,而形式不外为分行写、押韵、调平仄者,但诗意也有它的形式,对于一个写诗的人,它是诗的内容的一种先天的形式,诗的形式有限,而诗意和诗的内容无限,诗的内容比诗的形式复杂得多,好比人的行动比人的身体复杂得多一样。
由于诗意和诗的内容比诗的形式丰富多样,因此,到了一定时候诗人为了诗意的表达而不得不对形式进行突破,诗人写诗,有时候会:宁可形式不好。这种作法,发展到一定限度时,就产生了没有诗的形式的诗,这就是所说的散文诗了。说它是诗,因为它的内容是诗,好比便衣警察也是警察。高长虹还指出:“无韵诗、散文诗,也是诗的一种形式,无韵诗脱落了诗的押韵的条件,散文诗又脱落了分行写的条件,但音节(在《诗和韵》一文中,高长虹指出音节就是一句中字与字之间的节奏。但句与句之间也要有节奏,句与句之间的节奏是一首或一段诗的韵)的条件,它们都还保存着,因此,无韵诗是诗,散文诗也是诗。”
可见高长虹在这儿所命意的韵已非传统诗律意义上的“押韵”之韵,而是一种情绪的节奏和情感的起伏所形成的广义之韵了,这与郭沫若在《论节奏》一文中的观点大致相当。波德莱尔说,他梦想着创造一种奇迹写出诗的散文,没有节律(如西洋古诗的音节之间的种种清规戒律),没有脚韵(相当于中国古诗里的韵脚),但富于音乐性,而且亦刚亦柔,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可见波氏在那些“怀着雄心壮志的日子”里所要创作的这个奇迹——散文诗,正是高长虹所说的诗意要脱出形式的牢笼而作自然本真的流露的诗体。高长虹说:“散文家写诗,音节(字与字之间的节奏,往往是诗人苦吟所得,作者按)总不会很好,音节变成了诗的桎梏,有时候就会以脱出为快(不顾字与字之间节奏,而只顾句与句之间的节奏——韵),都盖纳夫(屠格涅夫)是这样,波德莱码(波德莱尔)也非例外。”
不过高长虹关于散文诗的兴起衰落与历史环境之关系的论述还有商榷的余地,他认为散文诗总的来说是人的情调(情感)的节奏的变体,就像婴儿突然遭受了一击(打击),他突然哭出,哭声长而没有音节,经一停顿,又一长声,再需一较小的停顿,这样逐渐恢复了哭的音节(节奏)。这“哇”的一声,在哭声中,就仿佛诗中的散文诗一样。情韵过于促迫,过于紧张,就会把形式毁坏,就像豫让吞炭,再也看不出国士风度来了。欧洲散文诗的风格,是在世纪末颓废时期,过一个时候,有韵诗又集合起来,结成队形,散文诗又衰落下去。
应该说高长虹对广义之韵的认识,甚至在上面这一段话里对散文诗文笔的惊厥性跳跃性的认识都符合散文诗的文体特性的,但他认为散文诗将来或许会衰落下去,并不符合散文诗的历史事实。事实证明,散文诗从法国扩散至全世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年代都有杰出作品的出现,散文诗作品层出迭现,散文诗研究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散文诗作为特殊文体其精神甚至与当代人文自由、民主、多元、开放的态势,互为发展,因此直至今日散文诗并没有出现衰落的迹象。
高长虹的散文诗遵循他自己主张的专摹情调(内在情绪)的美学范式,有一种“促迫”、“紧张”的内在张力流转于他的散文诗的句子与句子之间,这就是他称之为“韵”(广义之韵)的一种东西,其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怀疑一切”、“叛逆的快感”以及强烈的“自我扩张”意识,都与他的性格和时代氛围以及他从尼采、鲁迅那儿所受到的影响有关系。他认为散文诗行文的紧张感就象婴儿突遭一击,“哇”的一声长哭的急促的情绪变奏一样,虽然顾不得诗的诸种外在形式(分行,压韵,平仄),但它具有诗意的前形式(情感的节奏和情绪的起伏),按我们今天的说法,也就是人的前意识和潜意识或人类的集体记忆受某种外来的刺激而作出了反弹性的反映。纵观其一生,经历复杂,思想曲折,性格倔犟,偏激、怀疑、喜欢自我表现这些看来像是性格上的弱点的东西,在五四前后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刚好成为一个热血真情诗人的优点,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早期鲁迅很欣赏他到后来终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高长虹的梦幻散文诗依循散文诗探寻内心世界的波动性、跳跃性和惊厥性的现代审美精神,语言是言语式的书写,同时,其行文中多种修辞手法的穿插,甚至标点符号的有意强调都说明他是有意在以诗意本身的节奏(广义之韵)突破诗的形式而抵达诗的本真的书写,这种“裸体的诗”读来令人振奋惊奇。他早年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学加上他本人强烈的反叛性格,又使这类心灵探险的散文诗具有独立不羁、怀疑一切、推倒一切的思想锋芒和类似于“日神”精神的审美品格,具有鞭笞旧世界再造新世界的心灵憧憬和一股横扫一切的气势。比如其《黎明》中的我完全就是一个查拉图斯拉特的中国翻版,那睥昵一切、傲视群类的口吻和那预言般的呼唤(最后的两行“太阳!太阳!”)虽然有些模仿尼采的痕迹,但将它放在当时的中国现实背景下,不也恰好表达了一代人徘徊、彷徨、愤懑、无奈的思想情绪吗?鲁迅当年激赏高长虹的这类文字,是因为其中所包蕴的思想以及这种以现代白话别造新声的诗体很能契合他自己的心灵状态,因而彼此互相认同视为莫逆。
高长虹的叙事散文诗同样体现出散文诗精简、跳跃以及句与句之间,节与节之间韵律起伏波动的文体特征。《我家的门楼》虽然多用写实的叙述方法,但作者有意压缩每节的长度,围绕着“门楼”这个中心意象,诗思随着时空以及情绪的转换而左冲右突,尤其是最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反问句,使前面的诸多叙述一下化为这篇散文诗的大背景,使读者的眼界随着作者的诗思的跳跃获得了空前的高度,从而将一种深刻的哲理意蕴推入这行有意悬置巨大空白的文中,一篇叙事散文诗如果缺少这种“空白”之美(柯蓝称之为从一个意境到另一个意境的转换、跳跃、推进),那么它就很可能沦为叙事散文。高长虹的这篇散文诗前面数节的叙述文字之间固然有这种经简化、凝练之后而产生的空白美,但这最后一句所呈现的意境与前面的整个叙述部分的大跨度跳跃,加强了散文诗应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度,如果我们用绘画中的布白或音乐中的休止符来说明这种散文诗笔法的特征,不无道理。若用现代交响乐中的最后的音节的戛然而止,从而在音响与读者的心灵呼应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来说明散文诗(尤其是叙事散文诗)的笔法则更有说服力。散文诗历史上,类似的处理方式并不少见,比如与屠格涅夫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柯罗连科的叙事散文诗《火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作者在散文诗中多用省略号、破折号,造成意境与意境的空白处,而于全诗的收束处,用“啊!”感叹号,感叹号之后的省略号以及断续出现的两个感叹副词,将情绪的波动推向最高的波峰浪巅,从而一下子拉开了前面的写实叙写与作者的人生感叹之间的巨大距离,类似于交响乐演奏中最后的众响齐毕,全场肃穆使听者心惊股慄,惊遽之美由此而产生。
二、郭沫若、郑振铎的散文诗理论探索
20世纪20年代除了高长虹在理论上和创作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之外,尚有郭沫惹、郑振铎等人在中国早期散文理论建设上贡献突出。
郭沫若从诗的本质特征——情绪的自然消涨来说明散文诗的文体特征。他说“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extraneous rhythm),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散文诗便是这个”。[2]25这个观点与高长虹的观察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关于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以及散文诗的功能,郭沫若的许多观点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他说近代的自由诗,散文诗,都是些抒情的散文。[2]8将无韵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与抒情散文混为一谈。他一方面说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精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强调散文诗与现代社会的能指所指关系,但同时,他又说我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卜居》、《渔文》诸文以及庄子《南华经》中许多文字,是可以称为散文诗的。郭沫若此言一出,后来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散文诗这一文体的争讼就无由止息了。不仅如此,郭沫若甚至还认为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散文诗,原因就因为此书几乎全是一些抒情的书简所集成,叙事的成份极少,这就是说,在波德莱尔之前西方与中国一样早就有散文诗文体的存在了。
郭沫若这个错误的观点的提出与当时以新诗为武器挑战旧诗的革命情结有关,大声疾呼古代亦有散文诗的最直接的目的,是让一帮排斥新诗包括散文诗的遗老遗少们从情感上理据上无由贬低新诗的地位。他们攻打旧诗的主要论据为“不韵照样是诗”,与“不韵则非诗”的固有信条相抗辩,郑振铎在《论散文诗》一文中,首先就举上古民间歌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来论证古诗不一定必用韵,他虽然没有明说中国古代就有散文诗,但根据他对散文诗的大致说明——以散文体写的抒情诗,显然,像这种以上古口语写作的散文体带有诗的情绪和想象(郑振铎并说:自己将诗元素定义为一情绪,二想象,三思想,四形式,其中前二者为基本元素)的歌谣也是散文诗[2]23。他这个看法与郭沫若对散文诗文体特性的看法颇为暗合,郭沫若在《论诗的韵脚》一文中将韵文(有韵脚的散文,如赋),与散文诗的文体特性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韵文=PROSE IN POEM散文诗=POEM IN PROSE。
古人称散文其质而采取诗形者为韵文,然则诗其质而采取散文形者为散文诗,正十分合理。根据他的这个对韵文及散文诗的理解,他当然可以将古代的无韵的抒情小品看成古已有之的散文诗。
其实郭沫若在自己的论述中已构成了这种“古已有之”之见的悖论,他在《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一文中说:“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古人的言辞已不同今天的言辞,以今天的言辞(现代白话)写作的散文诗又何能等同于古人以当时的语言写作的无韵之诗。
总之,郭沫若对散文诗的定义过于宽泛,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诗的界定过于宽泛,他将诗上升到了SEIN(德语:存在)的哲学高度,因而他对诗的本质规定性近似于海德格尔“诗即思”的诗学思想。也就是说,在郭沫若看来,诗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诗的内容与形式可以表述为体相不分——诗的一元论精神亘古不变,因而古人只要在散文的形体里注入诗质,不管他是东方诗人还是西方诗人,皆可以称之为散文诗(郭沫若认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可以看成是散文诗)。这种散文诗观从诗的本体论上看可说得过去,但在文体论的范围内,可就无视文体演化的历史事实了,散文诗本来就是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里分化出来的新的文类,它与自由诗质同而表达的功能及语言的特性皆有分别,波德莱尔写出自由分行诗《头发》,复又写出了散文诗《头发里的半球》,而且一前一后,如果波氏认为《头发》一诗已表达了他的特定的诗情,为何又要做一篇更加细密具有散文性细节的文字呢?显然,他自己认为只有这种不分行,索性将句子连接起来的散文诗,才足以表现复杂的现代心灵,而且,这些不硬性断开的情绪的起伏连绵也只能以这种语流句式文字,得以真实的表现。试将《头发》取消分行,变成散文体,则其诗质必遭破坏,且有些不伦不类。散文诗的产生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在郭沫若的论述里几乎没有触及,而高长虹所谓散文诗的风行是在世纪末颓废时期,倒触及到了这一至关重要问题。
从文体论上看,郭沫若的这种散文诗文体观,有强为古人贴标签,以后来的文体类名硬套历史上已经确认的文体的嫌疑。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按郭氏的说法,历史上所有的文类则只有诗、散文、散文诗、小说、戏剧数类而已,并且诗意化强的小说也可纳入散文诗的范畴,如此一来,散文诗的名头是大了,没有人敢于不承认它的存在,但实际上这种无限扩张其概念外延的做法,等于瓦解散文诗的独特性和文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散文诗观是大而无当的,偏向于哲学的概念总括而缺乏科学的分析精神。
不能说郭氏本身不理解散文诗的质性,他在一系列文章里反复强调散文诗不易写好,认为散文诗总以玲珑、清晰、简约为原则,“当尽力使用暗示”等等,并且他也相当敏锐地意识到散文诗很难和中国3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相和合的问题,这都说明他对散文诗的表达功能以及散文诗语言的特殊性有其意解神会之处,并且,他还认为诗愈走向现代,愈散文化,以至于“竟达到了现代的散文诗的时代”,也就是说,散文诗的发展前途是不容置疑的,这些观点已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
郭沫若的散文诗写作表现了其对散文诗质性的把握。如其20年代的作品,《冬》、《大地的号》、《山茶花》、《寄生树与细草》及其40年代创作的散文诗独白,著名的《雷电颂》以及《银杏》等。《冬》、《大地的号》这两篇作品无疑是作者身处启蒙主义时代主体意识的强烈辐射,偏重于内心强烈情感的诗意化呈露,遵循他指出的内在律自然呈现的诗的书写模式,《大地的号》中结尾那三个可怕的连续警示,极其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内心对于大时代到来的某种预感,它颇似幻觉又让人倍感真切,正如他的《女神》吹响了时代的号角一样,这两篇散文诗从另一个侧面凸现出诗人作为时代的预言家的特殊秉性。《雷电颂》和《冬》、《大地的号》一样,着意于主体的内宇宙的诗意化呈现,《雷电颂》完全是内心语流式的恣肆流泻,悲壮雄阔,散文诗的语言特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其缺点(包括另外的几首散文诗)大概就是太过急切的抒情损害了散文诗重要的审美特性——暗示和意境的跳跃。
三、许地山散文诗的艺术创新
《野草》出版之前的三个集子:《空山灵雨》、《夜哭》、《将来之花园》普遍被认为是三部散文诗集,而在成就上应以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为最。当然,若以散文诗主要倾向探索现代人内宇宙隐秘的功能特征来看,《空山灵雨》那种融化了禅佛理念和悲悯情怀的抒情格调似乎与高长虹的《心的探险》走的不是一条路子,同样是将笔触深入主体的心灵世界,高长虹表现出来的是现代人的孤独、绝望和叛逆意识,而许地山借用散文诗的这种轻灵短小的抒情形式表达了企图以佛理来化解人生苦恼的写作意图。沈从文评价《空山灵雨》有言:“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
沈从文显然认为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精美的散文小品,但我们以散文诗的特性来对照《空山灵雨》,可以认为它是从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等探寻现代人内宇宙缤纷万象的西方散文诗走向另外的一个发展方向——以东方的禅佛心境对自然和人世进行诗与思的观照,从而将身边的一草一木琐屑小事,通过相当游离的叙写化为诗意颇浓的白话散文诗。《巴黎的忧郁》中50篇散文诗也有许多叙述性较强的散文诗,如其中的《老太婆的绝望》、《爱开玩笑者》、《小丑和维纳斯》、《狗和香水瓶》、《恶劣的装玻璃者》、《年老的街头卖艺者》、《寡妇》、《美丽的多罗泰》、《手术刀小姐》等。叙事散文诗与叙事散文的区别,在于叙事散文诗在行文中裹挟着一种情绪的暗流,而叙事散文的行笔却不能随意摆脱叙事元素(时间、场景、因果律)的纠缠而作纯粹的诗与思的聚焦式关注。波德莱尔在上述散文诗中不无叙述具体的述笔,但在行文中可见作者倾注的一种激情以及围绕着这种激情而展开的叙事场面,每一首散文诗都表达了波氏以一个现代的心灵对城市生活的可惊可怖的理解,把读者从都市之相的玩味引向哲理思考的层次甚至是宗教思考的层次。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的许多篇章与波氏的这类散文诗异曲同工,只不过,许地山的这种诗与思的关注是从古老的东方禅佛思想汲取智慧的资源,因此,他的散文诗获得了另外的一种审美品性,其哲理的呈示沾溉佛家的“空”观,以及立身现代社会的伤情忧生况味,格外催人警醒。如果说散文诗从一开始就带有对现代社会的强烈批判意识,那么许地山这些散文诗则是在更具深度的哲理层面上(东方佛家人生观和宇宙观)批判现代社会,并且是用一种更高的智慧为现代人解忧缓愁。因此,在中国早期散文诗的创作中,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将西方的散文诗的写作方法及其功能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这与鲁迅、郭沫若、冰心、王统照、高长虹、徐志摩的散文诗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许地山的一些散文诗名篇也难免有直接释阐佛理之嫌,如《香》、《鬼赞》,一陈说六根六识之虚妄,一揭示生命之虚妄,但他尚能做到将佛理的阐释置于作者亲历的生活环境中,有些直露但仍不失诗的品格。在当时一班知识文明人士纷纷以觉醒过来的古国新民自我标识,用西方的无神论和超人哲学击碎传统的道德和秩序的话语环境之下,许地山的这种声音和他的这种近于自觉的现代白话散文诗写作模式是独特的。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独特之“思”,使它的散文诗和同时代的散文诗文本相比,风格特异,在“思”的层面上,或更具阔大的包蕴性与诗美的恒久性。
[1]山西省孟县政协.高长虹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49-562.
[2]吴奔星,徐鸣放.沫若诗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Artistic Innovations of the Early Chinese Prose Poems
Huang Yongjian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Inevitably,the introduction of poetry into China leaded to China's new writers of literature a theoretical thinking.In the 1920s and 1930s,Guo Moruo,Teng Gu,Gao Changhong,Zheng Zhenduo showed their individu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se poems.Among all of them,Gao Changhong's view is more persuasive.But Guo's definition is overly general the prose poems.Moreover,there are some discords on his view.Relatively speaking,Xu dishan's prose poems are more artistic in innovation.
prose poems;the theory of prose poems;artistic innovations
I206
A
1673-8535(2010)05-0071-06
黄永健(1963-),男,安徽肥东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艺术学研究。
(责任编辑:钟世华)
201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