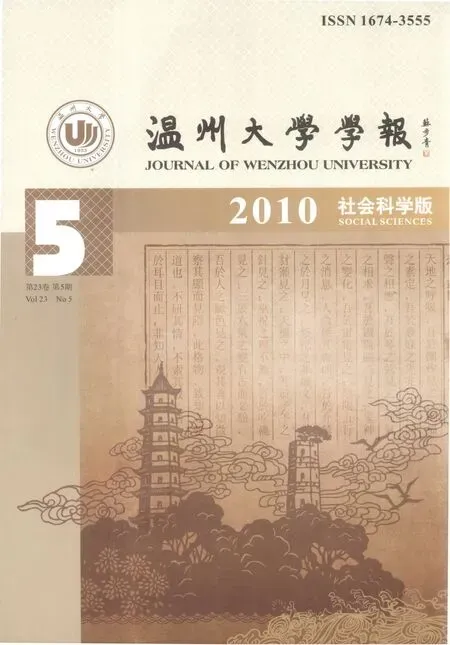复古国学中的“万叶空间”
—— 贺茂真渊《国意考》对建构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的奠基作用
沈德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复古国学中的“万叶空间”
—— 贺茂真渊《国意考》对建构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的奠基作用
沈德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贺茂真渊在《国意考》中,通过剿斥儒家道统,吸收道家的哲学思想,清理出“万叶空间”来安放自己的国学古道,为建构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奠定了基础。“万叶空间”中的主体缺乏神圣性,于是催生出本居宣长以神道作为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的后续举动。近世以来的日本文化,对自身绝对主体的强烈诉求,是复古国学最终转向复古神道的根本原因。
贺茂真渊;《国意考》;复古国学;万叶空间
日本近世以来的复古国学,是近代天皇制所赖以确立的重要思想资源,对当代日本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政治领域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贺茂真渊作为江户时代“国学四大人”之一,其富有原创性的国学思想,对建构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具有奠基作用。本文围绕贺茂真渊的《国意考》一文,“注目其思想在发端时,或还未充分发展的初期所包含的各种要素,注目其要素中还未充分显示的丰富的可能性”[1]96,以期获得认识复古国学的新视角。
一、对儒家道统的剿斥和对道家思想的吸收
《国意考》系贺茂真渊基于历年的草稿,于日本明和二年(1765年)改订而就。它属“五意考”之一,集中就何谓“古道”作了系统阐释,是贺茂真渊复古国学的核心篇章。他在《万叶集大考》点明了写作之缘起:“除此之外,凭借考证而能解明者仍有很多。譬如,吾皇御国之心,依唐言而遭误解,欲昭明此理,必拨冗繁,而书国意者以献。”[2]21“国意”一词由此而出。
(一)剿斥儒道,清理门庭
《国意考》开首便是[3]1-2:
余曰:……彼尧,让位于一介卑贱之身舜,于天下固然有益,在我皇御大国,‘善而至于发腻’者,正谓此太过可喜可贺之事。自尔以往,后世卑下者群起仿效,不经禅让,径弑其君,直夺其位,遂堕为‘恶而一至于发指’者也。……又殷商之世,不知持续几何;按其理,在其始,必夏禹以降有德者是让。果若其然,则缘何不克善终,竟遗国柄于无匹国贼商纣之手?逊位贤君,似独上古一二代之功业,[后世无以能继],亦不能究溯其本。……适当纣王作恶,深孚万民之心,遂武王伐纣,师出有名。惟伯夷叔齐二人,死谏周武,孔子誉其古之贤者,则周武如何?诚若称义,必纣之嗣是立;实则放逐其后于韩地,而传位于己之子孙。
……
孟子言,周公旦执政,翦灭旧殷诸侯四十有余。此四十诸侯,尽为不除为患之盗者哉?然周公视若大仇,悉数刃之。如此,何义之有?
真渊从攻击儒家道统中的上古三代王者尧、舜、禹始,一一驳斥了孟子“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的道统谱系中的诸位圣贤。可见,与堀川学派的伊藤仁斋和萱园学派的荻生徂徕“反朱子而倡古学”的方式相比,真渊的反儒立场远为彻底。一方面,起因于知识构成和治学体验上的差异:仁斋“多病年来不读书,却于心地着功夫”[4],徂徕则自称“余学古文辞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后古义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矣”[5],两者于儒家都有十年面壁悟道的经历,而真渊于儒道并无深切体味,便直接采取了攻击儒家道统中由尧舜至周公诸先王的立场。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真渊把一切“臣弑君”的行径都看做大逆不道,指责儒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带来“唐国贱奴弑君而登,此恶风吹染吾国,大不祥也”,欲从学理上把天皇失势归罪于儒家道统。野村公台在《读贺茂真渊〈国意考〉》指出:“真渊之言,盖谓我国上古,俗淳人朴,自然而治,上恬下熙。逮至儒教东渐,而凿混沌,牗聪明,离淳去朴,古风渐凘。美其冠服,壮其宫室,君尊于上,臣擅于下,智术益盛,俗日趋漓,卒至乱逆相继,王宫遂衰矣。是儒学之害,甚于释氏也。”[6]2
自公元五六世纪以来,天皇本人就是儒家经典的热心学习者,《日本书纪》有日本括出北方任那四岛,以使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的记录[7]。据此推算,真渊的无“儒学之害”的“上古之时”,应早于公元五世纪;日本最早的文献是712年编就的《古事记》,真渊要想恢复日本古道那种未遭儒道“污染”的空间,既没有文献材料,又缺乏证据支持,就只能虚构和想象了。
(二)自然之道,熔铸新说
贺茂真渊曾就学于徂徕学派太宰春台的门人渡边蒙庵,蒙庵著有《庄子口义愚解》、《老子口义愚解》等,其老庄学问对真渊的影响较大。《国意考》中“依老子所言,唯随天地化成,乃与普世道合”①以下段落中所引贺茂真渊的文字, 若未注明出处, 均出自《国意考》, 恕不一一标明.,充满了老庄的“无为”、“任自然”的旨趣。真渊与道家学说的相同之处,已有学者较为系统地论证过[8],此不赘言。本文强调的是,真渊的思想仅仅借用了道家的“自然之道”。
首先,真渊用“おのずから”(“自然而然”)定义了日本“上古之时”“道”的属性。这个“おのずから”之“道”“周流自在,宿荒山,居僻野,譬如此方神代之道,自广自大,不知所止”——虽显见与老子之“道”的亲缘关系,如野村公台所说,“独见我国上古淳素因循之治,与彼老聃无为自然之道相似也”[6]25,却没有上升到老子的决定万物本源的“玄之又玄”的高度。相良亨曾指出,日本的“おのずから”②根据沟口雄三在《中国的思想》(赵士林,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40)中作了详细解释: “‘おのづから’一词, 由‘おのづから’三部分组成.‘おの’为‘自我自身’、‘づ’为‘的’、‘から’在这里为某物所具本来性质、本性的意思, 归根结底是指自身本来所具或由内而外地表现出来的本性.”一词,不含有本性、本质、秩序这些偏向于“理”的属性,其核心是不带强迫性的纯粹的自发生成[9]。真渊认为,日本“おのずから”之“道”是温情脉脉、不以力逼的,是与他所认为的中国那由外部强加的具有“理”的属性的“道”所不同的:“万物渐变,冰寒火暑,朝夕昼夜,是以可耐。世界之中,去此柔和,谁将以生?”一切皆顺“道”而来,绝非突兀以至。由此,日本“おのずから”之道便具有了合乎人“情”的特性。自荻生徂徕以降,“情”开始被作为反对朱子理学“理”的武器而传播。徂徕在《学则》中提出:“夫圣人之道,尽人之情已矣。不尔,何以能治而安之哉?”[10]但这里的“人之情”还是指人的习性与欲求,需用礼乐约束。真渊却为这种“情”找到了具象的对应物——“丸”,即圆,而把与“情”相对之“理”比作“方”:“随于天地者,以日月为初,其自有自在,皆圆之态,如草上之露。……譬之经世,以此圆为本,则缥囊纪庆,玉烛调辰。以方为本,必千物争道,扞格不通,睹唐之世便知”。“唐之世”(即中国)“以方为本”、以理为道,导致“重物之理太过,民陷于乱”,以至于“千物争道,扞格不通”;而日本上古之“道”符合人情,故能“缥囊纪庆,玉烛调辰”,大治不乱。
其次,真渊古道图景中的角色,由“天地之道”、上古之民与“上”(即天皇)三者构成。“上”统治着下(上古之民),当“上下打成一片,互相亲爱,如手足父子,俾使知不单有‘主’(即天皇)之名,更应怀感恩谦卑之心”之时,这种和谐的统治关系就是“天地之道”。不言而喻,真渊的“天地之道”是“おのずから”的,是自发而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窥见了真渊古道论的“机关”:日本古代天皇制社会自平安时代(794–1192)结束后便终结了,而生于此后500年的真渊面对的是:天皇仍“合法”地存在于京都,但天皇不再有现实的权力。在真渊看来,正是中国儒道所倡导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信条搅乱了人心,“终至天武天皇,衍为大乱。其时,奈良宫内,衣冠器用,皆屈唐风,为之剧变……遂逐天皇于孤岛”,于是有了以武犯公、以下谋上的乱世。这是真渊面对德川架空天皇权力的社会现实在观念上的深刻反映。
二、“万叶空间”的诞生
岛木赤彦在《歌道小见》中评说《万叶集》时,谓“其作者,上自皇帝皇后、大臣将军,下逮农夫渔人、防人资人以至游行妇女和乞食者,所有阶级,无一不是以其必然的冲动,唱出赤裸裸的人类的歌”①转引自: [日]子安宣邦.江户思想史講義[M].东京: 岩波書店, 1998: 243.。纪贯之在《古今和歌集》的真名序中也说,“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可见,和歌一开始便与“心”和“群体”有关,这个“群体”某种共同的东西——“心”或“大和魂”被凝注在了和歌中。真渊就是通过对古代和歌严谨细致地解读,“解码”出日本“群体”之“心”或“大和魂”来的。
(一)万叶天地,政通人和
在《国意考》里真渊说[3]10:
古歌意词,存续已久。人无妨稍思古歌之言,实为慕古之心词也。观古歌,知古心,进而明古世之风。执此上溯,能思神代之事。在他最集中探讨和歌的《歌意考》中说[11]549:
呜呼,上古之代,人心古直。因其古直,其行也淳,其行既淳,其言也质。心有所动,形之言语,随口哼吟,故称为歌。歌为心声,声凭直常之语而成。久之,随情起伏,遂有节调。歌于古人,心之言词而已,故上古无歌人、非歌人之别。
对比上述两段引文可以发现,在相当于《万叶集》研究的综合论文《歌意考》中,真渊对古道的叙述自上而下,即直接描述“古人”“古歌”“古心”三者的关系,一贯而下,采取了俯视后世的视角;而近乎论战檄文的《国意考》则相反,“观古歌,知古心,进而明古世之风。执此上溯,能思神代之事”,是后世借由流传的古歌回溯上代,采取了仰视上代的视角。俯仰之间,真渊的古道观形成了一个貌似符合逻辑的闭合回路。但问题在于,作为集合体的“古人”,一个统一且同一的“古心”是否本来就已在事实上存在?由《万叶集》解码出来的景象,是否先天就是自洽自在、自然而然的世界?学者子安宣邦认为[12]256:
所谓万叶之歌的世界,是在追问万叶的志向之中被创建出来的。发现者声称,他第一次道出了这个被发现世界的景象。对于真渊,万叶集究竟是什么,以及在他那儿万叶世界是如何被发现的,被等同于这个世界是如何被言说、被叙述的问题。
在《歌意考》里,真渊自己也说[11]558-559:
至于万叶诸卷编纂,因人而异,少有佳者。淫秽猥亵者有,残词断篇者有,上句尚可观,下句转拙劣者亦有。今若欲奉万叶为楷模,决不可通盘因袭,必去粗取精。然取精甚难,无人能反掌而得。
在真渊看来,上古的万叶空间或说“万叶世界”,是需要“制作”和“剪裁”的。这个意义上,“万叶空间”是随着真渊的“回首”动作的发生而诞生的。由此,真渊不但虚构了万叶空间的存在,而且给出了自己对日本历史的一种认知:比起“古时良民,非不教,略教足矣”的淳朴质直,当今之世是“皇道隳颓,臣纲难继”,已然堕落腐朽了;但古今的断裂,源于“唐道入国门,人心转阴鸷”之初,也即始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入侵”之际。这恰恰是一个循环论证,即古-今的时间切分取决于中国文化进入日本这一事件,而该事件之所以有界石的意义,恰又因为它首先已被真渊定义为引起了日本古今的断裂。子安宣邦精辟地指出[12]263:
把后世内部的虚伪作为外部进来的“异质”在那边加以排斥的言说——正是这个十分国学式的言说,在这边创造出了作为“纯一”的、真实的、还未遭到“异质”污染的古代世界。这一切确实是文化的同一性形成的言说。
在这个文化的同一性世界中,“由上自下,委心于爱怜,皇室之人抑或陋巷鄙民,皆能懂此歌。此歌何等甘美纯直,关涉万物,映出真心,遍照人情所隐没处”[2]6。这样的世界,以天皇为中心,“皇如日月,臣似百星。百星之臣,协拱日月”,自然是君臣和合、百姓归一的王道乐土。
(二)圣人阙如,神主乃兴
固然,《万叶集》承载的古道空间和谐无比,但万叶空间中主体——天皇,缺乏神圣性,没有不可推翻的合法依据。面对天皇被架空的事实,真渊虽也期盼“待有好慕上古之风之君出,其欲光复上古之质直,不过十年廿载,世风可直矣”,但最终没能找到这样足够强大的“君”或神圣主体,而只一味强调古道深藏于歌中,读歌自能领悟,则古道对于受众完全是模糊的,这是真渊所构建的复古国学体系或说万叶空间的根本缺陷。由此来看本居宣长的作为,简要地讲,宣长对于复古国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为真渊虚寂的万叶空间找到了一个绝对主体,即天照大御神[13]:
天照大御神者,为治天之御神,宇宙间无与伦比,普照永存之天地,四海万国无不蒙此御德光所照,无论何国,亦不能一日片时不得大神庇荫而可自存者。
天照大御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尊为神道教的主神,成为日本古道的终极人格保证,天皇这一日本的象征就具有了合法性和神圣不可推翻的绝对性。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宣长强调对天照大御神的绝对崇拜。然而,问题在于宣长把《古事记》中的神话传说看成是毋庸置疑的信史。野崎守英指出:“他(宣长)看法中难以成立的核心之处,在我看来,倒未必是神话和历史的混同,不如说是在他的看来,古代是单一化的,只要是日本的古代,就被单一化处理。正是这一点很难成立。”[14]这种“单一化”地处理历史的做法,与真渊“纯一化”地缔造出万叶空间的方法如出一辙。至此,复古国学中的主体的神圣性确立,复古国学转轨并入神道的历史进程中。
三、建构文化之绝对主体的诉求
加藤周一将日本文化在本质上规定为杂种文化[15],或许恰恰因为日本文化的杂种特性,即是说,它长期以来是多种异质元素共时并置的,始终缺乏对先前思想的彻底清算;随着这种文化在江户时期臻至成熟,对自身文化的绝对主体产生了强烈的诉求。中江兆民认为日本没有哲学,这与日本人的思维疏于或说不擅长抽象思维有关,“凡是理论性的东西、概念性的东西、抽象性的东西,都遭到了日本式感性的抵抗和排斥”[1]59。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学家们采取了大胆的“想象”手法,虚构了一个绝对主体。贺茂真渊的万叶空间就是为寻求这种绝对主体而进行的重要尝试。虽然他没能在该空间中找到一个有效的绝对主体,但为绝对主体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万叶空间“建造工程”竣工后,真渊就一脚踢开历史事实,运用新获得的空间重新阐释历史,并要求对“新历史”无条件地盲信。可借贺茂真渊对待汉字的态度来进一步理解他的这一手法[3]9:
汉字行于吾国,以吾古之和音为魂,借彼今之汉词为魄,魄乃魂之注记而已。时日迁延,吾国‘字心’羼杂[汉意]而用,更专施以训读法,全然不顾和文之意。
真渊的意思是说在汉字传入之前便有和文存在,只是仅有语音而无书写系统罢了,故借用了汉字来书写,在借用的过程中,汉字污染了和文。野村公台反驳道,“即使真渊而不读华书,不假华语,则必不能有著作矣”[6]26,确为中肯之论。我们知道,日文存在对汉文词汇大量的借用,而与之紧密联系的是来自中国的概念随着汉文流入日本,也进入了日本人的思维,不是单单用训读就可以“驯化”得掉的。比如说,“天地”这个汉文概念,宣长在《古事记传》里对它究竟应读成“あめくま”还是“あめつち”十分动摇,最后还是采用了后者。如果没有“天地”这个汉语概念在先,《古事记》中的创世神话便无从表述。
一般而言,复古国学与复古神道的关系,有等同论、包含论和核心论三种说法[16]11-16,分别主张复古国学等于复古神道、复古国学包含复古神道、复古国学的核心是复古神道。对比之下,核心说较之于其他二者略胜一筹。持此说的岸本方雄认为:“总之,构成国学的中心、根干的,是复古神道的倡导,若没有复古神道,国学就只能单单停留在和学的范畴内,而不能具备作为国学的真正的形态”[16]14。然而,即便是核心说,仍没有把握住复古神道的真正“核心”。如果说复古国学的核心是复古神道,那么复古神道的核心便是在内容上供给了复古国学一个日本文化的绝对主体——神道中的“神”,而且是在鲜明的宗教形式下提供的。如此看来,复古国学是一种在梳理日本古典文献过程中逐渐清楚意识到获得文化绝对主体性的迫切性,并不断尝试对此加以塑造和建构的意志与诉求。这种意志与诉求先在“万叶空间”中奠基,继而在复古神道中实现。倘若没有这股炽热的诉求,复古国学只能是纯粹的关于古典的学问。学者梅原猛感慨,“现在的《古事记》解释,基本上是在宣长的《古事记传》的解释范围内所作的,后来的学者只是对宣长未弄明白的部分或说过头的部分多少作些订正,而辞典之类大多是根据宣长的观点而写的”[17]155,“就日本的语言来说,本居宣长是考虑最深的”[17]156。作为优秀学者的宣长,其《古事记传》之所以能推动复古国学走向复古神道,正是源自日本民族心灵深处处汩汩涌出的对于自身文化之绝对主体的意志与诉求。国学、复古国学和复古神道三者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得十分确切了。
[1]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M].区建英, 刘岳兵,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 [日]賀茂真淵.萬葉集大考[C] // 賀茂真淵.賀茂真淵全集: 第一卷.東京: 続群書類従完成会, 1977.
[3] [日]賀茂真淵.国意考[C] // 鷲尾顺敬.日本思想闘爭史料: 第7卷.東京: 名著刊行会, 1969.
[4] [日]伊藤仁齋.古学先生詩文集[C] // 相良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 第一卷.東京: ぺりかん社, 1985: 161.
[5] [日]荻生徂徠.論語徵[C] // 関儀一郎.日本名家四書註釈全書: 論語部5.東京: 東洋図書刊行会, 1926: 1
[6] [日]野村公臺.讀加茂真淵《国意考》[C] // 鷲尾顺敬.日本思想闘爭史料: 第7卷.东京: 名著刊行会, 1969.
[7] 王家骅.儒家文化与日本思想[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7.
[8] 张谷.道家思想对日本近世文化的影响[D].武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2006: 111-120.
[9] [日]相良亨.日本の思想[M].東京: ぺりかん社, 1998: 41.
[10] [日]荻生徂徠.学則[C] // 吉川幸次郎.荻生徂徕.东京: 岩波書店, 1973: 258.
[11] [日]賀茂真淵.歌意考[C] // 橋本不美男, 有吉保, 藤平春男.歌論集.東京: 小学館, 2002.
[12] [日]子安宣邦.江户思想史講義[M].东京: 岩波書店, 1998.
[13] [日]本居宣長.玉くしげ[C] // 大野晋, 大久保正.本居宣長全集: 第8卷.東京: 築摩書房, 1976: 310.
[14] [日]野崎守英.本居宣長のうちに住む歴史のかたち[C] // 相良亨.日本思想講座: 4.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社,1984: 284.
[15]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M].叶渭渠, 译.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257-274.
[16] 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M].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17] [日]梅原猛.诸神流窜: 论日本《古事记》[M].卞立强, 赵琼, 译.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Japanese Kokugaku and Space of Manyōshū—— Kamo no Mabuchi’s Attempts to Construct Subjectivity of Japanese Culture in Kokuikō
SHEN Dew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875)
Kamo no Mabuchi constructed absolute subject of Japanese culture by cleaning up the Confucian ideology, absorbing Taoistic philosophic thinking and proposing the “Space ofManyōshū” to interpret his idea on Japanese ancient culture.Since the subject of the “Space ofManyōshū” lacked of sacredness, Motoori Norinaga then proposed that the Japanese Shinto was the ultimate absolute subject of the Japanese culture.In modern times, the Japanese culture strongly appealed for the obtaining of itself absolute subject.An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Japanese Kokugaku turning to Japanese Shinto.
Kamo no Mabuchi;Kokuikō; Japanese Kokugaku; Space ofManyōshū
I109.4
A
1674-3555(2010)05-0096-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5.01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选华)
2010-05-14
沈德玮(1985- ),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