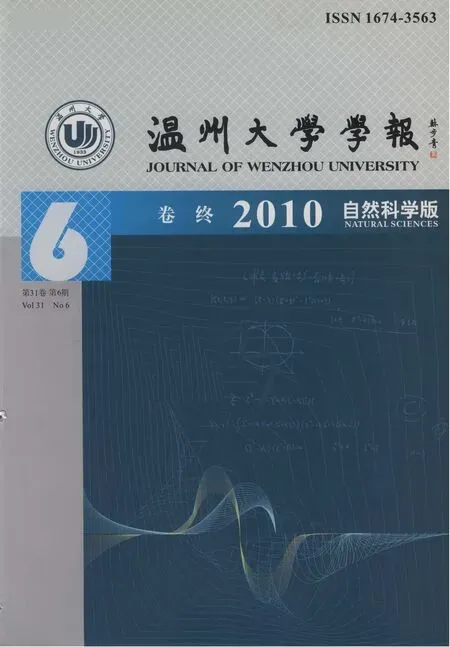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校教育质量下滑原因
冯成杰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校教育质量下滑原因
冯成杰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图书、仪器的损失及教职员的有形流失,高等教育规模的恢复与扩增,教育经费的减缩,教员及学生生活的困顿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高校教育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探讨这些原因对当今中国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启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质量
中国各高校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纷纷内迁,这保证了高等教育的延续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的大损失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38年起规模逐年扩增,在战争状态下不减反增,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并不能掩盖它所存在的问题.在战争持续破坏及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的双重干扰下,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教育质量.战时各高校图书、仪器的损失及教职员的有形流失,各高校规模的扩增,教育经费的减缩和师生生活的困顿等都导致战时教育质量的滑落.
1 图书、仪器的损失及教职员的有形流失
战争爆发后各高校的大迁移,使大学师生失去的不仅是长期安定的环境,更是在颠沛流离中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直接与间接的损失.姑且不计无形损失,战时各高校图书、仪器及教职员的有形流失就相当严重.
战时日军蓄意摧残中国的高等教育及文化机关,使大学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截至1938年12月底,各大学之设备、图书和仪器或被焚、或被劫、或遭轰炸,损失大半.战前大学及专科以上之学校,全国共108所,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底18个月时间里,其中14所学校受极大之破坏,18所学校无法续办,73所学校则迁移后方勉强上课,不能利用其原有之设备[1]401.最先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处于战争前沿的南开大学,1937年7月底,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该校秀山堂及图书馆变成灰烬①参见: 佚名: 南开大学损失奇重[C]// 上海书店. 《申报》影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740..金陵大学遭受的损失一点也不亚于南开大学.战前的金陵大学拥有图书317 839册,而到1938年5月,仅剩下16 946册,其中包括当年添置的603册②参见: 国民政府教育部. 金大1926 – 1937学年度学校概况统计表[R].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649卷, 第68卷..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的境况仅仅是战争初期全国各高校损失的一个缩影.
各高校迁移、安置后这种梦魇仍然在继续.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蓄意轰炸破坏高等院校的策略未曾稍有改变.为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日机长期对陪都重庆及大后方实行所谓“疲劳轰炸”.以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前身甘肃学院为例,1941年,在日机轰炸中,甘肃学院的不少房屋、物品、仪器和图书等被毁.其中,仅在8月31日日机的轰炸中,甘肃学院被炸毁、震倒和震坏校舍房屋共204间.而据1939年度的统计,甘肃学院共有校舍391间.仅此次日机轰炸,就使学院52%的房屋倒塌或受损[2].甘肃学院地处相对封闭的大西北,尚难逃日寇的轰炸破坏,更不必说那些临近战区的高校了.及至1946年6月,教育部第五次编制的《全国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战时财产损失统计表》中所列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损失为1 866 209 902元[3].短期内图书、仪器设备的损失无法得到恢复,即便国民政府拨款从国外购买,由于对外交通不畅,这些高校发展所急需的物品也很难及时运到中国.1939 – 1940年间国民政府拨款100万美元为大学购置图书和设备,由于对外交通的断绝,直到 1945年还尚未全部运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员及学生若欲做好研究,充足的图书、仪器设备是必不可少的.图书、仪器的大量遗失、破坏使得战时各高校失去了保持教育质量的利器.
战时师资严重流失也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升.战争初期,中国教师队伍受到很大波及.各高等院校仓促迁移,部分教员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随校迁移,滞留沦陷区;部分教员则因难以承受迁徙之苦而病逝或无法从事教育.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教授所写的《西行志痛》,记述离开广州的同行“行侣”43人,“中途离队者14人,受重伤者1人,病故者1人,到达目的地时仅27人.”[4]武汉大学在迁至四川乐山后,一批才华横溢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和萧君绛等因贫病而英年早逝[5].北京大学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和周作人等未南迁的教授成了留守教授,由学校寄给每人每月津贴费50元[6].教师的另一流向是应政府之召,担任行政职务.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于1937年底受教育部长陈立夫之邀,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于“七七事变”后即分别被政府征召为驻美与驻苏大使.走下讲台,担任政府行政职务符合一切为了抗战的总体目标;但这些学者远离自己所擅长的教学科研工作,势必成为教育界的一大损失.抗日战争烽火燃起后,一部分大学教员对战局产生悲观情绪,他们逃避现实、躲避战火,自营生计于国内外,过着类似隐士的生活.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即以研究为由出国避难,有相似情况的教员不胜枚举.日军的迫害也加速了教员的流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即死于日本人的暗杀.战时物质匮乏、生活窘迫,一部分教员为了生存而离开教职从事其它职业.教员是高校的生命线,高校教职员工的流失所产生的结果不难预料.
2 高等教育规模的恢复与扩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实力的悬殊导致中国方面在短时期内失去了东部和中部大片国土.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国民政府从抗战建国的长远目标出发,制订了与战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政策.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及1938年分别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对战时高校的迁移与安置等作了指示和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收容战区学生之用.”[7]372学校在受“轻微袭击时应力持镇静,必要时可作短时停闭,激烈战事时可暂停或迁移.”[7]374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训示:教育应循常轨,不分战时平时,所谓常轨也者,即是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8].此即“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国民政府声明:“抗战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员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故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宗旨.”[9]国民政府的声明弥合了社会及教育界关于办理战时大学教育的观点分歧,统一了思想认识,促进了高校的迁移与恢复.
中国战时高等教育的大迁移史无前例.根据《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法》,抗战时期中国高校(指国民政府统辖的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及部委属的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相当于专科一级的高级职业学校,外国在华办的私立院校)内迁的约124所.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损失后,由于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全国高等院校得以迅速恢复、扩增.战时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本应在恢复的基础上,限制其规模,保证其质量,使其在适度规模下,获得稳步发展;但事实恰恰相反,此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但不减,反而迅速增长,这使得高等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1936年全国高校仅为108所,经过八年战争的干扰,到1945年,高校反而增加到了141所,超出1936年33所;1945年高校的学生数及毕业生数是1937年的2倍和3倍①文中数据源自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的表六: 抗战期间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参见: 余子侠.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J]. 近代史研究, 1995, (6): 167-200..教员数量的增长则相对较为缓慢,而且特殊时期失去的教师中的精英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补充.暂且不论教员的素质问题,苏云峰认为:“如果强调教育质量与学生素质,则宜采取教员与学生人数的比较方法.比例高者表示学生得到教师较多的关照与照顾.”[10]以此而论,抗战时期教员与学生的比例由1936年的1∶5.5降低到1∶7.5,意味着学生与教员之间的关系在疏远,学生们无法得到教员们的充分关注.由于教员数量与学生扩招的庞大规模形成鲜明差距,从而导致教育质量下滑.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培养了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优秀学员,但毕竟西南联合大学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 179位正副教授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二十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是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二十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主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11]阵容如此强大的师资队伍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优越条件并不是所有高校都能拥有的.即便如此,西南联合大学仍受到多重限制,并陷入危机.1943年蒋梦麟致胡适信中抱怨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付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1]550西南联合大学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重点扶持的高校之一,然困难情形依然如此,国内其它高校的状况自不必说.
高校扩招使一部分有专长的中学生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青年才俊.但战时各高校损失严重,教育经费又一再缩减,且一时各高校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此时的高校扩招又加剧了图书紧缺、设备紧张等情况,高校教育质量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迁移后高校招生受地域的限制也异常明显.国立武汉大学于 1938年春迁往四川乐山,在武昌时仅有1名乐山籍学生,到乐山后第一届招生,就有乐山籍学生5人,以后逐年增多,到1946年已有30余名乐山学子加入新生队伍了[12]226.华中大学在西迁之前,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大西南”地区的学子少得可怜,而云南籍学子更加稀少.搬迁至大理后,西部地区尤其是云南籍学子的数量增长很快.1941年秋季注册的77名新生中,云南籍学生就占有32名.至1945年秋季时,云南籍学生更高达174名,占整个在校生注册人数286名的68%以上[12]226.从学生籍贯的变化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说西迁后的华中大学已成为一所西部地区的高校了.战前各高校的生源来自全国,迁移后生源主要局限于西部地区,有的高校(如武汉大学)为了协调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不得不对当地考生给予优惠.各高校逐渐地方化,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同一地区,不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素质的提高.
3 战时教育经费的减缩
中国大部分高等院校对政府的财政拨款有较强的依赖.“训练有素的教师、管理机构、特殊的教材、教学大楼、制服以及设备”是保证高校教育质量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都需要一定经费的支持.战时各高校却很难得到充足的拨款来保证自身的正常运转.随着战争的持续,军费开支庞巨,再加上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对外贸易中断、物资紧缺,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战争中期,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由此陷入混乱.高等教育的经费迅速受到波及,在国家总预算中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战争初期的1937年和1938年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分别为3.3%、2.13%,而1939至1945年的七年间高等教育经费所占国家总预算的比例从没有达到过1%,1941年更是降到0.15%,七年间比例最高的1942年也仅为0.64%[13].
1937年9月起,国民政府对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的拨款采取紧缩政策,按七成减发,且有一部分停发.省立专科以上学校有不少不得不停办;而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由于学生减少,其赖以生存的主要经费来源——学费自然也相应减少.1939年,政府拨款开始回升,以后几年,以数倍、数十倍甚至百余倍的速度增加,但远不及通货膨胀的速度.以1940年为例,根据当年12月重庆趸售统计指数,每百元法币购买力仅相当于1937年6月的7.83元,购买力持续走低,到了1944年每百元法币只相当于1937年6月的0.17元[14].虽然战时大学教育经费在1944年已达到18余亿元,但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1937年的300余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不得不承认“表面数字虽增加极大,而实际拮据更甚于前.”[15]507经费缩水如此之巨,而高等院校的规模不见缩减,反而逐年扩增.1937年教育经费3 000余万元用于教职员工8 623人、学生41 922人;而1944年300余万(以1937年的法币购买力为准)用于教职员工18 615人、学生78 909人.假定教育经费利用率不变,那么1944年教职员工及学生每人平均经费数远远低于1937年,教育质量在教育经费实际逐年降低的情况下,状况如何可想而知.
4 教员及学生生活的困顿
战争初期教育经费的减拨和中后期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因素对以固定工资为生的教员冲击尤大.教员工资有定额,增加有定时,而物价上涨却如野马脱缰;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甚至糊口都成问题.战前高校教员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曾任罗家伦助手的郭廷以有言:“一九三二年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近二十年来所未有.”[16]高校教员们的安定生活被战争打破,通货膨胀严重干扰了他们的生活.为了解决因物价上涨所造成的教职员生活困难问题,教育部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编订了《非常时期改善教职员生活办法》,规定从1941年10月1日起,发给平价粮食代金,凡教育部所办学校的教职员及其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属,每人每月可领取一定数量的代金.《非常时期改善教职员生活办法》的局限在于平价粮食代金仅适用于国立高校教员,而省立及私立高校教员无法享受到这一待遇.即便如此,随着国统区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教育部的这一努力也付之东流,教员们逐渐赤贫化.以 1943年的重庆为例,教员工资仅及战前的17%;而昆明大学教授的工资实际价值在1945年仅及1937年的3%[17].国民政府也认识到教职员生活状况在急剧恶化,1943年教育部向国民参政会报告教育界人士生活状况时承认: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各级教员的收入都无法养家.据此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通过了改善公务、教育人员待遇的提案.就连蒋介石本人也觉察到了教员生活的贫苦,1943年蒋介石曾表示:“我知道教员生活艰苦,但希望大家以简约、节省的方式,渡过经济的困境.”[18]国民参政会通过的提案及蒋介石的表态都没能对改善高校教员的生活有所帮助.抗战时期高校教职员工凄苦的生活境况一直未得到改善.
抗战中后期大学教授无法以购买力仅相当于战前 10元以下的月工资维持他们及家庭的正常生活,不得以只能靠消耗早先的积蓄、典卖衣物及书籍和卖稿卖文而生活,以至于出现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和儿女夭亡等现象.大学教授也竟然落魄至此,其他普通教员的境况更是令人难以想象.生活的困窘使教师原本可以用于教学与科研上的精力,不得不分散于兼职谋生,甚至另谋其它职业.实际上大学教员的的兼职是师资的一种隐性流失.
学生的生活也因战争而陷于困顿.战前绝大多数学生依赖家庭的供给,战事发生后,大多数学生流亡大后方,与家庭失去了联系,经济来源中断.为了解决大学生面临的经济困境,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使战时“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 80%”[15]12.值此军需浩繁、国库支绌之际,国家不惜出此巨资从事救济,使青年学生在困苦颠沛之余,因国家的援助,仍能维持学业.当然国民政府推行贷金,扩招青年入读高校,有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企图阻止知识青年流向陕北共产党统治区的意图;但这一创举还是应该给予适当肯定.
起初,学生的生活还能保证,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19]3441940年以后,中国大后方物价暴涨、法币贬值,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的生活.以昆明为例,1937年至1946年间,物价上涨了5 000多倍,学生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吃的是掺水发霉的黑米,菜是不见油盐的白水煮青菜.即使这样,学生还不得不把一日三顿改为两顿[19]229.战时学生饮食难求一饱,普遍营养不良,学生身体不断衰弱,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加上战时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差,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据1942年统计,武汉大学因卫生、营养条件甚差,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学生死于地方病的就达60人之多[20]203.高校学生相较教员境况更差,毕竟教员有薪资,而学生仅仅依赖有限的补助艰难度日;因此学生中的兼差之风盛行,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约有二分之一学生在校外兼差,当中小学教员、家庭教师的最普遍.学生因经济无着,被迫休学者比比皆是,有的学生时断时续,读了六、七年大学才勉强完成学业[20]229.在此过程中,他们身心俱疲,很难有心思一心投入到学习与研究当中去.教育质量的高低主要通过学生来体现,没有精神饱满的学生配合,教育质量势难得到真正提高.
5 余 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浩繁,中后期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使得教育经费很难按时足额拨付,而且经费实际上一直在缩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违背高校的正常发展轨道,大力扩大规模,教育质量的下降势所必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20世纪末,我国高校扩招的大潮席卷而来,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共招生565.9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 700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1 908万人),冠居全球;专任教师116.83万人[21].但教育经费短缺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各高校,利用银行贷款大兴土木,成为当下时髦.如此大规模的高校扩招给高校的管理带来沉重负担,也使得高校的教学、科研水平整体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引起各方的关注.探讨抗战时期高校的规模、经费等与教育质量的关系这一问题,对当今中国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启发.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张克非. 兰州大学校史: 上编[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 115.
[3]戴雄.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损失概况[J]. 民国档案, 2004, (3). 113-119.
[4]梁山, 李坚, 张克漠. 中山大学校史: 1924-1949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98.
[5]孟国祥: 大劫难: 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40.
[6]周作人. 周作人回忆录[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535.
[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8]秦孝仪. 战时教育方针[M]. 影印版.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1976: 295-296.
[9]伊继东, 周本贞. 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262.
[10]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51.
[11]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联大八年[M]. 昆明: 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 1946: 160-161.
[12]余子侠. 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3]熊明安. 中华民国教育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330-332.
[14]杨培新. 旧中国通货膨胀[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22.
[1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16]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649.
[17]于述胜.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七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240.
[18]张其昀. 先总统蒋公全集. 卷3 [M].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4: 3241.
[19]萧超然, 沙健孙, 周承恩, 等. 北京大学校史: 1898-1949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20]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会.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
[21]刘超. 中国大学的去向: 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J]. 开放时代, 2009, (1) : 47-68.
Reasons for Decline of Educational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FENG Chengji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730020)
Major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educational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could be concluded as the loss and damages of books and equipments, the physical drain of faculty, the recovery and amplification in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eduction in th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the hardship in lives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other situation. Exploring these reasons is instructive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National Government; Educational Quality
(编辑:朱青海)
K265
A
1674-3563(2010)06-0046-06
10.3875/j.issn.1674-3563.2010.06.00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3-28
冯成杰(1986- ),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book=0,ebook=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