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儿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植入后语言发育状况分析△
李蕴 陈向平 陶铮 吴皓
听力障碍儿童的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成为业内人士,乃至全社会的共识[1]。研究认为,听力障碍患儿的最终语言发育水平并不取决于听力障碍的严重程度,而取决于其被发现和干预的早晚,6个月内早期干预的儿童语言康复效果要明显好于6个月后干预的,即干预年龄是影响听力障碍患儿语言康复水平的主要因素[2~5]。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听力障碍的程度和干预方法的不同,干预的结果也会不同。因此,选择最合适的个体干预方式,对患儿的听觉语言康复很重要,尤其对重度和极重度听力障碍的患儿,不当的干预方法将会直接影响其语言能力的发育。本研究采用Gesell发育量表对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儿的干预效果进行分组评估,以了解不同干预方法对语言发育水平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1.1.1干预组 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上海市儿童听力障碍诊治中心确诊为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儿65例,在出生后6个月内进行听力干预,其中男37例,女28例,平均年龄22.28±3.89(10~41)月。听力障碍程度为:中度20例,重度19例,极重度26例,裸耳平均听阈为74.31±19.79 dB HL,干预后平均听阈为31.16±10.38 dB HL。验配助听器48例(均为双耳佩戴),人工耳蜗植入(均为单侧)17例,平均干预时间为19.60±3.32(6~24)月。根据听力障碍程度和干预方式分为中度听力障碍助听器干预组(简称MHA组)20例、重度听力障碍助听器干预组(简称SHA组)19例、极重度听力障碍助听器干预组(简称PHA组)9例、极重度听力障碍人工耳蜗干预组(简称PCI组)17例。
1.1.2未干预组 由于经济方面和其他未知原因家长未按医嘱及时对患儿进行干预者36例,其中男16例,女20例,平均年龄22.02±2.69(10~36)月。听力障碍程度为:中度12例,重度8例,极重度16例,平均听阈为70.47±22.43 dB HL。为了便于比较,将重度和极重度患儿合并为一组(简称“未干预S+P组”),共24例。
1.1.3对照组 选择听力正常、性别和年龄相仿正常儿童36例,平均年龄20.50±3.09(10~36)月,平均听阈为15.20±6.02 dB HL。
三组儿童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80,P>0.05,χ2=4.61,P> 0.05),干预组患儿裸耳听力水平与未干预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4,P> 0.05)。
1.2方法
1.2.1干预前听力评估 进行常规耳科检查排除外耳、中耳病变后,在隔声电屏蔽室中进行声导抗、声场下行为测听(采用纯音或啭音对能配合检查者)、听性脑干反应(ABR)、 耳声发射(OAE)、听性稳态反应(ASSR)等多项主、客观听力学诊断性检查,并结合头颅CT、MRI等影像学检查,得出诊断结果。以声场下纯音听阈测试作为听力障碍程度分级依据,如不能获得纯音听力图则以ASSR的校正听力图进行听力障碍程度分级。按照WHO1997年推荐听力障碍分级标准,以较好耳500、1 000、2 000、4 000 Hz的平均纯音听阈为分级标准,26~40 dB HL为轻度,41~60 dB HL为中度,61~80 dB HL为重度,≥81 dB HL为极重度。
1.2.2干预后听力评估 声场环境下行为测听(声场下纯音测听或视觉强化行为测听,采用美国GSI 61型听力计,专人在隔声室内进行测试。两侧扬声器与受试者头部处于同一水平面,成45°角,受试者距两侧扬声器1米。测试500、1 000、2 000和4 000 Hz 的啭音听阈。声场行为反应测听按照GB/ T 16403 的测试方法操作[6],隔声室的准自由声场按GB/ T 16296 的标准设置[7],并经声级计校准确定参考点。患儿助听器和人工耳蜗语言处理器的音量大小与日常所用一致。
1.2.3语言和发育评估 采用Gesell发育量表对各组儿童进行语言和发育评估,测试内容包括动作能、应物能、语言能和应人能4个方面,结果以发育商(development quotient,DQ)表示[8],DQ≥86为正常,76~85为可疑,≤75为异常,本次测试只采用语言能部分。评估由专职儿童保健科医师承担。排除智能迟缓、孤独症、广泛性发育障碍等器质性和精神疾患。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对各组平均听阈和语言能DQ得分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
各组裸耳平均听阈、干预后平均听阈、平均干预时间、DQ得分见表1。
干预组干预后平均听阈比未干预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中PHA组平均听阈最高,与其他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未干预组平均听阈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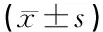
表1 各组裸耳平均听阈、干预后平均听阈、平均干预时间、DQ得分比较
注:*与干预组中其他各组比较,P<0.05;△与其他各组比较,P<0.05
干预组平均DQ得分比未干预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中PHA组DQ得分最低,与其他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未干预组平均DQ得分比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不同干预组间DQ得分比较发现,MHA组、SHA组与PCI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PHA组平均DQ得分在干预组中最低,与其它三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干预S+P组平均DQ得分在所有组别中最低,为57.63±26.96分,与其他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
3 讨论
0~3岁儿童是大脑及神经系统发育最快的时期,也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8],正常的听力是语言学习的前提[9]。听力障碍儿童如果在这一时期得不到及时干预和语言环境的刺激,轻者会出现语言发育迟缓、发音缺陷、学习困难和社会适应能力低下等问题,重者会导致聋哑。此时进行听觉语言干预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听力损失对儿童发育的影响。
本研究中干预组和未干预组儿童裸耳平均听阈无显著性差异,而干预组干预后听力水平和语言发育商比未干预组明显好(P<0.05),且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早期干预改善听力有助于语言能力的发育,使其基本接近正常儿童语言能力水平,说明新生儿听力筛查和早期干预对听障患儿语言发育很有帮助,与以往报道一致[10]。
目前对于中度及中度以上听力障碍儿童进行干预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助听器验配和人工耳蜗植入。助听器对于中度及部分重度听力障碍患者有良好的效果,能帮助听障儿童的语言发育,但其增益是有限的,必须在有一定残余听力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对于极重度和部分重度听力障碍患者效果很差。人工耳蜗是人工制造的电子听觉仿生装置,通过刺激重度或/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障碍患者的听神经纤维,使其获得听觉,进而恢复言语交流能力,重返有声世界。对语前聋儿童而言,人工耳蜗已成为其听力语言康复的重要手段。通常对于双耳重度或极重度听力障碍患者,不能受益于特大功率助听器且病变定位于耳蜗者,如无手术禁忌证,可以选择人工耳蜗植入。对于小儿患者,最小者年龄在12个月即可行该手术,在些特殊情况下,手术年龄还可以再提早数月。
Gesell量表作为3岁及3岁以下儿童发育状况的评估方法已经应用多年,是一种成熟的方法,采用Gesell发育量表中语言发育商作为一种语言发育评估方法,既可以有效的进行语言发育状态的评估,又有利于进行统计学分析。本研究中MHA组、SHA组与PCI组的语言发育商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这几组小儿的语言能力已经基本达到正常水平。PHA组的语言发育商低于其它三组,但高于未干预S+P组,说明助听器干预对中度和重度听力障碍者以及人工耳蜗干预对极重度听力障碍者都能够满足语言发育对听力的要求,但验配助听器对极重度听障患儿而言不是最佳的干预方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极重度听力障碍助听器干预组与人工耳蜗干预组裸耳听力基本相同,但PHA组语言发育商显著落后于PCI组(P<0.05)。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这两组平均干预时间和干预后平均听阈有明显差别,这是因为两组患儿都是从出生后6个月内开始干预,而两组患儿的平均年龄不同故平均干预时间不同,Gesell语言发育商是以同龄正常儿童的发育为基准评估相应年龄组患儿的语言能力,故消除了不同发育年龄(或者说上述的平均干预时间)对结果的影响,因此两组间的语言发育商数值具有可比性。而由于助听器干预的局限性,PHA组佩戴助听器已经无法再进一步提高其助听听阈。因此,两组之间语言发育商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预方式的不同,说明极重度以上听障患儿人工耳蜗植入后听力改善效果大于佩戴助听器,人工耳蜗植入更适合于极重度听障患儿。
本文结果说明听障儿童不仅需要早期诊断和积极干预,而且选择最合适的干预方式是获得良好语言水平的重要保证;对极重度听障患儿而言,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人工耳蜗植入是目前最合适的干预方式。
4 参考文献
1 王秋菊, 倪道凤. 早期听力检测和干预项目的原则和指南——美国婴幼儿听力联合委员会2007年形势报告[J].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08, 16: 359.
2 Judith EW,Warren RB,Richard CF.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what it means for providers of early intervention services [J]. Infants Young Child, 2003, 16: 249.
3 Yoshinaga-Itano C, Sedey A, Coulter D, et al. Language of early-and later-identified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J]. Pediatrics, 1998, 102: 1 161.
4 Moeller MP. Early intervention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ho ar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J]. Pediatrics, 2000, 106: E43.
5 Kennedy C, Mc Cann D. Universal neonatal hearing screening moving from evidence to practice [J]. ArchDis Child Fetal Neonatal Ed, 2004, 89: F378.
6 GB/T16403-1996声学. 测听方法. 纯音气导和骨导听阈基本测听法[M].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1997.
7 GB/T16296-1996声学. 测听方法. 第二部分. 用纯音及窄带测试信号的声场测试[M].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1996.
8 张风华, 金星明, 沈晓明, 等. 听力障碍婴幼儿语言、语音及认知的早期干预[J]. 中华医学杂志, 2006, 86: 2 836.
9 沈晓明. 新生儿听力筛查[J]. 中华儿科杂志, 2002, 40: 56.
10 李蕴, 吴皓, 陶铮, 等. 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儿早期听力干预效果分析[J].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08, 16: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