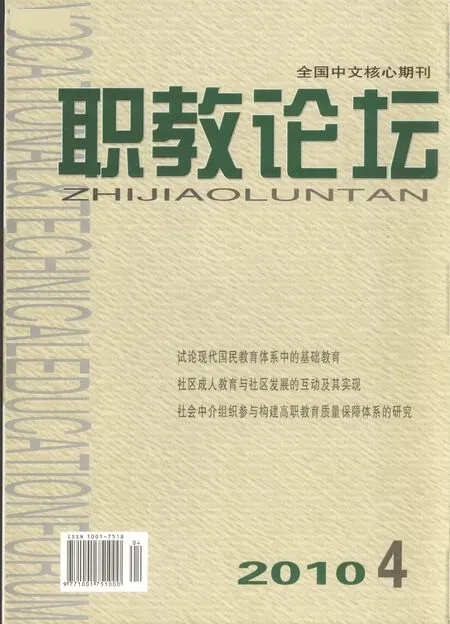民国时期劳工教育制度建设及其影响
□李 忠
本栏目由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课题组协办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制度建设及其影响
□李 忠
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民国劳工教育可划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劳工教育无法律而有相应制度,劳工教育实施视企业主或行业负责人对劳工教育与企业发展关系的认识程度及劳工对教育的需求程度而定,带有自发性特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大批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实施细则,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法律体系,并建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职能部门,承担劳工教育职责成为企业的法定责任,劳工教育带有强制性得以普遍展开,并取得一定成绩。然而,由于劳工教育法律本身及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最终使劳工教育走向自己的反面而陷于失败。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失败,不意味着劳工教育没有成功的可能,民国时期劳工教育中积淀的思想资源和域外劳工教育的实践经验,为今日劳工教育的成功提供有益参照。
民国;劳工教育;法律;述论
劳工问题是缘起于产业革命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到20世纪初,中国劳工问题“渐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中国劳工问题之解决,在目前已不容忽视”。[1](P序1)劳工问题涉及工厂法、劳工运动、劳工福利等一系列问题,解决劳工问题有改良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实施科学管理等多种方案。由于劳工生产能力与劳工地位、劳资关系及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因此劳工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提高劳工的生产能力,劳工教育被当作解决劳工问题的主要方式和根本手段,“劳工问题,在世界各国均极为迫切,其解决途径不止一端,然成年劳动教育之设施,实为根本之企图,各国对此方面之努力,均已有相当效果可观。”[2]“我们要工人问题彻底解决,必须要切实实行劳工教育,尤其是劳工保险、合作等事业的设施,实有赖于劳工教育为之先驱。于是劳工教育遂成为劳工事业之中心,因之劳工教育的声浪日高,劳工教育的潮流日盛,渐成为重大的问题。 ”[1](P228)劳工教育在民国时期逐渐受到重视,出台了系列法律、法令,作为实施劳工教育的依据,地方政府颁行大批实施细则,使得劳工教育得以广泛开展。民国时期的劳工与今日的农民工具有同质性,本文旨在对此做出初步分析,以期为今日农民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些许参考。
一、民国早期的劳工教育制度
由于中国古代信奉 “道成而上,艺成而下”的“重道轻艺”观念,这种观念与“学而优则仕”的取士制度、“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相结合,使得主流或正规教育机构中极少有技术教育的成分。然而,技术又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加之,“在任何情况下职业学校都不可能培养出熟练工人”,“像技工教育之类,如果不同工作场所有密切合作的话,是无法获得成功的。”[3](P279)所以,中国固有的技术教育和商业教育以学徒教育的方式加以传承,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学徒制。“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来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4](P200)“中国商人向无商业学堂肄习经商一切,故凡为商者,悉系父传子受,师传其弟。”[5]明清以来,学徒制更为严格,学徒教育也更加规范,学徒的招收、培养、出师等都有严格规定。学徒制在保持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和商业经营管理知识方面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由于学徒制本身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等缺陷,致使学徒教育的效果受到较大抑制。以至于近代以来,在应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中开始试办新式企业时遇到严重问题,近代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的失败,即是科技人才缺乏的直接后果。“吾国人士,素轻工商,业之以为耻,是以工商之教育全无,奈之何其不蚕食于外人乎!”[6](P152)所以,近代以来劳工教育制度变迁首先从对学徒制的冲击与突破中开始。在实践层面,对学徒制度突破从设立洋务企业与工艺局两个方面展开;在制度层面,清末新政过程中颁行的《癸卯学制》对学徒教育做出规定,标志着政府从制度层面开始关注学徒教育,使得学徒制发生重大变化,并为学徒教育的改造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期,新成立的商会组织开始改造行会制度,由此引发对原有学徒制的突破。
民国建成后,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企业性质的变化,对产业工人的素质和规格提出新的要求,关于劳工教育的呼吁不绝于耳。在1912年全国工商会议上,涉及到劳工教育的提案有:《推广模范工厂及养成职工案》、《普及工商业教育案》、《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兴办工商矿业专门人才案》等;1914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关于劳工教育的议案有:《速兴办商学以储商业人才案》、《讲求商学案》、《出洋学习工商各处创办商学案》、《限制商界学徒资格案》、《拟请商会劝各业多设商业学校案》等;1916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涉及劳工教育的议案有:《请政府倡办商业薄记学堂以谋薄记统一案》、《请创办中华全国商业联合会函授学校案》等。在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中,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提出 《强迫职工补习教育办法案》,其理由是:(一)我国本为农国,工人主要来自农村,在小规模家庭工业的手工技艺者,称之为艺徒;在大规模厂场学习新式机械工业者,成为职工,人数最多,中国工业的盛衰,实操于此辈之手。然而,经验有余,学术不足,如不亟谋此辈之教育,无论大学、专门、甲种工校之教育如何发达,譬之有将而无兵,断不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欲执世界工业之牛耳,不过付诸空谈。因此提议效仿德国,实施强迫艺徒职工教育办法。(二)今日言工业教育者,仅知造就新人才,而不知造就新职工,循至有技师而无助手;欲救此弊,非造就新职工不可,尤其是授以现从事生产之职工以相当之新知识或新技术。(三)强迫对象不仅限于艺徒、职工,还包括匠师和雇主。建议教育部颁布强迫教育办法,责成各公司厂场及工业团体,在营业费或会费内挹注,为附设职工或一如补习学校之经费,或资遣其工徒入实业学校及其他团体附设之此类学校,严于督责,勿令规避。凡设立此类学校且成绩优良者,给予奖励并补助之。于强迫之中,寓劝诱之意;(四)艺徒职工教育有一大障碍,即国民教育尚未普及,而普及国民教育非一时之功,当务之急是变通施教之方,招工徒中注明书算者入学,徐图进步,不可因噎废食。[7](P26-27)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钱天鹤在《提倡艺徒教育案》中指出:我国艺徒人数既多,所受教育又问题重重,亟需改良。改良之方在于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其一,政府出台法令,凡旧式手工场场主,应许年在十八岁以下之艺徒,有赴市县乡立艺徒学校上课之时间,每年受学若干小时,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如识字、写算、公民常识等)、职业教育(如本业所含学理及如何改良之类)、体育等。其二,办理艺工养成所,养成手艺工人;其三,由地方当局在工业较为发达之区设立艺徒学校若干所,招收艺徒入校学习。提案者认为,艺徒学校兼有职业学校及民众学校之长,艺徒人数众多,其效果也著。[8](P417-419)这些提案虽没作为制度被固定下来,但引起政府、企业对劳工教育的重视,为劳工教育法律的制定创造了条件。
伴随舆论的呼声,一些企业和行业开始主动突破原有的学徒制,实施劳工教育并形成相应制度。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商业银行等企业中开始创建教育设施,实施与以往学徒制不同的劳工教育,其中典型者是交通部所属各铁路段的劳工教育。早在清末,铁路系统即在各路段设立教育机构,如1909年4月创办了道清路工匠夜学校,同年8月京奉路唐山制造厂机器练习生处,9月创办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余夜课处,1911年3月京汉路在长辛店机场设立长工夜学所,等等。1917年12月,时任交通次长的叶恭绰等人鉴于各路沿线员司子女无处就学,遂联合京汉、京丰、京绥、津浦四路同人组成《铁路同人教育会》,拟定会章、章程及计划书呈报交通部核准。并言:“近世国际竞争炫人耳目,而究其根本政策,无一不基于教育普及。我国财用困穷,教育不振,遽求普及,势所难能,是非集合团体各谋部分教育,将终无起色之日。查日本南满等路,所设普通学校,兼营教育事业,我国铁路日多,地方既广,所有职员子弟往往无处就学,虽间有一、二路附设学校,然规模较狭,造就无多。同人等筹商再四,拟组织铁路同人教育会,以专司铁路团体教育事务,并于适当地方均立高等以下各级学校。”[9](P12)得到准许后,于1918年2月24日在北京召开“铁路同人教育会”成立大会,议决《铁路同人教育会章程》。1920年10月,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为增进职工的知识技能、培养职工的道德、提高职工的人格,设立铁路职工教育筹备处,在津浦、京汉、京奉、京绥四路各设职工学校三所,在工人较多路段创办演讲所四十所,并招收具有师范或专门学校毕业者96人入职工教育讲习会,以培养职工教育师资。1925年5月筹备工作完成并予以撤销,同时成立 “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该会职责除办学校、编教材、制图表之外,还有演讲、编辑出版《铁路职工教育旬刊》等事务,并逐渐形成包括劳工子弟教育、劳工教育、劳工师范教育、派出留学等劳工教育体系,形成比较完备的铁路劳工教育制度。[10](P12-13)叶恭绰指出:“吾国路工,未受教育,故工作效能低而损失亦大。此就国家生产力计,职工教育,实不容缓。”[11]并对劳工教育充满期望:“劳工问题应宜从根本上主张教育主义,起意固不仅在铁路职工以相当之教育,即对于全国劳工亦冀以教育之方法加以陶冶,使成为健全之国民,并希望世界劳动程度幼稚之各国,咸以劳工教育为培植劳工生活之基础。”[12](P3)铁路交通系统的职工教育在北洋政府时期具有典范作用。
劳工教育呼声与劳工教育实践遥相呼应,引起政府的重视并为出台相应制度创造了条件。1913年工商部指出:“以素缺学识之人,骤然为专门企业之事,工厂之组织所不知也,技术之研究所未习也,工徒之管理,营业之扩张均所未尝从事也,一旦而与外人立于对峙竞争之地,虽欲不败,岂可得乎”。[13](P2764)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政府开始制定劳工教育制度。1913年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指出:实业补习学校分农工商等种类,“为已有职业或志愿从事实业者授以应用之知识技能,并使补习普通学科”,“实业补习学校教授时间,不拘寒暑昼夜,以便捷学生教育为原则。”[14](P741)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商人通例》,对学徒培养、使用以及学徒与师傅之间的关系做出详细规定。首先,“商业学徒之修业,以契约定之”,在“修业契约前,得定试验期间,其期间至多不得过三个月。”以契约的形式规定商业学徒的修业,使学徒培养成为商业使用人的义务,并不再受行规的限制;其次,学徒培养应以本业为主,并要学习普通知识,“商业师应注意其本业之修习,使服其业务,又应予以通学之时间”;再次,明确学徒与业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学徒与业主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契约只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场所有效,契约到期,商业主人“不得因此限制致阻碍商业使用人事业之发达。 ”[15](P173)《商人通例》的颁布,大大突破以往学徒制对学徒的限制,使学徒获得较大的人身自由。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暂行工厂通则》,将“男子未满17岁、女子未满18岁者”定为幼年工,要求使用工人在100人以上的工厂主对幼年工在“本厂内予以补习相当教育并负担其费用”,每周至少应有10小时以上的教育时间。[16]这些规定虽然因为缺少相应的具体措施而多流于形式,但是对学徒教育的近代改造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
民国早期,虽然开始形成劳工教育制度,但在实践层面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视行业与企业对教育的依赖程度及其负责人对教育的认识程度而定。由于企业发展事实上依赖于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学技术人才,企业中出现了大批劳工教育设施,这种设施虽然处于对传统学徒制度突破与改造层面,但切合近代以来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并积淀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这些经验和资源为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劳工教育法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大批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和实施细则。按其目的和内容,可以分组建劳工教育管理机构法、劳工教育基本法、劳工教育实施法、劳工教育实施辅助法、劳工教育实施细则等,形成劳工教育法律体系,为劳工教育的实施和推广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使劳工教育带有强制性特点。
组建劳工教育管理部门的法律、法令。此类法律的颁布,标志着政府和立法机构开始参与劳工及劳工教育事务,并组建相应职能部门作为管理机构,包括全国性的劳工管理机构和专门负责劳工教育的职能部门。1927年8月7日立法院公布《国民政府劳工局组织法》,该法要求依本法组建劳工局,劳工局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依法管理全国劳工行政事务,下设总务、行政、统计三个处,其中行政处负责管理劳资争议的调解、仲裁,劳工教育;劳工卫生及保险等事项。该法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第一个针对劳工的法律,标志着政府从立法的角度参与劳工教育的开始。1931年5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为“促进劳工教育、增进工人知识”,颁布《实业、教育两部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依法组建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负责全国劳工教育统筹规划与管理。[17](P85)为保证劳工教育顺利实施,教育部与实业部于1935年11月1日颁布《各市县劳工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各省工业发达之市县,由省政府依本规程组织各市县劳工教育委员会,主管机构在市为市政府,在县为县政府,隶属于行政院之市为社会局及教育局。各市县劳动教育委员会以研究及促进当地劳工教育之实施为宗旨,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负责当地劳工教育事宜。[18](P258-259)另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劳工教育管理机构还包括国民党党部、地方社会局以及教育局的社会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此类法律、法令的颁行,不仅为成立相应部门提供了法律依据,并由此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管理机构。
劳工教育的基本法。为保证劳工教育有法可依,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31日颁布《工厂法》,正式规定工厂需使劳工受补习教育,违者处以百元以下罚金。随后,《修正工厂法》对此做出进一步规定:工厂对于童工及学徒应使受补习教育,并负担起费用之全部;其补习教育之时间,每星期至少需有十小时;对于其他失学工人,亦当酌量补助其教育;工厂所招学徒人数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一,当工厂所收学徒过度,对于学徒之传授无充分之机会时,主管官署得令其减少学徒之一部分,并限定其以后招收学徒之最高额;工厂对于学徒在其学习期内,须使职业传授人尽力传授学徒企业所定职业上之技术。[18](P107)为保证这些做法能得到切实执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又出台 《工厂检查法》、《工厂检查人员养成所规则》、《工厂检查人员养成所办事细则》与《修正工厂法施行条例》,对工厂法规定内容进行进一步细化,其中,后者在第十三条要求:工厂据本工人及学徒之补习教育时,应将办法及设备呈报主管官署,并应每六个月将办理情形呈报一次。[18](P111)《工厂法》及随后颁行的相关法律为劳工教育法令地出台及劳工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劳工教育实施法。1928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实施劳工教育》议案,在此基础上,工商部依据国民党 “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教育机会均等”及世界劳动运动之“三八制”,颁布《工人教育计划纲要》,并在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京、青岛等工业发达地区,开始大批成立劳工学校。“为增进工人之知识技能及其工作效率并谋工人生活之改进起见”,实业部会同教育部于1932年1月公布实施了 《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劳工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各地方应于最短时间内按工人教育程度分别实施;由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负责完成之;各厂、场、公司、商店等雇佣工人在五十人以上二百人以下者,应设劳工学校或劳工班,工人每增加二百人即递增一班,其不满五十人者得与附近之厂、场、公司、商店联合办理之,每班学生额数以三十人至五十人为准;劳工教育除学校教授各种科目外,举行工友访问、讲演会及展览会;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教学须在工作时间以外,每班每周至少八小时,教育时间最长不超过两年;劳工学校或劳工班对于毕业生应作校外修业指导,并设法尽量供给其自修教材;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费用由原设立机关担负,其联合办理者应共同担负之;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收学费及其他费用,所有书籍文具等均由学校供给之;各厂、场、公司、商店等于本办法大纲公布后六个月内不遵照设置劳工学校或劳工班者,除依《工厂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办理外,仍限令两个月内筹设成立。[17](PP82-84)《大纲》成为专门针对劳工教育实施的中央法令,指定各厂、场、公司、商店等成为劳工教育实施的主体,受教育成为劳工的福利,从而使得劳工教育带有强制和免费特点。同期,铁道部公布了《铁道部实施铁路职工教育计划纲要》,对铁路系统职工实施劳工学校教育和补习教育做出规定,随后又公布实施了《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铁路职工学校教育实施暂行通则》,对铁路系统的职工教育做出详细规定。为保证劳工教育有效实施,实业部与教育部还出台《劳工教育实验区组织章程草案》十四条,不仅划分出劳工教育试验区,而且对试验区劳工教育的具体实施环节做出细致规定。
劳工教育实施辅助法令。为了提倡劳工教育并使劳工教育得以普遍实施,南京国民政府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0年出台了《工商职工俱乐部计划大纲》、《工会法》、《工会法实施法》、《劳工教育奖励规则草案》。其中《工商职工俱乐部计划大纲》规定:凡雇佣职工在三十人以上之工厂、矿厂、公司、商店均应设立职工俱乐部,俱乐部以提倡高尚娱乐、改进职工生活、养成团结互助精神为宗旨,俱乐部事业分为体育、娱乐、智育、服务等四大类。每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如智育事业包括图书阅报、职工补习学校、职工子女学校、识字牌、幻灯识字、讲演、党义或学术研究会、学艺或工艺展览会、参观会、职业指导、发行刊物等事项或活动,以图劳工教育普及。[18](PP282-287)《工会法》“以增进知识技能,发达生产,维持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为目的”,规定工会应当办理以下工人福利事项:职业教育及其他劳工教育,图书馆、阅报室,出版刊物、杂志,交谊会、俱乐部及各种娱乐游戏。《工会法施行法》对此做出进一步规定,《劳工教育奖励规则草案》规定,视厂、场、公司、商店、公私团体所办劳工教育之成效,由实业、教育两部予以适当奖励。
劳工教育实施细则。劳工教育实施细则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制定并付诸实施,旨在细化中央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使其具有操作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相关地方法规,对劳工教育涉及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这些细则对中央颁行的劳工教育法令进行细化,如《浙江杭县劳工教育实施办法》规定,“各区应于最短期内按工人教育分别实施”,由“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17](P141)在上海市社会、教育两局联合颁布的 《上海市劳工教育实行细则》规定:本市各厂场公司商店等雇用职工在50人以上者,应该设立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满50人时,可将职工送往市私立劳工学校或其他学校附设劳工班学习。[19]《上海市立职工补习学校简则》规定“各校每日上课一百分钟,上课时间以不妨碍职工校外工作为原则”;《重庆市工人夜课学校章程》要求: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工徒均得入校修业;《察哈尔省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施行细则》指出:劳工教育的对象年龄差别不超过二十岁,其过老、过幼者应分班分组教授;学生上课时间,各厂、场、公司、商店不得减扣其工资”。[17](P144)企业是劳工教育实施的主体,一些工厂也颁布了劳工教育实施细则,如《湖南第一纺纱厂实施工厂法暂行细则》规定:本厂设有工余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凡在厂工作之童工、学徒、失学工人及其子弟得入校补习;《河南各县平民工厂章程》规定:工徒学习期间以一年为限,但同时只准专习一科。[17](P79)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实施细则,使得劳工教育有法可依。在形式上,劳工教育成为企业的法定责任也成为法律赋予劳工享有的福利;劳工教育职能部门的组建及劳工教育实施主体的明确,使得这种法律规定具有实施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些法律、法令的颁行,体现出劳工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对劳工教育的重视。正如时论所言,“实业、教育两部的各项计划,虽则尚未见诸实行,但是对于劳工教育的重要,可谓已有深刻的认识和注意。”[20]对于铁路系统颁布职工教育法令以来所取得的结果,则予以积极肯定:“铁道部于1932年春开办铁路职工学校,实施职工教育,两年以来,实施之效果,虽未能全部达到吾人所希望之圆满成绩,然各路文盲之减少,以及职工知识与技能之逐渐提高,亦即中国劳工教育史上之最大收获。 ”[21]
三、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实施的效果及其存在的问题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和实施细则的颁布与施行,取得了显著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体现在劳工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备、劳工教育职能部门的组建、劳工教育制度的形成上,为劳工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而且体现在劳工教育实施主体的明确与大批劳工获得教育机会,在提高劳工知识技能水准的同时,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积极作用。同时,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劳工教育从自发性走向强制性。这种变化,使得劳工教育偏向政党和政府的意图而非作为应该受益的劳工本人的意愿,劳工教育最终走向反面。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没有使得中国社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了社会性质的变化。
(一)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实施的成效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实施的成效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就劳工教育法制建设而言,取得明显效果,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劳工教育法律体系并以此组建了教育管理机构。正如上文所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颁布了劳工教育基本法——《工厂法》,并以此为基础,出台了劳工教育实施法、劳工教育实施辅助法、劳工教育实施法细则,由此形成以劳工教育为中心的劳工教育法令网络,为劳工教育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就劳工教育法律自身建设而言,即使今日中国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依据法律,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管理、指导机构,形成劳工教育管理体系,使得劳工教育制度日渐完备,为劳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使劳工教育不仅有法可依,而且具有了可操作性。劳工教育法律体系和职能部门的组建,体现出劳工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正如时论所言:在实际上,劳工法上所规定的一切标准,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大多数工人的地位,是没有改善。但是,在劳工法里面,已经明白规定了关于工人福利的条文,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P281)
其次,就劳工自身而言,劳工教育法律的颁行,使得接受教育成为劳工的福利,大批劳工获得受教育权力。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法令的颁布,使劳工教育带有公益性、强制性,从而带有义务教育的特点,“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费用,由原设立机关负担;其联合办理者,应共同负担之。 ”[17](P82)在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参与前提下,民国时期劳工教育在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所属的各个企业全面展开,成为全国范围的教育活动。民国时期劳工学校统计数字误差极大,据1933年山东省统计,省内设立劳工学校25所,而同期仅青岛就有劳工学校32所之多。[22](P179)实业部对此甚为惋惜:“本部一再向各行政当局方面搜集是项资料,乃结果答以本年均无调查,遂致无从觅得,至为可惜”,“查上海为吾国第一工业区域,各工厂雇主或工会所办之劳工学校,当属不少。”[22](P205)据1936年5月《国际劳工通讯》对上海从1935年8月到1936年2月的补充调查,上海“约有400多个劳工学校,分742班,学生人数35116人”。若加上其他未做统计的地区,全国范围内接受劳工教育的人数当非常可观。劳工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学徒,还包括已经出师的学徒、成年工人和劳工子弟。重庆市规定“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工徒均得入校修业”;上海市规定凡“本市区域内(四十五岁以下)不识字之工人一律受识字教育,……如至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以后仍未受识字教育者,应即日勒令停止工作”;青岛市则将全部工人纳入教育对象,“各厂工人均须一律入校学习,不得藉故规避”。[17](P144)大规模设立劳工学校,对提高劳工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水准起到推动作用,改善了劳工的素质结构并提高了劳工的觉悟,对教育普及以及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做出可贵探索。
再次,对企业而言,在获得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劳工教育法律规定,企业是实施劳工教育的主体,实施劳工教育是企业的法定责任。这种规定,不仅为提高企业职工智能水平从而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以及企业文化的形成营造了氛围。《工厂法》规定:“工厂对于童工及学徒应使之受补习教育,并承担其费用之全部。”[23](P64)《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规定:劳工教育由“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17](P84)由此出现了一批有特色的企业,其典型如教育型企业——民生公司,产学研结合的荣氏企业,兼顾工厂与学校教育优势的“学校化之工厂”与“工厂化之学校”——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带有体系化的劳工教育特点的行业——铁道部所属各路段公司。民生公司能成为近代中国最大船舶公司,劳工教育是重要因素,用卢作孚的话来说,“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而被誉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荣氏企业负责人荣德生,从1906年开始兴学活动,随着事业的发展,劳工教育设施颇为完善,其养成工制度曾流行一时,仅申新三厂举办的就有职员养成所、女工养成所、机工养成所、职工子弟学校、工人晨夜校、大礼堂、图书馆、阅报室、尊贤堂、功德祠等教育场所和设施,教育男女工人三千多人,效果卓著。1936年6月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陈海峰陪同国际劳工总局特派员伊士曼到厂视察后,以“规模宏大,组织完善,尤以关于工人福利事业之自治区,足树国内工业界之模范”为评价。[24](P737)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到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参观后,对其教育设施极为赞赏,称厂内设施“悉依科学管理法施行,甚为完备”,“尤以教育方面办理优良更为可钦可佩”,并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予以概括。
(二)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中的问题
民国劳工教育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在获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问题。这种问题既体现在法律本身,也体现在法律实施的环节中,更体现在劳工教育法律出台的意图上。其结果使得为提高劳工知识技能水准、改善劳工生存状况的劳工教育不断被异化,最终走向反面而陷于失败。
劳工教育法律中的问题首先体现在国民政府出台劳工教育法律的意图中。劳工的教育需求与企业的盈利本性相结合,劳工教育开始出现;政府的强力介入,使得劳工教育大规模展开。所以,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经历了由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为劳工教育在全国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本途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式是行为主体为国家政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政治目的选择制度安排的形式、规模和速度,可以利用政府权威动员更多参与力量,保证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优先发展某些重要事项,具有成本低、执行快等特点。劳工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即是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为谋文化、经济、政治在内的国民常识的普及,以法律、行政的方式,强制企业执行的结果,使得劳工教育成为全国性的教育运动,并取得一定成绩。然而,由于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来自外部,考虑更多的是政党意愿和政府利益而不是作为应当受益的劳工本人的需求,劳工难以分享到劳工教育带来的收益。所以,从劳工教育法律出台开始,劳工教育即开始被异化。时论分析政府颁布劳工教育法律时指出:“按其旨趣,专是督责厂场、公司、商店、公私团体去负责办理劳工教育,而仅由实教两部给予相当的奖励。我们细心考察,除认为是一种提倡劳工教育的手段以外,似乎觉得实教两部尚无决心去实行其他具体的计划,未免不无缺乏办理劳工教育的诚意。 ”[20](P72)
劳工教育法律中的问题还体现在劳工教育的内容之中。作为由政府主导、由各工商实体出资举办劳工教育,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将“三民主义”灌输于工人。在思想上,要“将三民主义融化于一切科学,使全体学员有深切之认识与信仰,并明了中国国民党之政纲政策及历次有关工运之决议”,“使学员认识国内一切反革命派及帝国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重要敌人”,“使学员明了共产主义之荒谬及违反三民主义之各种理论的错误。”[17](P72)根本目的在于抵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实现劳资协调,如青岛市就指出:“本市工厂林立,劳资阶级意识逐渐明显,尤非实施劳工教育纳入三民主义之正轨不足以消弭争斗之风而收互助之益。”[17](P141)国民党汉口市教育局对荣家申四、福五厂创办的 “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发出指令也称:“现在要他们明了劳资的共同利益,避免邪说的诱惑,应尽力办补习学校。”[25](P335)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致使劳工教育的目的不是通过提高劳工智能水平进而改善劳工生活状况和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而是通过灌输“主义”以消弭劳资纠纷,实现对劳工的控制,使其安心于学徒和工人地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如此一来,使得本身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陷于更为被动的地位。
劳工教育法律实施环节中,依然出现了问题。劳工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劳工也不同于一般学生。从劳工本身来看,中国工人工作时间过长,夜以继日,片刻无暇,精神不继,少有受教育的时间,此其一;其二,中国工人工资过低,每日工作所得之工资,不足维持一家生活。妻愁子泣,感到无限痛苦,受教育之兴趣亦减少;其三,中国工人组织散漫无纪。除少数有工会组织者得加以相当教育外,其余多无从着手;其四,中国语言文字的困难和不统一,一字数意、一意数字,非积年累月努力研求,难以应用,而工人受教育条件本身有限,也是办理劳工教育的困难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劳工本人被传统的陈腐观念所束缚,以为工人是天生的贱人,对于现实的生活,只求苟安,不思进取。是以在中国劳工界里多不愿去受教育,也没有多少人感觉有教育的必要。[1](P251)这种现实,加上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劳工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大受影响。由于大规模举办劳工教育是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作为劳工教育举办主体的企业同样不愿参与,尤其是技术要求较低的企业。时论指出:有人怀疑在工厂内实施劳工教育,必然加强劳工的团结,增加劳资对立的机会,削弱资方的力量。而更多的人认为劳工教育是多余的,因为厂内有聪颖的工程师、贤明的厂长等,指挥每个工人参加生产,已经足够了;尤其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办这种无谓的教育,是一种浪费。[26]因此,抵制劳工教育。
正如杜威在他的教育纲领中所坚持的:“我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基本方法,……所有的改革,如果只依靠法律的作用,或仅以某种惩罚威胁,或只借助机构和外部安排上的变动,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是无效的。”[27](P8)劳工教育的实施应该是积极的、启发式的,而非消极的、强制的,劳工教育的实施要以真正的民主政治作为实施前提;政治不民主,一切还是靠强迫、命令、独裁来维持,劳工教育问题仍不免落于空谈。[26]这样,以“增进工人之知识技能及其工作效率并某工人生活之改进起见”颁布的系列劳工教育法律,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陷于失败,致使中国社会的变革不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得以实现,而是通过劳工的暴力革命实现了社会性质的变革。
劳工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劳工教育被当作解决劳工问题的有效方式。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引发劳工教育的失败,不意味着劳工教育没有成功的可能。工业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形成了企业教育。企业是一个良好的教育场所,“首先是学习一系列技能,而且在这方面,工作具有培养人的价值,必须在大多数社会、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内得到进一步的承认。”[28](P98)前苏联的经验显示:企业中的教育以其不脱离物质生产领域,改善了国家劳动资源的利用,显示出很高的经济效率;企业内教育机构的学习人员参加物质财富创造过程,大大降低国民经济开支;企业教育直接发生在企业,学习人员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和磨合,大大提高办学效益。[29](P191)企业教育承担的职责已不限于技术和能力开发,开始拓展到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领导艺术等领域。企业已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不同于传统学校教育的教育场所,并获得以往只有传统大学具有的特权——颁发学位证书。美国著名教育史家克雷明将发生在工商领域内此类学习与教学体制的发展与体系化,称为“20世纪美国最为突出的教育发展成就”;[27](P539)日本学者细谷俊夫将企业教育与实施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和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并列,称之为“第三教育场所”。[3](P210)到今日,企业教育职能已被进一步拓展,成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与工业化国家“高技能、高薪水、全就业”的劳工教育政策相比,中国劳工教育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如何通过教育,将劳工、企业、政府三方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教育、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谐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摆在当前中国人面前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民国时期劳工教育中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都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需要予以重视。
[1]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M].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3.
[2]孟普庆.近代英国成人劳动教育运动史·序[J].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新声推广部,1930,(2).
[3](日)细谷俊夫著.江临丽译.技术教育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
[4]赵靖.穆藕初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商部奏为劝办商会以利商战角胜洋商折 [J].东方杂志, 1904,(1).
[6]乐农文史资料选.荣德生与兴学育才[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决议案[A].邰爽秋,等.教育参考资料选辑·教育史料类·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C].上海:教育编译馆,1936.
[8]钱天鹤.提倡艺徒教育案[A].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9]张毅,易紫.中国铁路教育的诞生和发展(1871-1949)[M].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10]卢鸿育.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成立的经过[M].铁路职工教育旬刊,1922(1).
[11]叶恭绰.总长叶恭绰发刊词[J].铁路职工教育旬刊,1922,(1).5.
[12]交通部.中国政府关于交通四政劳工事务设施之状况[M].北京:祁世宝印书局,1925.
[13]工商部发布天津商会速整顿棉纺业命令并〈调查纺织业报告书〉[A].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后编(1912-1928)[C]第3分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14]陈元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15]商人通例[A].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商业档案汇编(1912-1928)[C]第1卷.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16]暂行工厂通则[J].农商公报,1915(105),第9卷第9册.
[17]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M].第5编.南京:实业部,1933.
[18]顾炳元.中国劳动法令汇编[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
[19]申报.1934-1-13.
[20]王友智.普及劳工教育的方法[J].劳工教育·创刊号,1934,(1).71.
[21]王天觉.铁路职工教育之过去与现在[J].劳工教育·创刊号,1934(1).12.
[22]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劳动年鉴.第3编.[M].实业部,1934.
[23]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劳动年鉴.第4编.[M].实业部,1933.
[24]乐农史料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1896-1937)[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6]杜播.关于劳工教育的一点意见[N].新华日报,1945-2-7.
[27](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M].朱旭东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9]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M].(苏联—俄罗斯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王春桂
李忠(1972-),男,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教育社会学。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课题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问题研究”(批准号:EKA0702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G719.29
A
1001-7518(2010)04-008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