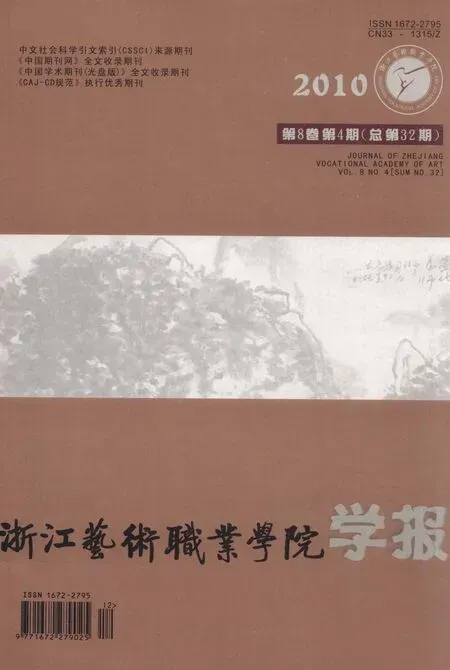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初探
杨曦帆
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
——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初探
杨曦帆
江南运河是中国京杭大运河在长江以南的一段,沿岸主要城镇包括镇江、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从民族音乐学角度看,民间音乐多受到与其相关的地理、历史、经济、民俗等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江南运河对于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流布也起到过重要作用。
江南运河;民俗;音乐文化
江南运河是京杭运河①在长江以南的一段。自“秦代所形成的江南运河,南起钱塘江畔钱塘县 (今浙江杭州),然后循今杭州上塘河东北而上,经临平、长安、崇德、嘉兴,再折而西北,经今江苏平望、吴江、苏州、望亭、无锡、常州、奔牛、吕城、丹阳、丹徒,北至镇江西北京口港与长江相通”[1]。这样,江南运河就北接长江,南接钱塘江,和金丹溧漕河、武宜漕河、锡澄运河、望虞河、浏河、吴淞江、太浦河、吴兴塘、平湖塘、华亭塘、杭甬运河等运河相连接,这既是江南河运的主干道,也是京杭运河运输最繁忙的航道。在历史上,航运曾经使一些重要码头非常繁华,京杭运河作为联结南北漕运的要道,对促进南北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产生了重要作用。运河沿线的镇江、扬州、淮安等既是著名漕粮转运口岸和商业都会,同时也是重要的民间游艺场所,各类传统音乐文化十分丰富。今天,尽管交通已经多元化,但江南运河仍然在起着作用。以前重要的商运口岸现在多变成繁华的城市,明清以来,江南运河沿岸的传统音乐也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江南音乐,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民间音乐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
一、江南运河文化的历史成因
江南,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理解。从字面上讲,本是指长江以南。从历史上讲,则是指自东汉以来,以建康为都城所形成的一个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朝诗人谢脁所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是其繁荣的写照。明确的“江南”一词源于唐代,包括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到清代以后,则逐渐的主要指以太湖为中心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
从地域上划分,江南运河属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一部分,起于镇江,通过苏州,止于杭州,全程330公里。占京杭大运河全程1794公里的1/5左右,也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最为富庶的地段。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运河开凿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与经济目的,特别是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运河的漕运功能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这也使得运河成为了历代王朝建都和稳定政权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后,漕运就几乎变成了历代政府将各地所征粮赋经运河运往京师或指定地点的专用名词。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漕运”作为朝廷最大的官运,一直是江南运河的重要内容。“元明清三代……京师用粮皆依赖江南。”[2]宋以来,以太湖为代表的江南核心地区的商货都是通过江南运河运至镇江,再继续向北方转运。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就是江南重镇无锡①四大米市分别为:无锡、九江、芜湖和长沙。。而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在历史上都是运河沿线富商巨贾云集的著名都市。从生产角度看,尽管运河的主要目的是漕运,但在保证漕运通畅的情况下,也给沿岸的农民生产提供水利之便,这也有力地保证了江南水乡丰富的物产。而人杰地灵、丰衣足食的环境,对于其间的文化风格必定有着根本的影响。
运河便捷的交通还极大地活跃了沿岸的商贸经济。沿岸码头多形成集镇与商业中心,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商贸最发达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这就如西方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在清中期,我们应该意识到江南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府邸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区域’,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3]。这种经济的崛起和城市的发展不仅使得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同时对于江南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人才荟萃,素有“金陵会稽,文士成林”之说。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外,江南运河在文化上也表现出多层面共荣的景象,不仅有明清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文人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也十分丰富。从音乐史的角度看,明清以来,以江南为代表的城市民间音乐已逐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文化之一。
二、运河民间音乐文化的民俗场景
江南以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所形成的民俗音乐文化与其他地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江南地区的无锡、苏州、扬州、杭州、上海、常熟和南京等地所兴起的音乐,既有相伴于城镇民俗活动而出现的小调、小戏、曲艺、戏曲等形式,也有因文人云集而出现的以古琴为代表的文人音乐,另外还有寺庙宫观的宗教音乐等。
从历史角度看,宋元以后,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和政治经济逐渐由西向东的转移,宫廷教坊乐舞渐趋式微。不过,紧跟着都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传统音乐却在民间演进而得到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比如,戏曲、曲艺、民歌中的小调等适于城镇的音乐形式渐成主流民间音乐。明清时期,随着都市音乐生活的进一步繁荣,民歌中的小调、俚曲、清曲,器乐中的丝竹乐器,各地的民间乐社,各类地方戏曲剧种、曲艺说唱等在都市、乡镇中得到很好的发展。起源于江苏昆山的昆曲,则成为了明、清戏曲的高峰。史书载,“乾隆六次南巡……迎驾必演昆剧”[4]。由此可见,昆剧在江南城市音乐文化中的代表性地位。除了昆剧,形成于明末清初,发源并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吴语方言区的用苏州方言表演的苏州弹词这种“小书”类曲艺说书形式也成为了人们喜爱的音乐品种,逐渐成为江南城镇音乐的代表。
从民俗文化角度看,自明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城镇得到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城镇不仅为市民阶层提供了生存空间,也同时接纳了乡村劳动力以及劳动歌曲等,比如,“流行于镇江一代的拉纤号子,一唱众合,其声凄婉。常唱‘张哥哥,李哥哥,大家用力一起拖。一休休,二休休,月子弯弯照九州’”[5]395。这样的劳动歌曲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城镇小调。城市的繁荣和人口的聚集都为以运河为纽带而带动的沿岸世俗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运河沿岸之各种“码头”也即为商业城市的起点。据杨荫浏先生考证,“码头”与“马头”为同音通假字,史传“马头调”即系泛指在码头上流行的曲调。[6]
对于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居住在杭州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诗称其为:“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其“笙歌处处楼”说明当时的杭州不仅城市繁华,而且城市中各类音乐已是十分丰富,这种繁华的城市民俗场景为传统音乐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江南地区家乐、家班开始盛行。明人顾起元所撰《客座赘语》载:
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
套北曲,乐器用筝 (上竹下秦)、琵琶、三弦子、拍板……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7]
这种明清以来的民俗“场景”说明了江南地区音乐生活的繁盛。从社会结构看,明清以降,江南士绅是“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8]。其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不仅逐渐建构了地方文化,同时也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
从乐器发展上看,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之乐器已较成熟。从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角度看:“先秦时期雅乐中盛行的弹弦乐器琴瑟,隋唐时期燕乐中崛起的弹弦乐器琵琶,元明时期散乐昆腔中领先的弹弦乐器三弦,晚清以来江南地方戏曲说唱音乐中普及的弓弦乐器胡琴。”[9]这说明,伴随着城市兴起的戏曲说唱中使用的弓弦类乐器已成为江南音乐的主要品种,比如昆曲之曲笛、乱弹之胡琴、坠子之坠胡、弹词之琵琶、琴书之扬琴、单弦之三弦,等等。另有大量戏曲曲牌逐渐演变为器乐曲。运河沿岸苏州弹词之表演音乐性强,说中夹唱,唱时多用琵琶、三弦伴奏,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个档”表演。在此基础上,将这些主奏乐器作为核心再编配出各具特色的戏曲丝竹乐队和说唱丝竹乐队。对于江南丝竹所用乐器,有学者从传播论角度指出,“近现代江南丝竹使用的乐器和乐器组合方式,是明清时期环太湖地区民间歌舞、戏曲、剧曲清唱和‘十番鼓’等多种表演艺术类型中丝竹乐器组合方式的继承与扩散”[10]。
从民俗文化的审美角度看,音乐表现的适当性、内涵性和音乐种类的丰富性一直是江南音乐的基本风格。从音乐种类的丰富性来看,不仅有具有代表性的、以凸显器乐为主的江南丝竹,也有徒歌形式的民歌,比如吴歌,即以民间口头演唱方式表演,口语化的演唱是其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
从音乐表现风格的适当性、内涵性来看,这一基本特征的形成也是和其地域文化的整体结构紧密相关的。“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取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它承认在一定范围内的要求是适当和必要的,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是浪费和奢侈。”[11]这种文化民俗观念对于江南音乐柔媚清新而又不失理性克制的风格形塑当有互动影响。
三、运河对于音乐文化构成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是江南运河的开创者,也是中原文化南下的传播者”。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唐代杭州城市开始崛起后,运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有学者指出,“杭州的文化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是时,这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杭州吸收北方先进文化的主要渠道”[2]52,58。显然,运河成为了民间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比如,原本是在杭州流行的歌谣“《东家囡伲爱长工》则采用了‘十二月花名’的传统曲调,用来讲述东家女儿与小长工之间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近现代以来,沿着运河一直向北,直至江苏境内”[2]193。不仅音乐的传承、传播受惠于运河,其他艺术种类也有相似情况。比如,天津的杨柳青年画,由于杨柳青靠着运河,在运河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年代,南来北往的客商、官吏把杨柳青年画带到了全国各地,有了便利的交通,也就有了市场。可以说,没有运河,也就没有杨柳青年画的久盛不衰。
江南运河沿线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既是著名的漕粮转运口岸和商业都会,同时也是重要的民间游艺场所,从城镇的空间结构来看,运河沿岸城镇都有自己比较丰富的娱乐场所,各类书市、酒楼、戏院十分丰富。这对于酝酿民间音乐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民国文献这样描述杭州民间游戏场所,“凡医卜星相,及捉牙虫卖草药,各色果点,各式摊场,皆罗列焉。又间以大书鼓道情隔壁戏花鼓调,以及各种游戏,终年如是,无间寒暑”[12]。
这样,运河就不仅是一条南北流向的,具有政治、经济意味的大运河,其所流经的地区,特别是江南运河段,更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各种河流、湖泊交错并列,水上交通线网状分布,不仅城镇间可通航,就是很多村与村之间也可通航。这种村村通航,舟楫往返无阻的水乡场景不仅孕育了富庶的江南,也孕育了以运河为基础的江南文化以及江南民间传统音乐。各种戏班、乐社大都也可通过水上交通便利地四处“巡演”。丰子恺先生曾回忆道:“戏班子远不及都会的戏馆里的那么出色,称为‘江湖班’,大都是一对演员坐了一只船,摇来摇去,在各码头各乡村兜揽生意的。他们的行头远不及都会的戏馆那么讲究,大都是几件旧衣,几幅旧背景,甚或没有背景。”[13]不少依靠水运而生活的民间艺人“以船为家,沿着运河水系,一路漂泊。每到一处,干脆就在自己的船上搭台,在这种被人们称为‘船台’的舞台上献艺。观众或在岸上看戏,或也坐了小船靠上去看戏”。或者是,“旧时在运河水系沿岸的城镇和乡村小镇上,每每有茶馆。艺人们在运河水系到处漂泊,就会去寻找这种茶馆,作为自己献艺的场所”[2]198,201。显然,茶馆既是市民休闲游艺欣赏戏曲音乐的场所,也是民间艺人传习民间音乐的重要领地。比如,“旧时,在苏南及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老百姓有坐茶馆的习惯,茶馆既是说书艺人的献艺谋生之处,又是广大听客的娱乐场所,苏州评弹与其他民间说唱也因之得到繁荣发展”[5]398。在历史上,“戏曲艺人在酒肆、茶坊中做场,宋、元时已有。不过那时是席前表演,并无特设的戏台。到了清代,在一些酒馆中开始设戏台,成为兼卖酒馔的戏曲演出场所。当时人们也称之为戏园或戏馆。此后,不少茶园也都改造成为设有戏台的戏园”[5]9。比如,清雍正年间的苏州郭园戏馆、光绪年间的无锡庆仙茶园等即是代表。在今天,无锡清名桥一带,从石桥、茶馆、窑址等痕迹仍可感受到过去的繁华。
当然,这种船上的音乐不仅仅限于民间,清代常熟画家王翚 (1632—1717)等人于1694年所绘《康熙南巡图》,画面显示为南京秦淮河花坊丝竹乐队为迎康熙南巡靠岸演奏丝竹乐曲情景。康熙皇帝玄烨曾于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 (1664—1707)的24年间,共6次南巡。《康熙南巡图·秦淮画舫细乐图》局部所绘即康熙第二次南巡至南京的景观场面。从画面可见,画舫载有九人组成的丝竹乐队,正奏乐于秦淮河畔,听者聚集岸边、楼台,静听品味。据辨认,画舫乐队可以识别的乐器有三弦、胡琴 (提琴)、笙、笛、云锣、擅板、小鼓七种,另两人所奏乐器不明。[10]另外,尽管同处于江南水乡,但城镇和农村在音乐风格选择上也还是具有审美上的差异性。有学者指出:“在当地城市和乡村流行的江南丝竹,在乐队配置和演奏风格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演奏丝竹乐时往往加用大件打击乐器,风格较为粗犷,旋律较为简朴;城市演奏丝竹乐则多精雅细腻、柔美流畅见长。”[14]
就民间艺术本身的生活依附性来说,围绕于运河的音乐文化的核心就是指与社会功能、民间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民间艺术。曲艺说唱便是一例,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形脱胎于茶馆文化,或者说肇始于江南的闲暇文化。从音乐风格上看,其风格柔和婉转,多以柔美秀丽见长,这样的音乐特色也是和其民俗场景相吻合的。又如江南丝竹也是如此,在风格上具有典雅、轻快、明朗等江南水乡风韵。
结 语
通过民俗与历史梳理可以确定,江南运河商业口岸的兴起以及人口的聚集促使了民间音乐的繁荣,民间音乐对运河沿岸的城市具有依附性。或者说,繁华的口岸滋养了民间音乐。
民族音乐学对于民间音乐的研究在方法上受到人类学、民俗学影响,强调全方位、全景式地“打量”研究对象。民间音乐的“民间性”植根于民俗生活,受制于历史地理背景、生活生产方式等因素。狭义的民间音乐与广义的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从传统民间音乐的角度管窥江南运河的文化意义,并从中总结出传统民间音乐与运河文化在学理上的关联,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江南运河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内在含义。
[1]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J].中华文史论丛,1979(2).
[2]陈述.杭州运河的历史研究[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
[3]林达·约翰逊.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M].成一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
[4]江苏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文化艺术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162.
[5]江苏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民俗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775.
[7]顾起元.客座赘语 [M].北京:中华书局,1959:303.
[8]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1368—1911)[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3.
[9]伍国栋.江南丝竹二胡源流与“声腔化”演奏传统 [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2007(2).
[10]伍国栋.江南丝竹乐队编制的历史继承与创新拓展[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2006(4).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1.
[12]胡樸安.中国风俗 [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69.
[13]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5.
[14]薛艺兵,吴艳.江苏传统音乐文化遗产区域分布调查统计 [J].艺术百家,2008(3).
Traditional M usic in Scenes of Folk Custom s—Probe into Folk Custom s and H istory of M usic Culture of Jiangnan Canal
YANG Xi-fan
Jiangnan Canal is a part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Themain cities along the canal include Zhenjiang,Wuxi,Suzhou,Jiaxing and Hangzhou.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musicology,folk music tends to be influenced by cultur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geography,history,economy,folk customs,etc..Jiangnan Canal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the folk music culture in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Jiangnan canal;folk customs;music culture
J607
A
1672-2795(2010)04-0037-05
2010-07-06
杨曦帆 (1969— ),男,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在站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学、艺术人类学研究。(南京 210013)
①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江南运河段指长江以南,即从镇江向南至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