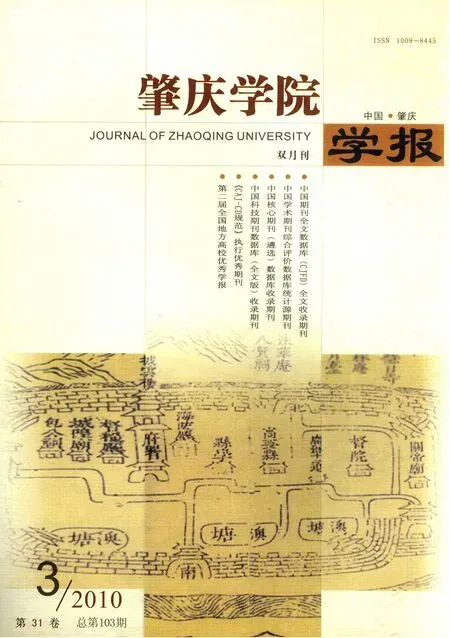机遇、挑战与文化自觉
李佩环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机遇、挑战与文化自觉
李佩环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中,全球化既为当代中国文化开启了新的精神之源,同时又使当代中国文化遭遇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化上做到自主、自知、自信与自觉,以全球性视界观照当代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关系,这是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关键。
全球化;文化交往;当代中国文化;文化自觉
全球化时代没有世外桃源。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处于普遍的文化交往关系中,任何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都必然涉及多元文化之间的交往。众所周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实践虽然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主导之下的文化交往实践,但同时也是多元文化自身发展与进步的“交往场”。因而,“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文化交往实践,自觉吸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参与不一定成功,但不参与则注定是失败。在当代中国,应该以这种“文化自觉”的心态来勇敢面对全球化的文化交往实践给当代中国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全球文化交往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精神之源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文化之所以悠长而强劲,正是由于它在与他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了他文化的优秀因子,使自身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更新。纵观中外文化交往史,中国文化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先后容纳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其中与印度佛教、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使传统的中国文化实现了华丽转身,形成了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同理,当代中国文化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定要在普遍建立的文化交往关系中借多极交往主体之镜而反观自身。这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文化交往的普遍建立,拓展了中华民族的视界,培育着交往主体宽容的文化心态,有利于建立和谐的文化交往关系,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不仅是由历史时间意识决定的,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同时也是由空间视域决定的,即通过与他文化的交往而得以拓展。“当今思想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而是要面对全世界,它就不可能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某些因素,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视野。”[1]文化交往的全球化,打开了文化主体的视界,使文化主体能够打破狭隘的民族性或地域性的视界,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环顾世界与审视自己,认识到自身文化只是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从而迫使自身摒弃那种狭隘的文化本质主义观念,走出偏执的文化中心主义,以全球意识关照自身,在多极文化主体的交往中取长补短。同时,在普遍建立的文化交往关系中,人们强烈地意识到,文化是人的“身份证”,人与文化并非工具性关系,人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就处于文化之中,而文化又始终只是人的文化,人与文化血肉相连。因而,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更新发展的任何文化皆有无限丰富的内涵,是不会从根本上被其他文化所取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交往就只能是一个基于宽容和理解来构建意义世界的过程。“文化是对话,是交流思想和经验,是对其他价值观念和传统的鉴赏。”[2]普遍的文化交往凸显着这一现实。只要尊重这一现实,和谐的文化交往关系就不会是困难,当代中国文化就能够在文化交往中顺利地发展。
全球文化交往是多元文化展示自身魅力的新平台,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辟着道路,为其发展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文化最早通过全球文化交往取得了世界性意义,它使整个时代处于现代化的漩涡之中。其主导精神是工具理性,集中于物质条件的完备。可以说,没有工具理性就没有现代社会。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日益张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文主义精神与工具理性精神以及精神自足与物质欲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不断激化,以至于人的物化状态本身成为人在意识与无意识层面反感和厌倦的生存处境。在这种情势下,西方现代性文化向后现代性转型。然而,后现代性并不反对现代性,而是在欣赏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绝对基础、唯一视角、文化中心主义等进行的解构。这种解构没有指向,不可能超越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伴随产品、批判性话语。现代性文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启蒙精神至今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现代性精神,因而这种文化的困境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困境。如此这般,对现代性文化的超越就必然进入一种全球性的视界。非西方的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应该成为这种全球现代性转型不可离弃的资源。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3]“以人为本”无疑是具有世界主义的价值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是拯救现代性文化危机的完备方案,而是旨在强调全球现代性转型(包括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应该是多元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相互调适的过程,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出现在全球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文化交往为当代中国文化提供了展示自己文化特质的舞台,搭起了通往世界文化的桥梁,同时也为其更新与发展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二、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交往中迎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支配性地位决定了它们在文化交往中的强势地位,而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现代化发展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上的不发达而只能在文化交往中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根据文化交往的信息流总是由高向低流动的普遍规律来看,这种“不对称”的文化交往给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
在当前的文化交往中,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都充塞着大量的西方现代性文化,文化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单向的文化输出,消解着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文化的单向输出使西方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可以渗透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全球性特征体现为“西方性”特征。特别是浸润着后现代精神的西方大众文化的扩张可以说是销蚀他文化精神的主要力量。后现代文化表现为无任何未来感的“这个思想的完结和那个主义的消逝”,是一种具有“决裂性”的文化逻辑。它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4]。它以大量的技术复制品从“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无孔不入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文化信息潮包围着我国的广大民众,把他们淹没在喧嚣四起的西方平民文化和由各种影像构筑的仿真世界中。文字让位于图像,思考让位于直觉,虚幻的形象置换真切的现实,形象化生存取代真实的生存,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失去存在的地盘,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广大民众的文化心态、知识结构乃至世界观,夺取社会文化生活的话语权。西方发达的大众文化具有较强的解构功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进行政治宣传、推行意识形态、审美文化及其素质教育的载体。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说:“只要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5]在人类文化交往实现了世界化和自由化的今天,这样肆无忌惮的文化输出无不彰显出拆解我国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意图。文化交往实践领域成为了新的思想文化斗争阵地,我国的主导文化价值观念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文化不仅具有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功能,它同时集消费功能、经济功能等于一身。在文化交往中,强势文化不仅冲击着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价值观,而且冲击着我国经济领域中新兴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大众文化产业化的产物,是以文化产品及文化活动为主体对象,从事文化的生产经营、开发建设、流通消费、有偿服务的产业门类[6]。在文化交往中,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成分,关系着一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文化作用于人的规模与范围;在经济发展系统中,它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的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当代中国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的需要,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才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初级性、艰巨性、不平衡性以及优长性等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文化产业是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桥梁和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发展的,目前已经超过了飞机、汽车等传统产业而成为出口的第一大产业。很显然,在文化交往中,交往主体之间的强势对比是明显的。2004年的中国行业发展报告指出,2003年我国累计出口书报刊766.05万册,总金额2 330.34万美元;而累计进口书报刊1 877.46万册,总金额达14 608.27万美元。出口音像电子出版物累计132.73万盒(张),总金额139万美元;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口累计104.02万盒(张),总金额达2 272.64万美元[7]。这些数据说明,在文化交往中,境外文化产品像“洪流”一样大量地或高额地流入我国文化市场,而我国流向域外的文化产品总体来说却像小溪一样的十分有限。这种状况不仅给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影响,而且给经济的发展也带来极大的冲击。
三、文化自觉:认识当代中国文化的秉性,适应时代的文化需求
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呢?费孝通先生提出并倡导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种对待人类文明的姿态,包含知性、理智、宽容、反思等诸多意蕴,是在全球文化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自主、自知、自信与自觉的主体意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意思,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目的不在于“文化回归”或“复旧”,同时也不在于“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在于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在实践基础上有机结合而成的当代中国文化来说,必须“知其所是”、明了其意义和价值。从当代中国文化产生、发展及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文化自觉有两个明显的关节点:一是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是全面了解与把握现时代的文化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可引导性,即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上,文化交往是其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对传统文化如何继承的问题是在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彰显出来的。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在西方现代性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传统文化何以整合西方现代性文化资源而创新呢?传统文化精神是这种创新的不竭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有: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键自强、以和为贵[10]。这些文化精神之所以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永动机”,是因为它们是文化变迁中传承与创新的焦点。尽管在不同时代文化精神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但它们始终能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因此,传统文化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是不受时代和地域限制的可适用于天下之通义。在文化交往中,传统文化精神尽显中华民族的本质与特点,并以其所蕴涵的生存智慧而走向世界而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坚持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就在于传统文化精神所具有的这种不断“膨胀”的生命力。不可否认,“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1]特别是经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铸造的中国传统文化,难免有许多历史的尘垢。由于这些尘垢在同一经济基础范围内繁衍传承数千年,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无所不在的、安身立命的文化本能,具有“超稳定结构”。在文化交往中,这种“超稳定结构”通常能够释放出包容一切现存、摧毁一切异端、铲除一切革新、同化一切差异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使文化精神的有效发挥被消解、融化、蒸发、变形与扭曲。因此,在文化交往中,文化自觉的必要性就在于充分认识到这种文化发展的阻滞力,从根基上对其进行干预,使传统文化精神的更新发展及其走向世界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当代中国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因而是一个可以自觉的过程。这种自觉性的动力源于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其要求在于根据时代的文化需求创造出一条真正切合自身发展的文化之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是遭遇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继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引发“西学东渐”的高潮之后,新文化运动又再掀中西文化交往的高潮。随着这次高潮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但是,较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无数“西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因为在众多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带来较少的文化震撼与文化错位。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是减少传统文化变迁阵痛的可选择范式。人类学家泰勒说:“人们所需要的不是高级的文明产品,而是某种适合于他们情况的和最易找到的东西。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接受新的文明和保持旧的文明。”[12]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随着全球文化交往的普遍建立,文化交往的需求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完善的根本立足点。如上文所述,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压力之下,尤其是对处于现代化建设初期的中国来说,这种压力特别突出。这种压力不仅在经济上表现为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而且在文化上有意识地潜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同化非西方文化的一厢情愿。这种情形给当代中国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对西方现代性文化来说,这是一个如何有效地同化他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如何有效地解决技术理性的扩张所带来的现代性文化困境的过程。其次,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如何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并以此超越西方现代性文化而走向世界的过程。因而在它们的交往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观照,通常在彼此之间引起共同反响的方面即它们的交汇处,会孕育着一种兼而有之的新文化。这种“新”绝不是补缺性的相互挪用而拼接出来的,而是以对方为反观之镜、审时度势地结合自身文化特质进行自我加工与改造的结果。因为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困境如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共同课题。当代中国文化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恰好可以为其提供有价值的资源;而当代中国文化所指向的理性追求,西方业已实现的现代性文化又恰好可以为其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这种彼此需要的特性是全球文化交往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它在全球化时代进入文化主体眼帘的方面明显有别于其他时代,因而这种关联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是由特定时代的视界所建构的,是当前文化交往进程中文化自觉的指向性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获得创新发展的切入点。任何文化在文化交往中只要找到这一切入点并以之来重新审视自身,就会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中抓住发展的契机,为自身文化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1]汤一介.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G]//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
[2]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5.
[3]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2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284.
[4]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420-433.
[5]刘伟胜.文化霸权概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33.
[6]柯可.文化产业论[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34.
[7]CEI中国行业发展报告(2004)——传媒业[R].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49.
[8]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15-2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10]张岱年.文化与价值[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12-220.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7.
[12]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
Opportunities,Challenges and Cultural Awareness
LI Peihu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he union provides new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meanwhile exposes it under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modern cultures in cultural exchang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critical to be culturally of self-determination,self-knowing,self-confidence and self-awareness,and to have a global view o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s,and the western modern cultur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s.
globalization;cultural exchanges;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cultural awareness
G02
A
1009-8445(2010)03-0005-05
(责任编辑:陈静)
2010-03-01;修改日期:2010-04-0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YA-02);肇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0707)
李佩环(1975-),女,贵州安龙人,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