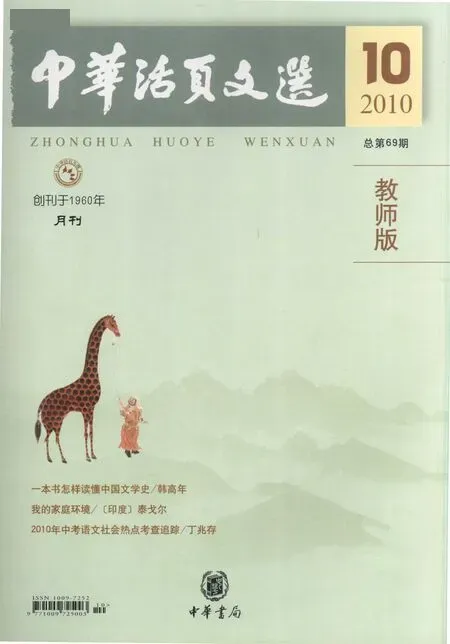“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一解
张 灵
阅读古文,难免会遇到各种一时不能理解的“拦路虎”,产生各种理解的困惑,其中有的属于生字怪词、特殊句法、特殊用典或古代文化典章制度知识掌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这类困惑往往因为问题明确,因而或通过向人求教,或通过查阅资料,似乎较易解决。但,阅读中常常还会碰到一种困惑,就是它们没有上述一类的明确问题,但对文意的理解又不能有充分的把握,心生疑问,但又感到无从下手解决。南朝吴均的传世名篇《与朱元思书》的头一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究竟如何理解,就常引人琢磨。
《与朱元思书》在不足两百字的短小篇幅中,对富春江一带的绝胜山水作了精彩的描绘,因而脍炙人口,常被选入各种文学读本或中学语文课本。为了便于探讨,我们不妨将其全文引列如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这篇文章不仅篇幅短小、文字精练,而且从骈体文的角度来说,也算得上是用语浅显,文笔流畅,琅琅上口,又不失笔致的摇曳多变和描摹的生动传神。全文以对自然的近乎客观的描写为主体,只有倒数的第三、四两句——“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顺其自然地以对比和让步的手法在对自然美景的赞叹中将笔触和思绪稍稍伸向了社会、隐微地表达了一点对社会人生的感叹,紧接着又让这点与人世的联系很快出神入化地消失在远离俗世的大自然的情景、怀抱之中——“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从而使全篇善始善终地保持在对自然浑然一体的描绘中。这些都是这篇短文受到经久不衰的欢迎的原因所在吧。
总体上说,这篇文章理解起来并无难处。作者在总体上采用的是一种总分写法。“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文章开始,作者就开门见山地、不由自主地先写出了自己畅游富春江一带美景后的总体感受和印象,这是“总”。紧接着才点出了这次畅游的具体所在,再一一刻画了一路的清绝、幽美的胜景,又由此种胜景不由自主地发出社会人生的感喟,随即又遁入对大自然枝繁叶茂的特写之中,结束全文。以对这片自然山水的总的印象感受始、以对这片自然山水的一个具体特写的镜头终,使全篇内容显得洁净、纯粹,余味无穷。
然而仔细品味全篇,对全篇起到引领作用的“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禁令人思索。其中的“风烟俱净”当然不会叫人产生理解的困难,关键的一点是“天山共色”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权威工具书的解释。上海古籍版《古文鉴赏辞典》的有关阐释是: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二句,以对句发端,从大处着笔,写登舟纵目的总体感受。江上风平浪静,烟光尽扫,两岸山色无垠,远于天接,视野是何等开阔,心情又是何等舒展!这正是一个秋高气爽,游目骋怀的大好时节。这两句景语孕情,大气包举,可谓善于发端。(吴战垒执笔)
江苏文艺版的有关赏析是:
第一层从“风烟俱净”至“天下独绝”,总揽胜景,启发下文。作者十分善于发端,“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头八个字就勾勒出这幅山水画卷的整个形势气象,使人觉得天光山色宛然在目。他在富春江下游离岸登舟,展眼眺望,视野深远,首先看到的是清秋季节的广阔景象。只见天高气爽,向远处伸延的连绵群山愈来愈远,愈远愈小,山色亦随之愈远愈淡;湛蓝的天空则愈远愈低,渐渐地一直望到山之尽头,天之尽头,天山终于融合为一。作者这里不单以天来衬山,或是单以山来衬天,而是让天与山互相烘托,互相陪衬,从整体上再现了美景。(费君清执笔)
从以上两段赏析文字的总体内容和其中的“两岸山色无垠,远于天接,视野是何等开阔”“只见天高气爽,向远处伸延的连绵群山愈来愈远,愈远愈小,山色亦随之愈远愈淡;湛蓝的天空则愈远愈低,渐渐地一直望到山之尽头,天之尽头,天山终于融合为一”的具体文字来看,两种辞典都是将“天山共色”理解做:远眺之中,由于天晴气朗、烟雾尽扫,视野开阔,所以见到连绵的山脉渐远渐低,在远处的天际线上,山与天融合为一。特别是江苏文艺版的解释更为详尽明确:“山色亦随之愈远愈淡……天之尽头,天山终于融合为一。”从常理上说,在晴朗的天空下,山脉在远处由青而蓝与天色融为一体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这里的阐释似乎没有什么不妥。然而,本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交代登高远眺等等的情况,到底如何“天山共色”并没有指明,而诠释者的解释无疑加进了自己的很多情景预设。在对古代诗文的串讲中加入适当的铺垫应是正常、合理的,问题是,本文的阐释中加入这些预设铺垫是否合理。通览全文,显然这两种解释都存在如下问题:(1)把统领全文的总写当成了一句具体情景的描写,而且需要读者在阅读时替作者做必要的情景预设铺垫;(2)把这句当做登高远眺、视野开阔、山色无垠等等的居高临下的景象描写的话,也与后文的“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的描写相矛盾,或者说前后文之间需要做补充交代、过渡;(3)假如这两句真如两辞典所解的话,这句登高远眺之句还与紧随其后的“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出现邻接问题:乍在山巅居高临下,忽在谷底江面任意漂流!显然于行文和理解均显突兀、悖谬。
那么“天山共色”到底在这里如何理解呢?我们试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即“天山共色”是总写富春江一带江水清澈透明,天光、山影、水色相映相融的突出特点。如上文所点到的,作者抬起笔来、情不自禁地首先想到的是富春江的清澈明丽。因此一开始总写感受:“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寥寥数字就将自己对这段江水的总体体验印象和盘托出,然后才是交代了这种美景到底是在哪里等等的具体信息:“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它们相对首二句来,实属追笔说明、具体交代,相对下文的描写,则又起一种内容上的统领。换句话说,其中的天下“独绝”之所在,正是文章开头所总括交代的。因此,“天下独绝”四字既是对前面的补叙、又是对下文更具体的描述的启引。而“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就属于对“天山共色”、水天一色的清湛江水的具体描写,但为了避免重复,作者省略了天光、云影、山色共同映照于水中的情景的更具体的描述,因为这里通过与首句的互文效果,已能传达出相应的审美信息、达到相应的艺术效果;在此基础上,下文的两岸山色的具体、细致的描绘与交代,就成了必然和自然的了。因此,可以进一步总结说,“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并不是作者登高远眺的一个具体所见,它们与“从流飘荡,任意东西”一起实际上描述了作者在富春江上畅游的总体印象和感受。特别是其中的“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一句因为是凝练、鲜明地概括出了富春江一带最为显著的自然特色,所以也就成了引领全文的总括之句,属于全文描写的点睛之笔。
如此理解,其实可以得到许多古今文本的旁证。这里不妨举例一二。如小学课本中选入的唐代诗人戴叔伦的名篇《兰溪棹歌》写道:“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这虽写的是兰溪,但同为浙中山水,自然是有共性的,特别是它明确指出了“越中山色镜中看”,——“镜”自然也是指水清如镜了。清代杰出的学者吴其濬在其名著《植物名实图考》的“芰”条中对江浙一带风情有如下描写:“余过邗沟,达苕霫,陂塘水满,菱科漾溢,宝镜花摇,櫜韜红绚,牵荇带而通舟,裹荷叶而作饭,乌睹所谓白足女郎踏桨倚柁,曼声烟波间乎?”这里的“苕”“霫”是指浙江的两条江水,而“宝镜花摇”也比喻其江水的清澈、花影的荡漾不定。鲁迅先生的《好的故事》中也借梦境描写了浙江一带山水的梦幻般的景象:“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映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个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合……凡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而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一句更像是对“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的最好注解:“水中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织,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而鲁迅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注者还引用了吴均同时代的作品《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句话,同样反映了浙江山水的明澈特色:“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当代建筑学家、散文家陈从周在《桐江行》一文中写道:“桐江上游到严州府的境地,水浅了,滩宽了,故称严滩。此时万象空明,秋入三更,滩声之美,幻入诗境。声是动,境是静,动静交织出极神秘的山景水色。”这其中的“万象空明”无疑也隐含着对这里的“水色”之清澈的指意。
总之,从古至今的大量诗文在描写浙江山水时无疑都留意到了那里的水色清美之绝,而这恐怕也正是吴均在《与朱元思书》的开头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总领全篇的缘由所在吧。
参考资料:
1.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724—725页。
2.吴功正主编《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第 639— 640页。
3.〔清〕吴其濬撰:《植物名实图考》,商务印书馆 1957年版,第 752页。
4.鲁迅《野草◦好的故事》,《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90—191页。
5.陈从周《陈从周散文◦桐江行》,花城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