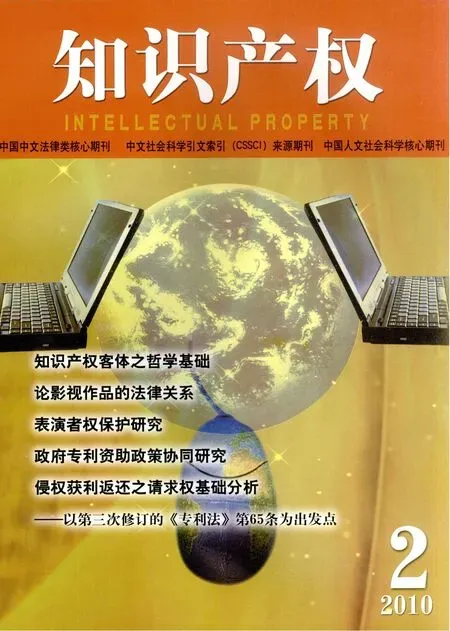侵权获利返还之请求权基础分析
——以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第 65条为出发点
■ 张晓霞
侵权获利返还之请求权基础分析
——以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第 65条为出发点
■ 张晓霞*
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损害赔偿额除了以权利人因权利侵犯受到的损失为计算根据之外,还可以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作为确定赔偿额的根据,形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特有的确定损害赔偿额根据的规定。但是,侵权获利返还在不当得利领域以及无因管理制度中有自己的请求权基础。以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第 65条规定中存在的疑惑为出发点,通过对德国判例和日本法律规定的比较研究,结合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额确定根据方面的规定,对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客观获利范围内,侵权损害赔偿与不当得利均是侵权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两者形成竞合;对超过客观利益部分的侵权获利,建议明确以惩罚性赔偿为请求权基础,而否定无因管理制度的准用。
侵权获利 侵权损害赔偿 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 惩罚性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计算权利人损失的方法,将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作为被侵权人损失予以确认的规定,在我国最早见于 1983年 3月 1日施行的《商标法》1该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以后《专利法》和《著作权法》陆续采取了相同的规定,形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特有的确定损害赔偿额的根据。自 2008年以来,为落实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要求,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与前两次“动因均来自外部”2郭禾教授在《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专利法》第三次修订评述》(《电子知识产权》2009年 2期)中,称第一次专利法修订迫于《中美备忘录》的压力;第二次修订为WTO相关规定的需要。的修订不同,《专利法》率先迎来了自发进行的第三次修订,其中第六十五条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特别强调了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侵权获利之间的序位关系,即“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尽管以往的规定并未如此限制,而是在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人获利之间,权利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鉴于规定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之立法意图在于对权利人损失的推定,所以,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与以往的规定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只是更加强调了规定侵权获利作为损失赔偿额的根据在于缓解权利人举证之压力。
在屈指可数的以侵权人之获利作为损失赔偿额的案件中,以被告侵权获利高达 3.3亿元作为损害赔偿数额的判决自然受到广泛关注3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施耐德电器低压(天津)有限公司侵权专利权纠纷,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温民三初字第 135号民事判决。被誉为 2007年最有影响的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一。。既然法律规定侵权人的获利是权利人损失的推定,作为法院不仅应当考虑被告侵权获利与权利人损失之间的关系,被告更应该以自己的获利超过权利人的损失等理由进行积极的抗辩。但是,通过判决书的阐述,无论是被告的抗辩理由还是法院的判理,围绕的重点都是被告利润的确定以及成本的扣除。而且,通过实务部门的调研报告所认为的以被告获利作为损害赔偿额的难点在于“被告不配合,法院依职权调查的力度降低,最终采用该种计算方式的案件并不多”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编著:《知识产权审判分类案件综述》,第 130页。之原因的分析,表明实务方面似乎将被告侵权获利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对待而不是立法所要求的权利人的损失的推定,表现出法律规定与司法之间的脱节。
另一方面,伴随着不当得利类型的扩张,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作为一种类型在不当得利领域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且因为“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之所以出现交融,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受益’这一事实。”5杨彪:《受益型侵权行为研究——兼论损害赔偿法的晚期发展》,载《商法研究》2009年第 5期。所以,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在知识产权领域,因权利受到侵犯尚未见一例以不当得利返还作为请求权基础提起的诉讼。但是,可以假设在上文提及的 3.3亿元的案件中,权利人以不当得利返还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应当如何确定返还的范围之问题必然凸显出来。正是由于侵权获利返还在不当得利领域有其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所以,以被告侵权获利作为请求数额不仅仅是权利人损失推定的问题,还会涉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选择。
侵权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之分析,在我国尚属一片需要开垦的处女地。
二、侵权获利返还相关理论学说的考察
(一)以侵权损害为基础的侵权获利返还
中世纪罗马法中虽然有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但并不存在统一而抽象的利益,更不存在统一的损害概念。“德国学者Monnsenn于 1855年着眼于日耳曼法6现行德国法前身。引自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月版,第 118页注解。而首倡”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月版,第 118页。的差额说“以统一的损害概念及因果关系作为判断损害有无及范围的理论架构,实践全部损害原则,并排除法官的肆意,以保护受害人。”8王泽鉴:《损害概念及损害分类》,载台湾地区《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 9期。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同,成为通说。差额说所确定的基本损失计算方法是损害发生前应有的财产状态和损害发生后的财产之间的差额。按照该学说的宗旨,侵权人侵权获利并不属于差额说所确立的损失概念之范围,甚至可以说,在侵权法范围内并不涉及侵害者利益返还的问题。
但是,1895年 6月 8日德国大审院 (Reichsgericht)针对侵犯著作权的一起判决9RG 8.6.1895=RGZ 35,63(66).,使实施许可费、被告侵权获利与侵权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并首先在知识产权领域创建了损害赔偿特有的计算方法。10(日)田村善之:《知的財產權と損害賠償》,第 90-91页。
案情是在制造和销售的自动演奏装置使用的唱片中,被告未经许可复制了权利人的音乐作品。但是,由于被告的复制行为使原告的作品被更多人所知,原告的销售额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为此,一审法院以损害未发生为理由驳回了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大审院经过审理,在其发回重审的理由中阐述到:1.本案中的违法性,体现在复制作品行为本身,而不是侵权者为了实际的利益而未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据此,当唱片中使用的作品构成对权利人的全部侵权情况下,所应有的财产状况和实际的财产状况的差额可以作为损害赔偿进行请求;2.如果没有侵权行为,也就是说,被告若得到权利人的许可,必然要支付许可费。所以,应该得到的许可费而现实中未得到,权利人可以以此为根据进行损害赔偿请求;3.如果没有侵权行为,而是原告自己实施,原告应该得到的利益,却因为被告的行为而未得到,同样可以作为损失进行请求。就这样,权利人的损失和被告侵权获利之间的对应性首先是在判例中得到确认。
日本在制定特许法11即发明专利法。过程中,对德国的判例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并以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我妻荣教授的损害赔偿理论为根据,于昭和 34年(1959年)发布的特许法对损害赔偿条文进行了修正,形成第 102条第一项规定:“发明专利权人或独占实施权人,对于因故意、过失而侵害自己之发明专利权或者独占实施权之侵害人请求赔偿自己所受之损害时,侵害人因此而受有利益者,其侵害行为所受之利益额,推定为发明专利权人或独占实施权人所受之损害额”。对此,有学说认为原告以侵权人获利作为损失赔偿额的根据仅仅证明侵权人的利益额还不够,还必须证明自己有实施该发明以及发生营业上之损害事实12中山信弘:《工業所有權法》,弘文堂,第 317页。。实务中,当专利权人自己不实施专利的情况下,判决不承认有利益损失的存在13东京地裁昭和 46、6、14判 266号。。
无论是德国的判例,还是日本的法律规定,关于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的认识都是以侵权法领域中的损害为基础,所以,对侵权获利的类推适用必然涉及权利人损失与侵权获利之间关系的论证。
(二)以不当得利为基础的侵权获利返还
损害赔偿理论中涉及的以差额说为基础而设定的损害概念,却是随着不当得利制度中涉及的损失要件舍取的争论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众所周知,不当得利返还以获利、损失以及获利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侵权获利返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关于损失要件的适用。德国学者海克 (Philipp Heck)认识到该问题,自 1929年开始展开了对利益归属学说的探讨14(日)村田大樹:“侵害利得論における‘割当内容を持つ権利’の判断構造”,同志社法学,六 0巻七号。,认为既然承认权利的存在,伴随着权利的行使、转让必然产生利益。尽管海克没有指明什么样的权利具有权利利益内容 (Interessengehalt),却以该理论为基础,提出不当得利返还的适用无须损害发生之要件,而是应当强调利益的归属。奥地利学者瓦尔特 .威尔伯格 (Walter W ilburg)继承了海克的理论,于 1934年摒弃了不当得利一元理论15(日)村田大樹:“侵害利得論における‘割当内容を持つ権利’の判断構造”,同志社法学,六 0巻七号。,将不当得利进行类型化分,分为因给付而产生的不当得利和利益归属型不当得利,利益归属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实现无须损害的发生成为通说。
在德国 1900年民法典实施以后,基于侵犯专利的行为,能否依照德国民法典第 812条第 1项关于不当得利返还之规定而支持返还财产,曾经有反对的判例16RG22.12.1913=JW1914,407Nr.8.,RG24.6.1908=WarnRspr1908,535Nr.658.详见田村善之:《機能的知的財産法の理論》,信山社,1996年版 ,第 208页。。但是,按照利益归属说,侵权者使用了法律赋予专利权人所享有的排他权利而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该说由于不再强调专利权人与侵害人之间是否有现实财产的移转,故以不当得利为财产返还的请求权基础成为可能。“而以前的学说都是认为,在现实的财产变更乃至移转之间方能看到获利,所以,在侵害全部或者部分专利权的案件中,是否定不当得利的。”17田村善之:機能的知的財産法の理論,信山社,1996年版,第 209页。1976年11月 30日,大审院改变了原来曾否定不当得利的观点,承认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侵权纠纷中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18BGH 30.11.1976=BGHZ 68,90=GRUR 1977,250-Kunststoffhohlprofil I转引于田村善之:《知识产权和损害赔偿》,第 109页。
受到不当得利领域学说的影响,侵权法领域关于损失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侵权人侵权获得的利益与权利人的损失建立了联系。正如学者所认识到的一样:“在对各国债法体系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比较观察后,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侵权法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始终伴随着不当得利法发展的全过程,而反之亦然;两者呈现出彼此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19杨彪:《受益型侵权行为研究——兼论损害赔偿法的晚近发展》,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 5期。
(三)以无因管理为基础的侵权获利返还
所谓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既未受委托,也不负有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其中管理他人事务的人为管理人,事务被管理的人为本人。罗马法中有一句格言:“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已为其后世诸国法律所确认。在大陆法国家,除法国之外,通常排除准契约的概念,将无因管理与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并列,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在知识产权特有计算损失方法创建以前,针对享有表演权的原告以被告侵害获利进行索赔的诉讼,德国帝国上级商事法院 1877年 9月 12日的判决开启了依照准无因管理理论支持侵权获利返还请求之先河20ROHG 13.9.1877=ROHGE 22,338(340).见田村善之:《知识产权和损害赔偿》,第 98页。。在德国民法典实施以后,尽管德国民法典有关于不法管理之规定21第 687条第二项是关于明知自己无权处理而将他人事务作为自己的事务进行管理情况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规定。。但是,由于其规定的条件为“明知”,在专利权人请求侵权人获得利益返还的案件中,并不是直接引用不法管理之条文,而是类推适用,判例上所反映出的仅仅是为判决寻找一个根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被告侵权获利的正当性问题,就是说并没有去探讨为什么侵害人的获利可以作为损害进行赔偿。所以,“当时除了公平的解释之外,尚未有更有意义而充分的说明成为事实。”22FritzLindenmaier,Die Herausgabe desVerletzrgewinns,ZAkDR1936,S.16;Reimer,PATENTGESETZ,S.1663(KarlNastelski)转引于田村善之:《知的財產權と損害賠償》,第 99页。
在日本,针对无因管理理论的准用,以我妻荣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表示反对,针对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问题,认为“如果侵权行为法和不当得利法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努力修正该理论 ”23我妻荣:《債權各論下卷》(岩波書店)第 928頁。转引自“著作権侵害を理由とする損害賠償、利得返還都民法法理”,京都大学法学論叢 156卷 5-6号。。
三、我国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之探讨
(一)侵权损害赔偿与不当得利请求权之竞合
我国专利法中虽然没有使用推定之概念,但是,对侵权获利作为权利人损失的确定根据之一之立法目的没有争议。
侵权人利用他人知识成果获得的利益一般包括两种:第一,侵权人的积极财产增加,表现为取得利益;第二,侵权人消极得利,表现为本应支付而没有支付的许可使用费。既然是作为权利人损失的确定根据,那么,仅仅证明被告有获利并不当然证明权利人存在损失,还必须考量侵权获利与权利人损失之间的关联,具体涉及权利人是否具有实施专利的计划和实施能力以及实施专利对侵权获利的贡献度。
针对侵权获利返还,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出现了不同的路径选择24详见杨彪:《受益型侵权行为研究— —兼论损害赔偿法的晚近发展》,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 5期。,我国不排斥竞合的存在。虽然《民法通则》第 92条关于不当得利返还的规定过于简单,但是,属于客观利益范围内的侵权获利,在理论上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竞合的可能。无论是以不当得利请求权为基础,还是以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基础,除了是否具有过错之要件不同之外,在确定被告侵权获利的客观要素方面,应当是一致的。我国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因此建议“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作为侵权民事责任体系的一项内容”25阳平:《论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6月版,第 75页和第 66页。,想必正是因为两者返还的范围一致之缘故。否则,难以理解如此逻辑混乱之观点。
(二)无因管理制度准用之否定
我国学者意识到,台湾地区“对于侵权人获利可根据不法管理——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定,要求受益人返还其全部所获利益 (包括利润),这一做法值得我们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不法 (无因)管理三种请求权的竞合。”26郭明龙:《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获利’因素》,载《商法研究》2009年第 1期。
但是,无因管理有其特定的立法目的,“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纯属自愿的,法律救济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其权益不致因救助他人而受损,对于受益人而言,法律是不带惩罚性的。无因管理制度价值上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反映出社会对于维护公序良俗行为的赞许。”27曾坚:《论无因管理之债的价值及其运用》,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 2期。对侵权获利返还以无因管理的准用为请求权基础,违反了无因管理制度设立之宗旨,否定准用,进而否定竞合是本文之观点。
但是,对无因管理之准用观点的否定,还远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在知识产权领域,积极获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以推定为权利人的损失;另一部分是超过了权利人的损失,可能是基于侵权人的营销能力、资金等与侵权行为完全无关的因素而获得的利润,这部分获利是超过权利人的损失的,对这部分获利的归属,现有立法并未涉及。
由于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都有干涉他人权益的情形,所以两者具有进行比较的基点。而且管理人有将管理过程中获得的利益移转给本人的义务,即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的过程中,如果因该管理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不论是从事事实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还是从事法律行为所获得的收益,都应该如数交付本人。同时,管理人有赔偿在管理事务过程中给本人造成的损失的义务。加之侵权损害赔偿和不当得利返还都受到权利人的损失或者说是客观利益范围的限制,所以,对侵权人因侵权获利的全部返还,成为主张准用无因管理的合理性根据。
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仅仅规定了无因管理,没有不法管理之规定,准用未免有些牵强。故应当考虑另辟途径,探讨超过客观利益的侵权获利返还之根据。
(三)惩罚性赔偿之明确
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具有系统的损害赔偿理论,而且以填补损害为原则,不承认惩罚性赔偿。所谓的惩罚性赔偿就是超过实际损失进行的赔偿,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受到大陆法系传统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未对惩罚性赔偿作出规定。但是,于 1993年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条的规定28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成为我国惩罚性赔偿的标志性规定,以此也表明惩罚性赔偿原则在我国已得到立法上的确认。
在专利法领域,对于侵权人来说,应当支付而未支付的实施许可费就是消极获利,而对于权利人来说,应当获得的利益而未获得就是积极损失。无论是以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基础,还是以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基础,都属于应当返还的范围。但是,我国《专利法》第 65条规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法律规定实施许可费的倍数,这一显然带有惩罚赔偿色彩的规定,却被一个序位关系牢牢地与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获利系在一起,难以判断我国立法对惩罚性赔偿之态度。另外,侵犯专利权的主体可以是生产方,也可以是销售方,对销售方采用实施许可费倍数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额,似乎更加偏离了权利人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这一基本出发点。
知识产权作为无形的具有财产属性的权利,其价值是通过实施体现出来的,而侵权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控制。维权成本高、侵权行为的难易控制,特别是在补偿性赔偿基础上,使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成为高收益、低风险的“职业”。因此,“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不仅可以使权利人在物质利益上,还有精神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补偿,而且通过对侵权人惩罚,产生的威慑,能够警示他人,避免侵权的再次发生。同时,还可以激发权利人的维权热情,激发其创造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些都是补偿性赔偿所无法达到的。”29温世扬,邱永清:《惩罚性赔偿与知识产权保护》,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 12期。为此,明确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成为大势所趋。
惩罚性赔偿不是仅仅涉及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还要兼顾民法体系。即将于 2010年 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特定的侵权行为规定了惩罚性赔偿30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所以,在知识产权领域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破坏民事责任体系之整体性。至此,惩罚性赔偿额的确定为超过权利人损失的侵权获利返还提供了适用的空间,也就是说,超过权利人损失的侵权获利返还为惩罚性赔偿的确定提供了根据。以此解决侵权获利返还的正当性问题。
四、侵权获利在知识产权领域外的适用
我国于 2009年 12月 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20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显然借鉴了知识产权法相关的规定,所以,对侵权获利返还请求权基础探讨的意义不仅局限在知识产权领域。
此外,于 2001年 3月 8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0条第 1款规定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六项因素,其中包括侵权人的获利情况。虽然该规定引起学界的关注,以“‘侵权人获利’因素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中的地位”为目标展开了“非独立说”与“独立说”的讨论31郭明龙:《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获利’因素》,载《商法研究》2009年第 1期。,特别是认为“人格权或法益被他人非法利用时,行为人所获得的收益应当予以剥夺。而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引入‘侵权人获利’因素即可以达致此目标。”32郭明龙:《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获利’因素》,载《商法研究》2009年第 1期。说明所谓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都是以在确定精神损害时的地位为基础,而关于侵权人获利作为损害赔偿方式的独立性并没有涉及。
一个案例33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7)海民初字第 13689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7)一中民终字第 13613号民事判决书。。金某诉某报业公司侵犯其肖像权,原审经过审理认为,某报业公司使用金某的肖像发布广告时未取得其的同意,并从中获利,侵犯了金某的肖像权,故判决某报业公司向金某赔偿经济损失 36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000元。金某不服,以赔偿数额过低等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所判赔偿数额,因未考虑侵权人因侵犯他人权利而获取利益的情节而明显偏低,故将赔偿金 36元改判为200 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000元予以维持。
由于侵权获利返还与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量的侵权获利之因素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所以,应当认可二审的判决思路。但是,与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问题一样,在确定侵权获利返还范围时,如果不涉及惩罚性赔偿的问题,应当限定侵权获利与权利人损失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客观利益的界定;反之,如果涉及惩罚性赔偿,应当限定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要件。两者应当界限分明,不可含混论之。至于何种条件下适用惩罚性赔偿,有待进一步阐述。■
*作者系北京大学 2006级民商法学博士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