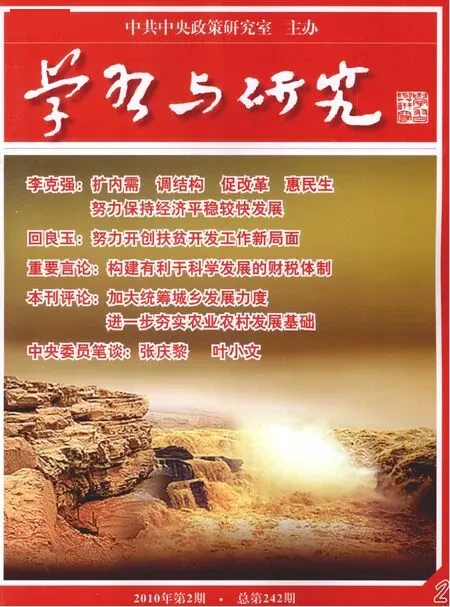论儒学对人类文明的建设性价值
方同义
(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科学地准确地把握评价儒学,应该着眼于整个人类、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着眼于“建设”、“建设性”。而“建设”本身就是“文明的建设”,应以“文明和建设性”评价儒学。唯有如此,才能超越一切固有成见,树立全局性、世界性的眼光,真正掌握儒学的精神实质和意义所在。
一、文明与建设性
从哲学上说,建设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和幸福的需要,所从事的以创造、维护和发展人类文明为目标的一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简言之,建设就是“合理化的实践”。建设的核心和价值是“促进文明的生长”。“文明”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积极成果和财富的总和,是为了人自身的,是服务于人的,是要使“人成其为人”,而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即适宜于人生存、发展、而使人幸福的世界。分而言之,物质文明是要在经济领域中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实现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进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是通过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所创造的成果,促进政治制度的改善和政治生活的进步及社会状态的进步,有利于社会的善治和稳定,保障人的权利和实现人的政治自由;精神文明是人类在精神领域中创造的财富和成果,实现精神产品的增长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在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中实现人的精神解放和意志自由,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精神上“回归人的本质”。
人类以建设性的方式即促进文明生长的方式去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各种各样人类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这将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这是在人类不断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起来的,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就更是如此。由此而言,“文明和建设性”是在宏观的层面上,构建一个价值尺度,它可以作为人们历史实践活动的评价的标准,也可以作为一切思想学说,包括我们今天对儒学评价的准则。
二、儒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建设性价值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待儒学,其中所包含的四大理念最值得关注、分析和探讨,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普遍的建设性价值。
一是民生。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乃是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任何国家、民族、政府、政党都必须将“民生”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即使在当代世界,“民生”仍是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置于第一位的大事,“民生”问题解决不好,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人的需要满足的主要表现,也是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削弱以至丧失了这个基础,所谓文明创造也就无从谈起。
以孔子为首的儒学从其产生以后一直形成了关注民生、纾解民困、为民请命的优秀传统,这在古代的各种思想中罕有其匹。孔子关注“民生”有三个关键词:庶之、富之、教之。庶之,是人口的繁衍;富之,是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教之,是民众的行为的规范化和人格的培养问题,是人的文明化建设。这三个关键词言简意赅,抓住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问题。孔子对统治者如何解决“民生”提出忠告,如“惠”、“敬”、“正人先正己”、“修己以安人”、“信则民任”等,这就为如何处理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提出了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原则。孔子的理想是社会的有序化、道德化,社会民生问题得到良好解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可以说,孔子开启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关心民生民瘼的深远传统。
孟子倡导“仁政”、“王道”,其中,“民生”是他关注的主要内容。孟子抓住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即小农的生存问题。他提出老百姓应该拥有一份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他称之为“恒产”——即“八口之家”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了这份私有财产,民众就可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孟子还设计了一种“井田制”和“九一而助”的劳役地租,以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有了“恒产”和稳定的小农经济,人们才有“恒心”,亦即安居乐业、接受教育、遵纪守法的自律之心。孟子还提出“省刑罚,薄税收”[4]、“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5]、“市廛而不征”[6]等等鼓励发展生产、促进商业流通、减轻百姓负担的惠民措施。在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上,孟子认为,执政者应将人民置于国家社稷和君主之先,应运用“仁义”、“王道”施政;而人民对于暴虐的统治者可以反抗,也可以推翻其统治。可见,孟子基于对传统农业社会和小农生存条件的理解深刻,对“民生”问题十分关切,他对民众的利益想得很细很周到,是一个值得后人敬仰的进步思想家。
先秦大儒荀子也是一个十分关切民生问题的思想家,他在《王制》篇中写道:“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将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统治者欲求安宁,必用“平政”“爱民”之法。较之孔、孟的的理想主义,荀子更多地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但仍不失其惠民爱民之心。
自孔、孟、荀以降,历代儒学思想家对民生的关注形成了一种传统,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野谋生,儒生士大夫都堪称社会上促进民生问题解决的积极、健康力量。如张载《西铭》有言:“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充分表达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思想家关注苍生的情怀。又如儒学巨擘朱熹除了在学术上对民生问题深入研究以外,还在家乡倡设“义仓”,以备灾年救济贫苦乡亲。
总结儒学思想家对“民生”问题的议论和关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富有入世情怀和现实主义态度,如孔子所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7]第二,与儒学的社会理想密切相关,是儒家理想主义的组成部分,如“大同”、“小康”都是儒学提出来的。第三,儒学思想家是和平主义者,他们要求改善民生,主要是通过他们的游说、“教化”和“师道”,使统治者改变态度从而采取有利于民众安居乐业的政策措施达到的,而非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第四,儒学思想家既是“民生”问题的思考者,也是力行者、实践者,中国历代的“循吏”、“好官”大都来自儒学的坚定信仰者即为明证。
综上所述,儒学在千年历史中所积累的有关民生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无论对于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都堪称是一种建设性价值,是极珍贵的思想资源。
二是仁爱。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是人类理性的最高层次的表征,亦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力量。没有爱的力量,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不可想象的。
考察人类思想史上各种关于“爱”的理念,有儒家之“仁爱”、墨家之“兼爱”、释家之“慈爱”(慈悲)、基督教之“爱人如己”、近世学者之“博爱”、费尔巴哈之“情爱”、马克思之“阶级的爱”等等。
如何看待儒学倡导的“仁爱”?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仁爱理想唯一本根的血亲之爱,却会由于肯定自身的至上地位而最终导致仁爱理想的根本否定。换句话说,儒家思潮虽然本来想在血缘亲情的本根基础之上达到仁者爱人的理想目标,最终却又为了维护这一本根的至高无上而根本否定了仁者爱人的理想。”因此,“仁爱”是“无根”的。[8]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可以从四方面考察“仁爱”的立论基础:“仁爱”的超验性依据、“仁爱”的血缘性基础、“仁爱”的社会性本质、“仁爱”的人性论底蕴,如此,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仁爱”的真谛。
首先,“仁爱”的超验性依据。儒学倡导的“仁爱”的超验性依据是“天”、“天命”、“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孔子认为,“仁爱”之道的价值理想和社会人生目标的根据就在于“天”,天、天命构成了“仁爱”之道的超验性依据。“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0]如此,将圣贤的“仁爱”之道与不可预测的“天”、“天命”紧紧联结在一起。孟子言“本心”、“良知”、“善性”,不是单从事实经验层面上去理解,它是天之禀赋,是“天之所与我者”,是人区别于它物的特征。并且,在人之范畴内是普遍的,即“心之所同然者”,“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圣人与我同类者”。[11]在此基础上,孟子特别强调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易大传》则言:“天地之大德曰生”,[12]又曰:“安土敦于仁,故能爱。”[13]“坤厚载物,德合无疆”。[14]“生”是天地之大德,是昊天之“仁爱”;“坤”即是大地,大地之德就是载物以厚,这种仁厚之德是无穷无尽的;人效法天地之大德,就是要安于所居之地,敦于仁而能于爱。如此,《易传》作者就将“仁爱”之“天人合一”的神圣性和超越性表达得淋漓尽致了。至宋明理学,更有张横渠的“民胞物与”、程明道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的“天理流行”、文天祥的“正气之歌”、王阳明的“一体之仁”;都可以看作是儒学的“仁爱”的形上性、超越性学说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仁爱”的血缘性基础。孔子言“克已复礼为仁”,[15]其中所说之“礼”与周人的礼制一致。但孔子的创造,在于他抓住了礼制僵硬外壳中的鲜活的精神,并加以思想的升华,即以“仁”去阐释“礼”。孔子将“仁”上升到哲学范畴的高度,并用以阐释社会的理想和人生的本质,实质上已涉及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价值问题。这样,孔子一方面以“仁”去阐说“礼”,如此“礼”就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新义,另一方面又用“仁”表达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因而,新与旧、继承与创新、现实与理想、个别与一般、起点与终点在儒家之道中就圆融统一起来了。
儒学“仁爱”的起点是血缘或血亲之爱。《论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6]“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7]“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18]“孝悌”是血亲之爱,这种爱,与“泛爱众”的普遍的广泛的“仁爱”不仅不相抵触,而且恰恰是一种连续的统一的关系;如果一定要将二者对立起来,就与儒学的本意相违拗了。这一点,孟子是与孔子一致的。他说“亲亲,仁也。”[19]“仁之实,事亲是也。”[20]同时,孟子又强调普遍的对所有人而言的“恻隐之心”和“心之同然”,也是基于血亲之爱与普遍仁爱的统一。
再次,“仁爱”的社会性本质。“仁爱”虽然以血缘的个别性为蓝本,却同时要求上升到社会的普遍性高度,“仁”是人的普遍性本质和社会化的价值理想。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21]“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这里的“己”、“人”都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概念。“忠”是对人的忠诚,“恕”是对人的宽恕,因为主体将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普遍的人,而在实际的思想和行动中又把别人看得与自己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是“以他人为重”,而这就是“仁者”。“仁者爱人”[23]也是将“人”作为普遍的类来对待,成为“爱”的对象,这与推己及人的涵义是一致的,即把“己”与“人”看作是同一的普遍的类,就可以类推之,如果不属于同一个类,推己及人也就不能成立。孔子认为,始终能以“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就是“仁人”、“圣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24]可见,孔子是要求把“孝悌”的为仁之道,通过推己及人行于整个社会,使“仁”具有社会化的意义和功能,并由此来规定人的应然和价值。
孟子进一步阐释了“仁道”的社会性本质,他更强调了“义”这一范畴,由“仁”而“义”,仁义连用,使儒家之道的内涵有所拓展和深化。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25]“义”规定了人的行为规范之应然以致必然,“大义灭亲”是对血亲之爱的制约,“义”确实大大强化了“仁爱”的社会性本质。孟子仔细辨别了己、亲、人、物四者的关系,“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勿仁;于民,仁之而勿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6]这里所用三个词“爱”、“仁”、“亲”,其义相融相通,但却有明显差别,“亲亲”、“仁民”、“爱物”是一种既包涵普遍性又承认差别性的关系,据此可以构建儒家道德理想王国,并体现了儒家精致圆融的思辨精神。
又次,“仁爱”的人性论底蕴。儒学所言“仁爱”是以人的本性真情为其人性论的根源。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27]所谓巧言令色,指用动听言词和谄媚之态取悦于人,如此之人就少有真诚的品质了。可见,“仁”的一个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以真诚待人,它以人的真性情为基础。《论语》中引用曾子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8]朱熹注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通过丧尽其礼和祭尽其诚,使民众的品德和性情归于淳厚。同样,如何对待祭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29]祭,无论祭先祖与神祗,都应竭其内心之诚,这就是“祭如在”。孔子认为,当祭之时,有故而不得与祭,使他人代为之祭,则虽然已祭,却与不祭同。这就是说,祭礼必须出于诚,与虚矫伪饰无缘。
由上所言,儒学所言“仁爱”,是下学与上达、形下与形上、现实与理想、特殊性与普遍性、血亲之爱与人类之爱的辩证有机统一,具有包容、圆融、博大的特点,从而与近世学者所言基于科学、逻辑的“博爱”观念既有相通、亦有区别。
三是教化。在中国古代,“教化”的主要载体或执掌者就是孔子和孟子以降的历代儒生士大夫。下面从教化的目的、内容和功能评价三方面阐述儒家教化的意义。
首先,教化的目的。儒家认为,兴教讲学和教化的目的主要包括人的素养的提高、促进国家的兴盛和社会的文明化。《易》称:“君子以振民育德”[30]君子的职责就在于振济万民,进行德教。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1]用法制禁令威慑百姓,诚然可以使他们免除刑责,却未能使其树立羞耻之心;只有在运用法制禁令的同时,着力以道德启导人民,用礼仪制度规范民众,这样才能使人民树立荣辱羞愧、自觉自律之心。可见,孔子强调的是人的基本道德素养的提升,也是人的文明水准的提高。个人文明化和道德素质的提升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32]孟子提出,国家管理者不仅要以“善政”治理天下,更要以“善教”引导人民。“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33]“善政”是要解决天下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善教”是使统治者得到民众的拥护,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贾谊认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而国丰富也。”[34]
其次,教化的内容。以人的文明化和社会有序化为目标的教化,其内容是十分广泛丰富的。儒家从人格的培养的内在要求来看,主要是“道、德”,“智、仁、勇”,“仁、义、礼、智、信”,“正心、诚意”等等;从外在的规范性要求来看,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以“礼、乐”为主,当然也包括“法”;前者可通称之为“道德教化”,后者可称之为“礼乐教化”。其经典文本即所谓“五经”、“六经”、“十三经”,宋以后则强调“四书五经”。事实上,各个时代各个思想家其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所论“教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成人”的各个方面。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35]即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6]“诗”为学之所兴之起点,“礼”为身之所立之节文,“乐”为德之所成之和融,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教育教养的渐进过程。孔子又言“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37]此言“仁、智、勇”乃“成人”所必备之品质。孔子将所有“教化”内容的最高境界以“道”来表述,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吾道一以贯之”[38]都表明“道”既是人的理想,也是社会和文明的理想。
孟子以人之天然拥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仁、义、礼、智”之四端,教化就是要使人之四端扩大而充实之。《大学》提出的教化理念可归结为三纲八条目,三纲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认为,这三纲八条目把古人的“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39]全部表达出来了。
与孔孟儒学有别,商鞅、韩非等法家提倡“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种所谓“教化”,其目的是培养对权力毕恭毕敬的奴才,是完全为极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服务的,而并不着眼于人的知识素养和道德品质的提高,而秦王朝的二世而斩则说明赤裸裸的专制说教并没有多少生命力。到了汉代,儒生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一方面保存了原始儒学的一些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对专制主义有所屈从,而这种屈从本身又为儒学争得了学术的正统的官方地位。至宋明时期,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倡导“存理灭欲”的同时,又不乏对皇权专制严辞批判的“诛心之论”。然而,“存理灭欲”之说为专制统治者长期利用,成了“以理杀人”的工具。可见,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教化”,训练愚忠的奴才是第一位的,而教化所要培养人提升人的素养的社会目的则并不重要。
总之,我们认为,儒学教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形成的重要力量,其正面价值要远远大于负面价值,应予以正确分析和充分肯定。
四是中和。中即不偏、适宜、正确;和即和平、和谐、和合。“中和”是儒学所倡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质上也代表华夏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特殊风格和特殊价值。
分析孔子的“中道”包涵三方面的内涵意义:
第一,“中道”是真与善的统一。《论语》里抽象地言“中”有两处:“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40]“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1]“允执其中”就是要真诚地笃信和牢牢地把握“中道”,据说这是尧对舜传位时的嘱托,意义十分重要。“中”是对世界的根本性质的把握,是一种世界观,同时又是人的实践和做事的方法论,这属于“求真”的范畴。并且,“中”、“中庸”又是德操的最高层次,是至上至圣的人格的表征,这又涉及“求善”的领域。孔子以“过犹不及”解释“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42]这里虽然是对具体人才贤否的评价,但“过犹不及”的结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人才之贤否既是一个“真”的问题,也是“善”的问题。求真合善就要尽可能地弄清事实真相和实际情况。“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43]一个人不可能无所不知,要紧的是老老实实从事物的两个方面(上下精粗本末始终)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情况,正确分析,作出合乎事实的判断,这就是“中道”。这里“中道”所包涵的是既“正确”亦“恰当”,即是真与善的一致。
第二,“中道”是情理与事理的统一。正确、全面把握事物的实际情况就是要弄清事物之理,而采取不偏激、不极端的态度就是合乎人之情理。孔子的“中道”原则是贯彻于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夫子温、良、恭、俭、让”[44],这是人格德性之“中”;“礼之用,和为贵”[45],是说礼的内在依据是“仁”,而礼的实际效用则是和与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6],是说君与臣之间是一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对待、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合乎“中道”的关系。孔子也将“中道”原则贯彻于他的教育实践之中。“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也,故退之。”[47]“中道”的适宜原则,是要求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状况施行不同的方法,如此,教与学之间才能构成互为适宜的关系,这也就是孔子提出的著名的“因材施教”原则。
第三,“中道”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中”是一个基本原则,然而,世界是复杂的,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因此,在复杂的动态发展的世界中,要把握“中道”,必须要求高度的灵活性。“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48]孟子对此评述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49]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七人隐遁不污,是古之逸民,且皆能守道之一节,但于“中道”之核心的持守不能不有所偏差,而孔子则是“无可无不可”。“可”指的是主体行为与客观实际情况的适宜调和,是主体对客观存在事实作出的正确判断与行动。客观实际情况千变万化,因而所谓“可”也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无可”是指无一定不变之“可”,“无不可”指的是无一定不变之“不可”。所以,孟子的四个“可以”指的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采取不同的行动举措,即保持“权”和“时中”的高度灵活性,孟子由此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圣”是真善合一,“时”是“无可无不可”,“圣之时者”即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结语
人类文明发展从历史到未来的走向,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提法也不尽一致,但其根本点是不能动摇的——这就是为了“人”。“人”是“文明”的主体,是“文明”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文明”则是“人”创造活动的结晶,也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而一切思想、学说、信仰体系和宗教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围绕着“人”和“文明”发展所提供的工具,是一种“文明”建设的方法。如此,任何学说的价值,都必须接受“人”——“文明”这一价值标准的评判。儒学仍然如同基督教、佛教一样,有着自身的力量和存在理由——即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而与文明共存的活的因素、建设性的因素。这种活的建设性因素,最核心的是前述四项:“民生”是攸关人的生命生存的物质文明建设基础的要件,是儒学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全力思虑和实践的主题,而充分体现了儒学信奉者人类物质文明建设者的角色;“仁爱”是表现人的德性和境界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儒学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教化民众而致力实现的理想,充分体现了儒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不朽价值;“教化”是人和社会的文明化并使文明得以形成、推广、传承的基本手段,是一代代儒学士大夫的社会目标;“中和”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最具潜在价值和未来价值的中心原则,如果人类舍弃“和而不同”的途径,要获得和平相处、繁荣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们认为,经过科学地分析批评,儒学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完全可以在人类未来文明发展中扮演“建设者”的角色。
注释:
[1]《论语·公治长》。
[2]《论语·季氏》。
[3][4][17]《孟子·梁惠王上》。
[5][49]《孟子·梁惠王下》。
[6]《孟子·公孙丑下》。
[7][48]《论语·微子》。
[8]《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载《哲学评论》2002年卷,武汉大学哲学系宗教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9][43]《论语·子罕》。
[10][37]《论语·宪问》。
[11]《孟子·公孙丑上》。
[12]《易传·系辞下》。
[13]《易传·系辞上》。
[14]《周易·坤传》。
[15]《论语·颜渊》。
[16][18][27][28][32][35][44][45]《论语·学而》。
[19][33]《孟子·尽心上》。
[20][25]《孟子·离娄上》。
[21][29][46]《论语·八佾》。
[22]《论语·卫灵公》。
[23]《论语·颜渊》。
[24][41]《论语·雍也》。
[26]《孟子·告子下》。
[30]《周易·蛊》。
[31]《论语·为政》。
[34]贾谊:《新书·大政下》。
[36]《论语·泰伯》。
[38]《论语·里仁》。
[39]朱熹《大学章句序》。
[40]《论语·尧曰》。
[42][47]《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