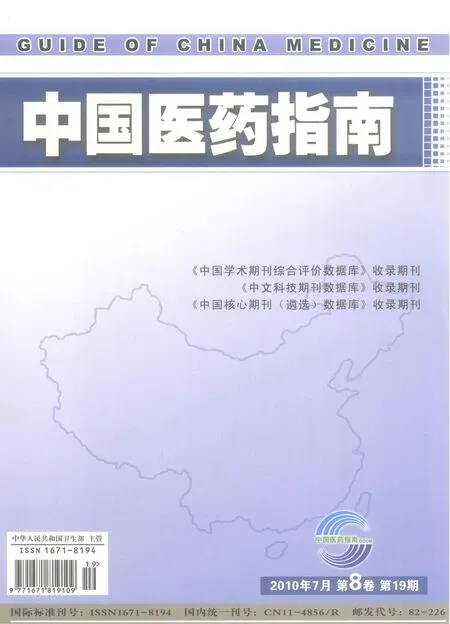金元四大家消渴病论要
窦立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203医院(161000)
1 刘完素消渴病论要
金代刘完素考《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补燥一条,总的精神是六气皆从火化。他说:“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他注解道:“枯,不荣生也;涸,无水液也;干,不滋润也;劲,不柔和也;皴揭,皮肤开裂也。”并指出消渴之病和燥热有关。即“燥渴为病,多兼于热”。
他根据《内经》治膈消,胸满烦心,津液燥少,短气,久为消渴,立消渴名方麦门冬饮子。所谓“膈消”者,以膈上焦烦故又名上消,源于心移热于肺,此方甘寒辛润,清滋并用,取法于《千金方》,人参甘草葛根益气健脾,麦冬知母茯苓润燥清热,栝蒌生津化浊,茯神竹叶清心滋肾,则源清流洁,消渴必止,燥热自除,实寓有养胃存津之旨。
他自制黄芪汤方主治肺消:“治肺消,饮水,小便多”,并明确其病机:“心移寒于肺”,就是心阳不足,不能温养肺气,肺气不温,则不能运化津液,所以饮水,小便多。其中黄芪益气甘温为君,人参五味桑皮麦冬为生脉散,一补一清一敛为臣,枸杞熟地滋肾生水为佐使,其服法令人称奇,“温服不拘时候”。即可以常服频服,现在观来上药皆为治消渴之要药,可谓方不虚传。
完素仿古意,又创食疗名方大黄甘草饮子。其组成为大豆、大黄、甘草。请看本方制方:“以上三味,用清水一桶,同煮6~8h,如稠浆至水少,豆软,盛于盆中,放冷,令患者食豆,食后消渴如仍不止,再照原方煮食。”当知此大豆富含植物蛋白,如大豆分离蛋白,浓缩乳蛋白,卵磷脂等,能“治五脏留滞,胃中结聚,益气解毒,润皮毛,补肾气”。大黄苦寒清热降脂,甘草和中健脾,二者皆有降糖之效,并提出本方适应症:“治男子、妇人一切消渴不能止者。”
完素对燥邪病机之补充,实开消渴病机学之先河,其根据火热论提出:“降心火,益肾水”为治疗诸热病包括消渴病的大法为后人所景仰。
2 张从正消渴病论要
金代张从正认为:“夫一身之心火甚于上,为膈膜之消;甚于中,为肠胃之消;甚于下,为膏液之消;上甚不已,则消及于肺;中甚不已,则消及于脾;下甚不已,则消及于肾。”所以,“火在上者善渴,火在中者消谷善饥,火在上中者善渴多饮而溲数,火在中下者不渴而溲白液,此其别也。”
张从正这些论据,显然凡是消渴病,姑勿论上、中、下三消都应诊断为“火”是发病的机制。兹就张从正的三消立论分述于下。
2.1 上消证有治膈消
“膈消者,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王太仆云……心移热于肺,久久传化,内为膈热。消渴而多饮者,此虽肺金受心火之邪,然只是隔消未及于肺也。故饮水至斗,亦不能止其渴也。其状多饮而溲数……此消乃膈消之消也。”
肺消。“肺消者,心移寒于肺……心为阳火,先受阳邪,阳火内郁,火郁内传,肺金受制。火与寒邪皆来乘肺,肺外为寒所薄,气不得施;内为火所燥,亢极水复。故皮肤索泽而辟著,溲溺积湿而频并,上饮半升,下行十合,故曰饮一溲二。”
此二节是张从正论述膈消与肺消的区别,认为膈消病轻,肺消病重。“膈消不为寒所薄。阳气得宣散于外,故饮一溲一,为易治;肺消为寒所薄,阳气自溃于中,故饮一溲二,为难治。”这是张从正对消渴病的上消证的发病机制的一种见解。
在《儒门事亲》一书中,麻知几编入刘完素《三消论》。论中说:消渴“肥美之所发也,其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而为消渴。”
“故治消渴者,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体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
张从正论治消渴,推崇完素自制神芎丸,“以黄芩味苦入心,牵牛、大黄驱火气而下,以滑石引入肾……以川芎、黄连、薄荷为使,将离入坎”;曾治数年不愈的消渴证,用三黄丸“加黄连一斤,作大剂,以长流水煎五、七沸,放冷,日呷之数次,以桂苓甘露散、白虎汤、生藕汁、淡竹沥、生地黄汁相间服之,大作剂料以代饮水,不日而痊”,他还用“缫丝煮茧汤,澄清顿服之而愈”。 “又以人参白术散、消痞丸、人参散、碧玉散、鸡苏散(六一散加青黛名碧玉散,加薄荷名鸡苏散)数法以调之,故治消渴最为得体。”
喻嘉言认为,“《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张子和谓膈消犹未及于肺,至心移寒于肺乃为肺消,如此泥文害意。岂有心移热于肺,肺传其热于膈,犹未及肺之理?要知心肺同居膈上,肺为娇脏,移寒移热,总之易入。但寒邪入而外束,热邪入而外传,均一肺消,而治则有别矣”(《医门法律·消渴门》)。嘉言对张从正的评论,提示《金匮》白虎加人参汤,说:“此治火热伤其肺膈,清热救渴之良剂也,故消渴病之在上焦者必取用之。东垣以治膈消,洁古以治能食而渴者;其不能食而渴者,用钱氏白术散。”属于上消见证:偏实热的。白虎加人参汤加麦冬、五味子;偏虚热的,钱氏白术散加麦冬、五味子。如因心移热于肺传为隔消,证显口渴心烦、精神短少,用《宣明方》麦冬饮子;心移寒于肺,饮少溲多,当补肺平心,用《宣明方》黄芪汤去桑白皮加葛根。
可是,张从正认为调治消渴一证,“调之而不下,则小润小濡,固不能杀炎上之势;下之而不调,亦旋饮旋消,终不能沃膈膜之干;下之调之而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病已可复作。能从此三者,消渴不足忧矣。”就是说,能够注意这3个方面的疗养,病就好治了。此即经验之语。
2.2 中消证
消中。“消中者,善饥之通称”。
风消。“风消者,二阳之病。二阳者阳明也,阳明者胃与大肠也。……火伏于内,久而不已,为风所鼓,消涸肠胃。其状口干,虽饮水而不咽,此风热格拒于贲门也,口者病之上源,故病如是。经曰“二阳结谓之消”,此消乃肠胃之消也。其善食而瘦者,名曰“食”,此消乃肌肉之消也。
此论中消由于心火移热于胃肠,既成消中,善食而瘦,所以又叫“食”证。中消的主要症状是消谷善饥,但是口渴尿多亦同时发生。由于胃火炽盛,胃中风火激荡,过量消化和消耗,所以又称为风消。张从正说是“肠胃之消”;风消的症状是多食消瘦,形容枯槁,体重减轻,精神疲乏,所以张从正又说是“肌肉之消”。他根据《内经》的说法,凡是多吃咸味和肥甘荤腻过多的食物,或服石类气悍药物,都足以资热。他说:“膏粱之人,多肥甘之渴,石药之渴。”意思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多吃肉类食物,或久服石药补阳,可以导致消渴病的发生。可是“藜藿奔走之人,多燥热之渴”。这就是说,生活水平低的,饮食粗糙,虽不影响成为消渴,但是奔走劳动于烈日之下,亦多发生燥热而渴。张从正认为,二者受病之因有所不同,而消渴之病则一。其实是有区别的,生活条件好的人,肥甘脂腻毫无节制,易患糖尿病,口渴而尿多;生活水平低的人,劳动于烈日之下,易患中暑病,口渴而汗多。前者属于饮食内因,后者属于暑热外因,二者不能混同论治。
张从正继承河间学说,用人参白术散治消中,多食溲数,肌肉消瘦,一切阳实阴虚,风热燥郁。猪肚丸治胃津被火劫而消中,方出《三消论》中。
2.3 下消证
肾消。“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肾消”(《三消论》)。
蛊。“脾气传之肾,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液,名曰盅。王太仆云,“消灼脂肉,如虫之蚀,日渐损削,此消乃膏液之消也”。后人论三消,指以为肾消,此犹可治,久则变,不救必死,此消乃消及于肾脏者也。”
张从正说:“后人断消渴为肾虚,水不胜火则是也,以八味丸治渴,其药则非也,水未能生而火反助也。”张从正这一论点,仍本完素“燥热太甚”的原理。所以说,虽有六味泄火养阴,而桂附之温热,反致肾水难滋,则上焦心火亢甚。因此张从正与刘完素的理论和治则基本一致。然张从正论断颇有偏执,倘肾气虚冷不能蒸腾谷气,小便多而肌肤槁,津液不生而病消渴,脉缓舌淡,则应温肾阳以蒸津液,八味丸又为适应的方剂。
下消的主要证,为小便“出白液”如脂。孙东宿引证《总录》论消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有脂似麸片而甜,消渴病也。”证实尿中有大量糖分渗出,大肉和腓肌消瘦显著,表现为营养障碍而缺乏。所谓“蛊”,描述肌肉日渐消瘦,像有虫在剥蚀一样。所以,上、中、下三焦的消证关键在肾。因为“肾为胃关”,关门开而不合,水下而无底止,必须滋水救阴,当用大剂六味地黄汤加生北查、北五味子甘酸化阴法,以滋养肝血、坚固肾关、控制尿糖和血糖。总而言之,三消和消渴是一种病,症状或见于“上消”口渴 或见于“中消”消谷善饥,或见于“下消”小便出白液而甜。它的突出症状一出现,一般症状亦相应发生,例如口渴、脉数大,必小便多;消谷善饥、脉实大,必口渴多尿。所有这些症状,或同时发生,或先后迭见,既互相联结又互相影响着。比如说,口渴与尿多的矛盾,消谷善饥与肌肉消瘦的矛盾,显然,渴甚当滋肺,食(包括多食与消瘦)当清胃,尿多当固肾,这是一般认识。比如说,治渴是以滋肺为重点,还是以固肾关为重点?从表象看应当滋肺,可是肾关开而不合,愈饮愈消,愈滋愈渴,水下而无底止,只有关门开而能合,自能津液上滋而渴止。又如,消谷善饥应是健康人的表现,可是多食反致消瘦,这种饮食不生肌肤的病症,是以益脾为重点,还是以泄胃为重点呢?有人说,消谷善饥为脾瘅,精气津液在脾,多食而瘦,应当益脾。可是,胃气“重强”,不能输精于脾充实肌肉的营养。张从正说,病从火断,当用寒凉,治法以泄胃火减弱胃机能亢进作用,使脾能恢复为胃以行其津液,肌肉才得以充实和健壮。
3 李杲消渴病论要
元代李杲提出:“饮食失常,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劳役过度而损耗元气。既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此为脾胃学说主要理论依据。一切内伤病发病病机皆不过此,消渴病也不例外。后世医家治消渴皆顾及脾胃,取益气健脾法子治病始终,得益于斯。
他认识到三消传变的某些规律,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处方之制”。即张从正的“七方十剂”法则。他说:“如高消中消,制之太急,速过病所,久而成中满之病,正谓上热未除,中寒复生者也。”制剂的选择应根据病变脏腑的远近,并提出制剂原则,即:“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皆适至其所为故”。上消证宜用小方,君一臣二,分次少服、频服,使药力逗留上焦而发生疗效,如白虎汤药;下消证宜用大方,君一臣三佐九,宜用药味少、用量重,食前顿服,促使药力速达下焦病所,如六味地黄丸药。
在所撰《东垣十书》中载有和血益气汤、当归润燥汤、生津甘露汤、地黄饮子、生津甘露饮子等方,均以脾胃为本,清热健脾,益气升清。处方严谨,行之有效。
4 朱丹溪消渴病论要
元代朱丹溪根据“阳有余阴不足论”,提出治疗内伤病又一法门:即“滋阴降火”法则。如云:“消渴,养肺、降火、生血为主,分上中下治。”又提出单味药:“天花粉乃消渴神药也。”又提出禁忌药:“三消皆禁用半夏。”在临床中确有其意义。
他研制的名方秘丹尤具特色,组成:“白藕汁、生地黄汁、牛乳汁、黄连末、姜汁、天花粉末,右以各汁调二末,入白蜜为膏,以匙抄取,徐徐留舌上,以舌汤送下,日三四次”。黄连苦寒,泻其上盛之火,花粉是消渴圣药,藕汁,地黄汁甘寒,滋其将涸之阴,乳汁、白蜜维持营养以代替肥甘,生姜汁刺激唾腺以增加分泌。上汁皆为滋阴生津润燥之品,长服可取,妙在舌上含服,有吞津生津之意。
传世名方如大补阴丸、知柏地黄丸等,但脾胃虚弱者必结合咸温以培下(八味丸,虎潜丸之类);如火炽而阴未伤,取针对性的单味药,如:大补丸泻相火,必有酒制,以发挥清热泻火的作用。在滋阴降火中还注意了肺胃阴虚,用生地汁、梨汁、藕汁之类,甘寒以滋液,分清苦寒为清,甘寒为滋,发展了河间泻火而不滋阴的用药原则;注意脾胃元气,又吸取了东垣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