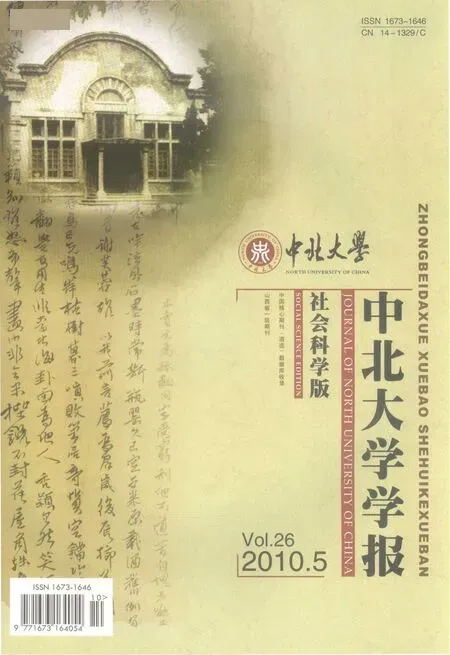用年鉴学派的技艺解读《心灵史》*
康建伟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用年鉴学派的技艺解读《心灵史》*
康建伟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心态史学是年鉴学派的重要分支。在年鉴学派的历史时段理论框架下,借助“事件”、“情势”、“结构”这一批评视角,对张承志的《心灵史》重新解读,必然能凸现出文本的深层意蕴,从而体味作者对宗教史情感贯注的文学书写。
年鉴学派;结构;文学批评
心态史学是年鉴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心态史(或译心理史)是《年鉴》以及聚集在这本杂志周围的史学家创立的属于心理学范畴的一个概念和方法。这里的心态是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心态史学在法国,乃至世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甚至有些人用心态解释全部的历史演变。张承志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宗教考古调查。作为一名科班出生的史学研究者,他不可能不对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年鉴学派视而不见,单就《心灵史》这一题目,就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了年鉴学派。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论者尝试用年鉴学派的历史时段理论重读《心灵史》。这里使用“技艺”这一术语是因为年鉴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布洛赫曾撰写过《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后来保罗·利科在《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这个小册子中列了“历史学家的技艺:年鉴学派”来介绍年鉴学派。
按照历史时段理论,让我们先来看看“短时段”“事件”。在这一层面是各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政治、军事事件。在小说中作者分七门(作者用哲合忍耶内部秘密钞本作家的体例,称之为“门”,而不是“部”或“章”)讲述了七名哲合忍耶穆勒什德(领袖、圣徒)的故事:创始人马明心在也门学教15年后受师命归国传教,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兰州被杀。其义女赛力麦为救其父在金城关战败自杀,教民苏四十三卫教造反血染华林山。第二代平凉太爷穆宪章因其教在靖远狼台山、石峰堡的反抗而连累入狱,监禁致残后病死,殁后传位于第三代船厂太爷马达天。他在迫害与喘息中维持了六年,仍不免在流放黑龙江布盔中被折磨病死;第四代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继任掀起了教内的一大复兴;第五代十三太爷马化龙面临屠城时自缚,以全族三百余人赎金积一带回民死罪,同治十年凌迟而终;第六代汴梁太爷马进城如一轮瞬忽的弦月,12岁受宫刑,不到25岁就在磨难中病死;而第七代沙沟太爷马元章把一个血脖子教劝导上了和平的道路,走向复兴,并实现了震惊西北的“沙沟太爷进兰州”。随后归乡,死于海原大地震。
七代穆勒什德,200余年里50多万哲合忍耶命丧黄泉,哲合忍耶“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鲜血染红了“绿旗”,以至被外人视为“血脖子”教。在这二百多年里,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哪怕任选一人,也足够成就鸿篇巨制。金城关、华林山、石峰堡、金积堡、东沟,一处处地名被鲜血染红,而一处处圣徒的拱北(圣徒墓)都是一处处血淋淋的纪念碑。但作者显然并没有将笔墨完全聚焦于某个人物或是某个事件上,惟此才能不粘着于事件的细节而丧失了深层意蕴的探求。布罗代尔认为事件史虽“最富于人类趣味”,却也最为肤浅。“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在外,黑暗统治一切。”事件是“表面的动荡,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尖”,“我们必须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它们”[1],而应更为关心个人与事件发生的语境,即“情势”。
所谓“情势”,这一术语挪用自经济学的“商情”、“行情”,也许使用“行情”似乎更为生动现象,也更能体现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它不是短时段的几天、几月或是几年,而是10年、50年、甚至100年的较长时段,它构成短时段中“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按照总体“行情”,我们可以根据哲合忍耶与执政者的关系(也即其流血与喘息的时间)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合忍耶的古代史,从第一代圣徒马明心出世(约康熙57年到康熙59年,即1719年至1721年。因文中未详细记载其出生年月,只提到在乾隆八年到十年之间,马明心回到甘肃,此时已年满二十五岁。)直到第六代马进城去世(光绪十五年即1890年)一百七十余年。在这一百七十余年里虽有过短暂的喘息(比如第二代、第四代),但总体而言,即使这喘息也是迫害的间隙,而就哲合忍耶的古代史来看,流血牺牲依然占绝对的主导。在这一百七十余年里执政者的残酷镇压迫害与哲合忍耶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构成了基本的主线。第二阶段是哲合忍耶的现代史,即马进城病逝(1890年)到第七代马元章去世(1920年)30年内,是哲合忍耶的空前复兴时期,在民国八年实现了震惊西北的“沙沟太爷进兰州”,使哲合忍耶飞跃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教派之一。马元章去世后,哲合忍耶迈向了当代史,这就是第三个阶段,而作者行文就此结束。从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把握作者对哲合忍耶与政治、社会环境的思考。哲合忍耶本是穷人的宗教,在贫瘠的大地上追求心灵的富裕和自由,然而在教派纷争和统治者的迫害打击下,这种基本宗教信仰自由都无法实现。哲合忍耶不断有人死去,不洗遗体、带血下葬,甚至舍西德(殉教者)都成了人人争抢的角色。哲合忍耶成为以追求束海达依(圣教牺牲、殉教之路)为最高境界的“血脖子”宗教。在第七代,哲合忍耶因其与清庭的血海深仇而在清末民初推翻清政府的战斗中与民国政府找到了共震点,哲合忍耶首次获得了执政者的认可,与官府达成默契礼让,双方放弃暴力。在这种“情势”下,马元章靠着他的权威和虔诚苦苦地劝说,把见惯了鲜血的一个被迫害的教派劝导上和平的宗教道路。由流血到和平如果用俩字说明原因,我们想到还是年鉴学派的“情势”。那么在“情势”之下又是什么呢?
现在该是我们触及到底座“结构”的时候了。“长时段”是“一部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流逝与变化滞缓的历史”,是在扫除了“事件闪光的尘埃”,分析了“行情”之后我们直面到的历史、心灵的深层真实。从这里我们看到仍然是对深度模式的探究。虽然作者使用独特的形式,用作者的话讲就是“不能用上述学科(指考古学、蒙古史、中亚探查、伊斯兰研究等史学范畴)和形式(论文、小说、诗和散文)界定的文本《心灵史》”。虽然文本中议论、教义、历史、文献、诗歌杂糅,但我们依旧把它看作一部小说,而其先锋探索意识相比内容本身而言并不是很强的。虽然在对历史的叙述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等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2],我们还是倾向把它作为一部追求历史真实的传统历史小说来读的。
在第一门作者描写了一方“圣域”,那么这方“圣域”指的是哪呢?广义而言指“东半个甘肃。南北全部宁夏——银色大川和西海固山地、青海一角。天山两麓的大半新疆绿洲儿。”但作者把更多的笔墨集中于以沙沟为中心的黄土高原东南角回民聚集地西海固地区(西吉、海原、固原)。在哲合忍耶那里,他们有独特而神秘的地理学。在《曼纳给布》中列举了如下的地名:鲁过闸、驼场堡、徐州(可能指淮阴)、秦州、凤翔、下堡、穆家槽子、平凉、石河子、玛纳斯、阿克苏……这是一种形象而奇特的地理观念。一个村庄完全可以大名鼎鼎,而一个大省却可以不为人知。透过这一独特的地名排列,我们看到了一种对现世城市、农村的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是信仰的地理,一个地方的地位完全由其在这方信仰的“圣域”中的重要性而决定。难怪在这方“圣域”中,即便是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也只是这方“圣域”的边缘,而名不见经传的沙沟却是这方“圣域”当之无愧的信仰的中心。然而在世俗人的眼中,这是一方怎么样的“圣域”呢?“庄稼是无望的希望。”“天旱的年头,种出去不仅颗粒无收而且割不回一堆麦草。”“女人们嫁不出去,她们穷得往往没见过邻村,没有一身衣裤。”“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风景凄厉,民性硬悍。除开神秘主义(苏菲主义)外,没有什么力量能适合于这里。”马克思说过,宗教是绝望的人的希望。也许是哲合忍耶这穷人的宗教产生的最好的注解。“在这样的天地里,信仰是唯一的出路。”“黄土高原依然是千沟万壑灼人眼瞳的肃杀。日子还是糠菜半年饥饿半年天旱了便毫无办法。但是穷人的心有掩护了,底层民众有了哲合忍耶。”“穷人的心,变得庄严了。”透过“长时段”我们终于触摸到了作者跳动的脉搏,这便是信仰,这便是宗教。她的力量征服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也征服了张承志这个在北方的草原上驰骋的汉子。“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3]”他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一名哲合忍耶。
那么什么是哲合忍耶呢?“如果要惟妙惟肖地、简化地给外人介绍,或是用一个画面来捕捉它——那么我想,所谓哲合忍耶,就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刚强回民,手拉手站成一个圈,死死地护卫住围在中心的一座坟。”那么哲合忍耶的哲学内容是什么呢?一是“伊斯兰的终点,是无计无力”;二是“川流不息的天命”。在对哲合忍耶的介绍中,作者的历史观、宗教观也渐渐浮出水面。张承志认为“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鉴于此,他用五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一名和西海固的贫民一样的多斯达尼(教民)。他认为唯有这种心灵相通才能理解历史。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它与感情相近,理性相远”,而“宗教是世界观,更是人、人性和人的感情的产物。”正是这种情感贯注的教史的文学书写铸造了《心灵史》辉煌篇章[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心态、心灵对哲合忍耶所做的重新的理解。
当然,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演变的企图是一种曲解和夸大。研究社会的心理学家一般没有从历史的层面而单纯从社会学家的视角进行观察,精神分析属于个人而非集体的事务。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有意创立的历史心理学的打算早就流产了,而今文史与心理的对话仍然举步维艰。但是,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它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视窗,也许我们借此可以看到从未有过的风景,也是张承志的《心灵史》再次带给我们的思索。
[1]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M].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张承志.心灵史: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2.
[4]王安忆.《心灵史》的世界[J].小说界,1997(3):181.
An Analysis of History of the Sou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nales School
KANGJianwei
(School of Humanities,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 730000,China)
Mental Hist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ranches of Annals school.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ory of Annals school,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History of the Soulwritten by Zhang Chengzh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ch literary criticism as″vent″,″situation″and ″structure″to probe into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text so that the author's feelings for religious history can be understood.
annals school;structure;literary criticism
I06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0.05.015
1673-1646(2010)05-0072-03
2010-01-22
甘肃政法院科研资助青年项目(GZF2010XQNLW52)
康建伟(1980-),男,讲师,硕士,从事专业:文艺学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
——从叙述者“我”的角度解读心灵之作《心灵史》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