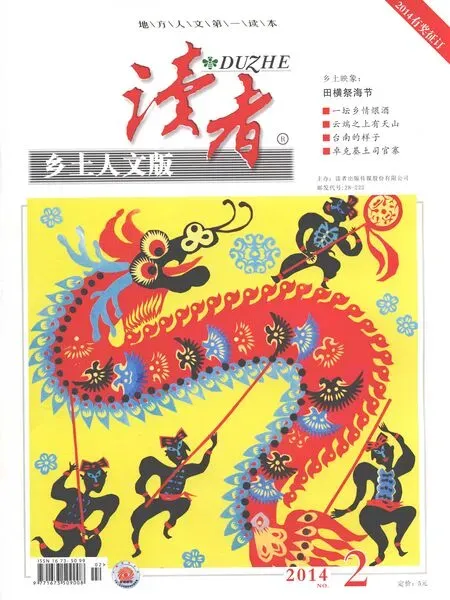去镇上喝牛肉汤
文/邓洪卫 图/小黑孩
去镇上喝牛肉汤
文/邓洪卫 图/小黑孩
我爷爷排行第二,人称“二太爷”。他哥哥,人称“大太爷”。大太爷走得早,面我都没见过。二太爷走的时候,我才六七岁,不太记事,什么事都是听我父亲说的。我父亲说,这两位太爷,个头都不高,一米五几吧,容貌也相似,小头小脑的,但脾气不同—二太爷性子慢,温温吞吞,实心眼儿;大太爷性子急,风风火火,脑子转得快,心眼多得跟葡萄一样,一嘟噜一嘟噜的。
两位爷爷天生是冤家对头,相互看不惯。大太爷说二太爷:“你这一辈子就没拉过硬屎。”二太爷说大太爷:“你拉屎都能拉出火药来。”
大太爷老是欺负二太爷。两家的水田挨着,中间隔着一道田埂子。大太爷绝,不断地削田埂子,越削越窄,硬是把多半的田埂削到自家田里。大太爷的田比二太爷的田要低几厘米,大太爷不服气,偷偷在田埂上打眼子,二太爷家田里的水就慢慢地渗到大太爷家的田里去了,二太爷家的水田成了旱田。
二太爷气,但他面皮薄、嘴皮厚,说不过大太爷,往往被大太爷“噼里啪啦”说得面红耳赤,回不出一句整话来。
二太爷没办法,惹不起还躲不起啊?他举家搬到一个荒草冈子上,盖房,开发新田地。
大太爷和二太爷离得远了,碰面就少,碰面了也不说话。
再怎么躲着,还是一个村子的人,怎么也躲不开。每个月至少碰两次面,在六套镇上的牛坊里。
镇上只有一家牛坊,杀牛,卖肉,逢大集的时候,免费供应牛肉汤。大太爷和二太爷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喝牛肉汤。每到逢集,大太爷和二太爷都会到牛坊喝牛肉汤。没吵翻的时候,俩人结伴一起走。吵翻后,就岔开时辰,分开走,到了牛坊,各自从怀里掏出一瓶三芋干酿的酒,两块烧饼,打一碗牛肉汤,慢慢吃,慢慢喝。他们不吃牛肉,吃牛肉要花钱,舍不得。有时候,大太爷为了寒碜二太爷,会狠下心买几片牛肉,故意嚼得“吧唧吧唧”响,让二太爷听到,显示自己的日子滋润。二太爷装着没听见,“呼噜呼噜”喝自个儿的牛肉汤。
牛坊的人,买肉的人,喝汤的人,瞅着这两个,都绷不住笑,脸上笑,心里感慨:“亲兄弟呀!”
二太爷走出牛坊,忍不住唾了一口,在心里骂道:“哼!叫你绝,断子绝孙!”
大太爷跟大奶奶结婚20年,没见一儿半女。
那一年,二太爷生病了,病得厉害,请镇上的中医克三先生来看。克三先生直摇头:“难治啊。”
克三先生一贯自信,他说难治,等于判了死刑。但先生又撂下几味药:“吃吃看看,好便好,不好就拉倒。有好吃的别落下,说吃不着就吃不着了啊。”
药一天天地见少,二太爷的病还不见好,眼见得一天天消瘦下去。奶奶想起克三先生的话,含着泪问二太爷:“想吃些啥?”二太爷咕噜着喉结,说话都含混了。正好大太爷来了。大太爷听说二太爷有今天没明天了,把恩怨吞进肚里,来看一眼。
二太爷的话大太爷一听便懂,说:“他问明天是不是集。”又自语道:“是集呢,他想喝牛肉汤了。”
奶奶说:“那可怎么好?”
大太爷说:“明天我去镇上端一碗牛肉汤来。”
奶奶说:“这么远,碗口大,存不住啊。”
大太爷说:“你家不是有一个罐子吗?加上盖子,慢慢走,洒不了。”

奶奶就把罐子拿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大太爷就抱着罐子去集上。过了中午,罐子回来了,人却没回来,罐子是邻居杨麻子抱回来的。
1939年3月26日,农历二月初六,日本鬼子在六套镇制造了“二六”惨案,屠杀了108个人。大太爷就在这108个人之中。
杨麻子说:“本来,大太爷跟我一起跑的,完全可以跑得快些,可他抱着罐子,怕跑快了洒了汤,就落在了我后面,正好遇上了鬼子,被刺刀挑了。等鬼子走后,我回去找在集上跑散的孩子,孩子没找到,碰到了奄奄一息的大太爷。他把罐子递给我,请我一定要带回来给二太爷喝。说完话,他就断气了。”
土黄的罐子已经变成了血红色。奶奶打开来,汤还有热气,搅了搅,还有几片牛肉。
喝了牛肉汤,再吃了几味药,几天后,二太爷的病好了,又活了40个春秋。
大太爷无儿无女,死后,我父亲每年都去上坟。二太爷死后,坟跟大太爷的坟相邻。每到鬼节,我父亲都带着我去烧纸。在两座土坟的中间,把纸分成两堆,点着。有一回,两堆纸刚烧完,风一吹,烟灰合到一处,飘上了天空。我母亲说:“是不是两个太爷又吵起来了?”
父亲摇摇头,说:“不是,两个太爷拿了钱,一起去镇上喝牛肉汤了。”
(甘 来摘自《小说月刊》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