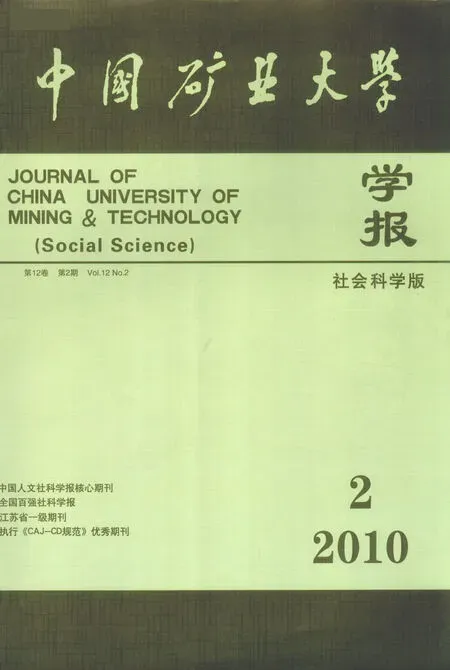福柯的身体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及其局限
胡可清
(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福柯的身体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及其局限
胡可清
(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福柯身体理论的主要论点是权力关系在社会领域内通过身体进行运作,女性主义由此得出结论,从生物差异角度建构的性别不平等理论对维持社会等级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尽管身体理论影响巨大,但在一些关键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如缺乏对身体性别特点的关注,更严重的局限性在于对权力单向度的分析,把个体降级为驯服的身体,因此无法解释妇女在当代社会的丰富体验。女性主义者通过对女性经验和历史的再发现和重估揭示了女性不再是被动牺牲品。福柯对个体作为被动身体的诠释在无意识中又将妇女推向被动的沉默地位。
身体理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福柯
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得到女性主义者的青睐和追捧,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广泛地汲取福柯的权力理论以及身体和权力相互关系理论来解释妇女压迫问题的有关方面。福柯认为性别不是身体内在的或自然的属性,而是特定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观点为女性主义者们提供了理论框架,来分析妇女的生存体验为何单调贫乏,妇女为何囿于文化传统决定的女性身份。一方面福柯的身体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女性主义理论中,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也敏锐地意识到福柯理论的局限。福柯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决定影响将社会主体降格为被动的身体,因此没有给个体开辟自主活动空间。女性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和重估女性生存体验,福柯女性主体论的缺乏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一、身体和后结构主义
身体理论不仅在福柯思想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法国解构主义思潮中同样如此。传统思维模式以二元对立思想体系为基础,身体理论则和后结构主义对经典思维模式的解构密切相关,因此处在主流思潮的地位。传统思维解构围绕两个方面展开:1)二元等级结构的倒置:精神与物质、理智和情感。2)提取二元结构中相互矛盾的元素并证明这些元素实际上构成叠覆关系。在经典思维模式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笛卡尔提出的思维/身体对立模式,这一对立结构推崇抽象思维,贬抑身体需求;抽象思维位于理性思想的中心位置,身体则与理性思维和精神相对立,譬如情感、激情和欲求。在对古典思维体系和主体哲学的批判中,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解构聚焦于特定的对立结构。对立结构的思想基础——理性和反思,是建立在身体需求的排斥和压抑之上的,后结构主义者通过证明这一点来颠覆稳定性和统一性概念。身体需求代表欲望、物质性、情感和基本需求,身体范畴的概念能够用来对抗人类文化的思想中心论,因此具有战略意义。南茜(Nancy Fraser)指出,“身体和感官享受理论能够以戏剧化的方式对抗中心理念——主体性、理想性和升华,西方文化赋予这些概念优先地位”[1]。
“要读懂福柯,一定要了解尼采,福柯曾自称为尼采主义者”[2]。福柯在《尼采、谱系、历史》中首次提出身体概念,他认为源自主体哲学的形而上学概念充斥历史,并批判了历史的传统形式。传统历史以超验目的论为基础,以普遍接受的模式和线形结构阐释历史事件,形成的统一性纯属假象。实际上,用统一性、整体性原则解释事件剥夺了事物的独特性和鲜活性。“我们熟知的世界最终不是简单的形式框架,过于强调本质属性,最终意义和价值往往会扭曲事件的真相。与此相反,世界是由纷繁复杂,错综交织的事件构成的”[3]89。福柯认为,传统历史研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倾注了大量笔墨,强调杰出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重大作用,强调人性中不变的元素;从宏观角度研究历史,历史发展被解释为揭示或印证人类的本质属性,在解读历史时自我陶醉地确认现在的身份感,任何否定的意识都被压抑。
针对历史研究的传统类型,福柯吸收源自尼采的权力至上论,将历史的外在化形式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相对比。历史不是平稳连续的发展或者通过理想的图式运作。不同力量集团之间持续不断地争战,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权。人类社会战事频繁,政权更迭,直到矛盾暂时达到平衡状态,法制才会取代战争,统治集团以法制实现暴力统治。福柯把身体置于不同力量集团斗争的中心位置,用身体概念取代自命为历史中心的主体带来方法论的变化。历史发展不再从意义揭示的角度阐释,而是被理解为不同力量集团之间的冲突—永恒的征战。处在政权争夺中心,身体被不同的矛盾力量左右。福柯从反本质主义的角度考察身体,“人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他的身体具备稳定性可以作为自我认识或理解他人的基础,身体在其表面留下往昔经历的印痕,身体是历史事件铭刻的表面。谱系作为对历史发展的研究,位于身体和历史话语当中,它的任务是揭示被历史印刻的身体和历史摧毁身体的过程”。
二、女性主义和身体
权力关系在福柯的身体概念中以具体的形式体现,对女性主义关于身体概念的思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相关的后结构理论中,福柯因强调身体是历史和文化实体,得到女性主义者最多的关注。巴特科思基(Bartkowski)因提出身体是历史实体的理论使福柯从包括德里达在内的其他理论家之中脱颖而出[4]。德里达将身体视为笼统的哲学差异问题的隐喻,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强调具体是更重要的,以女性身体作为隐喻再现关于差异的抽象哲学问题与妇女作为整体的性别差异的历史体验相去甚远[5]。福柯的身体理论对女性主义思潮所作的重大贡献是将身体视为具体的现象,未用思想性取代物质性。不从性别差异角度思考身体理论是困扰女性主义理论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身体理论在关于妇女压迫现象的分析中占据中心地位,因为性别不平等理论的合法化建立在男女身体差异的基础上,男尊女卑观念被生物学理论证明。要颠覆以生物功能定义妇女社会角色的父系体制,需要重新思考这一理论。妇女压迫根源于父权对女性身体的占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压迫来源于身体或自然性,在将具体的压迫策略合法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利用了自然的身体作为工具。如莫尼克(Monique Plaza)所说:“如果性在父权体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是因为社会彰显性的表面形式,从而遮蔽压迫的体系。”[6]将性别不平等理论置根于性差异会产生很多理论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女性主义者区分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概念,社会性并不等同于自然的身体,它代表身体的文化意义。自然性/社会性绕过了人的生物构成决定社会命运理论,在社会性之中,身体实际上被中性化了,所有的外部特征都被否定。自然性和社会性区分了性差异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社会性成为自由流动的实体,它的结果是女性的身体可能象征男性,而男性的身体可能象征女性。
从心理分析角度进行研究的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了纯粹社会学方法的局限性。从内化社会规范的社会学角度研究身体会导致性身份叙述的匮乏,绕开身体的物质性现实,欲望和精神活动的相互关系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身体的物质现实不应被完全排斥在理论体系之外,但要避免从纯粹生物学角度思考身体。布拉多蒂认为母性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女性主义思想在女性身体研究上的进步,较早的女性主义思想拒绝母亲身份的概念,现在的女性主义者把母亲身份看作父权统治的基础,同时也是维护女性身份的堡垒。身体被看作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交汇点和社会政治权力和主体范畴的交界。《性史》中福柯提出的身体观以反本质论的方式思考身体,与此同时没有否定身体的物质性。在《性史》中,福柯反对将性视为自然现象,性并不源于欲望,性实际上是文化建构,以社会统治和控制性行为作为根本目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性是身体自动的机能,权力关系掌握身体及其物质性、能量、感觉、感官享乐。在权力操控的性行为中,性是最内在的因素”[3]155。“自然性”概念的确立颠覆了性和权力的关系,性不是权力关系产生的现象,性被看作难以驾驭的力量,权力只能试图压抑和控制。性不再和权力有本质联系,而是置根于具体的、难以驾驭的迫切性,尽管竭尽全力进行控制。性和权力关系的颠覆打破了对性的历史建构,性挣脱社会桎梏成为自然性的显现。福柯关于性的概念打破了自然性/社会性中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社会性不再用文化限定自然性,而是指出性被确立的途径。朱蒂斯(Judith Butler)说:“社会性之于文化,自然性之于自然的关系被解构。”[7]福柯无意否认身体的物质性,实际上他强调了身体的物质性以驳斥性的精神性。权力的调用直接和身体相关——和身体功能和生理过程相关。因此不仅不能抹杀身体,还要彰显身体的存在。身体的生物性和历史性不是互相取代的,在现代科技权威的影响下越来越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福柯的理论模式显示,离开身体的文化含义不可能探讨身体的物质性,身体的冲动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它们在社会性的意义网络中产生。身体在排除文化影响下的本质无法认知,性解放也无法挣脱权力关系。为建构社会关系在身体中制造性——福柯的观点不仅为女性主义研究女性和女性思想提供了动因,而且激发了男性和男性身体相互关系的研究。
三、性别差异的忽视
福柯关于身体的思考对女性主义身体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不一而足。必须承认,女性主义者注意到福柯在处理性别问题时的缺憾,主要的问题是福柯的理论分析没有对身体惩罚措施的性别特点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缺憾导致了在社会理论中非常突出的性别盲视问题,福柯不加区分地将身体视为中性,因而不能解释男性和女性和现代规训制度的关系有何不同。福柯认为自然性是不存在的,不能先验地确定个体自然性的差异。通过分析有关妇女的不同实践和话语,巴特基(Bartky)揭示了女性身体如何受控于统治女性的权力。福柯的规训权力定位于监狱和疯人院,巴特基认为规范女性身体的制度很难定位,因为没有明确的实施领域。制度性结构的缺乏会导致这样的印象,女性主体秉承女性特点是自然的和自动的。巴特基还认为福柯没有考虑到为限制妇女行为采用不同的规训妇女身体的方法。在《规训和惩罚》中,性别盲视显而易见,权力采用同形结构对男性和女性身体加以控制。柏西亚(Patricia)这样批判福柯,在男性规则之外,没有关于女性身体的具体规则,福柯没有合理地区分女性和男性囚犯。布莱恩认为在某些方面,“不同性别的囚犯在年龄、社会背景和职业上有相似之处”[8]。导致女性入狱的罪行和男性一样,大多是盗窃。在社会学上,女性犯罪和男性犯罪在根源上有本质的区别。女性犯罪的主要根源在于女性次等的生物构成,显而易见与女性根本的生理特征有关——娇弱、紧张、多疑。妇女中的自杀和谋杀被看作子宫的功能紊乱,女性犯罪分析将女性性行为等同于病态和退化。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女性行为由生物特性决定,受社会的影响不大,因此女犯接受改造的可能性低于男性,男性犯罪的动机根源于社会而非机能紊乱。在很大程度上,惩罚制度在女犯改造中发挥不了明显的作用。福柯漠视两性差异,产生了植根于中性社会理论的性别歧视,导致了女性永远的沉默和弱势地位,尽管巴特基批评的大体走向是正确的。在她研究身体的理论方法中存在一些内在的问题,例如过分强调为控制女性身体采用和男性完全不同的策略,会形成孤立的女性压迫史,这样反而导致了男性女性生存体验人为的两极分化,其结果是女性被排斥在男性社会领域之外。巴特基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了女性是父权统治体系的被动牺牲品。控制女性身体的策略是完整的、永恒的、全面的,当妇女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的、经济的、性的自觉意识时,她们便完全处在父权统治的凝视之中。巴特科斯基似乎把在社会关系中的女性身份的建构简化为受男权统治的漫长的受压迫历史。勿庸置疑,分析统治策略无疑要考虑对待女性身体的不同方法,还必须注意不应使方法极端化或两极分化。女性身体的历史不应完全和男性分开,这不是否认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建构的差异性,而是去接受社会历史作用于女性身体的不同方法。女性身体概念晦涩难懂,分析女性身体有必要考虑女性专属的统治策略,还要考虑到女性身体史和男性身体史交织错综的关系,二者都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变迁紧密相关。
四、女性经验的遮蔽
批评福柯在某种程度上对性别差异视而不见是正确的,但他们指出的问题是白璧微瑕,而不是理论体系中的主要漏洞,更严重的局限性来自于权力的单向度概念,使理解身体和性别身份的关系产生了很大问题,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单向度批判来自于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福柯的理论宣称权力是庞杂的、异质的、生成性的现象①最重要的方法不是试图从中心演绎出权力,而是致力于发现权力在基层的渗透程度,必须对权力进行上升模态的分析,从最微不足道的机制开始,研究权力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技术策略。。他的历史分析将权力描述为集权的、铁板一块的力量,对被统治者进行无情的压迫和控制。福柯对权力探究的单向度导致权力定义的漏洞,权力关系仅从权力设置机构的角度思考,而没有从权力的控制对象思考。彼得(Peter Dews)指出福柯对惩罚体制内规训制度分析倾向于统治者的视角,而没有考虑被控制者的声音和身体[9]168。未能从官方惩罚体制话语之外的视角思考,福柯过高地估计了规训制度的有效性;对权力进行单向度的描述,福柯没有阐述受控于规训权力的被统治者的反抗。在理论上,福柯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权力关系,哪里就有反抗。权力无情地在被动的身体上印刻自己,福柯没有阐明身体的里比多能量如何反抗权力的恶意运作,身体实际上被剥夺了反抗的力量。对身体物质性进行扼杀的结果是权力成为普遍存在的形而上学。从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效果给身体下定义,福柯将被统治者理解为驯服的身体而不是个体。个体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抓住了福柯忽视的当代权力复杂、矛盾的本质。单纯指涉身体经验并不能达到对被统治者的理解,而应考虑法律的、社会的、心理的综合建构。把复杂性变成以物质为中心的规训权力,福柯抹杀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不同的经验模式。福柯强调,在19世纪女性身体被认为完全沉浸在性欲之中,在本质上是病态的,相关的知识允许权力控制女性欲望和性关系,调节女性和社会、家庭、孩子的关系。19世纪的统治政策对女性起到了有效的压制作用,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在妇道观的压抑和控制中,矛盾性和不稳定性有时给女性提供空间,突破当时的制度。将个体降格为驯服的身体不仅过度简化了性别身份产生的过程,还忽视了女性在当代社会中争取自由的重要性。当代社会关系不是千篇一律的生物能量的表现,而是各种形式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形式的权力和实际的权力有何差异,女性的自由大多来自于法律的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妇女获得投票权。其它的法律权利,如允许妇女流产,不能简单地视为对身体控制的新形式,这些权力的获得使妇女有更大的自由控制自己的生活。福柯将当代权力描述为身体控制的主要形式,遮蔽了控制权力运作的现实生活环境,抹杀了女性统治的本质,使权力在工业社会中的统治作用过于简单化。
结论
勿庸置疑,福柯的身体理论对女性主义分析妇女压迫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福柯的主要论点是权力关系在社会领域内通过身体进行运作,女性主义由此得出结论,从生物差异角度建构的性别不平等理论对维持社会等级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尽管身体理论影响巨大,但在一些关键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如缺乏对身体性别特点的关注,更严重的局限性在于对权力单向度的分析。把个体降级为驯服的身体,因此无法解释妇女在当代社会的丰富体验。女性主义者通过对女性经验和历史的再发现和重估揭示了女性不再是统治的被动牺牲品。福柯对个体作为被动身体的诠释在无意识中又将妇女推向被动的沉默地位。
[1] Fraser,Nancy.Unruly Practices:Power,Discourses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62.
[2]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3.
[3] Foul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M]trans.R Hurley Harmondsworth:Penguin,1978.
[4] Bartkowski,Frances Feminism and 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M].Boston:Northeastern UP,1988:56.
[5] Braidotti,Rosi.The Politics of ontological Difference:In Betwee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M].London:Routledge,1989:22.
[6] Plaza,Monique Phallomorphic Power and the Psychology of Women[J].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1978:9.
[7] 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Femis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York:Routledge,1990:7.
[8] O’Brien,Patricia Crime and Punishment as Historical Problem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J].Princeton:Princeton UP,1978:514-518.
[9] Dews,Peter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 of Critical Theory[M].London and New York:1987:168.
Impact and Limitation of Foucault’s Body Theory to Feminism
HU Ke-q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Xuzho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Foucault’s theory of body maintains that the power relations operate principally through the human body in the social realm.Therefore,feminist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heory of gender inequality constructed from biological differences is centr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hierarchies.Despite its great contribution,it is limited in some crucial aspects.It fails to give attention to the gendered character of the disciplined body.Furthermore,a more serious flaw is the un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power and the reduction of individuals to docile bodies,thus failing to explain the rich experiences of women in modern society.Feminists recognize the need to show that women are more than passive victims of domination through the rediscovery and revaluation of their experiences and history.Foucault’s interpretation of individuals as passive bodies has pushed women back into the position of passivity and silence.
body theory;post-structuralism;feminism;Foucault
I0
:A
:1009-105X(2010)02-0141-04
2010-04-12
胡可清(1976-),女,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