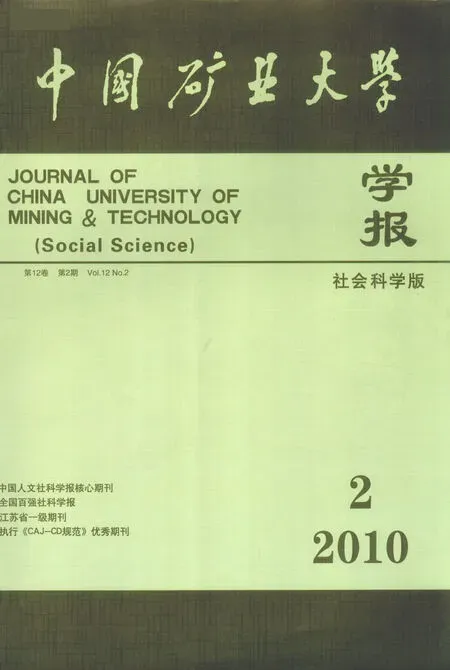生态文明的哲学变革
刘海龙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江苏南京 210037)
生态文明的哲学变革
刘海龙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江苏南京 210037)
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是人与自然关系重塑的过程,其中蕴含着自然观、伦理观和实践观的巨大变革。首先,人类需要对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机械自然观进行反思,进而建立有机论的整体自然观。其次,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从征服自然到保护自然的转变。然后,形成一种关爱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切实尽到关爱自然的义务。最后,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观并以之改变人类的实践模式。
生态文明;生态伦理;人与自然;实践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人类对于大自然采取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坚持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人们对自然任意宰割,无限度地和不顾后果地向自然界进行物质索取和开发。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源的迅速枯竭、环境的极大破坏和生物物种的加速灭绝,人类的生存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走出这种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人类可以在地球上长久的生存下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人类需要反思对自然的态度,重新定位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进而形成一种科学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并践行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的实践之中。
一、从机械自然观走向整体自然观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对自然本身及其运行规律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即树立科学的自然观的问题。自然观是人类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哲学基础。人类早期关于自然的知识非常有限,所以那时形成的是一种朴素辩证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自然界当作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认为自然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这种自然观来自天才的直观和大胆的猜测,它正确把握了自然界总画面的一般性质,看到了自然的整体性,但由于缺乏实证科学的基础,却不能具体说明自然界的联系和发展。这是一种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总体正确,但由于缺少细节,并不能科学地描述自然的本质及其具体运行规律。这也导致了神学自然观的出现并统治人们的思想达几千年之久。
自然观随着人们对于自然规律认识的加深而逐渐深化。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神学自然观的神秘光环逐渐褪去,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又重新得以确立。但在牛顿力学范式下形成的自然观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近代早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人们把世界预设为一台机器,认为这台机器可以还原为它的基本结构。笛卡尔主张“以最简单最一般的(规定)开始,让我们发现的每一条真理作为帮助我们寻找其它真理的规则。”[2]254霍布斯认为:“对每一件事,最好的理解是从结构上理解。因为就像钟表或一些小机件一样,轮子的质料、形状和运动,除了把它拆开,察看它的各部分,便不能得到很好的了解。”[2]254这种自然观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由某种宇宙之砖的终极实体组装而成并按照一定的规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运转的机器,相信人类完全可以根据纯粹的客观知识,利用技术手段去认识和操纵这架巨大的自然机器。机械论自然观缺乏辩证思维,割裂了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联系,忽视了万物的运动属性,强调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其中蕴含着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与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强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引下,人们对自然进行不顾后果的开发,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最终危及了人类的生存,生态文明建设呼之欲出。
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反思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并树立一种有机论的整体自然观。与古代朴素的整体自然观相比,有机论的整体自然观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具有实证的基础,是对自然更加科学全面的认识。这种自然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个世界就是由物质转换、能量流动、信息沟通的多样性运动和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统一体,一物的存在离不开与他物的联系和对整个系统的依赖。现在的生物圈是宇宙在几十亿年中进化出来的有机系统,它把地外物质环境、地球上的无机物和生物种群协调为一个维持自我平衡的和谐整体。地球上的生物圈、土壤圈、水圈、大气圈都是由生命创造的,也从而使地球本身成为生命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功能。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单独生存和发展,它们只能在大的合作背景下相互竞争和相互利用,在共同维护生命支持系统存在、促进生物圈稳定的前提下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发展,人类的生存也不例外。
在反思机械论自然观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自然整体性赋予全新解释。其中,由英国化学家拉弗罗克(J.Lovelock)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马古利斯(L.Marguli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盖娅”假说很好地阐释了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在二人的共同推动下,该假说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对人们的自然观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成为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和绿党行动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他们把世界视为一个生命机体,人类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拥有者,甚至不是那种纯粹比喻中的地球飞船的乘客。他们认为:“生物圈作为适应的调节系统,能够自动的维持地球的平衡状态”[3]。地球作为一个自我调节的实体,它保持着生命得以存在的陆地和大气条件。生命机体全都以一种经过进化的合作方式生存。它们对环境做出反应,并以能够确保它们集体生存的方式来调节地球环境。当一种生命有机体有益于它自身,同时也有益于环境时,它才能够持续发展,并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反过来,任何破坏环境的物种注定要灭亡。虽然他们的一些具体观点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其把自然看成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一点道出了科学自然观的根本特征。新的有机论整体自然观给出了不同于机械自然观的一种新的世界图景,它有助于人类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认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整体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并进而反思人的权利和义务,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范自身行为,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从征服自然到保护自然
早期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直观和肤浅的,生产力水平又极端低下,完全处于自然界的控制之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及其对生活的影响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就归结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人类的精神。在这种认识水平下,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形成的是敬畏自然和听命于自然的崇拜意识。
工业文明兴起以后,人类生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于是人们对其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强调人类利用自然的权利,人类俨然成为了自然的统治者。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提出:“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培根提出“人是人自己的上帝”的命题,把人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他也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一种征服自然的途径。洛克认为,人类要想从自然的束缚之下解脱出来,“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类从此开始在实践上同自然界展开斗争,并且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种把人作为自然的统治者征服自然的做法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使人类陷入到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不是很严重的时代,恩格斯就提出了对自然进行征服与控制的预警。而到了现代,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再加上消费主义与资本逻辑的推波助澜,当代生态危机的规模远远大于恩格斯生存的时代,并呈现加速恶化的趋势,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过程几乎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人与自然关系空前紧张。
建设生态文明,就要改变人类这种统治者的角色,改变人对自然的完全征服欲望和完全控制态度。首先,人类具有享用自然的权利,即在自然中栖息,利用自然的价值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和其他生物起源于一个共同的进化过程,面对着相同的自然环境。人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都依赖生态系统不间断的运行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生存。一切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都承认人与自然、精神与存在的物质统一性,承认人的自然性与生物性。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论述就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然性的理解之上的。他认为,在实践上,人首先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正是人的自然性与生物性决定了人必须以自己的实践行动来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其次,人类在享用自然的同时,还应当尽到呵护自然的义务。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这决定了人类关怀与呵护自然的必要性。自然是人的衣食父母和安身立命之所,是人为了不至于死亡而必须与之交往的物质对象。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存在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正常功能的发挥。要维护人类享用自然的权利,就要维护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要维护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就要维护自然。
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享用自然是人的权利,维护自然完整、有序、和谐则是人的义务。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以大量耗费自然资源和牺牲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的。可以说,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所有的人都应承担保护和恢复生态平衡的责任。同时,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发展的最高阶段,还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意识的主体,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有能力担负起维护自然的责任。如果只过分强调人在自然中的权利,就会造成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和破坏,其最终结果是人类遭到自然的报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人类在享用自然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呵护自然。
三、从强人类中心主义到新的生态伦理观
在机械自然观与控制自然观念的影响下,近代对于大自然采取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坚持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是世界运转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只将伦理原则应用于人类,将人类的需求和利益作为一种最高的价值取向。它认为人类以外的大自然事物,只有在满足人类需要的时候,才具有价值。它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只以人的利益或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把人作为道德的对象,只承认人的道德地位和权利。在这种伦理观的指引下,人类无视自然界中其它生命体和自然物的存在,对自然任意宰割。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的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人类的生存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当代一些学者将上述的伦理观概括为强人类中心主义。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反思这种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局限性,重新认识自然生态系统的地位和价值。建立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拓展伦理观照的范围,将关爱给予自然。这种理论探讨从两条路径展开:新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新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仍然主张人的价值至上,但其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张要关爱和保护自然。以美国哲学家诺顿为代表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一种理性的自然观。认为人类之外的大自然事物,都可以满足人类的“熟虑偏好”而具有价值。所谓“熟虑偏好”就是经过仔细的考虑,并且采用理性的世界观,运用科学理论构成框架,和以圆融的形上学、美学价值和道德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价值观。强调自然如同资源一样,对人类都是有价值的,应该予以保护[5]。以墨迪为代表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存在“既是一个等级系统(由诸如器官、细胞、各种酶等子系统构成),又是一个超个体的等级系统(人口、物种、生态系统、文化系统等)的组成部分”。因此,从生态的角度说,人类的存在依赖于“生命支持系统”正常功能的发挥。因此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并且必须保持在自然系统的限度内”的。为了个体和种的延续,人类应该选择那些可以保护我们“生命支持系统”的事情来做[6]。以澳大利亚哲学家帕莫尔等人为代表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保护自然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因为生态危机证明了人对自然做了些什么,也就是对自己做了些什么”。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自然生态平衡与人类的利益是同一的。人类不仅是自然的改造者,也是自然的管理者。人类应当担当起自然管理者的责任,以维护和发展自然,使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面演进[7]。因而,人类具有保护自然的责任与义务。
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将价值与权利赋予自然,扩大伦理观照的范围。动物权利运动首先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大到动物。辛格指出,动物具有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和利益,如果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牺牲动物的利益,那么实际上就是犯了一种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相类似的错误[8]。雷根认为动物也拥有与人类一样的天赋价值。动物拥有在一个自然环境中过完整生活的天赋权利,剥夺它们是不道德的,不管这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利益,应当把平等和博爱的原则推广到动物身上去[9]。生物平等主义进一步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大并惠及到其它所有生物。施韦泽曾提出著名的“敬畏生命”的理念。泰勒指出,自然界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一个生命的目的中心,人只不过是地球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人的生命并不比其他生命优越。那种认为人因为具有理性思考、审美创造、自主决定等能力就比其他生命更有价值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0]。生态整体主义更是把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利奥波德指出,伦理学的道德规范需要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要把道德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界的实体,并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11]。罗尔斯顿提出“价值走向荒野”的理念。他指出,传统哲学和伦理学从人出发,只关注人的价值,不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是一种认为自然界没有价值的哲学和伦理学。实际上,荒野是一切价值之源,也是人类价值之源。因此,应当使“哲学走向荒野”,“价值走向荒野”[12]。虽然上述理论观点可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其体现出的关爱自然的情怀却是值得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加以借鉴的。
当前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两者立论的出发点不同。新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价值出发,主张为了人的利益而保护自然,这既有对传统强人类中心主义的继承,也有反思和改进。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将价值与权利赋予自然,力图扩展伦理观照的范围,从自然本身的价值出发论证人类应当负有的责任。当然,非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以价值与权利的做法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其理论出路尚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新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均体现了对传统强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提倡关爱和保护自然。这给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巴西世界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理斯·斯特朗指出:“现在世界大家庭面临的我们在环境问题上造成的后果,给我们共同安全造成的危险要大于传统的相互之间军事冲突带来的危险。道德伦理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是人民和国家产生动力的最终的基础,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并表现在创立新的‘地球道德’,从而激励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地球的一体性,使之成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安全、平等和温馨的家园。”[13]只有树立了关爱自然的伦理情怀,才能切实履行人类对于自然的义务,也才能在实践中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从盲目开发到自觉的实践
在机械自然观和强人类中心主义指导的实践中,人们认为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环境的容量是无限的,可以无限地同化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和污染物。在实践中一方面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的生产和铺张浪费、追求奢华的消费;另一方面是将不加处理的大量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中去,严重破环生态环境。这种实践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其结果是造成资源的严重短缺、生态脆弱、环境容量不足,这些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不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不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现状,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会越来越恶化,这将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反思人类的实践观念,并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念指导下走向新的实践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就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理念。人类具有享用自然的权利,但与其它生物以本能方式享用不同,“人类以实践的方式享用自然”[14]。而这种实践应当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实践。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曾谈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及盲目性问题。他指出,人类应当合理地调节这种矛盾,尽量地克服盲目性:“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5]从对自然的盲目开发利用到通过自觉的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是马克思这种调节与控制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凸显。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自觉的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生存和发展。在这种实践观的指引下,人类的实践模式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源型经济要向效益型经济转化,着眼于降低消耗、节约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污染型生产要向清洁型生产转化,充分考虑“人—自然”系统的平衡及环境的承受能力,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维持生态的良性循环。在消费中,要强调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节约并高效地使用物质财富。既要满足人们正常的、合理的、适度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也要符合自然生态发展的需要,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在生态治理上,也要改变以前那种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状况,提倡防患于未然的做法,预防各种污染的发生。只有走效益型和清洁型生产的道路,提倡合理消费、绿色消费,并对自然环境进行积极全面的治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是可能的。
在当代,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模式。循环经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指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它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物排放。循环经济体现的是生态实践理念,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实践范式,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总之,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既有的理念与行为方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要从根本上变革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关爱自然并在实践中切实履行人类的义务。只有将关爱自然的观念贯彻到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去,自觉地转变人类的生存模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人类社会从生态危机中摆脱出来,走向人类美好的未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2]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 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M].曾国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31.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5] B.G.Norton.Anthropocentrism and Non-anthropocentrism[J].Environmental Ethi-cs,1984.131-148.
[6] W.H.Murdy.Anthropocentrism:A Modern Version[J].Science,1975.
[7] J.Passmore.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M].New York:1979.200.
[8] 辛格.动物解放[M].孟祥森,钱永祥,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9] T.Regan.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M].London:Routlege,1984:243.
[10] P.Taylor.Respect for Nature: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11] 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M].侯文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3.
[12] 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 王伟.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5-216.
[14] 刘湘溶,曾建平.作为生态伦理的正义观[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1-7.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Philosophical Chang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U Hai-l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remodeling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It contains a major philosophical change.First man should reflect on the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at has caused tens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n establish organic holistic view of nature.Second,man should re-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realize a change from conquering nature to protecting nature to form a new ecological ethics and fulfill the obligation to care for nature.Finally,a conscious practical concept,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hange the current practice pattern of 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ethics;man and nature;practice
B82-058
:A
:1009-105X(2010)02-0010-05
2010-04-23
2010-05-07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ZXB002)
刘海龙(1973-),男,哲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