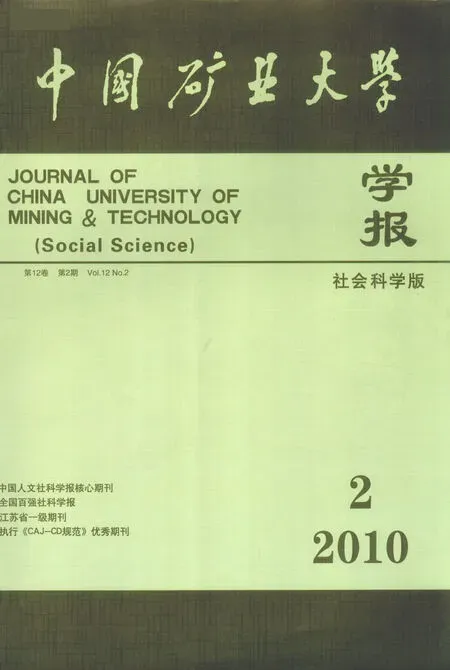论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的和谐美
曹金合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 274015)
论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的和谐美
曹金合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 274015)
小说《受戒》是阅尽人生沧桑的汪曾祺采取远距离的眺望和选择的回忆姿态构思的短篇佳构,“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的美学观使他更喜欢回归到单纯质朴的生命状态去打捞一种美好的记忆与梦想。这样,和谐与唯美的美学趋向展示出《受戒》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僧俗人情的和谐美和民间社会的和谐美生命本真的华彩乐章。跨越时空的和谐美也为当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汪曾祺;人与自然;僧俗人情;民间社会;和谐美
小说《受戒》是阅尽人生沧桑的汪曾祺采取远距离的眺望和选择的回忆态度构思的短篇佳构,外在的尘嚣和烦躁、功名和利禄、浮躁和凌厉、喧哗和骚动等转瞬即逝的浮华虚名经过幽默达观的平静心态过滤之后,沉淀并显影的是铅华洗尽、本色方显的生命本真醇美的滋味和和谐的乐章。在小说的最后表明写作日期的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之后,作者意犹未尽的把自己的潜藏心底的写作动机通过“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循着受到外在的理性和道德压制的心理情结指示的草蛇灰线,洞幽烛微的发掘潜意识的欲望和冲动,便可显而易见地发现作者对小说和谐美的艺术追求一直魂牵梦绕在潜意识的幽深暗箱里。欲罢不能的审美冲动只能把年轻时候的美好梦想通过压缩、移植、视觉意象和二次加工等方式显现为具体的形象,再通过包含作者生命感受的审美意像和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从而把种种被压抑的欲望化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情节和其他因素。”[1]在小说中通过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等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非常个人化的情感和行为串连起了民俗文化、生活习惯、花鸟虫鱼、职业风尚等远离时代政治主题的陈年旧影,其中体现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和谐之美和探寻生命本真的爱、美和自由的主题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梦境发生源头的1937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年代,战争的严酷环境和氛围追求的是文学毫无条件的服务于、服从于战争总动员的功利宣传需要,在解放后到“文革”时期的愈演愈烈的文学规范一体化追求中,最终把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从而使文学彻底陷入阴谋文学、帮派文学、工具文学的泥淖。不负载明确的政治宣传任务和思想意义的《受戒》所追求的表现人性和人情的和谐美与体现宏大的政治话语的主流文学的激烈崇高的斗争美学相比,无论在思想意义、表现主题还是在审美追求、文体观念上都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所以直到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才有机会实现自己探索小说自身审美功能的梦想,但即使是到了新时期写这种与当代文坛的美学风格格格不入的小说文体,作者也是有顾虑的。他在关于《受戒》的创作谈时说:“我在写出这个作品之后,原本也是有顾虑的。我说过: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2]279顾虑的原因和作者犹疑困惑的态度还原到当时具体的语境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涌动大潮注重的是配合当时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任务而受到政治舆论引导和扶持的,同时它也实现了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情感宣泄的抚慰功能和对历史灾难来龙去脉进行反思的广场意识。因此饱经风霜的汪曾祺是以非常清醒的态度来看待不容许另类探索小说出现的具体环境的:“不用说十年动乱,就是十七年,这样的作品都是不会出现的,没有地方发表,我自己也不会写。”[2]279这样的没地方发表的作品实际上是对约定俗成的小说一定要承担点什么、赞成点什么、批判点什么、思考点什么等沉重的功利观念的减负,《受戒》的发表引起的读者和作家的“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惊呼,实际上就是对深受社会功利旨趣浸染的读者阅读习惯的一次“受戒”。
《受戒》的和谐美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首先与作者的“小说是回忆”的审美价值观念密切相关,汪曾祺曾给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激烈的氛围的淡隐,凸显的是温馨祥和的和谐之美,丑陋肮脏、卑鄙龌龊的东西的过滤换来的是荸荠庵一带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团结友爱、毫无机心的桃花源般的和谐境界。其次作为一个温情的人道主义者,所钦慕的是孔子所说的“吾与点也”率性而为的无功利的动机和行为,对顺其自然不加约束的优美健康的合乎人性的赞许,使他把一个受戒的故事写成了一个破戒的激情飞扬的生命欢歌。当然也与他的不习惯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拷问和反思质疑的达观性格有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3]敛去锋芒的亲切和谐再经过复杂时事的风雨洗练之后,更喜欢回归到单纯质朴的生命状态去打捞一种美好的记忆与梦想。“判事那么清楚,而性格又那么随和,自然是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的。”[4]于是,祛除正统的历史文化、伦理观念、传统道德、权力政治等宏大的功能符号的遮蔽后,在《受戒》的舞台上尽情表演的是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村姑和小和尚的相亲相爱的和谐美的喜剧。喜剧中和谐与唯美的美学趋向展示出《受戒》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僧俗人情的和谐美和民间社会的和谐美的生命本真的华彩乐章。
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主客体之间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关系,在小说《受戒》中化作了海德格尔所钦慕的“人诗意的生存在大地上”的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悬置了斤斤计较的功利眼光才敞亮了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大自然的本真面目,在“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物我浑一的审美意识的观照下,纯朴恬静的大自然才显示出充满盎然生机和诗情画意的和谐美。汪曾祺用生花的妙笔描绘了一对小儿女生活和谐宁静的生态环境:明海出家的荸荠庵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门前是一条小河。门外是一个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面供着弥勒佛。”
高地、小河、柳树等天然的自然物与打谷场、弥勒佛等人化的自然物求同存异的和睦相处的景观,实际上通过弥勒佛的憨态可掬的形象和名士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得到了形象的诠释,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就这样在小和尚清闲自在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和谐地融为一体。与荸荠庵的和谐优美的风光相比,小英子的家更是充满了桃花源般的和谐景象:“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向荸荠庵。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小英子的一家人在风景如画的大自然的熏陶之下,“瓜豆蔬菜,四时不缺”的生活现状就与大门上的万年红的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相得益彰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这种温饱无虞、男耕女织的小亚细亚的耕作方式反映出的与机械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是一种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态度,它充满了一种摆脱功利意识的缠绕的世俗的和谐美:“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对一红一白的石榴树和栀子花的鲜明对照形成的极美的景致,作者以我观物、物我交融的审美方式对超功利的美感愉悦赞叹不已。
充满诗情画意的水乡泽国在水的梦想、菜的鲜嫩、花的飘香、果的丰硕的烘托渲染下显得那么富有灵性,连汪曾祺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5]28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谚形象地阐释了水的温柔明净必然会养育小英子这样纯朴、自然、率真、可爱少女的根源,对爱与美、温情与风俗、和谐与恬静的美学风格念念不忘的汪曾祺遥望生命的岁月时,曾深情地回忆起曾在庵赵庄的农家见过的小英子:“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美。”[6]336没有城市文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压迫导致的人的灵魂与心理行为的矛盾分裂,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相激相荡才孕育出小英子健康美丽、无忧无虑、活泼可爱、勤劳善良的形态品格;她性格开朗,成天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十分勤劳,整天帮父母干活,看到即将出嫁的姐姐忙着准备嫁妆,她就把田里的零碎活全包了;她直率天真,顺从人性的要求大胆地表露自己的爱情;她细心体贴,每次明海来画花,她都以煮个鸡蛋或煎几个藕团子的方式给他增加营养。可以说,大自然的和谐美代替了传统文化和文明的教育功能才养育出小英子这样的身心健康的和谐美的典型。同样水的柔性和阴性的审美品格也养育了汪曾祺喜欢在人生素朴的底子上刻画健康自然的小人物的艺术追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男欢女爱、两小无猜才行云流水般地融入《受戒》中和谐美的美学风貌中去。
特别是明海与小英子之间心性无邪、率性纯真的人际交往和朦胧恋情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显得那么和谐,人事与物事的水乳交融产生的和谐美在他们的初次见面时就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你叫什么?’‘明海。’‘在家的时候?’‘叫明子。’‘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明海就拨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泼水的声音:‘哗——许!哗——许!’”水的柔静愈加衬托出“哗——许!哗——许”的船桨泼水声音的洪亮,象声词之后连用的两个叹号实际上在动与静、喧哗与寂然之间二元对比中产生了“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审美效果,大自然的无机心也反衬出小英子的为人处世和待人接物方式的毫无机心,因此她才会首次见面就把半个吃剩的莲蓬给明海,未受现代文明的繁文缛节浸染的童真童心才会有顺其自然的心性行为,明海也水到渠成地接受馈赠而心里不感到别扭才有了“少年船头剥莲蓬”的动人画面。后来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一直处在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和谐状态之中,这是他们一起看场的精彩画面:“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蝉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由稻谷、石磙、青蛙、寒蝉、萤火虫、流星等物象和意象组成的童话般的看场夜晚,相依相偎的一对小儿女的神态也成了装饰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在水乡之夜的静谧凉爽的氛围包容下的小精灵与大自然的亲密无间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生和谐的关系。尤其在小说的结尾,自然美、意境美与人性美的高度契合使人物和故事达到了物我合一的至美境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风景如画的芦苇荡成了受戒归来的明海和小英子谈情说爱的场所,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美好情愫与怀念伊人的蒹葭的意象实现了蒙太奇式的镜头对接:“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表面上是对大自然的如诗如画的美丽风光的摹写,实际上所象征和暗示的是善良淳朴的明海和天真多情的小英子之间朦胧的异性情感,在呈现出浪漫色调的人生旅途中演奏出的最动人、最和谐、最真挚、最纯洁的美的旋律。“这种气氛化的小说展开在读者眼前,是一幅幅清新淡远、意蕴深厚、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民情风俗画。”[8]703在这色彩缤纷、动静相映的水乡泽国民情风俗画面的中央凸显的是小儿女的生命和恋情的欢歌,没有大自然的造化为他们提供触景生情的景物触媒就不可能有生命活力和情感的释放空间,因此在小说的结尾的神来之笔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唇齿相依关系最有力的明证!
僧俗人情的和谐美
严格意义上的佛门净地是看破红尘、六根清净的佛教子弟念经修行的地方,在青灯、古佛、木鱼等的相伴中枯坐修行、念经悟道中破除一切欲求、愿望、思虑、意识的孽障。因此遵守严格的戒规律条的僧庙生活与滚滚红尘中吃喝拉撒的世俗生活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汪曾祺在小说《受戒》中却打破了二者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荸荠庵里的和尚不是皈依佛门以寻求精神的超脱的潜心修行者,他们更多的受“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禅宗文化的整个大自然与自身目的性和规律性和谐合一的影响,宗教悟道向日常生活方式转变的世俗化使出家仅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样去庵里当和尚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和手段就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不比别的职业低贱。庵里的和尚出家的目的是因为作为和尚可以吃现成饭、赚钱放债等世俗的需要,目的与行为的世俗化使他们更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声色事物,过而不留,随缘自在,到处理成”。[9]210他们不但酒肉穿肠过,还在大殿的佛门净地杀猪,还可以找情人、谈恋爱、娶妻生子、唱酸曲。“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无人提起。”因此明海的三师叔仁渡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这样的酸曲而无人觉得不合适。僧人不受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束缚的率性自然的生活方式充满了世俗的人间烟火气,他们的为人处世具有了和世俗人情相统一的超功利的潇洒美和和谐美。“荸荠庵”代替“和尚庙”、“当家的”代替“方丈”或“主持”的名不副实的现象其实就是不受清规戒律束缚的从圣入凡的逆向化思维和行为的结果,“饥来便食、困来便眠”的和尚们的行为遵循的是顺从人的自然本性的内在要求,充分享受自由的欢乐与愉悦的世俗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所以荸荠庵里仁山和尚掌管钱财,干的是账房先生的职务;仁海和尚有家眷,其妻子每年都在庵里生活几个月;仁渡和尚风流倜傥,“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大殿里的杀猪景观和聚赌场面,打破了约定俗成的清苦和寂寞的佛门生活的观念而充满了世俗的欢乐和喧嚣。
在小说中小和尚明海和村姑小英子是作为僧俗人情和谐美的典范而被浓墨重彩地铺排渲染的。他们在佛与俗和谐共存的自由环境中无拘无束、适性而为的行为形成了和谐美的极致和意境。汪曾祺也用这种信马由缰、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描绘了明子清闲的日常生活场景:“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箩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自然时序轮回中感悟的不是思辨的逻辑推理,而是感性的日常生活经验使包容在单调的佛事仪式的内核深处闪耀着生命活力的火花,在浓郁的地域风情的生活氛围中洋溢着清雅温馨、自然恬淡的佛俗之间的和谐美。这种和谐美的意境氛围最突出的表现为明子和小英子之间健康明朗的诗意般的初恋,对温馨浪漫的朦胧恋情弥散的纯真无邪的自然神韵,深谙小说艺术技巧的汪曾祺表现得非常含蓄节制。当两人到田里挖荸荠时,柔软的田埂上便留下了小英子的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从两小无猜的天真无邪到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产生的关注异性的初恋情结,无论是小和尚还是情窦初开的村姑都是在人生的旅途上绕不开的美好情愫。在这里作者只用“一串美丽的脚印”就非常含蓄的点明了明海对小英子恋情萌发的根源,因为熟悉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脚在古代代表了女性的副性征,金莲情结正是怜香惜玉的男性潜意识中难以摆脱的审美心理,因此谙熟世俗风情和人情世态掌故的汪曾祺不经意之间顺手拈来的脚印,就成了负载传统的审美意蕴和沟通佛俗之间爱情的和谐美的桥梁。明海世俗爱情的本性一旦萌发,健康、自然、淳朴的人性就遵循生命本真的召唤以迎合英子的亲昵与热情,本乎自然本性的两情相悦就产生了涌动着人生快乐爱情的和谐乐章,因此受戒归来的路上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他们享受世俗生活破戒的开端,这是小英子摇船去接受戒归来的明海时的一番对话:“‘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的未受禁欲观念浸染的开放爽朗的性格已昭然若揭,劝说明海不当沙弥头也不当沙弥尾的话语和明海的应答说明他们的爱情是抛弃了庸俗的功利意识和门户观念的纯真感情,小船划进了芦苇荡之后,意象的飘动重叠和流动的思绪酝酿的情景氛围给人一种含蓄隽永、余音绕梁的审美感觉,僧俗人情的和谐美借助这种富有意蕴和韵味的景物描写达到了小说审美境界的高潮。
民间社会的和谐美
《受戒》构造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境界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美是作者祛除了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奸诈、肮脏龌龊、卑鄙丑陋、尔虞我诈等阴暗面之后的梦想寄托,隔着时间的河流回溯少年时代的美好梦境时,不由自主地以“乡土—童年”的方式代替严酷的现实生活的描摹而进入了作者的艺术构思和谋篇布局之中,作者对此童年非彼童年的物是人非的生命和生活感受是十分清楚的:“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80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的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6]336人与人之间在相融相洽的和谐氛围中培育的祛除奸猾和恶意的真纯质朴的人际关系始终是作者建构健全的和谐社会的梦想所在,所以在《受戒》这片自由、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沃土中作者“构造出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的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而温馨的所在。”[9]将个人灵魂的探索与漂泊造成的分裂色彩的火气浸润到童年记忆中美好乡土的生命深处进行消除,一种抚慰灵魂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田园牧歌情调就充满了艺术探索的空间。寄托着作者对人类美好生活前景的憧憬和向往的庵赵庄是一个处处洋溢着生活快乐气氛和人际和谐的世外桃源,每一个人都按照古老的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怡然自得地生活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培养了他们勤劳善良、质朴热情、团结互助、自由开放的人性和人格。小英子一家就是这种桃花源理想的典范:“他们家自己有田,本来够吃的了,又租种了庵上的十亩田。自己的田里,一亩种了荸荠,——这一半是小英子的主意,她爱吃荸荠,一亩种了茨菇。家里喂了一大群鸡鸭,单是鸡蛋鸭毛就够一年的油盐了。”勤劳善良的一家人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农家生活方式确实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最好写照。与此同时他们又打破了一家一户耕作时形成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塞保守的小亚细亚式的生活观念,而是“阡陌交通,往来耕作”的不记功利报酬的团结互助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农忙时节互助帮工的动人场面:“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这种把带有嘉年华会上喧嚣的节日气氛融入到田间互助劳作的动人场面中就形成了恬静美好和欢乐和谐的情感氛围,生活在自然经济的和谐状态中产生的超功利色彩的天堂般的人间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到了《桃花源记》中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和谐境界。
当然,民间社会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然净土,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相互交融构成的藏污纳垢状态是权力规范控制比较薄弱的自由自在的民间的本然状态。《受戒》呈现出的安乐祥和的民间社会和谐美与作者采用的平视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民间立场密不可分,“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10]他并没有采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立场对民间的藏污纳垢性进行批判和清理,也没有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三六九等的人群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更没有采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价值判断立场疾言厉色地对待民间社会的迷信和愚昧,而是认同下层民间多元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尽力挖掘和发现被封建传统道德和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所遮蔽压抑的民间对自由自在的品性向往和追求的生命力,所以在《受戒》中的民间社会才在恬淡和谐的生活氛围中涌动着生命本真的动人欢歌。那里没有流言蜚语、勾心斗角的龌龊事发生,甚至悬置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把“偷鸡的”也称作是“正经人”,更没有采取传统社会中对贼的恨之入骨的心态和态度鄙视讽刺这位“正经人”,相反,“明子曾经跟这位正经人要过铜蜻蜓看看。他拿到小英子家门前试了一试,果然!小英的娘知道了,骂明子:‘要死了!儿子!你怎么到我家来玩铜蜻蜓了!’小英子跑过来:‘给我!给我!’她也试了试,真灵,一个黑母鸡一下子就把嘴撑住,傻了眼了!”只有采取平视时的视角观察眼光感同身受到偷鸡的可爱之处时,才不会采用世俗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来衡量偷鸡贼的可恶之处,才描绘出了一对小儿女玩铜蜻蜓的欢乐和谐的偷鸡游戏图。对于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属于愚昧和迷信的事物,汪曾祺更多地是从民俗的角度来衡量和估价的,因此也就从审美的眼光悠然自得地欣赏民间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这里的人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的迷信行为只是娓娓诉说,并不作价值判断;对“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叫‘寒蛇’”的常识性错误只作客观介绍,并不加以纠正;对于荸荠庵里住的和尚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作者也顺着当地人的思维习惯加以推断说:“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由此可见,没有束缚人的伦理纲常、没有纷繁扰攘的桃花源般的生活只不过是汪曾祺自然、通脱、仁爱生活理想的表征和情感寄托而已。可以说,“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表现他熟悉的,经过他的情感、心智所沉淀的记忆。”[11]时间的大浪淘沙沉淀之后呈现的毫无机心的率真自然和天真无邪的记忆就化作了《受戒》中桃花源般的民间社会的和谐美。
作者以特别通脱宽厚的生活性情和审美态度实现了对世间和谐社会的执著追求的美学理想,这种和谐美以完整的形态艺术化地呈现为短篇小说的杰作,是与作者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思想的有意追求分不开的。他说:“我觉得孔子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一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5]290-291。因此,《受戒》自始至终都在有意识地建构一种自由自在、淳朴自然的和谐的审美理想境界,通过对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审美,描绘建构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由此召唤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美好的人性质素来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大厦。“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谐社会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状态。”[12]如何建构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达到全面的和谐状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反映出的和谐美为当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49.
[2] 汪曾祺.道是无晴却有晴[M]//汪曾祺全集:3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8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胡河清.汪曾祺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3(1).
[5] 汪曾祺.自报家门[M]//汪曾祺全集:4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 汪曾祺.关于受戒[M]//汪曾祺全集:6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 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9]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1-262.
[10]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46.
[1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0-331.
[12] 王翔,曾长秋.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J].宁夏社会科学,2008(2).
Harmonious Beauty of Wang Zengqi’s Novel“Initiation into Monkhood”
CAO Jin-he
(Chinese Department,Heze University,Heze 274015,China)
Wang Zengqi’s novel“Initiation into Monkhood”is the best short novel by Wang Zengqi who has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The novel is written by adopting a long-distance overview and choosing a recalling posture to formulate.What it seeks is harmony instead of profoundness.Aesthetic perspective of the harmony has made him to return to the simple rustic life to have a good memory and dreams.In this way,the aesthetic harmony and aesthetic trends exhibit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novel,the harmony of clerical and secular feelings and the harmony of civil society which is the true nature of life.The harmony across time and space provides useful inspiration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of the contemporary time.
Wang Zeng-qi;man and nature;monk and human feelings;civil society;harmonious beauty
I206.6
:A
:1009-105X(2010)02-0126-06
2009-12-07
曹金合(1973-),男,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