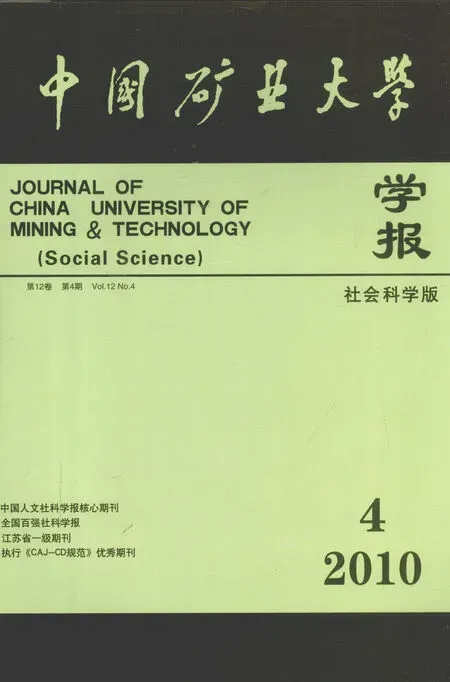论六朝山水画论的写形指向
周奕希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论六朝山水画论的写形指向
周奕希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虽然六朝山水画论有重传神的说法,但是通过对六朝时期文学艺术的研究,不难发现,从顾恺之开始,人物画论中“以形传神”的说法便已隐含着对写形的关注,绘画评论中对写形的论述也很多,山水诗文领域亦有“文贵形似”的形似论,这都说明六朝并未形成鲜明的形神对举、重神轻形的思维模式;形神关系尚处于争论探索阶段。该时期山水画论的写形指向确实存在,写形并非作为传神的工具,而具有与传神共存的独立价值。
六朝;山水画论;传神;写形
山水画肇始于六朝①山水画及画论的兴起主要从晋末宋初开始,其中山水画家如张僧繇等始有专门写山水景物的迹象,山水画论家如宗炳、王微等则开理论先河。,“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六朝士人迷恋山水以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精神境界,在诗文和绘画“以形媚道”的山水描画中得到更完美的体现。山水画论最早见于晋末宋初,正值玄佛合流之际,“以形传神”、“传神写照”——本出自顾恺之人物画论的传神说——运用在山水画论阐释中,成为六朝山水画论的本体论概括。学界大多关注山水画论传神说,认为以山水题材绘形的价值在于“传神”、“畅神”,形质是神的寄托之体,得山水之形方能写山水之神。对山水之形的关注,则或附着在山水画旨趣表达之中,或表现为构图造型等具体技法的概述,没有充分独立的空间。然而结合各领域的研究情况不难发现,人物画论中“以形传神”的说法实际上隐含着对写形的关注,山水诗文亦有“文贵形似”、“巧言切状”的形似论,这些都启示我们对山水画论应作进一步解读。
一、顾恺之传神论与六朝山水画论
多数论者认为顾恺之画论以传神为核心,而作为不同画科的山水画与人物画是一脉相承的,是对绘画领域传神论的开拓和延伸。认为顾恺之的画论强调以神为主,最有力的根据就是《魏晋胜流画赞》中的一段话:“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1]62人们常引用其中的“传神”、“以形传神”等词,而实际上,这段话中的关键词应是“悟对”。顾恺之的意思是只有“悟对”,始终不放弃“对”之物象,才能“通神”。“空其实对”恰是摒弃客观物象来聊抒胸中逸气,这样的创作只能导致“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后世所谓“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画正是顾恺之反对的不重形似只求神似的典型。因此,人们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顾在此所说“实对”的重要性被忽略了。顾恺之重视写形还有多处体现。“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的典故,“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的说法,其实都是对人物摹写的要法概括,尤其是“传神写照”一句,强调眼睛对于人物传神的重要性,没有对它精妙的刻画,就没有传神的可能。而《论画》、《画云台山记》中主要介绍的是绘画的模写方法,用笔、用色、临见妙裁、置陈布势等具体的写形方法,还有人物描绘时体态动势、人物布局、环境衬托等技巧方法,足见顾恺之对写形的用心探索。要评价他的理论贡献,忽视写形的独立地位是不完整的,他将绘画艺术价值的界定回溯到绘画自身,探寻以形的描画来表现绘画艺术性,探寻绘画艺术性的独立价值。这与先前汉代人物画有很大的不同。
两汉绘画以人物为主,宫廷、庙宇、陵墓壁画和画像石以颂功德、彰善行的风俗教化、先贤故事为题材,劝诫色彩浓重,叙事性较强[2]。台湾学者朱玄曾说:“汉之麒麟阁列士图,云台二十八将图,顺烈皇后宫列女图,唐的凌烟阁功臣图等,以及大禹治水图、孔子问道图、母仪图、巢由洗耳、卞庄刺虎与各项良善丑恶的人物画像,不胜枚举,无不含有教忠孝,示功勋,颂义烈,重典范的作用与意义”[3]。因此,虽然汉画人物鸟兽鲜明生动,姿态各异,也有“谨毛而失貌”(刘安语)这样顾全大体的画法,却没有对绘画艺术性强烈而独立的追求,最终落脚于“成教化,助人伦”(张彦远语)的政教功能。而六朝人物绘画在淡化叙事性的绘画政教功能的同时,更重视形神兼备的绘画艺术性价值的探索。以前论者大多能看到六朝绘画对写神的重视,以此区别于两汉绘画补助政教的功能说。其实物象之描绘不仅具有与传神同位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区别汉画政教功能的有力证据。顾恺之的画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阐释人物画的精髓,如果仅仅用“以形写神”、“传神”之语概括之,不免有失偏颇。
顾恺之的画论开启了中国绘画史上品评绘画的自觉意识,既谈画之神韵,也谈画之形美,这一点还可以从其他画论家的品评中得到佐证。谢赫《古画品录》中将顾恺之的画列为第三品,“深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4]360。“深体精微”指的是顾对绘画中所要表现的内容(物象)体验非常深刻精确,“笔无妄下”是说他不随便下笔,下笔非常谨慎,“迹不逮意”指他的画不能达到他自己的意图,不能达到心意所往的意境。谢赫以为顾的绘画“声过其实”,与他在画界的名望相去甚远。以上评价正好从反面说明了顾恺之在绘画实践中对形之绘写的努力,这是不容忽视的。“深体精微”四字正与《魏晋胜流画赞》中所述的“悟对”方能“传神”之意相契合。在那个时代,形之绘写时常成为品评不可或缺的标准。姚最在《续画品》中品评谢赫的那段话成为表现当时绘画领域极备写形指向的标志,“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髩,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5]371谢赫人物画精妙细致,时人皆效颦其写形的逼真精致,虽难穷尽其生动气韵,但可以看出他们对人物绘画写形价值的基本尊重。另外,谢赫绘画“六法”中除“气韵生动”之外的五法皆为绘形要法,姚最品评梁元帝“心师造化”的赞语,也是六朝画论在顾恺之之后表现出的对绘画自身艺术性价值的掂量和主张。
六朝山水画与人物画属不同画科,在“传神”论上常被认为出奇的一致。大多学者将二者并论,说明六朝绘画领域“以形传神”说的传统根基。若是二者真有如此天然的联系,山水画论受到顾传神论影响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前面所说顾恺之画论中写形指向的存在也应该成为影响山水画论的因子之一;若是二者的联系仅是盲目的链接、惯性的推论,那么山水画论以“传神”为核心,形之绘写只不过是传神的工具这样的论断就少了一份冠冕的证据。因此,在笔者看来,六朝山水画论强调传神的同时,如何对待写形品格,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六朝山水画论与山水诗文形似论
六朝士人对山水审美的好尚是非常浓烈的。《世说新语》不乏这样的记录:简文帝“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顾长康言山川之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高人逸士是人们理想的人物,山川林泉更是人们向往的境地。田园诗、山水诗、山水文学大量出现,一时掀起“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5]67竞相追逐的文风,这种“文贵形似”的创作风尚,与山水画论传神论大相径庭。学界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画论走在文论之前,但为何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文贵形似”的说法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即)字而知时也。”[5]694这里所说的“形似”,是指对风景、草木等物象的描摹,也就是“体物”,精妙密附,语言巧妙,切合景物,就像在印泥上盖印一样,不用雕琢地描绘,这是山水诗文写形的充分表现。刘勰对诗歌追求“形似”的看法并不是一己之见。如钟嵘在《诗品》中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谢灵运“尚巧似”,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称“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都说明追求形似是六朝山水诗文的基本特征和创作风尚。有人研究认为,这与汉赋雕琢铺排的体物功能有关,这种成熟的创作手法对山水诗文的影响很大[6]。朱光潜在《诗论》中分析说:“从赋的兴起,中国才有大规模的描写诗;也从赋的兴起,中国诗才渐由情趣富于意象的《国风》转到六朝人意象富于情趣的艳丽之作。”[7]文人用体物的手法描写,主张象的刻画,而于心物之间选择物的精确再现,是艺术创作的自觉选择,牟世金对此有精辟的解释:“以形似之言来‘巧言切状’,是诗人们才发现不久的妙用。在这个时候,和‘形’相对立的‘神’的观念是不可能产生的。只有在尚形的文学创作有了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要求君形之神的思想”[6]。我们暂不论那个时代形神观的发展阶段,只就山水诗文论对形似的重视和支撑,可以看到写形指向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和价值。山水画论研究不能漠视这一现象的存在,而执泥于传神论,造成后人对它的误解。
误解需要澄清,我们从山水诗文形似论既没有把形神并举,又不直接强调神似的现象中可以反思,形似之“形”的真正内涵。前面引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言“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即)字而知时也”,描摹体物最终追求的还不仅是雕琢,还有“瞻言而见貌”、“印(即)字而知时”的程度。这种程度的形似才是物象的最佳再现,才能达到“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尽而情有余”[5]694的审美效果。这里的形似之“形”不仅是客观物象的再现,也是融进主观情意的表现。但这形似中的情指的是山水审美获得的情绪,并不指向“以玄学对山水”那种玄学精神的形上高度,没有老庄玄学“以无为本”、“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全焉”体道悟道的形上高度。
如果说,同时代的绘画理论与山水文学论相悖,二者毫无关联,自然不合情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联系,正是探讨山水画论写形指向的突破口。宗炳《画山水序》开端即言:“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1]109,圣人之道是形而上的,道映于万物,如何能感受到“道”,精于言理的宗炳知道“味像”是得道的现实途径,这种实际的体味与刻画比任何缜密推论阐释都更实在而智慧。此“味像”意即咫尺披图探幽,需要“以形媚道”,用具体物象俘获圣人之道,用“涤除玄览”的静心体味天地精神。这里既主张传山水之神,更微妙的表达物象绘写的价值,体道必须调动最好的形式,因为“存形莫善于画”(陆机语),“栖形感类”方能“畅神”。山水诗文形似论主张融合情思的形之描写,山水画论写形指向则在于与神思相栖的形之描画。现今虽难觅六朝山水真迹,却能从其画论中感觉到画家恣意于“写”的美妙姿态。宗炳主张“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绘图山水,做到“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让方寸之内的绘图展现“自然之势”,既重视摹写山水本来之
形色,又探索空间处理与山水之势的微妙关系;王微主张“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凭记忆与想象勾画山水,至于如何用笔,他以一句“横变纵化,故动生焉。前矩后方出焉”提醒后人,横纵构思方能成就山水动变之势,笔墨变数方能完成画图的真实再现。由此可见,六朝山水画论中并不缺乏写形的痕迹,其中行笔用墨的浓淡、迅疾和连贯无不洋溢着“写”的自然和生动,而穷奇变巧、纵势横逸的构图经营又无不表明“写”的便捷和灵巧。正是由于对“写”形的专注,画家们才能尽情展现自己的神思玄趣于始终;寓“形”于“写”的绘画法则,成为名士聊抒情志、表达玄趣的不二选择。从这一角度来说,山水画论形与神并存共栖,“传神”其实就是“写形”,不过,这里所指的“形”是经过“悟对”而传“神”化的“形”;“写形”就是“传神”,是以“悟对”而“神”化的“形”来表达“神”的存在。写形品格真实存在,不是作为传神的工具,而具有与传神共存的独立价值。
三、玄佛合流背景下的形神之辩
学界对六朝山水画论传神说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思想界形神之辩的理论背景。他们多以宗炳为例,这位朝廷征召不应却执意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的名士,之所以提出“畅神”二字,与他的玄佛之学不无关系。这也就容易让人把他与慧远“形灭神不灭”的形神观联系起来,得出宗炳重神轻形、形神分殊的结论。然而王微与宗炳形神观相反,这点少有人注意到(即便有人注意到,也以对绘画要求在本质上一致,即“传山水之神”一笔带过)。《宋书·王微传》记载,他临死时“遗令薄葬”,可见他信奉形死神灭、神形一体的观点,代表着当时形神之辩的另一派主张[1]128。我们不能无视二者在形神问题上的分歧,更不能忽视当时思想界玄佛合流背景下形神之辩的历史事件,想当然地以中国古代山水画论重神轻形、贬形似重神似的主流倾向笼盖萌芽期形神并重、互倚相栖的现象。笔者试图在粗略解读当时佛学宗派借玄学之力阐释形神关系的基础上,佐证形神难分混沌统一局面的历史现实,进一步说明传神说对写形指向的忽视,论证写形指向的独立地位。
西晋中叶以后,魏晋玄学清谈在士大夫阶层广泛流行,为佛教般若学的介入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社会土壤。在这种条件下,一大批佛教般若学者以般若学的概念、范畴和命题附会玄学,迅速形成了一股蔚为风尚的般若学思潮,实现了玄佛的合流。若谈这时期山水画论形神关系的确立,不能绕开玄佛合流时形神之辩盛行的理论背景单就某位作者的哲学思想而论。纵观晋宋之际思想界学派林立、争辩日盛,无论是以慧远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形神之辩,还是被誉为“六家七宗”各流派代表人物释佛义时的主张,都可以看到当时并未形成鲜明的形神对举、重神轻形的思维形式,而是处于争论探索阶段,这正是六朝山水画论写形指向独立存在的根本原因。
慧远代表作《沙门不敬王者论》[8],其第五部分《形尽神不灭》记录论难者与他本人论辩的内容,以此阐明形神观念。其中可见当时形神之辩中截然对立的两派观点。论难者主张先秦以来道家一元论形神观。道为无,自道以降,万物都是阴阳二气和谐的产物,人自不例外,正所谓“夫禀气极于一生”,“生尽则消液而同无,神虽妙物,故是阴阳之化耳”。神虽妙,也逃不出阴阳二气的范围,生与死都只是气的“既化而为生,又化而为死,既聚而为始,又散而为终”,神与形始终是同步的,即“神形俱化,原无异统,精粗一气,始终同宅,宅全则气聚而有灵,宅毁则气散而照灭;散则反所受于大本,灭则复归于无物,反覆终穷,皆自然之数耳。”神与形都是气,只是有精粗的差别,形是神之宅舍,即神是依附于形的。慧远依据老庄理论驳斥论难者的观点,认为神是“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强调神妙于形,意图在于说明佛教形神为二、形神相异的形神观。他又借文子之言,说明形灭神不灭的观点。《二十二子·文子缵义》有曰:“故形有靡而神未尝化,以不化应化,千变万转而未始有极;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9]形体有所靡散,但精神不会死亡,以不死的精神回应能死的形体,尽管千变万化也不会到终极。形体的死亡会重新回到无形的状态,精神则与天地共存。《庄子·知北游》:“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9],也明确形体的生灭是以“精神”为本的,这与文子大致相同,从而也成为慧远驳斥论难者阐发形神对举、以神为本的强大证据。正因为这样的论辩,让我们看到六朝时期以神为本还是形神并重成了论辩的焦点,无论哪样的观点都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客观上造成形神观念混沌难分的局面。
较之唐宋以后重神轻形、“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重神似观念,玄佛合流的六朝思想界流派分立,形神观念对峙并存,给写形指向提供更宽阔的空间。佛教般若学大致分为“六家七宗”,又可归总为三大派,即所谓本无派、即色派和心无派。释道安的本无义和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是极其相近的。王弼言:“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道安则言:“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强调世界的本体是无[10]340。支愍度的心无义和裴頠的崇有论相类似。僧肇《不真空论》中评述心无义说:“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否定本体,却肯定现象即有,裴頠认为“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贵无论煽起虚浮旷达之风,危害社会的道德风俗,只有崇有才有益于世道之心,所谓“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强调有的重要性,看到有的价值,发现形之重要地位[10]442。支道林的即色义和郭象的独化论是对应的。郭象“独化论”主张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即任何事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块然自生的,从而否定了形而上的本体。也可以说,现象和本体是不可分的,本体寓于现象之中,不能离开现象去认识本体。这种观点和支道林的“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很类似,色指一切事物的现象,他认为一切事物的现象都不是自己形成的,而是由因缘合和而成,所以“虽色而空”;但就一切事物现象本身来说,却是实际存在的,所以“色复异空”,既说本体的重要性,又不离现象,强调现象的存在价值和独立性,是对本无、心无两派的综合[11]。由此可见,玄佛合流的特殊时期并未形成明确稳定的形神观念,正是这种形神观的争论使得这个时期和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一样,在绘画领域里更具备对这门艺术写形指向的尊重和关注,完成其绘画象形功能的诠释。
论者认为六朝山水画论提倡传神,是后世不求形似的写意指向的源头,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用写意为主的宋元画论解读六朝传神说,忽略写形指向的的独立价值,甚至有意区分绘画与文学的发展状况,认为画论走在文论之前,难免有些牵强。这其中的失误在于以后世形神对立、重神轻形的观点来看待六朝时写形与传神还未曾分化尚处在浑沌统一之中的历史状况,并且割裂了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统一的进程,忽视了它们自身艺术性本质的双重价值。当然,若要进一步论证六朝山水画论的写形指向,需要通过细读宗炳、王微等人的作品,具体归纳其中写形品格表现出的实、理、法等三大特征,尚需另文撰之。
[1] 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M].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2]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M].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12.
[3] 朱玄.中国山水画美学研究[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97:4.
[4]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版)(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5] 刘勰.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 陈建农,苗贵松.“文贵形似”与东晋南朝诗学中的形神问题[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3):46.
[7] 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56.
[8]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 吴勇.晋宋之际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J].宗教学研究,2006(3):81.
[10]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 方勇,杨妍.论魏晋佛学与庄子学的互相倚重[J].浙江大学学报,2004(3):129.
Expressing Form of Landscape Painting Theory in Six Dynasties
ZHOU Yi-xi
(Chinese Department,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205,China)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theor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ividness and conveying the spirit in the painting,but through studying on literature and ar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x Dynasties,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us to find that painters had already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form early from Gu Kaizhi.The theory of“achieving vividness by form”in the figure painting implies the concern for the form.Much discussion of the form could be found in the painting commentary.There were also theories of“form similarities”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poetics.All this shows that there were no clearcut contrasts between the form and spirit or no emphasis was laid on the spirit rather than on the fo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irit and form was still controversial.In this period there existed the tendency of form expression in the theory of landscape paintings.The form was not just the tool for conveying spirit.It had its own value and coexisted with the spirit.
Six Dynasties;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theory;vividness and conveying the spirit; expressing form
J222.35;J201
A
1009-105X(2010)04-0098-05
2010-08-18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课题(项目编号:XYS09S42)
周奕希(1980-),女,硕士,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