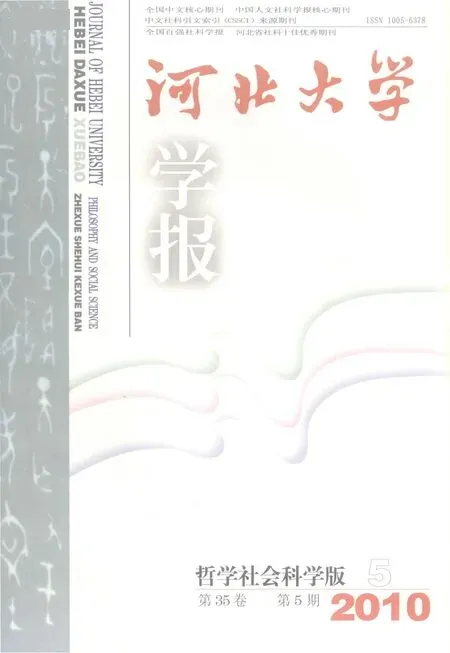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
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
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宋代真理学,实由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三大部分为构件。宋代学者,于此三大构件或有所偏重,而不少名家往往对三者都加以探索并卓有创获。然而,从宋元明清以来,学术界存在一种将宋代真理学缩小化的运动,各有取舍,不仅排出了物理之学,而且剔出了大批探索三理富有成绩的伟大学者,往往只剩下程朱理学及其抗辩派,遂使宋代理学面貌严重不全、失真。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纠正这一偏失,努力发覆,从“理学”扩展到“宋学”,迈出可贵的第一步。现在,需要突破这些局限,从“宋学”再拓展到“真理学”,已到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了。只有全面复原匡失,建立符合宋代实际的理学体系,才能展开科学的研究,得其真蕴奥义。
理学;宋学;真理学
一、导论:人类探索的一般规律
古往今来,人类的探索对象不出两大类:一是人,二是物。当然,不管研究前者还是后者,都必然要多多少少地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暂时撇开作为研究主体的人,那么,所有研究对象都是物,人是物的一部分,并且是晚出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只要有研究,只要一提到研究,就必然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二者须臾不能分开。因此,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和以自然物质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之间,既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内部各个具体学科之间,也是如此。其相互独立,是相对的、暂时的;相互联系,是绝对的、永恒的。
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浅到深、从现象到本质、从偶然到必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人类研究探索的一般规律。不论在近现代还是古代,都是如此。当然,古代的人类探索活动,表面的、浅近的、感性的内容和结果更多一些。然而,决不能说古人不作深入的、遥远的、理性的探索。相反,他们在这方面曾作过长期的、艰辛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有些成果和积累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960—1279年)社会的发展水平,显著地超过以前各朝代,并雄居当时全球最高峰。以精英学者为代表的宋代人的研究活动,以求理、讲理为主流,蔚然成风,热潮迭起,形成时代特色,并彪炳史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宋代的“理”,与前代和后代一样,是个多义字。但学者所研究探讨的理,一般指事物的规律。宋人探讨的学术范围,颇为广泛,但以理学研究为最高水平、最具代表性。本文主要针对学术界对宋代理学的缩小化偏失,探索宋代理学的构件,还原宋代求理的基本范围和理学的真实。
二、宋代真理学的三大构件
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是人类的基本研究对象。但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人们的研究重点、学科构成、语言表述等,会多少有所不同。例如,源自印度的佛学,认为大千世界是痛苦的、虚幻的,探讨的重点是人以及人类心灵的解脱。中世纪的欧洲,探讨的重点是神学。“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渐转向现实的存在,并无所不究。
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探索范围即已相当广泛。《易经·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从类万物之情。”概括言之,当时人探讨的是“三才之道”,即天道、人道、地道①关于《系辞传》的作者及其年代,最早不过孔子,最晚不过西汉。但作者对先秦人探索范围的描述是正确的。。道就是规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人研究范围依然很广,但对“天人感应”更为关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人的研究范围,因印度佛学的传入和流行,获得巨大拓展,特别是对人类心性问题的探索得到空前重视。
宋代人的研究范围,全面继承前代,虽无重大突破,但在高度上则大为超越,以探索道理为最突出的时代特色。宋代真正的理学,决不是像后世一些学者说的那样狭窄。据有关记载:共城县令李之才听说邵雍苦志好学,便自造其家。
问雍曰:“子何学 ?”雍曰:“为科举进取之学。”之才曰:“科举之外,有义理之学,子知之乎?”雍曰:“未也。愿受教。”之才曰:“义理之外,有物理之学,子知之乎 ?”雍曰:“未也。愿受教。”之才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学,子知之乎 ?”雍曰:“未也 ,愿受教。”于是雍传其学。[1],[2]卷113《李之才传》
此事约在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3]31,394,必定由邵子自述并流布于世。这段问答表明,至少有部分北宋精英学者认为,当世的学问,除科举进取之学外,共有三大类,即义理之学、物理之学、性命之学(宋人亦称性理之学,本文采之)。稽诸史籍,这三大类学问,确实是北宋乃至整个宋代人探索研究的三大领域,是宋代理学的三大组成部分,最具时代性。兹分别胪述如下。
(一)先看“物理之学”
“物理之学”一词,出自李之才之口,决非偶然。“华山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邵)雍以象学”[2]卷113《李之才传》。陈抟是五代末宋初间著名道士,精通象数学,李之才是其再传弟子。这些学者,“其流源为最远,究观三才象数变通 ,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者”[4]卷19《李挺之传》。另外 ,李之才还精通历法。可见李之才物理之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象数学、历法。而邵雍后来成为宋代象数学最著名的大家,“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5]《邵伯温序》。以邵雍为突出代表的宋代象数派学者和以杨辉、秦九韶、李冶②李冶为金朝人,但在学术上继承宋代人。为代表的数学家,以数为指归,以数来推衍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之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此其特点和优长。他们也很重视对物的观察,像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的方法和主张,反对“以我观物”,确有深刻独到之处[5]卷12《观物篇六十二》。张载和二程,对天地万物之理很有研究,并以此作为观察和论述人类社会的基础。程颐明确主张:“物理须是要穷。”[6]157然而,他们不重视物质的细致观察和实际测验的缺点,都比较明显。
以沈括为杰出代表的宋代自然科学家和医药学家们,则很重视对天地万物和人体器官具体而细致的实际观察和测验,并且很注重探寻其中的规律——理。如众所知,沈括上至天文、历法、彩虹、云雨雷电,下至地理、地质、水利、植物、生物,中至度量衡、乐律、建筑、冶金、医药等,兴趣极为广泛,几乎是无所不探,逢物必究。最可贵的是,沈括决不满足于道听途说、纸上谈兵、闭门苦思,而是非常努力地进行实际观察观测、主动进行受控实验。因此,他能够探索出一些“水之理”、乐理、谐振之理、太阳匀速运行之理、胎儿倒生之类的“物理”等[7]第134条,[8]。另一位与沈括同时代的学者苏颂,“博学,于书无所不读。图纬、阴阳、五行、星历,下至山经、本草、训诂文字,靡不该贯……朝廷有所制作 ,公必与焉”[9]卷3《赠苏司空墓志铭》。尤其在天文观测和本草学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巨大成就。南宋著名学者郑樵和朱熹,对自然界的研究也比较广,并且也很注意实地观察、观测。而更多的宋代学者,则是在专门领域中求索真理。宋代依然十分重视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的研究,一直有一批专职和业余爱好者投身其间,并且很关注天体运行规律和“历理”问题[10]236-239。在观测记录和观测仪器方面,都有新贡献。在化学领域,胆(矾)水浸铁化成铜现象,至迟在西汉前期即被发现,但很少有学者去作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推广工作。直到一千年后的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1086—1098年),布衣学者张潜、张甲父子,“体物索理”[11]卷5《截留纲运记》,根据古书记载 ,经过亲自试验,撰成《浸铜要略》一卷,献给朝廷,得到推广[12]88-109。两宋之交的著名农学家陈旉,在实践中深入研究农业生产中的田土、天时、种苗、耕耨、灌溉等问题,很注意总结其中各方面的规律,阐释“物理”[13]。所著《农书》,成为中国古代农书中最重“农理”的科学著作。宋代专门针对一种物品展开探讨的学者,陡然增多。如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桔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陈翥《桐谱》、王观《扬州芍药谱》、王灼《糖霜谱》、杜绾《云林石谱》、范成大和史正志《菊谱》、杨天惠《附子记》、费著《笺纸谱》、苏易简《文房四谱》、唐积《歙州砚谱》、朱肱《北山酒经》、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等。上述著作为尚存者,未列述或已散佚者还有许多种。对一种物品,如茶、酒、砚等,往往有数人加以专门探索。宋代学者对专门物品研究之广且多,是空前的,像朱肱、韩彦直等学者还很注意寻究其中“深远”的“道”、“妙理”或“物理”[14]卷上,卷下[15]序,卷中。
宋代学者对物理研究最多、最深、贡献最大的,是医药学界。医生治病,第一步是要观察了解病症。而了解病症的前提,是必须了解人体结构和各个器官的特点。宋代之前,医疗界的人体解剖知识已达到较高水平。宋代人体和医学研究的进步之处,主要有五:一是王惟一首次铸造成针灸铜人,使人体经胳和穴位首次直观而鲜明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二是钱乙首次把儿科从中医中独立出来;三是陈自明把妇产科知识系统化,从而使妇产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儿科和妇产科的独立,说明宋代人对人体的研究更加细密、更加科学。四是宋慈首创法医学,表明宋代对人体伤亡现象研究之高度重视和首次系统化。五是首次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绘制出比较详细而正确的人体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环中图》。这五方面的进步,表明宋人对人体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精度。第二步是分析并判断病因。南宋名医陈言继承以前病因学说,提出三因致病说。其中 ,寒、暑、燥、湿、风、热六淫致病为外因[16]卷2。宋代医生,大都注重气候和外部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第三步是治疗。除精神疗法外,按摩、针灸、气功,都多少牵扯到物理问题。而最普遍的药物治疗,必须研究了解一千余种植物、动物及矿物等物品的形状、性能、加工、药效等问题,实为非常典型而精深的物理之学。北宋人明确提出:各地所产各种药物,“其物至微,其用至广,盖亦有理。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费其功,终亦不能活人。圣贤之意 ,不易尽知 ,然舍理何求哉”[17]卷1《衍义总序》?宋医认为,不仅应该究明药物之理,而且还要“穷天地之妙,通万物之理”[18]卷九,143。而万物之理也包括人理。宋代医药精英们的物理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最为广泛,而且最讲求验证,因而最为科学。
宋代有一些身份各异的学者,专门从事物理之学的研究探索。除数学家、医药学家、天文学家外,还有不太为人注意的僧人赞宁。赞宁著有《物类相感志》一书,虽未正式公开地探讨各物之“理”,实则书中多讲诸种物质本身固有的性能和物质之间相生相克、相成相害的固定联系,其实即是研究揭示“物理”①《物类相感志》丛书集成本题苏轼著。经四库馆臣考证,应为宋初僧赞宁著。[19]。宋代一些精英学者,特别是哲学家们,尤为倾心宇宙问题,谈天说地,论气探虚,也是探索物理之学。
陈其荣指出:“公元前4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撰写的一部自然哲学著作《物理学》,它不但探究自然界的普遍原理,论述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总规律,而且还包括天文学、地学、化学、生物学等在内,涉及整个自然科学。”②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对物质世界运动变化总规律的研究探讨及其水平,在古代世界罕有匹敌,亦非宋代任何一个学者所能企及。(此据陈竹明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0]2因此,宋代所谓“物理之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陈植锷研究发现:“宋儒对自然科学的特定称谓‘物理之学’,也为当时的科学家所采纳并用以表述、记载自己或他人及前人的研究成果。”[21]520对自然界普遍原理或总规律的探索,中国人在宋代之前早已开始,宋代著名学者如周惇颐、邵雍、张载、二程、王安石、朱熹、蔡元定等,也颇为重视,并以此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基础。毫无疑问,排除掉“物理之学”,则“义理之学”、“性理之学”乃至整个宋代思想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再看“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
“义理之学”一词出自李之才之口,李之才很重视“义理”问题,似乎极不合常理。因为李之才的学问受自穆修、陈抟,又授给邵雍、刘义叟等人,均属《易》学中的象数派,不是义理派。实际上,现存李之才的文献记载太少,李本人关于“义理”的态度和造诣已难详考,但《宋史》本传说他教邵子先学“五经大旨”,说明他并不排斥经学义理。至于邵雍,虽以象数学知名于世,但明确主张:“若得天理真乐 ,何书不可读 ?”[5]卷14《观物外篇:下》也是以读书得理为宗旨。其传世著述中讲义理之处,确实不少。
李之才和邵雍探讨“性理之学”,只要我们未忘其道教徒身份,就知这是极自然的事情。唐明邦指出:“性命之学,原先是儒家提出的人性论、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主张尽性知天知命;后来成了道教专门研究的问题,即关于人的自然本性(即命)和后天修养的思想品德(即性)的关系,讲如何修身养性,以求长生久视。这性命之学,的确是道教祖师陈抟长期研究的课题。”[3]33所以,邵雍的《观物外篇》第十二专论“心学”,大凡宋儒热衷探讨的性、诚、德等问题,均有涉及和论述。
究竟何为义理之学,何为性理之学,二者有何异同,宋代乃至元明清学者并未给予明确的界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植锷博士曾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给予一些研究和探讨。
1.二者“自然有其共同或者说互相联系的一面”,但内涵和外延都有区别,不仅“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不可以互换,而且在时间顺序方面,也有个先后出现的问题”。
2.义理之学主要是从治学的方法上立名,指出宋学偏重于从总体上探究和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乃至整个儒家传统文化之精神实质,与汉唐以来盛行的只以对经典字句的解释为务的训诂之学相区别。性理之学则就宋学所具有的前此传统儒学所未具的新内容而言,指宋学摆落汉唐训诂转向义理之后学者们所共同关心和探讨的基本理论,即道德性命之说。
3.性理之学特指王、洛、关、蜀学派,义理之学泛指疑传派以来的宋儒各学派[21]219。
若仅从狭义的宋学、理学来看,陈植锷之言颇具卓识。当然,其中的某些说法与事实不合,如道德性命之说,并非“前此传统儒学所未具的新内容”,孔子始言及,思孟学派论述转向繁密,故宋儒特重《论语》《孟子》《中庸》。如拙文前述,道家和道教学者,早就开始并长期地探究道德性命之学。
如果我们打破门户之见,暂不关注儒家、道家和道教、佛学之区别,而是把“宋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就会看到,宋代精英学者,不论他属何教何家何派,其关心的范围不外乎人、社会、物质;大多数精英学者的探讨重点是人与社会。义者,宜也。所谓“义理之学”,既是对各家各类经典文书所含精神实质的研究阐释,也是对人类必须遵守的事物应该之理、当然之理的研究阐释;前者是探索书本义理,后者是探索行为义理。像王安石、二程、苏轼、朱熹、陆九渊,无书不读,“惟理之求”[22]卷6《曾子固讽舒王嗜佛》。他们都要改变悖理妄行、人欲横流、混乱黑暗的现实社会,为当时人和后来人寻究循守天理、和谐相处、健康发展、必遵不渝的正确道路。
宋代的“义理之学”,首先是研读经典文本的一种高级境界,确实不同于汉儒训诂之学。此乃宋元明清以来学界共识,已成定论,不必赘言。这种“义理之学”,这种有别于“汉学”的“宋学”,仍未脱离“经学”之窠臼。但须另加注意之处有二:一是宋代以来的学者,多看到宋儒读经重义理是受到佛家和道家学者的深刻影响,很少有人看到这是儒家经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即使没有道家和佛家学说,即使不读释老之书,也会有这种“义理之学”的出现。秦汉之前,孔子和思孟学派,《易经》之系辞和易传作者们,早就开始独立地阐释经典文本的“道理”了。二是探讨经典文本之理,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目的,除考试得官做官外,是为探讨人如何与人相处、人如何与天地万物相处的应该之理和当然之理。这就迫使一些精英学者,既研读经书文本,探索书中之理,又研究人和天地万物,探索书外之实实在在的义理,以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3]376。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圣人。
要探明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正确相处之道,又必须进而探明人、天地万物本身固有的性质和道理。于是,义理之学必然发展上升到性理之学。
所谓“性理之学”,是对人的本性及其活动规律、天地万物的性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探讨。到北宋中叶的神宗朝,学者们探讨性理之学已经蔚然成风了。司马光说:“性者,子贡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24]329“性理之学”在宋代的暴发勃兴,首先导致“人学”的空前活跃。而当时的人学,实分医学家和哲学家两种。医学家关注的重点,自然是人的身体器官及其结构。但中医重综合、辨阴阳,有很深厚、精细的哲学理论基础,宋代也是如此。哲学家并非丝毫不关心人的身体,像二程就很重视人体结构和医理药性[10]66-67,但他们探索的重点在于人的本质德性和活动规律,热衷于研究人性、人欲、人情等,寻究人与动物的异同、人与天地万物的异同、人的终极构成、人类活动的不变法则。同时,宋人对第二种性理即天地万物之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探讨,始终热情不减。对天地的探讨,除天文历算等专门研究者之外,张载、邵雍、二程、朱子、蔡元定等哲学家们,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植物、动物等自然物和人类制造的非自然物的探讨,除药学家、农艺学家等自然科技专家外,上述张、邵、二程、朱、蔡等哲学家们,亦颇为留心。
宋代哲学家对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的探索,按其方法和倾向,可分两派。第一派是“内求派”,强调自我反省体悟,反对或不太提倡对外在事物的具体而繁琐的探究。此派以程颢、陆九渊和禅宗为典型代表。第二派是“内外结合派”,既提倡自我反省体悟,也提倡对外在具体事物的细致研究。此派以程颐、王安石、朱熹、吕祖谦和道家道教为典型代表。不过,“内外结合派”对外在具体事物作细致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和实践,虽明显高于内求派,但远远落后于医药学家,也远远落后于物理学家。
宋代学者尽管各有长短优劣,但其探讨范围均不出这三理之学。就某一个具体学者而言,学问必自识字读书始,所以首先从事的多为义理之学。当他们从经典书本中跳出来,面对的是更加繁难费解的无字之书——人和天地万物。有些人的探讨重点,在于天地万物和人体器官的现象和规律;有些人的探讨重点,在于古往今来的人和天地万物的本质,前者形成物理之学,后者形成性理之学。当然,任何一个学者,侧重点固然不同,但独钻一理一学而毫不旁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存在的。性理之学,必然包涵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
三、对宋代真理学的缩小
宋代三理之学的研究探索,取得巨大成就,超迈前代,最具时代特色。华夏文化之所以能够“造极于两宋之世”(陈寅恪之见解),与宋代对三理的探索热潮及其丰硕成果具有直接关系。但是,元明清近现代以来,宋代以物理之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为三大构件的真理学,在人们的视野中被缩小了(更严苛一些来看,是惨遭割裂,横罹窒息之灾)。这种令人哀憾局面的出现,主要在于后世人之不明不智,但内源却在宋人本身之偏失。
(一)宋代“道统论”之自缩自闭
宋代道统论源于唐后期的韩愈。韩愈认为,不同于老、释的先王之“道”,有一传授系统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5]145。他用杜撰出来的这一儒家道统,排斥老、释之学。其说法和做法,对宋代许多儒学家产生深刻影响。当然,韩愈和宋儒都受佛教、道教之教统论之刺激和启发。元丰八年(1085年),程颐为兄程颢撰写的《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6]640元祐二年(1087年),范育为师张载《正蒙》作序说:“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23]4-5在洛学的道统中,排除了韩愈,直以二程上接孟子。在关学的道统中,既排除韩愈,也排除二程,径以张载上接孔孟。朱熹的道统说是宋代最为丰富者,对后世影响极大。他在绍熙五年(1194年)写道:
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26]4446
朱熹也排除了很多学者,但首次把周惇颐提高到宋代上承孔孟、“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的第一人的地位[26]4105。在朱子及其弟子看来,朱子道学所承继并发扬光大的,除张载等人外,主要是二程洛学。
朱子学的道统说,高自标置,以真理化身自居,力图夺占言论的制高点,一则用于排斥佛老,一则用于训育君臣万民。其动机和效果,在此皆可搁置不论。特需在此指出的是,朱学道统论对宋代真理学的缩小化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第一,对宋代义理之学、性理之学中的其他学者学派,统统排斥。除道统论肯定的关学、洛学、朱学外,宋代还有司马光涑水之学、三苏蜀学、朔学、荆公新学、浙东事功学、陆氏心学、张栻湖湘学,另有曾巩等不成学派的学者,都在义理或性理的探索方面做出大小不等的贡献,却都被道统论者排出于“道统”之外。在实际讲学、讨论过程中,宋代道统论者尽管对本朝其他学派学者从整体上予以否定,但在局部问题上时加肯定。但道统论的出现,却人为地高立一条藩篱,或明或暗地告示人们,在内者正统而正确,在外者异端而谬误。第二,对物理之学的排斥。在道统论中,绝大多数对物理探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均不在道统之列,统统拒于道统之外。只有邵雍是个例外,受到他们的较高推崇,但受到肯定的主要是其义理、性理部分,最能代表邵雍水平、属于物理之学的象数学却受到冷落。这一点,二程表现得非常典型。炮制出道统论的关学、洛学、朱学,对自然天地万物及其研究,并非真正贬斥,为了探寻道、理之终极根源,也很重视物理之学,然而,他们对专门细致地研究物理之学则持一贯明确的否定态度。故沈括、陈旉和天文学家、医药学家等在物理探索方面很有贡献的自然科技名家,一概斥诸道统之外。
道统论把真理的广泛探索活动划出一个小圈子,既人为地压缩了老释之学、物理之学的活动空间,也人为地缩小了义理之学、性理之学的活动空间。道统论对道学(理学)是一种自缩自闭行为,对宋代真理学也是一种自缩自闭行为。
(二)元明清政府之缩小运动
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洛学在北宋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南宋时,洛学逐渐发展,朱子时已经名动天下。但南宋前期,程朱理学既未很快取得主导地位,有陆氏心学、浙东事功学与之抗衡,也未得到官方独尊地位。宋理宗时才公开推尊程朱理学,其自吹自擂的正统地位一跃成为政府正式承认的正统地位。空前高的学术地位,产生空前广的文化影响。这种地位和影响,竞延续数百年之久。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政府下令恢复科举考试。经学考试规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诗经》《周易》也以程朱注解为主[27]2019。胡炳文说:“方今程朱之学行天下。”[28]卷1《乡贤祠记》元末鲁贞说:“上自京师,下至州县,莫不有学。学有生徒,有廪膳,而又表章程朱之学,以为教于天下。”[29]卷2《江山修学复田记》元代重视的是程朱之学 ,研究视野开始狭窄,在义理、性理之学上也无显著进步。倒是对程朱之学不甚热衷的部分学者,在物理之学上做出突出贡献。
明初“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而天下翕然向风矣”[30]卷7《崇正学辟异说疏》。至明成祖又“益张而大之 ,命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而传注一以濂洛关闽为主;自汉儒以下取其同而删其异。别以诸儒之书,类为《性理全书》,同颁布天下”[30]卷7《崇正学辟异说疏》。在朝野上下独尊程朱理学的形势下,其他学说都遭到严重压制。然而时间一长,程朱理学本身的缺失日益暴露,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不适应的问题日渐突出。于是,明初不占主流地位的陆氏心学,在王阳明(守仁)的大力倡导下重获生机,王学“不胫而走”,风靡海内[31]卷28《陆桴亭先生传》。不过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不少差别,但很多内容是重合的,特别在性理问题上多有相同相近之处,故后世学者多把陆王心学视为宋明理学的一大组成部分或其发展。尽管如此,王学大胆质疑程朱理学而产生的思想解放效应,更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明朝后期,特别是明末清初,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都有新的进步。
满清从军事上征服明朝,大约用了40年。从思想上征服明朝遗民之心,则用了100多年。显然,夺明人社稷、土地、肉体易,夺明人之心难。清政府夺心战略有二:一是通过文字狱等强硬手段,镇压反清思想。二是通过诏谕命令和科举考试,推奖儒学和程朱理学。“颁发《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升紫阳(朱熹)为十二哲”[32]2。康熙时的一批官僚型学者,“大旨以朱子为宗”[33]828。如张伯行撰写的《性理正宗》,对明胡广等人编的较为全面的《性理大全书》大加砍削,“尊道统正清其源,述师传以别其派……大旨在辟陆王以尊程朱”。对宋代物理之学,更是蛮横地予以删出。“至于天文、地志、律历之学,即《朱子大全集》中亦未尝不论及之。伯行以性理、事功,歧而为二,故卷中于宋儒如邵子之《皇极经世》、蔡元定《律吕新书》,皆在存而不论之列”[33]828。把宋代的真理学,压缩到空前狭小的范围之内。清代虽有西学东渐的冲击,也有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但真正统治学术思想界的仍为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
元明清时期,仍有一些学者探索物理之学,做出新贡献。“异端”和西学对学术界的冲击,也很猛烈。但政府一直以孔孟程朱为正统,大力公开提倡的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最受推崇。官方对程朱理学的极力尊奖,选择的重点是其心性义理内容,对程朱的物理学内容并不重视。宋代对三理之研究成就和水平,全球第一,举世无双。明清仍然在宋人基础上兜圈子,没有重大突破。而同期的欧洲,在各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尤其在“物理之学”方面把明清远远甩在后边。由程朱道统论和明清政府政策导向所造成的宋代真理学的再缩小,历史后果是非常消极而严重的。
(三)近现代以来学术界的再缩小运动
鸦片战争西方以坚船利炮炸开中国沉闷的封建大门之后,政府和学者都对“物理之学”空前地重视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巨变。
受此时代风潮的激发,特别是受英国李约瑟的推动,宋代“物理之学”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对宋代“物理之学”的研究论述,多关注具体的科技成就,较少关注宋人对物体之理的探索史,把“物理之学”作为宋代真理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并研究三者关系者就更少了。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界和中国历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实际上是把宋代真理学切掉三分之一,只剩下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
对宋代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的研究论述,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完整的,重程朱理学、陆氏心学而轻其他学派学者。这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表现得颇为明显[34]。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北宋部分,除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之外,只论述了周惇颐、张载、二程、邵雍五人[35]。对“惟理之求”、大张性理之学的荆公新学不予论列;对智圆、晁迥、李觏、三苏等人的道学理学不予论列。陈来《宋明理学》的北宋部分与上书差不多,只增列一个谢良佐[3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宋代部分,只论列周惇颐、张载、二程、朱熹和陆九渊6人:孙振青《宋明道学》宋代部分与此略同,只多一个邵雍,宋代理学的范围被压缩得更加狭小了[37-38]。在诸多“中国通史”的宋代部分和宋史断代史中,对宋代真理学论述之少,简直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
道统论的自缩和后代的压缩,对宋代真理学的发展造成严重锢闭,使后人对宋代真理学的研究和认识造成严重失真。这种局面,不可能、也不应该恒久不变。
四、发覆与局限
持久而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决不会被人为掩盖住。有缩必有张。自元明清以来,对宋代真理学努力发覆、试图复原者,大有人在。然其成果,都有局限和缺失。
(一)元明清时期
元代对两宋社会历史的全面回顾与总结,以脱脱等人主持编修的《宋史》为代表。《宋史》虽是元人编成,但底本实为宋代历朝旧有《国史》。元人的观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宋史》的有关论、赞、序、《进〈宋史〉表》中,也体现在对宋代旧《国史》底本的取舍。在《进〈宋史〉表》中,明确表示《宋史》的编修原则是“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39]14255。《宋史 ·道学传》只列述濂、洛、关、闽四派,重点是程朱理学。所以,清代钱大昕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为宗。”[40]1494然而,《宋史》毕竟以宋代旧《国史》为底本,而程朱道(理)学毕竟到南宋后期才占据主流地位,故《宋史》对程朱道(理)学之外的学者对三理的探讨也有所记述。特别是对宋代的物理之学,除纪、志、传中散见不少记载外,刻意保留了《方技传》。并在《方技传》的序言中说明,方技家之言“近道”,“孰得而少之哉”[39]13496?众所周知,《宋史》以繁芜杂乱著称。对宋代三理之学的记述,极为疏略肤浅。删去了旧国史中的《老释志》和《符瑞志》,也是一大缺失。尽管如此,《宋史》仍是二十四史中理学特色最突出、三理之学史料最丰富广泛的史书之一。
元末明初学者张九韶,于元末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编著成《理学类编》,“凡天地一卷、天文二卷、地理一卷、鬼神一卷、人物一卷、性命一卷、异端一卷。以周程张邵朱六子之言为主,而以荀子以下五十三家之说辅之,复于每篇之末绎以己见……不蹈讲学家门户之见”[33]790。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胡广等人奉命编成《性理大全书》,虽然也以周张邵程朱为主,但“采宋儒之说凡一百二十家”,颇为“庞杂”[33]790。“杂采天文、地志、律历、兵机、谶纬、术数之学及释家、参同契、纵横家言,概有取焉”[33]828。说明在元末明初,学者对宋代真理学尚能作出较为全面的关注,也不冷落宋代物理之学。但《类编》发明不多;《大全》全是分类摘抄,毫无新见。明朝后期,王守仁、唐枢、刘宗周等学者,大力提倡并发展心学,重陆学而轻程朱,但对宋代物理之学很不关心。
清代梳理、探讨宋代真理学最重要的著作,是黄宗羲、全祖望编修的《宋元学案》。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派门户之见,收录范围较广……扩大了视野,注意到‘各家之宗旨’,从单一的道学史向一般性的学术史迈进了一步”[41]7。然而,该书除了对荆公新学、苏氏蜀学依然持否定和轻蔑态度外,对宋代物理之学同样不太重视。四库馆臣在编辑《四库全书》时,对宋代三理之学均不偏废,罗列较全,但极乏阐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认为:“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42]119梁氏此论,也大致适用于《宋元学案》和《四库全书》对宋代真理学的态度。
(二)近现代以来
受世界局势巨变的重大激发,严复、梁启超首先奋起翻案,重新肯定王安石[43]331-342。之后,荆公新学日益受到学界重视。
1931年吕思勉《理学纲要》问世[44]。该书对程、朱、陆以外的学派学者给予较多关注,也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但深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影响。1933年,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出版。该书突破程朱理学道统论的束缚,把以前颇受轻忽的欧阳修、李觏和王安石的理论学说归结为“江西学派”,给予专门阐述[45]。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贾丰臻著《中国理学史》。该书在宋代理学部分,研究范围也不太广,并未超过《宋元学案》。但该书宋代之前部分,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对上古、夏商周至魏晋隋唐各代理学状况均有探索[46]。由此表明,作者认为宋代之前早有理学,理学并非宋代独有特产。这种认识,符合实际,宋代理学家也早已有之,而后来多数论著误指理学首创于宋,这些都反证了贾著之可贵。当然,贾著也未考察物理之学,对义理、性理之学的探讨也颇为粗疏。到20世纪40年代,任继愈撰写《理学探源》一文,溯宋代理学源渊于孔子,对汉学、玄学、佛学、道家道教等学说施予宋代理学之影响和启示,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尤其是对前代有关学说中的宇宙论对宋代理学的特殊重要价值,颇为究心。惜对宋代物理之学的其他内容注力不多[47]301-338。
钱穆自三四十年代开始,对宋代理学有长期而精深研讨。他不囿于宋儒道统论之偏见,对佛教、道家和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刘敞等人的理学均有论述[48-49]。大陆学术界对道家、道教、佛教与宋代哲学的相互关系,一直比较重视;对宋代道教、佛教本身的理学探索,虽有研究,但很不充分[50-51]。惜对宋代物理之学,都不甚关心。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下册于1959年撰成并于1960年出版。该书对宋代真理学的论述,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以前的同类著作。尤其可贵的是,在该书上册第四章和下册第十七章,设专节探讨了佛教“华严宗‘理事’说与程朱‘理学’”、“宋元之际的道教及其与道学的关系”[52]。但对宋代三理之学的探讨,还很不充分,对物理之学亦付诸缺如。
宋德金、张希清等撰写的《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视野开阔,论列广泛,可补前此论著之缺失。局限性在于,平铺直叙,对宋代学者在三大领域的求理热潮和特点,论述不够[53]。
张立文、祁润兴撰写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的宋代部分,既比较好地抓住了宋人热衷求理这一时代特点,观察和论述范围也比较广,是研究宋代真理学最值得重视的著作之一[54]。主要缺憾,一是宋代科技部分,内容单薄,亦不太重视宋人的“物理”研究。二是把荆公新学视为宋代理学的“非主流派”,至少在北宋时期殊可再加商榷。其实,荆公新学在北宋中后期风靡学界数十年,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在义理之学上贡献颇巨,在性理之学上造诣更深。
1984年,邓广铭指出:“由翦伯赞主编、于1962年首次印行的《中国史纲要》,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是由我执笔撰写的,我在这一部分的《两宋的哲学思想》一节中,开头便说道:‘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我现在必须说,上面的这几句话是完全说错了的,是亟应加以纠正的。”认为理学家这一学术流派出现较晚,“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55]l。此种转变,代表着中国大陆宋史学界开始突破程朱理学道统论的狭窄偏见,开始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观察探讨宋代学术。1992年,陈植锷出版《北宋文化史述论》。该书实以宋学为主题,视野空前广阔,对宋代义理、性理和物理之学均有探究。惜对南宋涉猎不多[21]。从1994年开始,漆侠专攻宋学,于2002年出版《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该书最大特点,是以作者丰厚的学术底蕴,将宋学与唐宋社会历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大大突破了从思想到思想的治学局限。惜对物理之学不太关注,因猝然辞世而内容不全[56]。
同时,思想史界也在纠偏求全,并有显著成就。贡献最大的,是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该书对宋代三理之学,均予探索。特别是对宋代物理之学,格外重视,作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论述[10]。遗憾的是,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界,对该书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自然科学技术史界,对宋代物理之学的发掘研究成就最大。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是: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文明史》[57]、中国台湾叶鸿洒《北宋科技发展之研究》[58]、日本山田庆儿《朱子的自然学》[59]、中国大陆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60]、吕变庭《北宋科技思想研究纲要》[61]等。他们的工作和成果,弥补了思想史和宋史学界的缺失,对复原宋代真理学贡献很大。其局限性主要在于多未将物理之学作为宋代真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三理之学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尚不够充分。
综括来看,元明清时期对宋代真理学的探索重点在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在此领域,又偏重于程朱理学和陆氏心学,对其他学派和学者注力不多。近代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局面大变,对宋代三理之学的各个方面均展开研究,成绩斐然。被元明清忽视、排斥的许多学派学者和领域,重新得到重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缺点是各自为战、独钻一门居多,通盘观照、综合考论较少。
五、结语
宋代真理学的构成及其顺序,大致如图 1所示:

图1 宋代真理学的构成及顺序
至此已显而易见,鼎之三足,缺一不可。以往的哲学史界、思想史学、学术史界、历史学界,对宋代真理学的认识和研究,都有偏失。最突出的是把许多重要学派学者排出于理学之外,另一方面是对物理之学弃置不顾。至于其他的专攻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局部不顾整体,甚至以偏概全、视点为面等问题,都相当常见。内容丰富、范围颇广的真正宋代理学,被压缩、砍削得面目全非,往往只剩下程朱一系及其反对派。仅就程朱理学而言,《近思录》所概述的四子理学(周惇颐、张载、二程),朱熹的理学,实际上也由物理之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三部分构成。忽视或去掉任何一部分,都是错误的。研究论述两宋真理学,更不可忽视或去掉任何一部分。宋代求理讲理者极为广泛,儒家、道家、佛家、自然科学家等都在求理讲理,各有千秋,不可偏废。宋代理学,决非儒家、更不是程朱等人的专利。
三理之学,各有独立的构成要件,自成系统,彼此不容混淆。其职能和作用,也是相对独立的。此其一。其二,三理之学之间,又互相联系、依存,不容截然分割。其职能和作用又是相对同一的。其三,三理之学的职能、作用和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存在高、中、下之级差区分。对宋代三理之学的相互关系问题,需作专门研究和阐明。届时,对宋代真理学的压缩及其偏失之弊害,将揭示无遗。在此仅简略地指出两点。第一,宋人或后人,有的喜以义理之学来概括宋代理学,有的好以性理之学来概括宋代理学(明清人尤其如此,编成几种《性理大全》《性理精义》等,流布甚广),忽略宋代的物理之学。实际上,任继愈和李约瑟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很早指出:宋代之前的儒学重人事,轻自然,缺少宇宙论的根基与支撑,因此导致儒门淡薄,释老盛行。宋儒有鉴于此,吸收佛老和前儒宇宙论精华,并加以扩展创新,才使传统儒学脱离困境,重获新生[47]335,337[48]222-278。而宇宙论,实属物理之学。抽掉物理之学,等于挖掉了宋代新儒学——理学之根。第二,宋代物理之学成就最大,超过前代,明清虽有发展但并无重大突破。性理之学大致上也是如此。宋代书本义理的研究成就,独占中国古代最高峰。而行为义理的研究,情况最差,元明清更糟。当代的宋明理学研究,往往最重视义理之学,其次是性理之学,忽略物理之学,实属轻重错位。
本文仅仅是指出宋代真理学有三大构件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并进而指出后世一些学者将之压缩的另外一个事实,最后指出后世有一些学者力图将之复原的第三个事实。这项工作说明,窄而不宽、偏而不全、专而不通的研究方法,万万要不得;专与通的有机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要真正全面揭开宋代理学的底蕴真相,必须首先确定其构件和范围,还有大量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探讨。
[1]邵伯温.易学辨惑[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2]王称.东都事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3]唐明邦.邵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晁说之.嵩山集[M]//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5]邵雍.皇极经世书[M]//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沈括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9]曾肇.曲阜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0]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1]赵蕃.章泉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2]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13]陈旉.农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4]朱翼中.北山酒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5]韩彦直.桔录[M].百川学海本.
[16]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7]唐慎微.证类本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8]赵佶.宋徽宗圣济经[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赞宁.物类相感志[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陈其荣.自然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1]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2]释惠洪.冷斋夜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23]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4]司马光.司马光奏议[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25]余冠英.唐宋八大家全集:第一卷[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26]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27]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8]胡炳文.云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29]鲁贞.桐山老农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30]高攀龙.高子遗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31]全祖望.鲒埯亭集[M]//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32]唐鉴.清学案小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4]张岱年.张岱年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35]侯外庐.宋明理学史:第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6]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7]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8]孙振青.宋明道学[M].台北:千华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
[3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0]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1]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本,1986.
[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3]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4]吕思勉.理学纲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5]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6]贾丰臻.中国理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47]汤用彤先生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燕园论学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4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49]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台北:学生书局,1984.
[50]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1]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3]宋德金,张希清.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54]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5]邓广铭.略谈宋学[M]//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6]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57]李约瑟.中国科学文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8]叶鸿洒.北宋科技发展之研究[M].台北:银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
[59]山田庆儿.朱子的自然学[M].东京:岩波书店,1978.
[60]卢嘉锡.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61]吕变庭.北宋科技思想研究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The Construction Members and the Acceptation or Rejec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JIANG Xi-Dong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and College of History,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The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Dynasty is made up of three parts:the knowledge of innate laws of things,the knowledge of ideal state in learning classicals,and the knowledge of natural instincts.The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lay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three parts.At the same time some famous scholars probed all the three parts,brought forth new ideas and obtained gains.But from Song,Yuan,and Ming Dynasty on,there was a movement to reduce the scope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sphere of learning.They lay different stress on the three parts.They not only ejected the knowledge of ideal state in learning classicals,but also ejected some famous scholars in this field.Only Neo-Confucianism of Cheng-Zhu was left.The movement led to the serious incompleteness and the fidelity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Neo-Confucianism.But at the same time some scholars tried to correct the impartiality.They took the first step.Now it’s the time to take the second step to restore the Neo-Confucianism.Only by overall restoring the defect and setting up the Neo-Confucianism system that accord with the reality of Song dynasty,can we make scientific study and obtain its lingering charm and real meaning.
the Neo-Confucianism;the Song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the knowledge of innate laws of thing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理学与宋金元文明》(2007JJD770034)
姜锡东(1961—),男,山东平度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暨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K244—245
A
1005—6378(2010)05—0001—11
2010—05—23
[责任编辑 郭玲]
-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金融危机视角下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
- 地方公共产品空间研究导论:一个即将的前沿领域
- 汉字情绪信息对阅读中语音加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