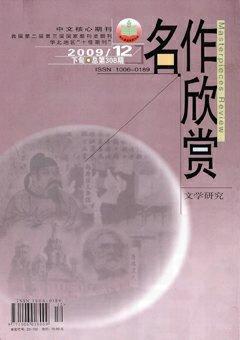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百合花》中“我”的形象分析
关键词:《百合花》 同故事叙述
摘 要:茹志鹃的《百合花》小说写了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本文试从女性形象分析的角度进入文本,借助“同故事叙述”细读文本发现作品中“我”的双性色彩。
茹志鹃的《百合花》小说写了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但没有演绎也不可能演绎成《青春之歌》的模式。“十七年”,是男性话语中心的时代,女性被边缘化,甚至缺失。但是并不意味着作家放弃对女性的追问和求索。很多人简单地将《百合花》中的“我”用“母性”和“妻性”来概括,我觉得是不准确的。本文试从女性形象分析的角度进入文本,做深层次解读。
同故事叙述(homodiegetic),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一个概念,是指叙述者与人物处于同一个层面,就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若第一人称叙述者聚焦于自己的个人经历,则构成‘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这是‘同故事叙述中的一种。”①显然《百合花》是同故事叙事,准确地说应该是“同故事+故事内”叙事②。“我”既是叙事者,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女性人物,可是相对新媳妇来说,“我”的女性色彩不够浓郁。作者自己也承认“要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③。这是作者作为一个女性对年轻战士尚未获得爱情的特殊同情,是母性的怜悯。但是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这种母性的释放,其实借助了父性的外壳。
一、母性的光辉
战争的背景下,女性性别被压抑着,但是无法阻挡母性——女人最基本的情感的释放。“我”虽然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子君——“我是我的”,这么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但至少是一个准女性。
在去包扎所的路上,“我”看到的是被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的秋庄稼,嗅到的是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我”真以为是去赶集。这是一双女性的眼睛在审视战争背景下的风景,甚至连通讯员步枪筒里几根稀稀疏疏的树枝都是装饰点缀。一路上,青涩的通讯员,对于性别差异的羞涩,和“我”保持了没有言语的默契。既不把“我”甩得很远,又不让“我”靠近,使本来有些生气的“我”,不禁对他发生了兴趣。“我”身上的女性被青涩的通讯员唤醒了,当然这种女性是以母性的面目释放的。在“我”的眼中,通讯员是幼小的,是需要保护的,是需要怜爱的,虽然一路上都是通讯员在保护“我”。“我”的这种保护心理的苏醒,使“我”不断地走近通讯员,关心“我”的小同乡,兴趣竟然慢慢地升腾为亲热。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这是一个母亲目送儿子离开的心情,这是母亲看到孩子衣服破了而没有来得及缝补的一丝自责。
“但是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这哪里是没有意思的问题呢?这分明是一个母亲对战斗中孩子命运的担忧和牵挂。在看到一个通讯员被抬了下来,“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以为是自己的小同乡,发现不是后,才稍微镇定下来。可是血、垂危的生命再次唤醒了她隐匿的母性情怀。
“……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这里,母性冲破了战士性别的束缚。白天还给自己开饭的小通讯员,孩子般的小同乡,就这样牺牲了,“孩子”的死,强烈地刺激了“我”的心,母性释放到了极致,以致“猛然跳起身,磕磕绊绊”。
二、父性的外壳
刘再复提出性格的二重组合论,认为“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两极的排列组合”④。“我”的性格中既有母性的柔,也有作为战士的刚。性格是二重的组合,性别也可以是二重的组合。“十七年”文学,应该有三种性别:战士(另一种形式的男性)、男性和隐藏的女性。文本中的“我”,在性别的呈现中,时常表现出和女性、母性相反的一面,姑且称之为“父性”。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文中的“我”从一开始就认可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是我们在发现她是个女性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作为男性话语中心的团长竟然会对一个女同志没有办法,抓了半天后脑勺。从某种意义上说,团长意识到她是一名战士的同时她又是一名女性,意识到了男女性别的差异,所以没办法像指挥通讯员那样指挥“我”,所以陷入了窘境,失语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男女性别差异对男性中心话语地位的一次挑战。“我”的反应也很奇特:“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这里的“我”并没有遭遇性别差异带来的窘境,坚定认可一个战士的身份和性别,是战士怎么能贪生怕死呢?“我”在不自觉中性别发生了移位,女性性别隐匿到战士性别之下。或者说“我”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可是建立在对战士身份的认可之上的,女性不过是战士的附庸。
在去包扎所的路上,通讯员是保护者,“我”是被保护者。起初的节奏是通讯员定下的,“我”在后面紧紧地追赶,但是很快,“我”取代通讯员成为节奏的控制者,引导者,通讯员成了从属者。“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显然,在“我”和通讯员的二元世界里,“我”是占据优势的。某个层面上可以说,在路上,“我”充当了通讯员的长辈,不,是首长这样的父亲角色。
“我”和通讯员在休息间隙的谈话,本来想驱散尴尬、拉近距离,结果造成了更深的尴尬。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在审讯。我想审讯未必够得上,但这像极了革命电影中,首长拉着战士的手,父亲般的看着战士,慈祥地、亲切地询问着,而小战士感到了首长的关怀而内心激动。文中的“我”不自觉地在充当那样一个首长,散发出父性的光辉。可是,不但没有让通讯员安静放松下来,反而更加局促不安,“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大汗淋漓。显然,通讯员对“我”的这种以女性身份充当父性角色的做法,无法接受。这或许给我们解释当“我”让他回团部时,“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担架队员如此虔诚地恳求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而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医生。医生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依靠和希望。这里,“我”的女性身份早已不重要。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我”对通讯员的称呼虽然带上了具有母性色彩的“小”的称呼,如小伙、小同乡、小通讯员等,但是这种称呼还是建立在同志、战士基础上的。是庄严的外壳下亲切的怜爱。
不管怎么说,“我”身上的母性被唤醒,但是这种母性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却是披上了父性的外衣。
笔者以为,“我”这个准女性形象,本就是在“十七年”那个时代被政治压抑而成的畸形女性形象。并且这个形象是贯穿于文本始终的,是政治在文本中的投影。
作者简介: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1}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742.
{2}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
{3}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研究专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42
{4}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60.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