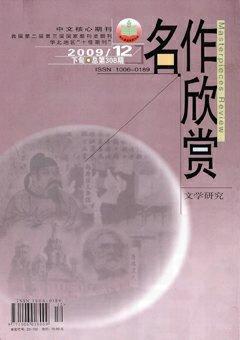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八月之光》中的母亲角色
邵 娟
关键词:威廉·福克纳 《八月之光》 母亲角色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的文本细读,分析福克纳对作品中母亲角色构思和塑造上的艺术特色。通过人物身份的设计、人物对故事情节的作用、人物写作手法的选择等方面,福克纳描绘出了20世纪初美国南方社会的种族的、阶级的和两性之间的矛盾。小说中的母亲角色不是因情节设置需要而任意添加而成,她们的处境和性格关联映照出了另一主人公克里斯默斯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并影响着故事的发展和结局。
威廉·福克纳发表于1932年10月的《八月之光》,通过杰弗生镇十天的社会生活的描述,揭示了几个主要人物的一生及其三代家史,体现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实情感、爱情、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Faulkner:680),表明了作家反对种族偏见和宗教偏见的态度。
作为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中最长的一部小说,《八月之光》以多重叙事角度的情节结构而闻名。故事主要分两条线索,一条讲的是克里斯默斯,他从小被送进孤儿院,因被怀疑是黑白混血儿从此失去了“身份”,受到社会种种虐待,最终促使他杀死了白种情人而被白人私刑处死;另一条讲的是农村姑娘莉娜与情人相恋,怀孕后遭到遗弃,却千里迢迢徒步来到杰弗生镇寻找情人。
20世纪以来,随着符号学和叙事学的发展,对这部作品文艺层面的探讨已成为福克纳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读者的阅读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对故事主要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上,小说的二线人物和细节描写逐渐成为阅读的一个新焦点,而二线人物中的母亲角色尤为引人注目。
《八月之光》中的女性几乎或者说全部都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配角,而这其中的母亲角色除了莉娜外,其他人更是影影绰绰,有的(比如米莉和麦克依琴太太)甚至没有机会替自己说上一句话;有的只能让读者透过她们的只言片语去揣测其内心世界(比如老海因斯太太和阿姆斯特德太太)。本文尝试从《八月之光》中的几位母亲角色入手,探求母亲角色对于小说故事情节的推动以及对错综矛盾的映照。
一
在那不具有感情色彩的开头——恬静从容得令人吃惊——莉娜·格鲁夫的出现,就已经是一个类似于史诗的画卷。一个怀孕的大腹便便的年轻女人,从千里之外徒步跋涉,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感——生活中那种近乎弱智的单纯和善良——来寻找孩子的父亲。
莉娜·格鲁夫自然是小说中母亲队列中的主角。《八月之光》写于福克纳的第一个女儿早产而夭折之后,正如福克纳作品的法语译者库安德罗在他翻译的《喧哗与骚动》的前言里说,感情上的刺激是促使威廉·福克纳写作的重要因素。面对夭折的早产儿、孱弱的产妇,在悲痛的父亲福克纳眼里,健壮的孕妇和孩子就是最为珍贵的。1931年8月开始写作的《八月之光》,最初题为《黑屋》,但内容和题目经过再三修改后,《黑屋》就变成了《八月之光》。平静生活在自己天地的莉娜·格鲁夫(Lena Grove)也成了小说中带来光明的人物之一,虽然所耗笔墨有限。
父母早丧,莉娜从小和哥哥一家一起生活。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她似乎只是按照人的健康本能和冲动行事。她受了那个爱讲俏皮话的卢卡斯·伯奇的诱骗而未婚先孕,对逃跑的未婚夫伯奇深信不疑,并下决心寻找他。一路上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她风尘仆仆来到杰弗生镇。孩子的父亲,无赖卢卡斯·伯奇在出现在她面前几分钟以后,就撒谎溜走了。
生活在那年代里,作为一个没结过婚的遭人遗弃的母亲,她的生活只能在贫困、辛劳中渡过,她却泰然自若,毫不感到羞耻。她只知道自己命中该有丈夫、该生儿育女。小说开始不久,福克纳用莉娜风尘仆仆、不停行走的意象来唤起对济慈《希腊古瓮颂》中田园世界的联想。莉娜与其说是福克纳塑造的一个代表顽强的生命力、超然人格的女性形象,“不如说是他有意运用了一个非人格化的意味隽永的象征”(福克纳:11)。
《袖珍本福克纳选集》的编者马尔科姆·考利说过,福克纳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对命运逆来顺受的味道。但福克纳自己却并不以为然,有的人物如《八月之光》里的莉娜·格鲁夫“就是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的”(李文俊:238),她的男人是不是卢卡斯·伯奇并不重要,只是由于他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生父,才不远千里一路步行从亚拉巴马州来到杰弗生镇找他。卢卡斯·伯奇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她的命运,她的命运无非是嫁个丈夫,生儿育女。这一点她心里很明白,所以“她不要别人帮忙就走出家庭,去和自己的命运周旋”(李文俊:238)。
另一方面,莉娜的感性形象,让我们脱离了那些深远的意蕴和古老的象征,看到一个植物般茁壮单纯的年轻姑娘。当莉娜长成大姑娘后,穿上邮购来的衣裙的莉娜每次去镇上,总要在镇口就从马车上下来,光脚丫子走在人行道上。她当然不是享受平坦的街道,而是一厢情愿让路人相信她也是个住在城镇里的人。这种小女儿的虚荣和娇憨令人忍俊不已。
当被卢卡斯·伯奇诱骗而未婚先孕后,哥哥咒骂她、斥责那个男人时,莉娜却不肯认错,一味替卢卡斯·伯奇开脱。像通俗小说中私奔的女主角一样,夜晚拖着沉重的身子的她从窗子里爬了出去,除了零碎东西还随身携带了自己全部的钱——三毛五分硬币。
一路上遇到满是善良的叫不上名字的乡亲,往往不等他们询问,莉娜便会从头到尾地讲述她的故事,慢条斯理,一本正经,简直“像一个说谎的孩子”(福克纳:16)。当她回想起在阿姆斯特德家吃早饭的情景时,还自豪地感觉自己“吃东西像位贵妇人,像贵妇人那样旅行”(福克纳:17)。而拿着阿姆斯特德太太给她的一些零钱买沙丁鱼时,她连沙丁鱼的音都发不准,说成“花丁鱼”。惹得售货员也跟着她说“花丁鱼”调侃她。
莉娜在杰弗生镇做了母亲——自己的头生子出生了,其间另一主人公克里斯默斯杀人后外逃、被抓、再逃,最终被私刑处死。就在同一天,一方面是新生命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血腥的死亡,为了平衡小说——也许也为了平衡自己的信仰——福克纳才创造出了莉娜这样完美得近乎于天使一样的人物。
二
小说中随着故事的展开,关于莉娜的笔墨渐次淡去,主角克里斯默斯开始登场。作为小说最重要的线索,身份不明的克里斯默斯,成为小说用笔最多的人物。因为被怀疑是“黑白混血儿”而失去了“身份”,“作为小说中唯一的悲剧人物,克里斯默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就故意拒绝任何人”(Vickery:2)。最终促使他杀死了白种情人而被镇上的白人私刑处死。
围绕克里斯默斯,小说中又出现了几位母亲,他的生母、外祖母、养母,以及他怀有身孕的情人。克里斯默斯的外祖父老海因斯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他矮小、好斗,一天到晚叫嚣着要把黑人统统杀死。当女儿米莉和一个疑是混血黑人的马戏班墨西哥人私奔时,老海因斯骑马追上后,在雨夜一枪打死这个马戏班“黑人”,而米莉此时已怀有身孕。等米莉到了分娩的时候,老海斯拒绝为她请医生,眼睁睁地看着她难产而死,留下了父母都死于非命的孤儿克里斯默斯。在小说中米莉自始至终没有为自己说上一句话,就在十八九岁时闭上了眼睛。虽然她曾憧憬自由的生活,身穿节日盛装,拿着手提袋同情人试图逃走,逃离阴仄好斗的父亲,但终归失败。
克里斯默斯杀人后在摩兹镇被捕,他的外祖父母老海因斯夫妇恰巧住在此镇。当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老海因斯夫妇30年来死水一般的生活又被搅起,老海因斯竭力煽动乡亲们的情绪,告诉人们,“他是那畜生的祖父,养了个魔鬼的后代,一直监管到今天”(福克纳:301),一定要把克里斯默斯处以私刑。老海因斯太太则要形影不离地看住他,不让他那样做。穿着怪模怪样、陈旧衣服的老海因斯太太,从摩兹镇追着中了魔的老头到了杰弗生镇。但她哪里又能阻止魔鬼缠身的老海因斯!她无法阻止老海因斯用枪劫回私奔的女儿,也无法为难产时挣扎的女儿请医生,眼睁睁看着她死去。
克里斯默斯被外祖母辛苦抚养了几个月后,被老海因斯偷走丢到孤儿院里。老海因斯太太整整30年没有见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独立行走,没叫过一声他的名字”(福克纳:249)。在看护莉娜生产时,她恍惚中产生了幻觉,时空交错,以为是30年前女儿米莉在生小孩。在杰弗生镇,她在监狱终于见到了被私刑处死前的外孙克里斯默斯。她竭力想让外孙死得体面一些的卑微愿望最终也破灭了,克里斯默斯还是被珀西·格雷姆私刑处死。
克里斯默斯的情人伯顿小姐像莉娜一样也是位孕妇。但她却没有莉娜那种大地母亲般的坦然,从从容容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儿女。在杰弗生镇,离群索居的伯顿小姐是个异类,住在黑人聚居区一座孤零零的楼房里。由于她的祖辈是来自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她自身还在惯性地坚持着父辈的工作。当情欲使她与克里斯默斯走近时,克里斯默斯一下就看穿“她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女人,但不知道该咋办”(福克纳:160)的心思。而克里斯默斯自己“知道永远不可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是谁,他对自己灵魂唯一的救赎就是拒绝任何人,生活在任何人之外”(Vickery:3)。这种身份混乱的危机使这对情人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克里斯默斯不想被头发刚刚花白的伯顿小姐套牢;伯顿小姐则欲生下胎儿并让他接手自己帮助黑人的业务,克里斯默斯却“不肯在白人社会中承认他是个黑人”(俄康纳:170),“新英格兰冰河凄厉的狂怒突然遇上新英格兰神圣的地狱火焰”(福克纳:172-173)。最终,怀揣手枪的伯顿小姐死在了克里斯默斯的剃刀之下。他一刀两命。
克里斯默斯的养母麦克依琴太太像是丈夫身后的影子。麦克依琴冷酷无情、顽固偏执,而她是“一个善于忍耐、精疲力竭的可怜动物,浑身没有性别的标志,除了整齐地夹在一起的灰白头发和裙子”(福克纳:110)。从克里斯默斯五岁进这个家起,她一直千方百计待他和善,非常迫切地表现对养子的好,反被他讥笑为“那种种细微笨拙而又徒劳无益的努力,都出于她受尽挫败的遭遇和她拙劣愚蠢的本性”(福克纳:112)。夹在心理扭曲的养子和顽固、暴戾的丈夫中,无论她如何好心待他,克里斯默斯都憎恨她的温情善意甚至超过惩罚。对麦克依琴太太来说,最终尘埃落定,养子为了暗娼用凳子砸死她的丈夫,远遁他乡,拿走了她一角一分偷偷为他攒的钱。
莉娜和克里斯默斯在小说中自始至终没有见面,她作为参照物而存在,为这样一部充满扭曲、暴力、残忍的小说涂上一层亮色。围绕着克里斯默斯的四位母亲,她们在克里斯默斯的生命链上,努力过却改变不了他的命运,只是恶化了自身的命运。生母米莉给了他生命,也开启了他的悲剧命运;外祖母老海因斯太太要接替难产而死的女儿抚养这个孤儿,但阻止不了老海因斯对孩子的迫害,孩子几个月大就被他从家里偷走扔进孤儿院;养母麦克依琴太太也竭力给孤儿温暖,只换来憎恨和自身更悲惨的命运。情人伯顿小姐和克里斯默斯像两头角力的野兽,因情欲而吸引,因信仰和身份而相互残杀,死亡拉上了斗争的帷幕。
三
在小说的开始,也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母亲角色,那就是阿姆斯特德太太。农夫阿姆斯特德出于好心,让大腹便便的莉娜搭乘他的马车并借宿在他家。
拉扯大五个孩子的阿姆斯特德太太,从丈夫的三言两语对莉娜的叙述中,就看穿了这个年轻女人的窘境,十分怀疑诱奸了莉娜的伯奇“会在那儿等着,把房屋家具一切都准备好了”(福克纳:10)。在阿姆斯特德太太眼里,莉娜只是一个被男人欺骗而心甘情愿蒙在鼓里的糊涂女人。当莉娜讲述自己和卢卡斯·伯奇的故事时,阿姆斯特德太太冷峻轻蔑地看着她,不留情面地戳穿了无赖卢卡斯·伯奇以及莉娜为他做的辩解。莉娜依然心平气和、却固执己见地对阿姆斯特德太太说:“我想小孩出世的时候一家人应当守在一起,尤其是生第一个,我相信上帝会想到这一点,会让我们团聚的。”(福克纳:14)阿姆斯特德太太则不耐烦地说,上帝也只好这么办了。
晚上阿姆斯特德太太找出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的瓷公鸡,敲碎后拿出钱,嘱咐丈夫:“太阳一出来就套上骡子,领她离开这儿。”(福克纳:14)第二天当莉娜离开前,她起来做好了早饭就故意躲了出去,却出乎意料地把一分一角攒的卖鸡蛋得的钱让丈夫转交给这个她看不起却理解同情的外乡女人。在四个星期目的地不明的徒步旅行中,只带了三角五分钱的莉娜之所以没有风餐露宿,衣衫褴褛,无不是因为有阿姆斯特德夫妇这样的乡亲,出手相助,才一路顺利地到达杰弗生镇。像阿姆斯特德太太这样的母亲也许是母亲层面上最普通最常遇到的类型,恪守妇道、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含辛茹苦抚养儿女。
而在故事发生的杰弗生镇,“镇上的永久居民,他们以往的个人生活,不同的家庭背景在小说中很少被关注”(Millgate:45)。不管是“人们”,“镇上的人”,“女人们”,都有着基本上无差别的对社会和种族的态度以及宗教信仰。母亲角色,除了有孕在身的伯顿小姐外,没有被特别描述或提及。这可能基于,杰弗生镇的人们在小说的构建中,有着共同的“对社会现象的接受和抗拒,以及对小镇以外陌生人的态度”(Millgate:45)。也就是说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八月之光》中的母亲角色几乎都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配角,根植在美国南方这块有着独特文化、独特传统的土地上。她们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却不失生活的勇气和执著,代表了生活本身——不管发生了什么,日子还要继续。《八月之光》中大多数男人,如克里斯默斯、老海因斯、格雷姆等,都带着一种狞厉的面貌。不断衍生的矛盾、不断的彼此伤害,冷漠、残忍、暴力、焦躁,这些情绪永远萦绕在小说中。莉娜、米莉、麦克依琴太太、老海因斯太太和阿姆斯特德太太等母亲角色,平衡了小说的氛围和格局,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作者简介:邵 娟,上海电力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商务英语。
参考文献:
[1] 福克纳:《八月之光》,蓝仁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2] 李文俊编:《福克纳的神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3] 俄康纳编:《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张爱玲、林以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责任编辑:水 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