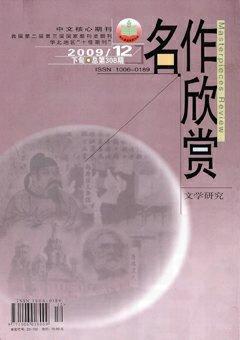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恩主》:一场自由的梦
唐 蕾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 《恩主》 梦 自由选择
摘 要:梦和现实是应当截然分开的,但在小说《恩主》中却表现出奇妙的融合。本文借助四个梦的内容着重阐述有关自由选择的问题;从梦的艺术形式和自由选择的艺术内容来探寻《恩主》的哲学思考,讨论了桑塔格艺术选择对于创作影响的问题。
苏珊·桑塔格(1933-2004)被誉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的良心”,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一直活跃于美国的文坛上,完成了小说、戏剧、评论以及相关论著40多部。《恩主》是她第一部小说,成书后,却被可能成为桑塔格出版商的英国柯林斯出版社拒之门外,理由是“缺少生活”,柯林斯的编辑沃尔森对桑塔格“能否成长为其艺术能够完全、合适地吸收其思想的小说家”表示怀疑。卡尔·罗利森和莉萨·帕多克解释小说之所以没有卖点的原因在于它试图“阻止人们从作品中获得真正的愉悦”。其实,仔细研读,人们便会发现不是“缺少生活”,而是有太多的生活需要去选择、参与;作家巧妙地把自己隐藏于作品背后,将话语权交给阅读者,实际上,恰恰说明了桑塔格深谙小说家之道。桑塔格通过《恩主》将批评者的思想和艺术家的灵感完美地融合于一体,让人耳目一新。实际上,就桑塔格的小说归类问题历来是评论界争论的难题,桑塔格本人对所谓的贴标签也深恶痛疾。本文无意就《恩主》是艺术的还是哲理的这一问题作深入讨论,而是就桑塔格对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理论的运用探讨一二,并借以强调,只有超越传统类型解读的误区才能真正理解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强调,典型的当代小说一定是心理的,它再现的是自我的一种投射及具体化。在对卡夫卡、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家作品的分析后,她发现在西方文学中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艺观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梦魇般的感受,她称之为“后经典小说”。桑塔格曾经说过:过了多少年之后,人们再次提起以前曾经做过的梦,依然十分清晰。梦是抛弃时间、空间和情境的唯一方式,在背离了这一切先入之见后,所讨论的问题变得显而易见。小说由无数个梦堆砌而成,而讲梦的主人公希波赖特就生活在梦和现实这两个空间里,现实和梦难分彼此、亦幻亦真。“两个房间之梦”、“非常派对之梦”、有关“自生教派”的宗教之梦以及“演出场地之梦”分别阐释了桑塔格最为关注的几个问题:趋利避害、秩序、自给自足以及尊严。贯穿作品始终的是桑塔格对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思考和讨论,因此,这部小说也被人们看作有关自由选择的试验之作。桑塔格强调自由选择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权利,人一旦选择就得承载起责任。小说开头引用了德昆西的一句话:“要有什么差错,就让梦去负责任。梦目中无人,一意孤行,还与彩虹争论显示不显示第二道弧形……梦最清楚,我再说一遍,该由梦去负责任。”{1}
一
面对痛苦,人总是本能地选择逃避;面对幸福,人又总是本能地选择接纳,人们称之为趋利避害。希波赖特是《恩主》的主人公,也是梦的叙述者。他出生于富裕家庭,由于家人长年在外奔波和丧母之痛,使得他养成了孤独和沉思的习惯,上大三时,他退学了,原因很简单,学校的生活太枯燥,而且过于呆板。因此,他想要过一种自由的生活,由于他写作了一篇文章,为一个文艺沙龙所接受,成为安德斯夫妇的客人。成年之后的希波赖特做的第一个稀奇古怪的梦是“两个房间之梦”。在这个梦中,总有一个穿着紧身的黑色羊毛泳裤的男人,拿着一个铜制的笛子敲打希波赖特并且强迫其站在凳子上跳舞,在希波赖特最痛苦的时候,他又会突然不见,一个白衣女子出现,端坐在椅子上,本来抑郁的希波赖特心血来潮跳个不停并且想和白衣女子做爱。这个梦之后,希波赖特试图去破译它,小说里这样写道:“我说了,我首先要做的是释梦。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梦当作礼物,而是把它看成一个要完成的任务。这个梦也让我内心产生了某种反感。因此,我竭力想弄明白它,从而控制它。我越是想这个梦,就越感到责任重大。但是,我做出的各种解析都没有让我松口气。这些解析非但没有减轻这个梦对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压力,反倒增加了。”{2}如果把这个梦简单概括一下,就会发现有一对非常奇妙的矛盾存在,即“不自由的选择”与“自由的选择”。希波赖特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被黑衣人逼迫去跳舞,是一种“不自由的选择”,而白衣女人的出现让他有了一种求爱的欲望,是一种“自由的选择”。黑衣人的存在似乎可以理解为荒诞无情的外在世界,在逼仄的环境里强迫人做出选择;而白衣女子却完全象征着美好的、纯粹自由的理想,是人们心甘情愿的、由衷的选择。在梦境中,黑衣人对希波赖特的折磨只是现实生活对人的压制和异化的一种延伸,而如期而至的白衣女人,是希波赖特渴望突破束缚、实现自我的最真实的心理表现。对黑衣人的逃避,体现了希波赖特不自由的、被动的生存状态。逃避的态度看似不选择,实际上还是一种选择,即“逃避”的选择;对白衣女子的追求,表现了希波赖特自由、主动的生存意念,积极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介入”生活的选择。萨特说过,“自由是选择的自由,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是选择了不选择”{3}。这种看似悖论的阐述,恰恰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人们在情境当中一定会面临选择,无论选择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必须有所交代。这也仿佛给人们提了一个醒:选择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权利。
二
桑塔格这样说道:“我思考的是,做一个踏上精神之旅的人并去追求真正的自由——摆脱了陈词滥调之后的自由,会是怎样的情形;我思考的是对许许多多的真理,尤其是对一个现代的、所谓民主的社会里多数人以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提出质疑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梦被称为“非常派对之梦”。安德斯太太和希波赖特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梦和现实里,希波赖特让这个女人帮助自己实现了改变生活的梦想。安德斯太太性感迷人,但也有恶俗的地方就是喜欢别人拍他马屁。在梦里,希波赖特等人做了一个“U”字形的游戏,游戏之后,他和安德斯太太两情相悦,但这个女人喋喋不休地说话让他非常讨厌,愤而离去。这个梦情节十分简短,但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希波赖特接下来所有关于安德太太何去何从故事的开端;同时,借助于这一个梦也把希波赖特不可告人的秘密说了出来,并且付诸实施,那就是和安德斯太太偷情。平日里安德斯太太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而且周围聚集着形形色色恭维她的食客,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大家都不敢对她有不敬之辞。但在梦里,希波赖特似乎向这个女人证明了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并赢得了芳心。而安德斯太太的弱点似乎在梦里也毫无掩饰地暴露了出来。希波赖特既欣赏她但又蔑视她,出于礼貌,在平日里只表现了前面的态度,而潜在的鄙视则在梦中得以呈现。“非常派对之梦”是希波赖特最长的一个梦。在梦里,他引诱安德斯太太和他私奔,最后将她卖给了阿拉伯人做了奴隶。而这一切,安德斯太太欣然接受,与此同时,希波赖特如释重负,丝毫没有罪恶感。这个故事同样地晦涩难懂,但似乎又显而易见。小说后半部分写道:“人类只有历经各种体验之后,才能获得拯救”,“他们称之为完备的知识”。改变生活并不意味着从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跳进另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而是不停歇地从一种生活投入到别的生活当中,尝试不同的人生体验。这是希波赖特为之渴望的自由状态——没有规则、没有秩序、形式多样、不拘小节。但要实现这种生活,要么是由于缺乏财力,要么是因为生性懒惰,或者其他种种,最终使得这些怀着自由之梦的人们抱憾终身。很显然,希波赖特也属于这一类的人,因此,他把梦交给了看似最有可能完成其自由之梦的安德斯太太。有人曾经说过,女人离家出走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回来,要么堕落。但这个故事最为荒诞的是桑塔格给我们安排了两种假设:堕落后回来了;功成身退。希波赖特在梦和现实中看到两个女人都自称安德斯太太,前者在战争结束后,变成一个需要别人施舍的可怜虫;后者功成身退,从奴隶变成了奴隶主,而且在贫瘠的异国他乡成就了女人无法成就的理想——成为无数男人的精神领袖。
在沙龙里,有沙龙的游戏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在梦中,安德斯太太要把游戏者分出胜负来,与此相反,希波赖特则视之为恶俗,小说中这样写道:“我不明白这么好玩的游戏中干吗一定要产生优胜者。在我看来,既没有规则,也不要决出胜负,游戏才有劲。”{4}这段话清楚地向人们提出了第二个疑问,那就是规则和秩序有无意义,人们是否都得执行这一套游戏规则。黑塞把游戏看作完全等同于生命、世界、精神以及信仰的形式,而生命是一种随意的游戏,并且,他也说过,一切游戏均是没有野心、没有求胜意愿的本色生命行为。人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看作来源于席勒。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完整地阐述了人类本性的“游戏冲动”。就生命本质而言,“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5}。同样,在U形游戏当中,希波赖特体验到了人的自由本质,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幸福,小说中写道:“隔壁房间在开音乐会,我跟边上的游伴,也就是那位黑人芭蕾舞蹈演员说音乐会的事。我们正聊着,他开始劈叉,直到双腿在地板上成一线。他闭上眼,呼中气,我边上的人也照样子滑下,他们的身体碰撞到一起,一个叠一个,一个个都呼口气。大家看上去都非常开心,我自己心里也突然感到平静、快乐。我叠在最上面,一种巨大的轻松感溢满全身。”{6}希波赖特称这种幸福感为“自愿的孤独”、一种“纯净”,尽管“这一体验无法与人分享”,“只有在我心里”才能细细地品尝到它的滋味。席勒认为就艺术创造而言,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最猥琐的对象,经过处理也必须使我们仍然有兴致从这个对象直接转向最严格的严肃,最严肃的题材,经过处理也必须使我们仍保持把它直接转调成最轻松的游戏的能力”{7}。而U形游戏正是用看似荒诞的游戏形式实现了最为严肃问题的讨论。桑塔格把游戏看作一种精神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形而上的生命活动、一种有灵的讨论。
三
人类总是试图去寻找一个精神的偶像去顶礼膜拜,桑塔格曾批评过现代人的弱点:走极端,要么怀旧,要么空想。总之,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少。随之而来的便是丧失个性、丧失自我。在“宗教之梦”梦里,布尔加劳教授向他讲述了关于“自生教”派的教义:黛安努斯是“自生神”的孩子,双性同体,与其父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每隔一阵子,他都要冒险来到人间,受到人们的膜拜、攻击和折磨。唯有这样,他才能继续享受他那神圣的睡眠”{8}。希波赖特试图对该梦做出合理的解释,文中写道:“我做的梦难道不是有关自给自足和不可避免地开始对某种东西有了了解的理解吗?”“这个神话有一部分讲到黛安努斯必须定期受折磨,但那不是要拯救人类,而是神要舒适和健康。我非常喜欢这个部分。这是最庄严、最坦率的造神方式。”{9}这又是一个关于自我与他人问题的讨论:宗教到底是要拯救他人还是拯救自己?桑塔格通过希波赖特似乎已经回答得相当清楚,为了自己,为了自我内心的宁静。个性在小说《恩主》里被理解为一种“重量”。“自生教”派其实完全是一种“反行为准则”,在它的教义里面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区分,只有轻重之别。人们藐视道德法则将最终使得自己完全失重,离群索居,为社会所摒弃。文中的主人公希波赖特一直沉湎于对自己的梦的解析,让他久未谋面的家人都误以为他已经精神失常,连自己的小侄女都不敢多和他讲一句话。很显然,在对自我的过分关注下,其恶果就是失重,个体将成为孤家寡人。桑塔格在书里写道:“个人的个性必须在逾越所伴有的尖刻言辞中受到抑制。”“自生教”派鼓励人们将自己看作最后一片净土,追求内心的沉寂,不要同流合污,不要人云亦云,但最让希波赖特感动的不止是这些,而在于教义的初衷不是为了他人的安逸而仅仅是在于神对自己的尊重。美国传记作家卡尔·罗利森和莉萨·帕多克说道:“像桑塔格的艺术观一样,希波赖特的梦也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一如桑塔格,他把自己想象成自给自足。”{10}我们可以理解为桑塔格在希波赖特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做梦的载体,而希波赖特在“自生教派”主神黛安努斯身上找到了自给自足的信念。神的“自私”和“天真”大大地鼓舞了希波赖特继续“做梦”。
四
萨特说过,当孤独的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存在处境时,有没有一种个体主体性,有没有一种敢于独立自为的勇气,一种不畏虚无而绝望反抗的勇气,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他曾经具体解释:“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处境和历史,我应当把它重新修复,对它负起责任,为了自己和他人而改变和维护这个世界。”{11}所以,人积极或消极地选择都会对自我和他人造成一定的影响。最后一个梦是“演出场地之梦”,在这个梦里,希波赖特看了一出杂技团的表演。有一个演员受伤了,请求找个替身的观众。结果,一个人被请上了舞台。一切在开始都是温和的安静的。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却让希波赖特大为震惊:杂技演员一边安慰观众不会有事,一边用刀子在观众的脸上切割而且伤口似乎无法复原。当希波赖特在担心观众会因此死去时,那个观众又变成了自己,自己又变成了观众。杂技演员将观众的头颅真的切开时,希波赖特被惊醒了。文中写道:“我梦醒时,从未有过这样大的恐惧感。接下来几天时间,我老想这个梦,并重新感受这次梦的高潮——恐惧和愤恨。”{12}这个梦仍然讨论的是顺从和对抗的问题。当一个人即将或者正在被剥夺尊严时,他是选择顺从还是反抗,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在梦里,希波赖特看着这一切,感到非常迷惑不解,因为这个配合的观众连一句痛苦的或者责备的话都没有;让希波赖特愤恨的是,那个被切割的观众他是那么相信杂技演员,这么顺从他,而实际上,他却一直是对方迫害的对象。显然观众是麻木的、被动的,杂技演员是强硬的、主动的,双方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平衡的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我为鱼肉,人为刀俎”。除此之外,希波赖特的恐惧和愤怒源于他已经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梦境中受虐者一会儿是观众席上的陌生人,一会儿又变成希波赖特,恰恰表明了人们不自由的生存状态。桑塔格向人们号召:“我们要与他们结合,砸碎铁栏。”
四个梦均是割裂的,但有内在的统一性,即人与外在世界的矛盾与对抗。桑塔格相信无论过程怎样崎岖,最终的结果是服务于人的自我价值,以实现自我价值为衡量标准。人所受的痛苦都是为了能早是获得幸福,换句话说,只要能实现自由、安全和幸福,磨难和痛苦完全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光明就在眼前,即使灾难深重,人最终仍然可以自由选择。存在主义哲学告诉人们:世界是荒诞的,但人仍然可以自由选择。《恩主》里梦和现实错综复杂交织于一体,体现出世界的荒诞和不可捉摸性,以及人认知世界的艰难;无数次故事的重新讲述,又体现了人积极地试图改变现实、实现自由选择的可贵精神。希波赖特每次做不同的梦,其实是在尝试着做不同的选择,让人们联想起萨特小说《自由之路》里的主人公玛第厄,也是有无数次犹豫不决,但最终做出了自我选择,玛第厄告诉自己:人生本无意义,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才能确定价值。人生活在自己的境遇之中,要做出抉择,获得自由。萨特强调人必须融入社会、投身于社会活动中去实现自我价值。《恩主》中的主人公希波赖特却在梦中看到自己身染重疾,无法行动,小说的结尾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悲观主义格调,小说写道:“等到那些梦不再纠缠我的时候,它们便把我冲出水面,撂在海滩上。这时候,我都老了。”{13}
本论文系江苏省2009年教育厅项目“时间意识与经典小说的意义阐释”资助项目,编号为09SJB750023
作者简介:唐 蕾,硕士,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江苏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重点学科成员。
①②④⑥⑧⑨{12}{13} 苏珊·桑塔格:《恩主》,姚君伟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19页,第24页,第24页,第77页,第77页,第198页,第234页。
⑤⑦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第114页。
③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汤永宽、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⑩ 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11} 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责任编辑:水 涓)
——王阳明《月夜》覆议
——芭芭拉·秦访谈录